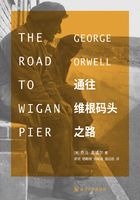
第1章
清晨钻入耳中的第一缕声响来自磨房姑娘们的木质拖鞋在鹅卵石小道上的敲打。比那更早的,恐怕便是工厂的集合哨声了,尽管我从来没有在醒的时候听到过。
我的床在右手边离门最近的角落里,床脚那头还挤着另一张床,两张床紧紧地挤在一起(只有这样放才能开门)。于是我每日只能蜷着腿睡觉,否则就会踢到另一张床上那个人的后背。那张床上的房客是个叫雷利先生的长者,在煤矿“顶上”勉强做个技师。好在他每天五点便要去上班,之后我才有幸伸直腿好好睡上几个钟头。我的对床是一个苏格兰的矿工,遭遇了一场矿难(一块大石头在他身上压了好几个小时才被人撬开),拿了五百磅的赔偿金。他四十来岁,是个高大英俊而又强壮的男人,稍稍泛白的头发和修剪整齐的胡须让他看起来更像个兵长。他会在床上抽着他的短烟斗一直躺到午后。还有一张双人床则被各种旅行推销员、报纸推销员和按揭推销员占用着,他们通常只住几个晚上。这张双人床大约是这里最好的一张床了。我在这儿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在这张床上度过的,不过后来不得不转而让给新来的房客们。依我看来这张床似乎就是一个“诱饵”,所有新来房客的第一个晚上都会睡在这张床上。房间里的每扇窗户都关得严丝合缝,并且底下用红色的沙袋抵着。每天早晨,这房间臭得就像个臭鼬笼子。人在房间里的话是无法察觉的,但倘若你一早出了门再回来,这恶臭就会像一记重拳扑面而来。
其实我从未留意过这间屋子里有多少个房间,不过奇怪的是在布鲁克一家来之前这里便有了浴室。屋子楼下是常见的敞开式厨房,接连着客厅,每日烟雾升腾。屋子的唯一光源来自于一扇天窗,因为房子一边是一家小店,而另一边是一个储藏室,连通到某个更深不可测的内脏贮藏室。一张不成形的沙发堵住了贮藏室半边的门,而沙发上倚坐的则是似乎永远抱病,裹着脏兮兮的毛毯的房东太太:布鲁克夫人。她大而蜡黄的脸上无时无刻不透露出焦虑,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什么毛病。不过以我的推测,大概只不过是因为她吃太多罢了。火堆前面几乎一直有湿答答的衣服挂晾着,而中间的大餐桌则供家里人和所有房客们吃饭。我从来没看见餐桌整个儿露出来过,各时的覆盖物却又不尽相同。最下面是一层沾着伍斯特沙司的旧报纸,上面则是一层黏黏的白油布,再上面是一层绿色的哔叽布,之后又盖了一层粗麻布,从来不曾更换也很少被揭下。早餐留下的面包屑基本上晚餐时还在桌上。我就曾经可以凭外形认出每一块面包屑,并观察它们在餐桌上日复一日颠簸来回。
小店是那种狭窄阴冷的房间,窗户外侧粘着一些白色字母,是些陈年巧克力广告纸遗留的碎屑,如星星一般散落着。窗户里侧有一块大石板,上面铺着一层层白花花的牛肚子,还有灰色毛茸茸的东西,被他们称为“黑肚子”[1],还有一些已经煮熟的惊悚的半透明猪脚。这其实是一间再平常不过的卤煮店[2],除了面包、香烟和一些罐头食物就再没什么别的存货了。虽然窗口也写着有茶供应,但是如果客人想要一杯茶的话,通常会被以各种理由而推脱掉。布鲁克先生从前的职业是矿工,尽管他已经失业两年了,他和他的妻子却一直开着各式各样的小店作为副业。他们曾经开过一家小酒馆,但是因为纵容赌博而被吊销了执照。我很怀疑他们有没有哪一桩生意是盈利的,其实他们经营这些生意大概主要是为了能有些什么东西来抱怨。布鲁克先生皮肤黝黑,小骨架,有着一张愠怒的爱尔兰人脸,而且惊人的脏。我从未见过他的手有干净的时候。因为布鲁克太太现在是个病号,他要准备大多数的食物。而且像所有双手永远脏兮兮的人一样,会用一种非常紧握而缓慢的方式拿东西。比如说他给你一片黄油面包,上面一定会有个他专属的黒手指印。大清早他下到布鲁克夫人的沙发后面的神秘巢穴去把牛肚捞出来的时候,手就已经是黑的了。关于贮藏牛肚的地方,我从其他房客那里听说了很多可怕的故事,传说那里爬满了蟑螂。我不清楚他们多久订一次新鲜的牛肚,但是间隔时间一定很长,因为布鲁克太太每次都会用这来记事。比如“让我想想,在那之后我又进了三批冷冻牛肚”之类的。我们房客从来都没吃过他们家的牛肚,当时我以为是牛肚太贵了,但后来想想,大概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因为我发现就连布鲁克夫妇他们自己也从来不吃牛肚。
仅有的长期房客们是那个苏格兰的矿工,雷利先生,两个年事已高的退休人员,和一个拿社会补助的失业人员,乔,他是那种没有正经家族姓氏的人。那个苏格兰矿工,如果你近距离接触他,会发现他其实十分无趣。像大多失业者一样,他花太多时间看报纸,如果你不打断他,他可以就黄祸[3]、行李箱分尸案[4]、占星学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分歧谈上好几个小时。那两个高龄的退休人员,和很多老人一样因为收入调查[5]被家人赶了出来。他们每周向布鲁克夫妇交10先令,以交换价值对等的可想而知的食宿,即小阁楼里的一张床和以黄油面包为主的伙食。其中一个老人为人高傲,又恶疾缠身命不久矣——我估计是癌症。他只有在去拿他的养老金的时候才会下床。另一个老人被大家称作老杰克,从前是一个矿工,78岁高龄并且有着超过50年的矿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他是那种谨慎又智慧的长者,但是奇怪的是他似乎只记得他少年时候的事情,而对于所有现代矿山的机械及其发展都忘得一干二净。他还曾给我讲过在狭窄的地下矿道和野马打斗的故事。当他听说我打算下几个矿区看看的时候,曾非常轻蔑地声称像我这个头的人(6英尺2.5英寸)[6]绝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旅行”。而且就算你跟他说现在的“旅行”比以前好一些了也是完全说不通的。但是他总是十分友好地对待每个人,而且总会在爬上他房梁下面某处的小床上之前,跟我们恰到好处地大喊一声“晚安,小伙子们”。最让我敬佩的是老杰克他从来没有向谁乞求过什么,他总在一周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抽光了他身上所有的烟,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拒绝别人递过来的香烟。布鲁克夫妇已经为这两位老人上了在那种一周6便士[7]的保险。据说有人偶然听到他们焦虑地询问保险推销员“癌症患者能活多久”。
乔,和那个苏格兰人一样,看了太多的报纸,而且几乎成日地泡在公共图书馆里。他是那种典型的未婚无业游民,看起来颓废不堪且着实邋遢。他那一张圆圆的几乎是稚气的脸上总是带着天真顽皮的表情,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被人忽略的小男孩儿,而不是一个成年人。我猜完全是因为责任感的丧失才让很多这样的男人看起来比他们实际年龄要小。仅看外表的话,我会以为乔大概二十八岁的样子,而让我极为惊讶的是他居然已经四十三了。他钟爱引用名言,并且对于自己逃避婚姻的机智选择洋洋得意。他总是对我说“婚姻是枷锁”,显然自认为这是非常微妙且有先见之明的论调。乔的总收入是每周15先令,他交付给布鲁克夫妇的房费便要6、7先令了。有时候我会到看他在厨房的火炉上给自己煮一杯茶,但是其他时候他都在外面吃,我估计也就是一片干面包或者一包炸鱼薯条之类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旅行推销员、报纸推销员、旅者艺人这样的比较穷困的流动房客。旅行演员在北方比较常见,因为在北方大多数的酒馆会在周末的时候雇用各种艺人。而报纸推销员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一类人,他们的工作在我看来毫无希望,可怕到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选做这行而不干脆去监狱蹲着。雇他们的一般是周报或者周日报,他们会拿到一些地图和一列街道的名字作为指引,从一个镇穿梭到另一个镇来完成他们每日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能完成每天最少20笔订单的指标,那就会被炒鱿鱼。只有完成指标任务,他们才可以得到一点微薄的薪水——我估计是一周两英镑。有超额完成的部分,他们还可以拿一点儿少得可怜的佣金。不过这份工作也不像听起来那么难,因为在工薪阶层所在的小区几乎每家每户都会订一份两便士的周报,然后每隔几周会换一种,但是我很怀疑有人能坚持工作上几周。这些周报会吸引一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可怜人,比如失业职员和旅行推销员这样的人,他们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疯似的争取把销售额维持在最低的水准。过一段时间这种丧失人性的工作会把他们的精力消磨殆尽,然后他们会卷铺盖走人,新人又会来填补他们的空缺。我曾经结识了两个替那种臭名昭著的周报干活儿的人。两个人都是人到中年必须养家糊口,其中一个甚至已经做了祖父。他们每天要奔波十个小时,在指定的街道上“工作”。晚上还要填一些他们周刊暗藏猫腻的表格——里面通常有些小把戏,比如如果你连续订上六周他们的报纸再汇上两个先令就可以得到一套陶具之类的。那个胖胖的祖父经常脑袋耷拉在一堆表格上就睡着了。他们两个都付不起布鲁克夫妇家每周一英镑的全套食宿费用,一般只付一点床位钱,然后在厨房的角落里糊弄一点有失体面的食物,一般来说是他们存在行李箱里的一些培根、面包和人造黄油。
布鲁克夫妇有很多个儿女,大多数都已经逃离这个家很久了。按照布鲁克夫人的说法,一些孩子在“加拿大镇”。他们只有一个儿子住在附近——一个体格庞大像猪一样的男孩儿,在汽车修理厂工作,而且经常来他的父母家蹭饭。他的妻子每天都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待在这里。大多数洗衣做饭的家务活儿都是他的妻子和艾米在做。艾米是布鲁克夫妇另一个在伦敦的儿子的未婚妻,是个鼻子尖尖、一脸不悦的金发姑娘。她在磨房工作,拿着食不果腹的收入,还要每晚在布鲁克夫妇家做苦力。我听说他们的婚礼被无休止地延期,而且很有可能永远都不会举行了。但是布鲁克夫人已经擅作主张地视艾米为媳妇,并用那种病人特有的斤斤计较的方式对她喋喋不休。剩下的家务活都是由布鲁克先生负责的,当然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做。布鲁克夫人除了去吃她的饕餮大餐以外几乎从不离开过那张沙发(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她都在那张沙发上度过),而且她过度虚弱以至于什么都不能做。一直以来都是布鲁克先生看店,为房客们提供伙食,清理客房。而且他可以用让人难以置信的缓慢速度完成一件令他讨厌的工作,然后开始另一件。晚上六点客房的床还没铺好是很正常的事。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在楼梯上碰见他,端着满满的夜壶,而且拇指还紧紧地扣住壶口。早上他会端一盆脏水坐在火堆旁边用慢镜头一般的速度削土豆。我从来没见过谁可以像他这般哀怨地削土豆,似乎你都可以看见他口中的“该死的娘们儿干的活”的怨恨,像苦涩的汁液一样在他心头发酵。他是那种会像反刍一样把自己的不幸反复抱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