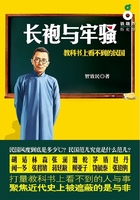
第6章 中国知识分子与“九一八”事变
今年(2011)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考察一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反应,也是一种很好的纪念。
一、胡适的心情
1931年9月19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入侵略!(《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155~15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日记中的“在君”,就是著名学者丁文江。1931年8月初,胡适在参加了一个复兴北京大学的会议之后,便带着儿子祖望与好友丁文江一同到秦皇岛避暑去了。丁文江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对军事问题颇有研究,二人在秦皇岛避暑时,自然会谈到40年前的甲午战争,以及战争以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情况。
尽管胡适对于“九一八”事变早有预感,但这一事件还是让他的心情十分恶劣。由于什么事也不想做,他回忆起几个月前陈寅恪请他在其岳祖父唐景崧遗墨上题词的事。于是,胡适写了一首律诗题在上面: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早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就因为招抚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在越南抗法有功,受到清廷的褒奖。随后,他以道台身份被派往台湾,通过办书院、兴科举、修铁路、劝农桑等方式,为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已经是布政使兼台湾巡抚的唐景崧,曾经七次致电朝廷,反对割让台湾。《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拒不执行朝廷放弃台湾、撤回内地的命令,准备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为此,他与丘逢甲、刘永福等人创建台湾民主国。民主国成立后,大家推举唐景崧为大总统,并制定以“黑虎”(黑色纹路的老虎)为图案的国旗。不久,日军在台北登陆,唐景崧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返回大陆。在此期间,胡适的父亲担任过台湾营务处总巡和台东直隶州知州,不仅参加了唐景崧领导的抗日斗争,而且还在回国途中因病去世,所以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自然会想起这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
9月26日,胡适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不但将上述律诗录入,还两次提到自己的心情一落千丈,十分“没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8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在这以后,一位署名为“敬”的人多次致信胡适,讨论应对时局的办法。此人在信中说:所谓办法,“有枪杆子与笔杆子两种”,有枪杆子就应该革命,有笔杆子则可以“唤起全国同情”(同上,85页)。此外,他认为“以党治国”的国民党“可谓恶贯满盈”,劝胡适不要为政府出谋划策(同上,90~91页)。
二、俞平伯的建议
“九一八”事变的前四天,也就是1931年9月14日,经过整顿的北京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在此之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为了提倡学术研究,拨出特别款项对北大实行资助,其中研究教授的年薪,从4800元到7200元不等。享受这一待遇的有15人,其中除了胡适以外,还有大家熟悉的丁文江、徐志摩、周作人、汤用彤、李四光等人。在北大设置研究教授的目的,用胡适的话来说,是为了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并希望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学生纷纷罢课,并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的俞平伯十分忧虑。他担心长此以往,普通民众和青年学生将会误入歧途,被人利用。于是他专程拜访胡适,建议胡适像当年办《新青年》那样办一个周刊,用“深沉之思想”、“浅显的文字”告诉大家,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应该在“息心静气,忍辱负重”的基础上,“提倡富强,开发民智”,从而实现“吾辈救国之道”(《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83~84页)。
俞平伯的建议其实是知识界的共同心愿。据蒋廷黻回忆,当时著名学者叶企荪和陈岱荪住在清华大学北院7号。“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他和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萨本栋、钱端升等人都喜欢去那里讨论时局问题,所以北院7号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沙龙,即蒋廷黻所谓“非正式俱乐部”。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聚餐,出席的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张奚若、吴宪、任鸿隽及其夫人陈衡哲等人。席间蒋廷黻提议应该办一个周刊,讨论中国面对的问题和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这一建议遭到陶孟和的反对,但是却得到丁文江的支持。在丁文江的倡议下,大家拿出个人收入的5%作为办刊经费,并且由胡适负责编务。又经过一番酝酿,《独立评论》终于问世。
三、左舜生的言论
“九一八”事变以后,以左舜生为代表的中国青年党人则是另外一种表现。
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长沙人。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系,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任该会评议部主任,负责《少年中国》的编辑工作。1924年,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左舜生加入该党以后,担任过《醒狮周报》总经理职务。“九一八”事变以后,左舜生与青年党人陈启天在上海创办《民声周刊》,并写了大量文章,呼吁“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1931年10月24日,左舜生发表《且看今后的国民党》一文,希望“国民党能变成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党派”。他认为这样一来,其他党派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因此,“国民党能团结起来,不仅是国家之福,也是其他党派之幸。”(《左舜生年谱》,94页,台湾“国史馆”1998年印行)
10月31日,左舜生在《注意日本的所谓条件》一文中指出:“日本这一次的出兵占领辽吉,完全是对中国抱着一个算总账的态度,日本既下了一百二十分的决心,在他们是大有不达目的不止之势。我们立在国民的地位,遇着这样一个死不争气的政府,假如我们也不抱定一百二十分的决心,也不抱定一个与日本算一回总账的坚决态度,则不仅辽吉两省有名存实亡之忧,就想要在最近的中日交涉上稍稍有一点补救,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同上,84~85页)
11月21日,因为日本要利用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因此左舜生在《日本利用溥仪复辟的严重性》一文中说:这件事一旦成功,日本每年支付数百万供养这个傀儡,而东北“一切军政、财政、交通、金融、警察的大权,则完全入于日本人的掌握。名义上是民族自决,满人治满,实际上则东北三省,已完全夷为朝鲜第二”了!(同上,85页)
11月28日,国民政府拟召开国难会议,左舜生在《我们理想中的国难会议》中说:“希望它不是一个虚应故事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敷衍残局的工具,它应该是在这个国难期中能够彻头彻尾去完成它救国工作的唯一机关。”与此同时,左舜生还希望“这个会不开则已,如果要开,它应该是全国经济、智慧、良心的总团结”。(同上,85~86页)。
此外,青年党领导人曾琦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也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建立国防政府,以武力收复失地”;二是“取消一党专政,合全国一致对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19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发行)
四、丁文江的假设
1932年1月底,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向上海发动突然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史称“淞沪抗战”。随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形成蒋介石主管军事、汪精卫主管政治的局面。
8月初,汪精卫通电辞职,理由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张学良不仅没有任何行动,反而“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还说,“当此民穷财尽之际”,我绝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随后,张学良也发表谈话,决定辞职。
对于这样一个局面,胡适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时期,负中央重责的行政院长不应该因对一个疆吏的不满意就骤然抛弃他的重大责任。”第二,政府对于张学良“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的大罪,应该明令惩处,追究责任。第三,汪精卫在通电中说张学良“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有攻讦之嫌。这说明政府还没有走上健康的政治轨道。(《独立评论》第13号,2页)另外,针对张学良也要辞职的表态,胡适还有如下劝诫:“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坏他的身体和精神,壮年的惨痛奇辱也许可以完全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他能决心离开他现在的生活,到外国去过几年勤苦的学生生活,看看现代的国家是怎样统治的,学学先进国家的领袖是怎样过日子的,——那么,将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尽有他可以服务效劳的机会。”这段话既推心置腹,又毫不客气。可惜张学良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忠告。
与此同时,丁文江以《假如我是张学良》为题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他说:“大难当前,军政首领依然不能合作,真正使我们觉得中华民国的末日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只希望他(指张学良)牺牲一部分的实力,为国家争点人格,使日本人取平津必须出相当的代价。”
他还说:“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的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可以利用喜峰口、古北口、南口等天然屏障,另一方面是可以得到太原兵工厂“比较新式”的武器。
由于张学良还向中央政府索要巨额军费,所以丁文江又说:“假如我是张学良,我一定请中央一面派人点验我的军队的枪支人数军实,一面把所有华北的税收机关由中央派人接收。”言外之意,张学良在军队实力上有暗箱操作之嫌,在财务税收上有乘机搜刮之虞。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丁文江作了这样的结论:假如张学良能够改弦易辙,“中华民国也许还有一线的希望!”(同上,5~6页)
此外,另一位著名学者任鸿隽也在《为张学良进一言》中说:既然有人指责张学良“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那么张学良就应该“做出一个毁家纾难的义举,自己拿出三五百万来做抗日的军费”(《独立评论》第15号,8~10页)。这样一来,所谓“聚敛”、所谓“要挟”、所谓“搜刮”等说法就会不攻自破,大家对张先生的人格与决心,也就不会怀疑了。
五、傅斯年的看法
“九一八”事变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给自己的老乡、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去信说:“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他还表示: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傅斯年全集》第七卷,10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年以后,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的纪念文章。文章首先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它不仅是近百年来东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也是20世纪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的第三件大事。
紧接着,文章对这一事件做了进一步分析。傅斯年认为,从表面上看,“九一八”事变给我们带来四大失望:一是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统治者居然拿不出一个对应的办法来;二是面对如此巨变,普通老百姓仍然是醉生梦死,毫无振作的气象;三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始终是隔岸观火,麻木不仁;四是中国政治居然没有一条很好的出路。失望至此,就会绝望。因此不免想到以下三个办法:“一、自杀,免得活着难过。二、暗杀,暗杀国贼巨丑,乃下至污吏奸商,或者自己的仇人也可以。三、穷极享乐,只顾今朝,快乐反正赚到,因此死了尤妙。”
通过一番分析,傅斯年得出如下结论:如果从浅层次来看是绝望的话,那么从深层次来看则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傅斯年全集》第四卷,30~38页)
此外,著名学者刘文典也在《独立评论》第19号、20号发表题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的长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