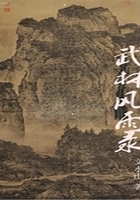
第79章 剑芒乍展
“艄公爷爷,远哥哥昨夜走夜路丢了魂魄么?”时至午后,宇文远仍是那般失魂落魄模样,一招一式便像是在摆架子一般。郑润儿自中午吃饭时就见宇文远这般模样,越看越是心慌,忍不住对独孤胜道。独孤胜见她说的认真,反是一愣,郑润儿连忙道:“就是我这村中小孩子,晚上出门,碰见不干净的东西,惊丢了魂魄,要烧纸拜祭,还要叫唤他的名字,才能唤的回来哩。”
独孤胜这才明白,郑润儿这村中有这风俗,他也曾见过,不由一笑,对着郑润儿道:“他不是失了魂魄,是失了师父。”
“失了师父?昨日那和尚师父不是还在这里么?再说和尚师父天天出去,哪里就失去了?”独孤胜见她也是不明所以,也不再多说此事,却道:“艄公爷爷跟你说件事情,过几日,艄公爷爷要到远地方走一趟,只怕有些时日才能回来,你自己手上这功夫,要勤加练习,切莫耽搁了。”
郑润儿闻言一愣,迟疑道:“那这里每日岂不是只剩下远哥哥一个人了?”独孤胜看了看宇文远道:“你远哥哥也去!”郑润儿身形忽的一停,满脸惊慌道:“那这里岂不是没有人了么?”独孤胜略觉诧异道:“正是,待得我再回来,不就又有人了么?你慌甚么?”郑润儿这才呆呆转身道:“我没慌,我没慌”言语间,眼圈微红,半晌一语不发,又去练功,只是一招一式间,不免跟宇文远一样,纯是摆了架子,毫无半点神韵。
两人自此都是痴痴呆呆,每日里便如木偶人一般。倒叫独孤胜甚觉头痛,不过也多少知道他二人心事,不去管他。直到将及半月,天气渐凉,两人这才慢慢将各自心事搁下。只是宇文远这几日,心事虽减,招式却愈来愈是散漫,常觉胸闷气短,说道像是有甚么堵在胸口,积郁不出一般,独孤胜知他心脉那股古怪内力散功殆尽,伤势不免便要显露出来,也不去说,只是命他每日将每日里内息运转时辰减少一半,免得有所差错。
又过七八日,宇文远症状愈来愈重,非但郑润儿忧心忡忡,就连每天内力运转周天之时,独孤胜也不在垂钓,就于宇文远身边盘膝而坐,以防不测。这一日午后,独孤胜照例吩咐宇文远同郑润儿相对拆招,两人来来去去过了三十余招,只见宇文远脚步虚浮,招式错乱,一个失神之下,便中了两指,郑润儿刚笑说了一声:“远哥哥今天怎地这般不济…。。”一句话还未说完,宇文远跄然跪倒,喉头咯咯有声,口中黑血喷出,惊得郑润儿面色惨白,只道是自己一个不小心伤了宇文远。倒是独孤胜赶忙过来,说到这乃是宇文远自己内伤发作,与郑润儿无关,她如今招式虽练的似模似样,内力却还在吐纳之初,指端劲力微弱,莫说是伤宇文远,就是寻常纸张飘于空中,尚且不能穿透。幸好郑润儿这些日子以来,于这内劲、经脉、内伤等等已是略有所知,这才慢慢定下神来。
宇文远连吐十余口黑血,这才渐觉胸中烦闷之感渐退,正要起身,心口一阵剧痛袭来,刚刚撑起的身子又跪倒在地,口中一股腥甜跟着冲上,此番吐出的已不是黑血,渐转血红,连吐了四五口,口鼻之中都是鲜血涌出。独孤胜脸上露出一抹喜色,命郑润儿扶着宇文远到草屋内躺下,这才道:“看来明日便要走了,你去告知虞先生一声,让他收拾行装,明日一早过来罢!”郑润儿愣了半晌,又看了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宇文远,低眉垂目应了一声,神色萧然,十分不情愿一般拖着步子去了。独孤胜这才扶起宇文远来,右手单掌抵在他大椎穴上,左手食指在自己手背一点,一股内力激荡而入,就听宇文远咳咳几声,顿时醒转过来。
“独孤前辈,我莫不是要死了么?”宇文远虽是醒转,只觉心口疼痛异常,如被撕裂一般,只道是自己内伤到底无救,只怕已是到了弥留之际。独孤胜却笑道:“死?死还早些,你如今体内古怪内力以被尽数化去,不过也久伤成病,心脉一时不能复原,已不是老夫力所能及,明日老夫便带你上路,入川寻医,有那三个怪物在世,只怕就算你娃娃想死,也有些不易。”
当夜独孤胜一晚不睡,潜运内力,疏通宇文远各处经脉,及到天明,宇文远虽仍是那般有气无力,脸色苍白,心口却不再那般剧痛,自觉气力也恢复不少,便如同当日从临安往浙西去一般,虽有些气力,也不过是能勉强行路罢了。试着运转内力,几次都是行至半途便再也提不起来,心中一惊,独孤胜这才道:“你身上原本借力搭桥之处已然不在,如今真力乃是依着你本身脉络而行,心脉有损,内力过而无力,待你这经脉伤好,便能运转周天了。”两人正说间,就听外面脚步声响,独孤胜出门一瞧,正是虞允文背着包裹,身后跟着双眼通红的郑润儿相跟而来。
“师父!”郑润儿到了近前,忽然跪倒在地,嘤嘤叫了一声,脸上泪水涟涟。倒叫独孤胜一愣,赶忙道:“这是作甚?”虞允文这才道:“郑姑娘昨日到我处,说之前大和尚说她不该叫前辈做艄公爷爷,但她却不知该叫甚么,便来问我,虞某自作主张,便告知她该是称前辈为师父,若是有不妥之处,还请前辈责怪虞某便是。”
“责怪你作甚?”独孤胜呵呵一笑,扶起郑润儿道:“师父也罢,艄公爷爷也罢,不过是个称呼罢了,不过你今日既然称老夫一声师父,你我也算有缘,切记为师不在这些日子,传你的那些功夫不可搁下,不然等为师从峨眉回来,若是考校你毫无长进,只怕连艄公爷爷都没得叫,你明白了?”
“徒儿明白了……”郑润儿哽咽道,又拿下肩头包裹道:“这里面有几件衣服,还有些银子干粮,我爷爷说让师父路上带着……”
“带它作甚!”独孤胜将那包裹一推道:“为师这里有前几日秃驴备好的盘缠,不用你爷爷再来准备,你且拿回家去。”郑润儿见独孤胜不要,心中更是惶急,泪水一阵一阵落下,倒是虞允文道:“前辈,多少也是老人家和郑姑娘一片心意,依我说,银两便不用了,衣物干粮留下,我替前辈和远哥儿背着,如何?”独孤胜见郑润儿一脸可怜,也不由点点头,虞允文便将那包裹打开,拿出几件衣物和干粮,银两之物依旧裹好,递给郑润儿轻声道:“你师父既有盘缠,路途之上只怕还有人接济,料来不会缺钱,银两之物你便带了回去,告知你爷爷,就说你师父领了他的心意了,可好?”郑润儿见如此,又素来知道独孤胜性子怪异,若在多说,只怕连这衣服干粮也不带了,当下抽抽噎噎答应。独孤胜这才命宇文远出来,自己提了癞和尚留下当做盘费的银两,三人便要上路。
“前辈,借一步说话。”虞允文见宇文远出来,又瞄了一眼神色紧张的郑润儿,暗自一笑,便与独孤胜使了个眼色,独孤胜微微一怔,不知何意,见他一副神神秘秘样子,便上前两步,虞允文这才往后一努嘴,独孤胜转头一瞧,见郑润儿似是对宇文远有话说,又不住抬头看着二人,心中明白,哈哈一笑,反倒扯着虞允文大步而行,头也不回道:“远哥儿莫耽搁太久。”
宇文远原本出门便要上路,被独孤胜这一声吩咐,倒弄的莫名其妙,心中不解,如何便是耽搁了?刚要转身跟上,就觉手臂一紧,被郑润儿紧紧抓住,诧异之下回头,就见郑润儿不似方才那般楚楚可怜样子,长长的睫毛上还带着几滴泪水,脸上却绽出意思微带苦楚的笑意来,伸手从怀中掏出一个香囊,递给宇文远,红着脸道:“远哥哥,这个……这个香囊你带在身上罢,这是我在家中菩萨面前祷祝过得,求菩萨娘娘保你这一路平安…。”宇文远依言接过,见那香囊针脚簇新,看来是郑润儿连夜做成,心中不由一番感动,正要放进怀里,郑润儿却连忙道:“带起罢,我续好的线头,最结实了!”说着拿起香囊来,展开缠在上面一缕丝线,也不管宇文远一脸尴尬,踮起脚来,亲手挂在宇文远颈中,又将香囊放入他领口之内。宇文远此刻身子僵硬,心中迷茫,只闻到一股淡淡幽香透鼻而入,也不知是那香囊上的香气,还是郑润儿身上的香气。
郑润儿将那香囊给宇文远挂好,面带笑意看了良久,眼中泪水却又涌出,慌得宇文远也不知是该劝,还是该说些甚么话来,只是呆呆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郑润儿见他如此,带着泪水噗嗤一笑,宛若梨花带雨一般,向着四周看了半晌,方才幽幽道:“以前我最喜欢这片河滩,无拘无束,既空旷,又安静,除了河水的声音,就只有鸟叫,蛐蛐叫,青蛙叫,常常一个人偷偷跑来玩耍。常想我若是长大了,能住在这里多好。可我知道只能是想想,因为我长大了,爷爷就要我嫁人了,便再也不能来这里了……后来,师父来了,盖起这座草屋,他不撑船的时候,就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钓鱼,不钓鱼的时候,就是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从早至晚都不出一声,不像我爷爷,一天到晚总是唠叨想给我找个婆家。再后来,虞先生来了,和尚师父来了,你也来了……我长这么大,这个河滩从未像这几日一样热闹,就算每天只是来送一次饭,看你跟我师父一样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练练功夫,我都觉道这日子如在梦中一般……无论刮风下雨,我都要每天来一次,亲眼看看才觉得心安,就算在梦里,我都能梦到这里,梦见这草屋,这树,这河……可是今天,你走了,艄公爷爷也走了,虞先生也走了,你们是一个个来的,却为何一起走了?往后,这里只剩下这孤零零的草屋,孤零零的树,孤零零的河,连我都是孤零零的……果真像一场梦一般,梦醒了,便甚么都没有了……远哥哥,你还会回来的,是么?是么?”郑润儿越说越悲,说到最后,竟而放声痛哭起来,宇文远被她这一说,看着这荒凉的河滩,心中也是一阵阵悲凉伤感之意,停了半晌,只觉自己眼中也是眼泪流出,对着郑润儿嗯了一声,狠狠点了点头,郑润儿这才破涕为笑,眼中无尽酸楚期盼之意,推了他一把道:“赶紧去罢,师父和虞先生要等急了……”
宇文远这才木然转身,走了几步,回头望望,见郑润儿仍是向他挥手,又转回头,走了几步,回头看时,郑润儿仍在哪里,如此这般三五次,听得前头独孤胜呼喊,这才埋头向前而行,隐隐听见风中传来依稀呜咽之声,再回头时,郑润儿已然站在河岸高处,仍是不断挥手,身后一个苍老的身影踽踽而来,应是郑老头放心不下孙女,前来接她回家来了。宇文远心中感慨之下,伸手入怀,手指还未触到那香囊所在,却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心中猛的一颤,自是当日思玉让卢颖儿送来的那半幅纱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