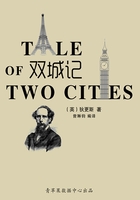
第10章 五年后
伦敦法学会大门旁的台尔森银行就算在一千七百八十年也早以算是个老式的地方。它很窄小,很阴暗,很丑陋,很不方便。它之所以是个老式的地方,如果从道德属性上讲,银行的股东们都以它的窄小、阴暗、丑陋为骄傲,以它的不方便为荣。他们甚至于炫耀它的这些突出特点,并因一种与众不同的信仰而热血沸腾:它要不是那么可厌就不会那么可敬。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信仰,而是一种能够在比较方便的业务环境中挥舞的积极武器。他们说台尔森银行用不着宽敞,用不着光线,用不着那么华丽,诺克公司可能需要,斯努克兄弟公司可能需要,可是台尔森公司,谢谢上帝!——假如有哪位董事的孩子想重新建设台尔森银行,他就会被取消了继承权。在这个问题上,台尔森银行倒是跟国家非常相似。国家老是剥夺提出修改法律和习俗的儿子们的继承权,因为法律和风俗正是因为它们长时间使人深恶痛绝而尤其可敬的。
其结果便是台尔森银行的不方便反倒是它一种完美的成就。它的大门白痴式地顽固,你把它硬推开时,它的喉咙就咕哝一声细小的声音,让你脚步摇晃直落两步台阶掉进银行,等到你反应过来,就已进入了一个可怜的店堂。那儿有两个不起眼的小柜台,柜台边衰老不堪的办事员在光线暗淡的窗户前核对签字时,会弄得你的支票簌簌发抖,就好像是有风在吹着。那窗户永远都沾有从舰队街上飞来的泥水,又因它自己的铁栅栏和法学会一层层的遮蔽而更加昏暗。如果你因为工作原因而必须会见“银行当局”,你便会被送进后面一个像“死囚牢”的地方,让你在那儿因不小心走错道路而认真的忏悔,直到“当局”双手插在口袋里慢慢的走了进来,而在那令人恐惧的昏暗里你连惊讶得眨眨眼也很难办到。你的钱是从被虫蛀的木质抽屉里取出来的,也是送到那儿去的。开关抽屉时木料的粉末就飞进你的鼻子,钻进你的喉咙。你的钞票一股霉臭味,好像很快就会被分解成碎纸。你的金银器具被塞进一个容纳肮脏之物的地方,一两天之内它们的光泽就会被周围的环境腐蚀掉。你的文件被塞进暂时将就使用的保险库里,它是用厨房的洗碗槽改变而成的。羊皮纸里的脂肪全被压了出来,搅和在银行的空气里。你装有家庭文件的比较轻一点的箱子则被送到楼上一间巴米赛德型的大厅里,那里永远摆放着一张巨大的餐桌,却从来没有设立过筵席。在那儿,就算是到了一千七百八十年,你的情人写给你的初恋情书和你的幼年的孩子写给你的第一封信件刚刚差一点受到许多人的偷看,没有多久那一排首级挂在法学会大门口示众。这种做法十分麻木、野蛮和凶狠可以跟阿比西尼亚和阿善提相比较了。
可是事实上死刑在每一个行业中都是一种时髦的窍门。台尔森银行当然也不会落后。死亡如果有利于大自然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立法上不能够采用?因此仿冒文件者处死。使用伪币者处死。私拆信件者处死。盗窃四先令六便士者处死。在台尔森银行门前为人管马却偷了马跑掉者处死。仿冒先令者处死。“犯罪”这个乐器的全部音阶,有四分之三的音符如果有谁触响了都会被处死。这样做对于防止犯罪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值得一提的倒是:事实正好相反——可它却砍掉了每一桩细节明确案件带给这世界的麻烦,抹掉了许多麻烦的事情。这样,台尔森银行便在它存在的日子里,跟它相同时代更大的企业一样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如果是在它前面落地的人头不是悄悄地解决掉,而是摆放在法学院大门口,它们便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银行底层现已不多的光线。
蜷缩在台尔森银行各种昏暗的柜橱和半截门上一丝不苟地工作着的是些年事已高的人。年轻人一进入台尔森银行就会被送到某个地方秘藏起来,一直藏到变成个老头儿。他们把他像奶酪一样存放在黑暗的角落里,等它长出蓝霉,散发出真正的台尔森香味来,再让他出来见人。那时他已在很威风地研读着厚厚的账本,并会把他的马裤和套鞋熔铸进那个机构,来增加它的分量。
台尔森银行外面有一个打杂的,不时的应应门,跑跑腿,除非有人叫,否则从不进门。这人起着银行活招牌的作用。上班时间他从来不缺席,除非是跑腿去了。可他走了也还会有他的儿子代理:那是个十二岁的丑陋的调皮小孩,长得跟那人一模一样。大家知道台尔森银行颇有气派地接纳了这个打杂的。银行一向需要容忍一个人来干这种活,而情势和潮流送到这个岗位上的就是他。这人姓克朗彻,几年前在东部的杭兹迪奇教区经教父母代为宣布厌恶魔鬼的行为时接受了杰瑞这个名字。
地点:克朗彻先生在白袍僧区悬剑胡同的私人住所。时间:安诺多米尼一千七百八十年三月一个刮风的早晨七点(克朗彻先生总把“安诺多米尼”说成“安娜。多米诺”。认为基督教纪元是从一个叫安娜的女士创造了多米诺骨牌,并且是用自己的名字为它命名而开始的)。
克朗彻先生住所的环境并不温馨,全部只有两个编号,另外一号还是一个小屋,只有一块玻璃作窗户。但这两个房间都打扫的十分干净。那个多风的三月清晨虽然时间还早得很,但他睡觉的屋子却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极其清洁的白台布已经铺在一张粗糙的松木餐桌上,上面摆好了早餐要用到的杯盘。克朗彻先生盖了一床白衲衣图案颜色鲜艳的被子,像是呆在家里的丑角。刚开始的时候他睡得很沉,后来就开始翻来翻去,最后他干脆翻到被面上,露出了他那一头凌乱的头发。此时他十分生气地叫了一声:
“他妈的,她又干起来了!”一个干净整齐,看起来很勤快的妇女从角落里站了起来(她刚才跪在那里),动作非常迅速,却带着一丝的害怕,表明挨骂的正是她。
“怎么,”克朗彻先生坐在床上找着靴子,“你又在干了,是不是?”
他用这种表达敬意的方式问了早安之后,便把靴子向那女人扔去作为第三次问候。那靴上全都是泥,可以说明克朗彻先生家庭条件的奇特情况:他每天从银行下班回到家的时候靴子总是干干净净的,可第二天早上起床时那靴子就已涂满了泥。
“你又在搞什么,”克朗彻先生没打中目标,便改变了问候方式。“又找麻烦是不是?”
“我只不过在做祈祷。”“做祈祷!多么可爱的女人!”“咚”一声跪在地下来咒我,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咒你,我只不过是在为你祈祷。”“没有。你要是真的在为我祈祷,我会那么凶么?过来!你的妈妈可真是个好女人,小杰瑞,她祈祷你的爸爸失败,不让他发迹。你那妈很有责任感,儿子。你那妈很信上帝,孩子。然后跪在地上就祈祷她唯一的儿子嘴里的奶油面包被别人抢走。”
克朗彻少爷(他这时正穿着衬衫)一听这话肯定生气,转身便向妈妈表示强烈抗议,不想让别人抢走他的食物。
“你认为你那祈祷值几个钱?”克朗彻先生说,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态度和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你这个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女人,你说你那祈祷能值几个钱?”“我是发自内心的祈祷,杰瑞。只值这一点,再也没有多的了。”
“再也没有多的,”克朗彻先生重复道。“这么说,它根本就不值几个钱。不管怎样,我不允许谁祈祷我倒霉,我告诉你。我受不了。我不可以让你叽叽咕咕祈祷得我倒了霉。你想跪可以跪,你还是为自己的家人祈祷点好的,可别祈祷他们倒霉。要不是我老婆那么不近人情,这可怜的孩子他娘不那么不近人情,我上个星期就可以赚到钱了,就不会挨人咒骂,没有得到上帝保佑,倒大霉了。他妈的!”克朗彻先生一边穿衣服一边说。“我上个礼拜运气太差,遇到了一件又一件的倒霉事,一个老实的可怜生意人所遇到的最倒霉的事!小杰瑞,穿衣服,我擦靴子的时候,你帮我盯着点你娘,她只要想跪下来你就叫我。因为,我告诉你,”他回过头又对他妻子说,“像现在这样我是不会出门的。我已经像是一部快要散架的出租马车,困得像鸦片瘾犯了一样。我的腰也累坏了,若不是因为它疼,我真的连哪里是我,哪里是别人都搞不清楚了。可是口袋里还是没有增加几文。所以我猜想你每天都在祈祷不让我的腰包鼓起来,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他奶奶的,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克朗彻先生自言自语地说着话:“啊,不错,你也信上帝,你是绝对不会干出对你男人和孩子不利的事,你不会的!”说着便从他那飞速旋转的磨盘上飞溅出讥讽的火花,同时擦着靴子做上班前的准备。这时他的儿子很听话的监视着他的母亲。这孩子头上也长着尖刺一样的头发,只不过软一些,一双年轻的眼睛靠得很近,像他爸爸。他时不时地跑出他睡觉的小屋(他在那儿梳洗),小声的叫道:“你又要跪下了,妈妈——爸爸,你看!”一番瞎折腾之后他又带着忤逆不孝的傻笑跑到屋里去了。他就这样不停地干扰着他的母亲。
克朗彻先生一直到吃早饭时脾气依然没有好转,他对克朗彻太太做祈祷感到特别的厌恶。
“够了,他奶奶的!你又玩什么花样了?”他的妻子回答说,她只不过在“乞求保佑”。“可别求!”克朗彻先生看看四周说,似乎希望面包因为他妻子的乞求而消失。“我可不希望给保佑得没了房子没了家,饭桌上没了吃的。闭嘴!”他双眼通红,脾气很大,好像昨晚都没有睡觉参加了晚会回来,而那晚会又一点意思都没有。他不是在吃早饭,而是在拿早饭发脾气,像是动物园里的居民一样对它嗥叫。快到九点的时候他才放下他耸起的鬣毛,在他那本色的自我外面摆出一种受人尊敬的公事公办的样子,出去开始他一天的工作。
虽然他喜欢把自己叫作“诚实的生意人”,其实他的工作很难被叫作“生意”。他的全部资本就是一张木头凳子。那还是用一张破椅子砍掉椅背做出来的木头凳子。小杰瑞每天早晨都会带着这凳子跟他爸爸到银行大楼,在离法学会大门一边最近的窗户前放下,再从路过的车辆上扯下一把干草,让他打零工爸爸的脚不感到寒冷。这就完成了全天的“安营扎寨”任务。克朗彻先生干这个活儿的地方在舰队街和法学院一带的名气很大,也跟这一带的建筑一样非常丑陋。
他在八点三刻“安营扎寨”完毕,刚刚来得及向走进台尔森银行年纪大的老头子们碰碰他的三角帽。在这个多风的三月清晨杰瑞上了岗位。小杰瑞如果没有进入法学院大门去骚扰,向路过的孩子们进行尖利的身体或心理伤害(要是那孩子个子不大,正好适合他这类友好活动的话),他就站在父亲旁边。父子二人非常相像,什么都不说地看着清晨的车辆在舰队街上来来往往。两个脑袋和他们那两对眼睛一样紧靠在一起,很像是一对猴子。那成年的杰瑞偶尔还咬咬干草,再吐出来,小杰瑞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舰队街上别的东西一样骨碌碌地转着、望着他。这时,两人就更加相像了。
这时,台尔森银行内部一个正式信使把脑袋从门里伸出来,说:
“要送信!”“太好了,爸爸!一大早就有生意了!”小杰瑞像这样祝贺了爸爸,就在凳子上坐了下来,对他爸爸刚才嚼过的干草产生了兴趣,并沉思起来。“永远有锈!他的指头永远有锈!”小杰瑞小声地说。“我爸爸那铁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儿并没有铁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