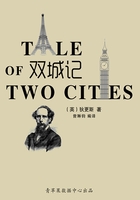
第5章 准备(2)
“只要您乐意就好,先生。”“曼内特小姐,我是个生意人,我在执行一项任务。你甚至可以把我当作一部传话的机器——我的地位本就是这样。你若是同意,小姐,我就告知你有关其中一个客户的故事。”“故事!”
他似乎刻意要误解她所重复的那个词,匆忙补充道,“是的,客户。在银行业务中和我们有过交易的人都叫做客户。他是个法国的绅士。搞科学的,颇有成就,是个医生。”
“难道是波维人?”“当然是,是波维人。跟令尊大人曼内特先生一样是波维人。这人跟令尊曼内特先生一样在巴黎也颇有名气。我有幸在那认识了他。我们之间虽然是业务关系,但是彼此都十分信任。那时我还在法国分行工作,那已是——啊!三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您能告诉我具体的时间吗,先生?”“我是指二十年前,小姐。他娶了一个英国的女士,我是替他操办婚礼的人之一。他跟许多法国人和法国家庭一样把各人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了台尔森银行来处理。同样,我是,或者说曾经是,数十上百个客户的经办人。都只是业务关系,小姐。不涉及友谊,也无特别的兴趣和感情。在我的工作中我曾换过许多客户——现在我在工作中也不断换客户。简单地说,我是没有感情的机器。”
“可你要告诉我的是关于我父亲的事。我开始觉得——”她奇怪地皱紧了眉头观察着他——“我父亲在我母亲去世后两年也去世了。是你把我带到这儿的——我几乎可以肯定。”罗瑞先生握住那信赖、却徘徊着走来想跟他握手的姑娘的小手,礼貌地放到唇上,然后把那年轻姑娘送回了座位。然后便左手扶住椅背,右手时而摸摸双颊,时而整理耳边的假发,时而低头看着她,手舞足蹈说了下去——她坐在椅子上看向他。
“曼内特小姐,是我带你回来的。你会明白我所说的是真实的事:我没有感情,我跟别人的关系都只是工作。你刚才是在暗示送你过来之后没有探望过你吧!不,从那以后你就一直受到台尔森银行的保护,我也忙于台尔森银行的其它工作。感情!我没有时间谈感情,也没有机会,小姐,我这一辈子就像是一个大无边际的金钱机器在运作。”
说完了这段关于他日常工作的奇怪描述之后,罗瑞先生用双手压平了头上的亚麻色假发(那其实全无必要,因为它那带有光泽的表面已经无法更平顺了),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姿势。
“到现在为止,小姐,这只是关于你那不幸的父亲的故事——这你已经意识到了,现在我要讲的是跟以前不同的部分。如果令尊大人并没有死去——别害怕,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了吧!”
她的确大吃一惊。她用双手抓住了他的手腕。“请你,”罗瑞先生安慰她说,把放在椅背上的左手放到紧抓住他的求援的手指上,那手指剧烈地颤抖着,“保持冷静,不要激动——这只是工作。我刚才说过——”姑娘的神色令他非常担心,他只好暂停他要说的话,走了几步,再说下去:
“我刚才说:如果曼内特先生并没有死,只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果他是被绑架了,而那时即使猜出的只是找出他被弄到了什么可怕的地方,难的只是找到他。如果他的某个同胞背叛了他,而那人却能运用某种人们不敢谈起的特权,比如凭一张空白拘捕证就能把任何人送进监牢,让他在所需要的时间内被世人忘记。假如他的妻子向国王、王后、宫廷和教会请求调查他的下落,却都杳无音讯——那么,也许这就成了你父亲的历史,也是那波维城医生的历史。”
“我求你跟我再多讲一些,先生。”“我当然可以。我马上就告诉你。可你能承受得住吗?”
“除了你现在不要再让我惶恐不安,我什么都受得了。”
“你这话确实还有自制力,而你——也确实镇静。好!”(虽然他的态度还是有所顾虑)“这是工作,就把它当成工作吧!——一种非做不可的工作。好,如果那医生的妻子很有勇气,很有魄力,在孩子生下来之前受过了大风大浪——”
“你说的那孩子是女的吗,先生?”“是女的。那是业——业务工作——请别难过。小姐,若是那可怜的太太在她的孩子出生之前经过了大风大浪,而她却决心不让孩子承受任何过去引起的痛苦,只愿让孩子相信她的父亲已经死去,让孩子就像这样长大——不,别跪下!天啦!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要知道真相。啊,亲爱的,善良仁慈的先生,我要知道真相。”
“那是——是业务。我的情绪被你搞乱了。心弄乱了怎么能谈工作呢?咱们得要保持清醒。如果你现在能告诉我九个九便士是多少,或是二十个畿尼合多少个先令,我会很高兴的。那我就放心你的心理了。”
在他温柔地把她扶起后,她静静地坐着,虽没有给他答复,但抓着他手腕的手却比刚才平静了许多,于是贾维斯·罗瑞先生才稍微松了口气。
“您是对的,您是对的。鼓起勇气!这是工作!你面前有你的工作,你能起作用的工作,曼内特小姐,你的母亲跟你一起办过这事。在她心碎地与世长辞之前她一直坚持寻找你的父亲,尽管毫无结果。她在你两岁时离开了你。她希望你像花朵一样开放,美丽、幸福,无论你的父亲是不久后全身而退,还是长期在牢里消磨时间憔悴,你都不会生活在阴霾里,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
他说这些话时怜爱地低头望着她那金色的飘洒的秀发,似乎想象着它会立即染上灰白。
“你知道你的父母并没有可观的家产,他们的财产是留给你的母亲又留下来给你的。此后再也没有发现别的任何财富,可是——”
他感到手腕被攥得紧紧的,便住了嘴。刚才他格外看重的额头上的表情已变得沉重稳定,表现出了痛苦和恐惧。
“可是我们已经——已经找到了他。他还活着。只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几乎是必然趋势。几乎成了废人——难免会这样,虽然我们可以想象的好一点。毕竟还活着,你的父亲已经被接到一个他过去的仆人家里,在巴黎。我们就要去那儿:我要去确认他,如果他没有面目全非的话。你呢,你要去延续他的生命、爱、责任心,给他休息和安慰。”
她全身颤抖,那颤抖也传遍了他的全身。她满脸惊恐的表情,仿佛梦呓一样喃喃地清晰地说:
“我一定要去看他的鬼魂!那只是他的鬼魂!——而不是他。”
罗瑞先生默默地抚摸着那只抓住他手臂的手说,“好了,好了,好了。听我说,听我说,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切。你马上就要看到这个蒙冤受屈的可怜的人了。如果一路顺风的话,你很快就会到他身边了。”
她用几乎相同的声调说,只是近似耳语,“我一直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却从未被他的灵魂纠缠。”
“还有一件事,”罗瑞先生为了让她回过神来,加重了说话的语气,“我们找到他时他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他自己的名字早就已经被忘掉了,或是被抹掉了。现在去追究他的名字似乎也只是自寻烦恼。去追究他这么多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消失的,也会是自寻烦恼。现在再去追究任何问题都是自寻烦恼,因为很危险。这个问题以后就忘了吧——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别再提了。只要想方设法把他带离这个国家就行了。我是英国人,是安全的,台尔森银行在法国也有很高的声望。可就连我和银行也都要避免提起此事。我身上没有只字片语正面提到这个事。这完全是件秘密业务。我的委任状、通行证和备忘录都包括在一句话里:‘死人复活了。’这话可以作任何解释。可是,发生什么事了?她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曼内特小姐!”
她在他的手下纹丝不动,一语不出,甚至没有靠在椅背上,却已经完全昏迷了。她瞪着眼睛注视着他,还带着那最后的表情仿佛塑像一般呆立着。她的手还紧紧地抓着他。他担心伤害了她,简直不敢把手拿开,只好停在那,大声叫人来帮忙。
一个满面怒容的妇女在旅馆仆役之前跑进屋里。尽管罗瑞已经非常激动,却还是注意到她全身一片红色。
红头发,尤其是裹着她的身体的红衣服。难以置信的女帽,好像是王室卫队掷弹兵用的大容量的木质取酒器,或是一大块斯梯尔顿奶酪。这女人马上分开了他和那柔弱的小姐——她用一只结实的手朝他的胸口一推,便让他倒退回去,撞在靠近的墙上。
(“她真像个男人!”罗瑞先生撞到墙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想。)“都在做什么,你看看你们这些人!”这个女人对旅馆仆役大叫,“你们站在那楞着做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赶快去拿东西啊?你们快去拿嗅盐、冷水和醋来,我会给你们颜色看的。快去!”
大家马上行动,去取上述的解救剂了。那妇女把病人小心翼翼地放到沙发上,娴熟地开始照顾她,叫她“我的宝贝”,“我的小鸟”,而且自毫地小心地把她一头金发摊开披到肩上。
“那个穿棕色衣服的先生,”她怒气冲冲地转向罗瑞先生,“你为什么把这些不该她知道的东西跟他说了,把她吓坏了?你看看她,漂亮的小脸儿一片煞白,手也冰凉。你认为自己的行为像一个做银行业务的吗?”
这问题不知如何回答,使罗瑞先生狼狈不堪,只好远远站着,同情和羞渐的感觉似乎因此有所减弱。这个健壮的女人用“若是你们再瞪着眼睛望着,我会给你们颜色看的”这种莫名其妙的神秘恐吓轰走了旅馆仆役之后,又一步步做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她哄着姑娘把她软垂的头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希望她现在能舒服一些,”罗瑞先生说。“就是好了也不是你的功劳——我可爱的小美人儿!”
“我希望,”罗瑞先生带着微弱的同情与羞愧沉默了一会儿,“你能陪曼内特小姐到法国去吗?”
“当然可以!”那结实的妇女说。“如果有人帮我去过海,我的命运就不会只被困在这地方了。”
这又是一个不知该如何回答的问题。贾维斯·罗瑞先生只能退到一旁思考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