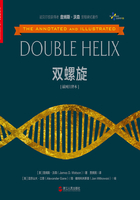
![]()
07
与克里克的第一次相见
从走进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自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离开剑桥大学了,因为我很快就发现和克里克交谈真是乐趣无穷,离开剑桥真的太愚蠢了。 在佩鲁茨的实验室里,居然可以找到一个同样认为DNA比蛋白质更加重要的人,我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如释重负:我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午餐时,我和克里克的交谈很快就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即基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刚到剑桥大学后的几天之内,就和克里克明确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模仿鲍林并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在佩鲁茨的实验室里,居然可以找到一个同样认为DNA比蛋白质更加重要的人,我真是太幸运了。而且,还有一件事也使我如释重负:我不用再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蛋白质X射线分析技术了。午餐时,我和克里克的交谈很快就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即基因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在我刚到剑桥大学后的几天之内,就和克里克明确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模仿鲍林并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鲍林在多肽链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功提醒了克里克,用同样的方法或许可以解决DNA的结构问题。但是,只要克里克身边的人没有认识到DNA是万物之本,那么与国王学院实验室在人事方面潜藏的矛盾就会使他无法真正开始研究DNA。而即使血红蛋白算不上剑桥大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克里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待的两年时间也并非毫无作为。当时蛋白质研究领域冒出了无数新问题,迫切需要有人从理论角度进行解释。

沃森、克里克与卡文迪许实验室同事的合影,摄于1952年

沃森和克里克在国王学院的后院散步,背景是国王学院教堂和克莱尔学院,摄于1952年

约翰·肯德鲁正在制作肌红蛋白模型,摄于1958年
但在我到达卡文迪许实验室后,克里克就只想着与我讨论基因问题,他再也不想把有关DNA的想法束之高阁了。当然,他也不打算放弃对实验室内其他问题的兴趣。而他每个星期花几个小时思考DNA,并帮助我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应该也不会有人介意。
不久之后,肯德鲁就看出我不大可能帮助他解决肌红蛋白的结构问题了。由于他不能制备肌红蛋白的大晶体,一开始他还希望我能在这方面助他一臂之力。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的实验技术还比不上实验室里的那位瑞士化学家。在到剑桥大学大约两星期后的某一天,为了制备新的肌红蛋白晶体,我们到一家屠宰场去取马的心脏。如果我们运气好,把马的心脏立即冷冻起来使其免遭破坏,就有可能避免肌红蛋白不能结晶的问题。后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得到结晶,但最终的结果并不比肯德鲁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结果倒是使我解脱了。因为如果结晶成功的话,肯德鲁可能会要求我继续从事蛋白质X射线衍射研究。
制备晶体的失败为我和克里克每天进行几个小时的交谈消除了障碍。当然,一天到晚光是空谈是不行的,这样做连克里克也吃不消。于是,当他在推导公式过程中碰到困难时,他就会问我一些噬菌体方面的问题;而在其他时间,克里克就努力教我结晶学知识,这些知识通常只能通过耐心阅读专业期刊上刊载的论文才能获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认真讨论了鲍林的思路,以便搞清楚他究竟是怎样发现α-螺旋的。
不久之后,我就明白了,鲍林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之上的,并不是复杂数学推导的结果。虽然在他的论证过程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公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用自然语言进行阐述也就足够了。鲍林成功的关键在于运用了结构化学的简单定律。鲍林之所以能够发现α-螺旋,不是靠盯着X射线衍射图谱看的;恰恰相反,他的主要方法是探讨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用纸和笔,他的主要工具就是一组分子模型。从表面上看,这些模型与学龄前儿童的玩具非常相似。
因此,我们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DNA的结构问题呢!我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我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先制作一系列的分子模型,然后把玩它们。如果我们运气足够好的话,也许会发现DNA的结构也是螺旋型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结构都要比这种结构复杂得多。在没有排除存在简单答案的可能性之前就去考虑复杂答案,无疑非常愚蠢。如果一味地探寻复杂的结构,鲍林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在我与克里克第一次讨论时,我们假定DNA分子包含了大量核苷酸,这些核苷酸按直线排列的方式有规律地联结在一起。我们这样推理是基于简洁性的考虑。

亚历山大·托德(Alexander Todd)的研究小组在1951年时设想的DNA结构中的“一小段”。他们认为,所有核苷酸之间的联系都是通过磷酸二酯键实现的,这种键将一个核糖上的5号碳原子联结到相邻核糖的3号碳原子上。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都是有机化学家,他们关心的是原子如何联结在一起,而没有考虑结晶学家关心的原子的三维排列问题

亚历山大·托德和莱纳斯·鲍林在康河划船,摄于1948年
虽然亚历山大・托德实验室的那些有机化学家认为,这就是核酸的基本排列方式,但他们还不能用化学方法证明所有核苷酸之间的键都是相同的,他们离这一步还远着呢。
如果DNA分子中的核苷酸不是规律性排列的,我们就无法理解DNA分子怎么能像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指出的那样,堆积在一起形成结晶聚合体。因此,假定今后在这方面没有新见解问世,那么把DNA的糖和磷酸骨架看成是规律性排列的,并试图找到一种三维螺旋构型(其中所有的主干基团都处于相同的化学环境之中),就可能是解释DNA分子结构的最佳方法,除非最后发现,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不可能有任何新进展。
很快我们就发现,解决DNA结构比解决蛋白质的α-螺旋结构更加困难。在α-螺旋中,单一的多肽链(即许多氨基酸的集合)是通过自身基团之间的氢键聚拢起来后折叠成螺旋型的。但威尔金斯曾经对克里克提及,DNA分子的直径比一条单独的多核苷酸链(许多核苷酸的集合)的直径要大些。因此,威尔金斯认为DNA是一个复杂的螺旋,包含了几条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多核苷酸链。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在开始认真构建模型以前,必须先搞清楚这些多核苷酸链之间究竟是通过氢键联结在一起的,还是通过与带负电荷的磷酸基有关的盐键联结在一起的。
再者,人们已经发现DNA含有四种不同的核苷酸,这个事实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在这个意义上,DNA其实并不是一种有规律的分子,而是一种高度无规律的分子。但这四种核苷酸并不是完全不同的。每种核苷酸都含有相同的糖和磷酸成分,将它们区别开来的是各自的含氮碱基成分。这种含氮碱基要么是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要么是嘧啶(胞嘧啶和胸腺嘧啶)。

1951年前后,人们通常用上面这种方法来表示DNA的四种碱基的化学结构式。因为没有标出位于五元环和六元环的电子,所以每个碱基都呈现为平面,厚度为3.4埃

弗洛伦丝·贝尔拍摄的DNA结构X射线衍射照片(取自她的博士论文),摄于1938年

威尔金斯和戈斯林拍摄的X射线衍射照片,分辨率的改善显而易见

阿斯特伯里,摄于20世纪50年代
由于核苷酸之间的联结只与糖和磷酸有关,因此我们的假设——相同的化学键联结了所有核苷酸——不受任何影响。于是,在构建分子模型的过程中,我们假定糖-磷酸主干是非常有规则的,而其中的碱基序列则是非常不规则的。如果碱基序列相同的话,那么所有的DNA分子就全部相同了,将不同基因区分开来的多样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虽然鲍林在几乎没有任何X射线衍射资料的条件下解决了α-螺旋结构问题,但是他还是了解那些X射线衍射资料的,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它们考虑进去了。根据X射线衍射资料,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淘汰掉一大部分可能的多肽链的三维构型。如果我们有机会利用精确的X射线衍射资料,就能更快地提出更加精确的DNA结构模型。事实上,只需要浏览一下DNA的X射线衍射图片,就能避免在开始时走上弯路了。幸运的是,在已经发表的文献中,我们找到了一张不怎么清晰的DNA图片。它是英国结晶学家阿斯特伯里在五年前拍摄的。在我们开始构建模型的初期,它派上了不小的用场。

阿斯特伯里和弗洛伦丝·贝尔,摄于1939年
如果在一开始时就能够得到威尔金斯所拥有的更加清晰的结晶图片,我们也许可以节省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但威尔金斯是图片的所有者,这个事实令我们既苦恼又无奈。
要想拿到威尔金斯的照片,除了和他商量以外别无他法。不过令我们又惊又喜的是,克里克竟然毫不费力地说服了威尔金斯,后者答应在某个周末到剑桥大学来。威尔金斯很快就接受了DNA结构是螺旋型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螺旋型结构这种猜测显而易见,而且威尔金斯自己在剑桥大学举行的一个夏季讨论会上也已经使用过“螺旋”一词。事实上,在我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的六周之前,威尔金斯曾经把那张DNA结构X射线衍射图谱拿出来展示过,那张图谱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在子午线上看不到任何反射迹象。威尔金斯的同事、理论家亚历克斯・斯托克斯(Alex Stokes)告诉他,这个现象与螺旋结构相符。据此,威尔金斯猜想DNA的螺旋结构是由三条多核苷酸链构成的。

莫里斯·威尔金斯,摄于20世纪50年代
然而,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威尔金斯并不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利用鲍林构建模型的方法,即使没有更多的X射线衍射结果,也能很快解决DNA的结构问题。我们平时闲谈时也总是会涉及富兰克林。她引发的麻烦正在与日俱增。她现在甚至坚持认为,即便是威尔金斯本人,也不应该继续拍更多的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了。威尔金斯想方设法地试图说服富兰克林,但他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谈判者。威尔金斯把自己刚开始进行这方面研究时所用的全部的高质量DNA结晶都拱手让给了富兰克林,并让步说自己仅研究其他DNA,结果到了后来他才发现留下来的DNA无法结晶。

鲁道夫·塞纳于1950年提供给威尔金斯的DNA样本
事态还在进一步恶化,最后发展到了富兰克林甚至不肯把自己得到的最新结果告诉威尔金斯的地步。威尔金斯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了解事情真相的最早时间很可能是在三个星期之后,那是在11月中旬,当时富兰克林已经准备好了要开一个讨论会,总结她过去六个月来的研究工作。威尔金斯说,欢迎我去参加富兰克林的讨论会,对此我当然非常高兴。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有了学好X射线结晶学的动力,我希望自己不会听不懂富兰克林要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