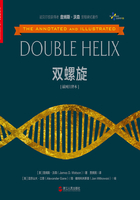
![]()
02
DNA是什么
在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克里克对DNA及其在遗传中所起作用的研究较少涉及。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思。恰恰相反,克里克放弃物理学,转而对生物学产生兴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在1946年读了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写的《生命是什么》一书。 这本书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想搞清楚什么是生命,就必须先搞清楚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薛定谔写这本书的时候(1944年),人们普遍认为基因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蛋白质分子。但是,几乎与此同时,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O.T.Avery)正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进行一系列实验,他的实验表明,纯化的DNA分子能够将遗传性状从一种细菌传递到另一种细菌。
这本书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念:基因是活细胞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想搞清楚什么是生命,就必须先搞清楚基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薛定谔写这本书的时候(1944年),人们普遍认为基因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蛋白质分子。但是,几乎与此同时,细菌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O.T.Avery)正在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进行一系列实验,他的实验表明,纯化的DNA分子能够将遗传性状从一种细菌传递到另一种细菌。

薛定谔,摄于1926年

奥斯瓦尔德·埃弗里,摄于20世纪20年代
众所周知,DNA存在于所有细胞的染色体中,因此埃弗里的实验结果造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暗示:将来的实验应该能证明所有的基因都是由DNA组成的。克里克由此意识到,如果事实果真是如此,那也就意味着蛋白质并不是那块能够解开生命之谜的罗塞塔石碑。相反,DNA却能提供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能确定基因究竟是如何决定生物性状的。这就是说,基因不仅决定了我们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而且很可能也决定了我们的智力水平,或许还决定了我们让他人开怀大笑的能力。


奥斯瓦尔德·埃弗里写给自己的兄弟罗伊的一封信(局部)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当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们错了,那么这就意味着核酸不仅在结构上是重要的,在功能上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它能够决定细胞的生物化学活性和特性。这也就意味着,通过一种已知的化学物质,就可以诱导细胞发生可预见的遗传变化。这正是遗传学家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里面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我暂时还无暇顾及。我们第一步要解决的是转化因子的化学性质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剩下的其他问题自然会有其他人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将影响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涉及化学酶、细胞代谢和碳水化合物的合成等问题。最终我们需要大量有据可查的证据来说服大家,脱氧核糖核酸,这种无蛋白质的钠盐具有生物活性和化学特性。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正试图获得更多可靠证据。把泡泡吹大当然很好玩,但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别人试图刺破它之前,自己主动去刺破它。”
当然,有些科学家认为支持DNA决定遗传性状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他们更愿意相信基因也是蛋白质分子。不过,克里克对这些怀疑并不担扰。科学界的许多人都很刚愎自用,他们总是押错赌注。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下面这一点,那么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与媒体和那些科学家母亲所说的截然不同,相当多的科学家不仅器量狭小,而且反应迟缓,甚至就是愚人一个。
但在那个时候,克里克并没有打算马上冲进DNA领域。DNA虽然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但是在当时还不足以促使他离开蛋白质研究领域。那时克里克在蛋白质领域才耕耘了两年,而且刚刚获得一些独到的心得。而他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同事们对核酸的兴趣也不是很高。即使有最充裕的经费保障,要从头建立一个主要用X射线观察DNA结构的研究小组也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伦敦国王学院,摄于1950年

莫里斯·威尔金斯,摄于1958年
而且,这样的决定还会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造成令人尴尬的局面。当时的英国,出于各种实用目的在分子层面上研究DNA的有很多,但这些工作完全被威尔金斯一个人垄断了。威尔金斯当时还是一个在伦敦国王学院工作的单身汉。 与克里克一样,威尔金斯本来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也以X射线衍射法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手段。从英国科学界当时的惯例来看,如果克里克在威尔金斯已经研究多年的领域里插上一手,似乎很是不妥。而且,情况甚至还可能更糟,因为他们两人年龄相近且彼此相识,克里克再婚以前他们经常见面,常常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借机一起讨论科学问题。
与克里克一样,威尔金斯本来也是一位物理学家,也以X射线衍射法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手段。从英国科学界当时的惯例来看,如果克里克在威尔金斯已经研究多年的领域里插上一手,似乎很是不妥。而且,情况甚至还可能更糟,因为他们两人年龄相近且彼此相识,克里克再婚以前他们经常见面,常常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借机一起讨论科学问题。
如果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事情就会容易处理得多。英国式的友善似乎织就了一张网——所有重要人物,即使不沾亲带故,也似乎全都相互认识,再加上英国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所有这些都不允许克里克染指威尔金斯的研究课题。在法国,这种“费厄泼赖”精神显然并不存在,因此也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美国学术界也不会形成这种局面:如果出现了一个一流的研究课题,你不可能指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仅仅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已经有人率先展开研究,就将这个课题拱手相让。但是,在英国,这种做法却会被认为是不妥的。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摄于1955年
更糟糕的是,威尔金斯似乎从来没有对DNA表现出过足够的热情,克里克一直觉得有点灰心。威尔金斯似乎特别喜欢从容不迫地、甚至过分谨慎地阐述重要的论点。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威尔金斯缺乏智慧和常识,很明显,他两者兼备。他率先将DNA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这一事实就是明证。令克里克觉得苦恼的是,他无法把这个想法告诉威尔金斯:当手里握着像DNA这样具有革命性的东西时,也就无须谨慎小心了。威尔金斯当时正在因他的助手富兰克林而感到费心劳神。
威尔金斯并没有爱上富兰克林,恰恰相反,几乎从富兰克林刚到威尔金斯的实验室时,他们两人就开始闹别扭了。威尔金斯当时还是一个做X射线衍射研究的新手,在专业上非常需要他人的帮助,因此他希望富兰克林作为一个久经训练的结晶学家能够帮助自己推进研究工作。但富兰克林却不是这样想的。富兰克林明确表示,她已把DNA作为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且认为自己不是威尔金斯的助手。
我猜想,威尔金斯一开始还是希望富兰克林能平静下来。然而,只要稍稍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富兰克林不是会轻易屈服的人。富兰克林丝毫不看重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特质。她看上去给人的感觉很健壮,但仍然相当有魅力。事实上,如果她愿意在衣着上稍微花点心思,那么足以迷倒一大批人。但是富兰克林并没有这样做。她从来不涂口红,不然的话,她的红唇与满头黑色直发相映衬,也许会相当美艳呢。虽然已经31岁了,她的衣着却仍然处处显示着英国青年女学者的特色。总之,富兰克林的外表很容易让人将她想象为一个事事不如意的母亲的女儿。这样的母亲过分强调职业生涯选择的重要性,认为有了好的事业,聪明的女儿便不至于嫁给蠢汉。当然事情并非如此。富兰克林所选择的这种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简朴的生活,显然不能这样来解释。事实上,富兰克林是一个博学的银行家的女儿,家境殷实,父母的生活都非常安逸。


当时的情形很清楚,富兰克林要么离开,要么服从威尔金斯的领导。当然,考虑到她的倔脾气,离开可能更合适。但是,如果富兰克林离开了,威尔金斯要想继续在DNA研究中保持主导地位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只有保持这种主导地位,威尔金斯才能放开手脚研究有关问题。当然,富兰克林觉得不满的其中一个原因,威尔金斯心知肚明。伦敦国王学院有两间餐后休息室,一间男用,另一间女用。这种安排显然大大落后于时代。 女休息室一直简陋失修,而男休息室则装修考究,威尔金斯和他的朋友们身处其中喝咖啡时都会觉得心情愉快。虽然威尔金斯本人并不需要对这种情况负责,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时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女休息室一直简陋失修,而男休息室则装修考究,威尔金斯和他的朋友们身处其中喝咖啡时都会觉得心情愉快。虽然威尔金斯本人并不需要对这种情况负责,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时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不幸的是,威尔金斯找不到任何体面的办法解雇富兰克林。在一开始洽谈时,她就被允许在实验室工作几年。而且,不能否认的是,富兰克林确实拥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假如她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她应该可以给威尔金斯提供很大的帮助。但希望通过改善关系来促进合作研究的愿望,说到底只不过是威尔金斯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加州理工学院杰出的化学家鲍林已经决定参与到竞赛中来了,而他并不受英国式“费厄泼赖”观念的束缚。那时的鲍林刚刚年过半百,他注定要尝试夺取所有科学奖项中最重要的这顶王冠。毫无疑问,鲍林对此非常感兴趣。

莱纳斯·鲍林在观察晶体,摄于1947年
事实上,鲍林如果没有认识到DNA是所有分子中最重要的王牌,他就不配被称为最伟大的化学家,这是最根本的原则。现有的确切证据证明,鲍林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鲍林曾经给威尔金斯写过一封信,向他索取DNA结晶X射线照片的副本。在犹豫了一阵以后,威尔金斯回信说,在他发表这些照片以前,还需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相关资料。

兰德尔写给鲍林的信,写于1951年8月28日
对于威尔金斯来说,富兰克林无疑是最令他心烦的。物理学研究导致了原子弹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 这引起了威尔金斯的反感,为此他转而研究生物学,结果又发现生物学也没好到哪里去。现在,鲍林和克里克两人组成的联合阵线紧紧地盯在他身后,经常使他夜不能寐。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鲍林远在9000多公里之外的美国,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的问题是富兰克林。威尔金斯无法抑制这样的想法: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最好还是打发她另谋高就。
这引起了威尔金斯的反感,为此他转而研究生物学,结果又发现生物学也没好到哪里去。现在,鲍林和克里克两人组成的联合阵线紧紧地盯在他身后,经常使他夜不能寐。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鲍林远在9000多公里之外的美国,克里克离他也有两小时的火车路程,真正的问题是富兰克林。威尔金斯无法抑制这样的想法:像富兰克林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最好还是打发她另谋高就。

威尔金斯(左起第五)在伯克利,摄于194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