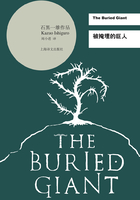
第5章
“我们要上儿子的村里去,”埃克索说,“他等着迎接我们呢。不过,我们希望天黑之前能到一个撒克逊村庄,晚上要在那儿过夜。”
“撒克逊人做事有点儿野,”那老妇人说道。“不过,看到行路的,他们比我们自己人还要热情。两位,坐下来吧。后面那段木头是干的,我经常坐那上面,很舒服。”
埃克索和比特丽丝听从她的建议,坐了下来,雨仍旧在哗哗地下,大家又沉默了一会儿。这时老妇人那边似乎有动静,埃克索转脸去看。她在用力拽兔子的耳朵,兔子拼命挣扎,她那只手却像鹰爪一样死死抓住。就在埃克索看着的时候,老妇人一只手突然拿出一把生了锈的大刀子来,放到兔子的咽喉上。比特丽丝吓了一跳,埃克索这才意识到,他们脚下,乃至整个破损的地板上,到处都有一块块的黑色,原来竟是血迹,在常春藤的气味和潮湿石块的霉味中,还夹杂着杀戮留下的气息,微弱却依稀可辨。
把刀放到兔子咽喉上之后,老妇人又不动了。埃克索发现,她深陷的眼睛正盯着另一头的那个高个子男人,好像在等他发出信号一样。但那个男人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僵硬姿势,额头几乎都快碰到墙了。他要么没注意到老妇人,要么就是一心不予理睬。
“好心的太太啊,”埃克索说,“要是必须杀,您就杀了这兔子吧。干干净净拧断脖子。或者找块石头,一下子砸死。”
“要是我有这个力气就好啦,阁下,可我没力气啊。我只有把刀,刃口还算锋利,没别的。”
“那我很乐意帮助您。不必用您的刀子。”埃克索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但老妇人没有任何放开兔子的动作。她一动不动,刀子仍旧放在兔子的咽喉上,目光凝视着房间对面的那个男人。
高个子男人终于转过身来,面对着大家。“朋友们,”他说,“刚才看你们进来,我也很吃惊,但现在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得出来,你们是好人,所以我请求你们,在等待风暴过去的时候,听听我的困难。我是个普通的船夫,把旅人渡过汹涌的水域。这工作干活时间长,如果等候的人多,我就没什么觉睡,每扳一下桨,胳膊就疼,但这些我都不在意。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日头毒辣,我都要干活。但我劲头还算足,我可以盼着休息的日子。因为我们有几个船夫,每人都能轮流休息,不过每一轮要干好几个星期。休息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地方要去,朋友们,这儿就是我的地方。我曾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这幢宅子里长大。宅子和以前不一样了,但对我来说,这儿有宝贵的记忆,我到这儿来,只求能够安安静静地享受我的记忆。现在请你们评评理。每次我一来,不到一个小时,这位老妇人就会从拱门里走进来。她坐好之后,就开始奚落我,没日没夜,一刻不停。她没有依据地狠心指责我;在黑暗的掩盖下,用最可怕的语言诅咒我。她不肯给我片刻的安宁。有时候,你们也看到了,她会带来一只兔子,或者其他小动物,就为了杀掉,用血玷污这个宝贵的地方。我想尽了办法劝说她离开,但是,无论上帝赐予了她的灵魂多少怜悯心,她都置之不理。她不走,也不停止对我的奚落。现在多亏了你们突然进来,才让她暂停了对我的烦扰。不久我就要回去了,到河上开始几个星期的劳动。朋友们,我请求你们,想点办法让她走吧。劝劝她,这样做是对神不敬。你们是从外面来的,也许能影响她。”
船夫说完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埃克索后来记得,当时他隐隐有回答的冲动,但同时又觉得这个人是在梦里跟自己说话,没有真正的义务要回答他。比特丽丝似乎也不觉得必须回答,因为她眼睛还盯着老妇人,这时候老妇人已经把刀从兔子咽喉上拿开,用刀刃的边缘抚摸着兔子的毛,那样子几乎充满爱意。最后比特丽丝说话了。
“我请求您,夫人,让我丈夫帮您杀死兔子吧。在这样的地方,没有必要流血,又没有盆接住。那会给这位诚实的船夫带来厄运,还有您自己,以及到这儿来休息的所有过路人。把刀收起来吧,换个地方仁慈地杀死这只兔子也就是了。他是个卖力的船夫,您这样戏弄他有什么好处呢?”
“公主,我们还是先不要急着跟这位女士说重话,”埃克索轻声说道。“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这位船夫似乎很诚实,可话又说回来,这位女士到这儿来这么做,可能也有正当理由。”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老妇人说。“我这辈子也没多少日子了,这样打发有什么趣味吗?我倒宁愿走得远远的,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正是因为这个船夫,我才和丈夫分开。先生,我丈夫可是个明智、谨慎的人,那次旅行,我们计划了很久,多少年都谈着它、梦着它。最后总算做好了准备,需要的东西都备齐了,我们上了路,几天后找到了那个海湾,渡过去就到了岛上。我们等着船夫,不久就看到了他的船。真是走霉运啊,来的就是那个人。你看看他个子多高。他站在船上,手里拿着长桨,背后就是天空,就像演戏的人踩高跷一样。我和丈夫站在石头上,他来到跟前,把船系好。他骗了我们,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太信任他了。岛近在眼前,这个船夫带走了我丈夫,却把我丢在岸上等着,我们在一起四十多年啊,几乎没分开过一天。我不明白他怎么能骗住我们。他的声音可能让我们进入了梦境,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划着船,带走了我丈夫,我还在岸上。可那时候,我还不相信。谁会想到这个船夫如此狠心呢?所以,我就等着。我心里想,可能是船一次只能载一名客人,那天水有些急,天空几乎和今天一样暗。我站在石头上,看着船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点。我还在等着,不久那个点变大了,船朝我这边来了。很快我就看到了船夫,脑袋光滑得像鹅卵石一样,船上没有客人。我想这次该轮到我了,很快我就能和心爱的丈夫在一起。可是,他来到我等待的地方,把绳子系到桩上,然后摇着头,拒绝让我渡过去。我又讲道理,又哭又喊,可他都不听。反而呢——真是狠心啊——反而给我一只兔子,说是在岛边的陷阱里抓到的。他想,我第一次一个人过夜,兔子带给我当晚餐倒不错。然后他看看没别人要坐船,就开船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岸上哭,手里还拿着他那该死的兔子。随后我放开兔子,让它跑到石楠地里——跟你们说,那天晚上我可没胃口吃东西,后来很多个晚上都一样。我每次来,也带个小礼物,就是这个原因。带个兔子煮给他吃,感谢他那天的好心。”
“那只兔子本来是给我自己当晚餐的,”船夫的声音从房间那边传来。“我同情她,才给了她。就是好心帮个忙。”
“先生,你们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比特丽丝说。“但是,骗这位女士,把她丢在岸上,听起来的确很残酷。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我好心的女士,这位老太太说的,可不是一般的岛。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些船夫渡了好多人过去,现在岛上的田地树林里该有几百人了吧。可那是个奇怪的地方,人一到岛上,就只能孤单地在草地上、树林里行走,看不见其他人。偶尔,如果晚上有月亮,或者风暴即将来临,也许能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但大多日子里,对每个旅行者来说,他都是岛上唯一的居民。我倒愿意把这位太太渡过去,可等她明白不能和丈夫在一起,她就说不愿意孤单地过,所以不上岛了。我听从了她的决定——我必须这么做啊——让她自己走了。兔子呢,我说过,只是好心才给她的。你们看看,她是怎么答谢的。”
“这个船夫嘴巴会讲,”老妇人说。“你们是外面来的,可他还是敢骗你们。他会让你们相信,岛上每个人都是孤魂野鬼,可实际上不是这样。我和丈夫很多年做梦都想去的,难道会是那种地方?实际情况是,很多夫妻都被允许渡海,到岛上一起生活。很多人手挽着手,在树林里和安静的沙滩上散步。我和丈夫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两位好心人啊,你们在记忆里找一找,现在就能想起来,我说的是真的。在岸边等的时候,我们哪里知道,划船过来的,竟会是一个这么残酷的船夫。”
“她说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船夫说。“偶尔会有一对夫妇,获得允许一起上岛,但这种情况很少。需要两人之间,有罕见的深爱紧紧相连。偶尔会有,这我不否认,所以如果遇到夫妻,甚至是还没有结婚的情人,要我们渡过去,我们就有责任仔细盘问他们。判断两人之间的爱是不是深到可以一起过去,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位女士不愿意承认,但她和她丈夫之间的爱就是太弱了。让她先扪心自问,然后再来说我那天的判断对不对。”
“夫人,”比特丽丝说。“您怎么说?”
老妇人不说话。她低着头,气呼呼地继续用刀摩擦着兔子的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