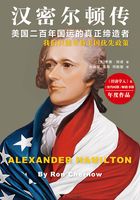
![]()
序言 年纪最大的独立战争遗孀
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日子里,当人们走过白宫附近H大街的那一片房子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那位坐在窗边收拾花草的老寡妇,是最后一位尚健在的与美国早年建国的光辉岁月有所瓜葛的人。就是在五十年前,在新泽西州威霍肯镇的一块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隐蔽的岩壁上,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小亚伦·伯尔(Aaron Burr Jr.)向她的丈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射出了致命的一枪,用卑鄙的手段除掉了这个在他看来是自己前程最大障碍的人。当时汉密尔顿才49岁。这位妻子从此被迫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七个儿女,比她的丈夫整整多活了半个世纪,几乎挨到了南北战争的前夜。对这个中年丧夫的寡妇来说,真不知道命运对她到底是仁慈还是残酷。
伊丽莎白·斯凯勒·汉密尔顿(Elizabeth Schuyler Hamilton,又被称为艾丽萨·汉密尔顿)虽已眼盲耳聋,但直到去世时依然保持着高贵与典雅的气度。这个坚忍的女人从未自怨自艾过。她那温和的性格、乐观的精神、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荷兰人特有的坚韧,支撑着她独自面对异乎寻常的不幸命运。甚至在她90岁的时候,这个坚强的女人在做祷告的时候依旧十分虔诚地双膝跪地。她身上裹着披肩,头戴一顶反映着那个时代美国人俭朴生活的镶着白色花边的帽子,衣领浆得硬硬的,穿一件黑色的斜纹布外套,这种外套是寡妇们在社交场合的典型装束。她那曾经让乔治·华盛顿将军(George Washington)属下一位年轻军官一往情深的双眸,在一副金边眼镜后面闪烁着睿智的光芒,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讲述着一段拒绝向过去屈服的记忆。
在这栋艾丽萨·汉密尔顿夫人和她的女儿合住的房子的前厅里,充满着对她来说已经远去的婚姻生活的回忆。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这位身材矮小却腰杆笔直的白发老人就会拄着拐杖,艰难地从那镶着由她亲自设计的花边的黑色沙发上站起来,带着客人回顾这段历史。首先映入客人眼帘的是一幅出自吉尔伯特·斯图亚特(Gilbert Stuart)之手的华盛顿画像。接着,艾丽萨会自豪地带着客人欣赏一个被精心放置在客厅中央桌子下的银制葡萄酒冰桶。这个葡萄酒冰桶是乔治·华盛顿送给艾丽萨的礼物。对于艾丽萨来说,这件珍贵的礼物有着特殊的含义。在她的丈夫被人陷害,卷进美国历史上第一起性丑闻的时候,华盛顿用这件礼物暗示了他的立场。接下来,艾丽萨会让客人欣赏一尊古典主义风格的大理石半身像。这座雕像是意大利雕塑家朱塞佩·塞拉其(Giuseppe Ceracchi)在汉密尔顿政治生涯的顶点——担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时雕刻完成的。汉密尔顿被雕塑家描绘成了一位肩披宽袍的高贵的古罗马参议员。雕像中的他神采奕奕,眉宇间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淡淡的微笑照亮了整个脸庞。这正是艾丽萨心中的那个汉密尔顿的形象:热情洋溢、充满希望、永远年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尊半身像。”一位年轻的访客回忆道,“因为那位老夫人在带着我们参观她的房子时,总是会在那半身像前停下脚步,拄着她的拐杖,凝视着,凝视着,就好像她永远也看不够一样。”
艾丽萨会让少数的客人看那些对她来说异常珍贵的、她丈夫留下的手稿:汉密尔顿早年所写的赞美诗,汉密尔顿在圣·克罗伊岛度过的那段穷困潦倒的少年时代时所写的一些信件……在她提到汉密尔顿的时候,她就经常会变得很忧郁,流露出马上想和“她的汉密尔顿”重新团聚的神态。一位访客回忆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她显得很忧伤,看起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当客人们在客厅等她的时候,她却一个人坐在壁炉边玩西洋双陆棋。一盘棋下罢,她便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就好像睡着了一样,许久之后,屋里的寂静被她的呢喃自语打破‘我真的很累,日子太久了,我好想他’。”[1]
艾丽萨·汉密尔顿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一项对她而言无比神圣的事业中:拯救她丈夫那被无数谣言谤语所玷污的声誉。因为,在汉密尔顿死后的很多年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汉密尔顿的其他政敌对这位已经永远不可能再为自己申辩的人的中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为了保存她亡夫的遗物,艾丽萨雇用了将近30名助手来整理汉密尔顿生前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文件材料。然而,由于艾丽萨实在过于内敛和谦逊,她所做的工作完全是基于对亡夫的敬爱,以至于在她保留了汉密尔顿留下的每一篇文字的时候,却没有保存下她自己的信件。这无疑是一大憾事,然而,艾丽萨的工作仍然是不朽的。她投入自己的一生来做这件事的精神支柱,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一本百科全书般的权威传记问世,以捍卫她亲爱的汉密尔顿在共和国先贤祠中的地位。对这本书的长久等待足以让人发狂,在一个又一个的传记作家半途而废或者皓首穷经却依然无所作为之后,自然而然地,这巨大的责任就落到了艾丽萨的四子——约翰·丘奇·汉密尔顿(John Church Hamilton)的肩上。最终,他将他父亲的事迹整理出了一部7卷本的“浩大的”传记。可惜的是,在这件原本应是送给艾丽萨的最好的礼物最终完成之前,她却先走了一步。在1854年11月9日,艾丽萨·汉密尔顿离开了人世,享年97岁。
在看到母亲为了那本能够让父亲不朽的传记而苦苦等了半辈子却最终一无所获的时候,愤怒的艾丽萨·汉密尔顿·霍利(Eliza Hamilton Holly)毫不客气地责备她那位没能及时完成任务的兄弟,“这几天,每当我悲伤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些深深地影响着妈妈的事情。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像亲爱的妈妈那样对我们的父亲一往情深。一想起妈妈的音容笑貌,一想到妈妈为了这本传记能够问世而孜孜不倦、殚精竭虑的时候,我便有了同样的使命感,‘一定要为我的汉密尔顿讨回公道’! ”[2]正如艾丽萨·汉密尔顿·霍利在这封信中所强调的那样,汉密尔顿夫人留给她的孩子们的遗言和任务便是:一定要为“我的汉密尔顿”讨回公道。
那么,他们真的为汉密尔顿讨回公道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人物能够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饱受争议,支持他的人热情地讴歌他,反对他的人恶毒地咒骂他。直到今天,他仿佛仍被“杰斐逊的民主政治”与“汉密尔顿的贵族政治”的争论所困扰。对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支持者——憧憬温馨的乌托邦生活的人们来说,汉密尔顿是美国的梅菲斯特 ,是诸如银行、工厂、股票交易所这样的“邪恶事务”的鼓吹者。汉密尔顿被他们妖魔化成了一个英国人的爪牙,隐藏的保王党人,秉承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阴谋家,一个可能在将来篡夺共和国的权力的恺撒。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强调,汉密尔顿的“野心、傲慢与飞扬跋扈”,注定让他成为“这个国家的邪恶天才”[3]。汉密尔顿所强调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州权服从于中央政府、积极行政等政治观念,无法不让人担心这种如英国王室当年的统治方式会在美国复辟。汉密尔顿那表面上对财富的热衷使得批评家们将他描绘成一个蔑视人民大众的财阀的走狗。对于另外一些批评者来说,汉密尔顿始终坚持美国应当拥有一支专业化军队的主张更是表明了他是一个潜在的暴君。“从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里都能读出拿破仑似的冒险主义。”[4]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断言道。即便是汉密尔顿的一些崇拜者对这位有着西印度群岛移民背景的伟人的态度也很暧昧。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勉强地称赞汉密尔顿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不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5]
,是诸如银行、工厂、股票交易所这样的“邪恶事务”的鼓吹者。汉密尔顿被他们妖魔化成了一个英国人的爪牙,隐藏的保王党人,秉承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阴谋家,一个可能在将来篡夺共和国的权力的恺撒。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强调,汉密尔顿的“野心、傲慢与飞扬跋扈”,注定让他成为“这个国家的邪恶天才”[3]。汉密尔顿所强调的美利坚民族主义、州权服从于中央政府、积极行政等政治观念,无法不让人担心这种如英国王室当年的统治方式会在美国复辟。汉密尔顿那表面上对财富的热衷使得批评家们将他描绘成一个蔑视人民大众的财阀的走狗。对于另外一些批评者来说,汉密尔顿始终坚持美国应当拥有一支专业化军队的主张更是表明了他是一个潜在的暴君。“从他所写的每一个字里都能读出拿破仑似的冒险主义。”[4]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断言道。即便是汉密尔顿的一些崇拜者对这位有着西印度群岛移民背景的伟人的态度也很暧昧。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勉强地称赞汉密尔顿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不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5]
然而,仍然有许多著名的评论家与艾丽萨·汉密尔顿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们对汉密尔顿的批评有失公允。汉密尔顿不像其他的开国元勋那样,被人们用堆积如山的传记去歌功颂德。英国政治家布莱斯勋爵(Lord James Bryce)指出,在美国的缔造者中,唯有汉密尔顿没有得到应有的后世评价。在他的《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这本书中,布莱斯勋爵总结道:“对于欧洲人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是谈及这个伟大人物时,他的同胞——无论是他的生前还是身后——似乎都从未承认过他的非凡天赋。”[6]在以民族主义和积极政府为特征的改革派共和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赞扬“汉密尔顿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家,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智者”。[7]他的白宫接班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同样称赞汉密尔顿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政治家”。[8]可以说,从未担任过总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恐怕远比某些当过总统的人物要深远得多。
作为一个思想家、实践者,高谈阔论的理论家与手腕干练的执行者,汉密尔顿对于许多美国的开国元勋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双重的威胁。他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是召集美国制宪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作品《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更是一部浓缩了美国立宪精神的文本。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和年轻的联邦政府架构的主要设计师,汉密尔顿将宪法原则带进了日常生活,将抽象的宪政理论融入了现实的制度。他那务实的态度影响了很多方面。他设计了可以平稳运转的联邦与州权分治架构及其预算体系、国债制度、税收体系、中央银行、海关和海岸警卫队,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来证明这些制度的合理性。他的这些成就为行政权限界定了一个极高的标准,以至于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如果说杰斐逊用他的才华让政治演说充满了诗意,那么汉密尔顿可以说是“美国政体”这篇大散文的最佳作者。再没有哪个美国开国元勋能够像他那样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有着如此清晰的洞察力,也没有哪个开国元勋能够像他那样,将这些机制整合在一起,使这片土地真正凝聚成了一个国家。
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那繁忙的几年并没有为其短暂而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增加更多的故事。从他作为一个私生子在尼维斯岛出生到他在威霍肯德血腥决斗中丢掉性命,汉密尔顿的一生充满了太多的喧嚣,以至于这样的经历只有在最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的笔下,才会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一个灰头土脸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在美国改头换面,虽然没有正当的出身和良好的教育,却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汉密尔顿从圣·克罗伊岛一个郁闷的小职员,变成乔治·华盛顿内阁里手握大权的要员的经历,既是一篇有关个人成长的传奇,更勾勒出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从她出生到蹒跚学步的一幅全景图。除了乔治·华盛顿之外,没有哪个人能够像汉密尔顿一样,从1776年到1800年,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的中心地位;也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他那样,跟那个时代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所瓜葛。这个无所不在的汉密尔顿给美国这个咿呀学语的新生儿带来了荣耀、激情和丑闻;这个无所不在的汉密尔顿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冲突中,无论是阶级冲突、地缘矛盾、种族隔阂、宗教纠纷还是意识形态间的争斗,他总是处于风口浪尖,为千夫所指。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政治人物也因为汉密尔顿的存在,而似乎注定都要扮演一个还击者的角色,需要费尽心机地去抵挡汉密尔顿抛来的一个个投枪与匕首。
汉密尔顿是一个能够用魔鬼般的速度制造大量文字的天才。他一定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在49年时间里写出最多文字的人。然而,对于他的私生活,他却是出了名的守口如瓶,尤其是对他那段不堪回首的在加勒比度过的少年时代,其他的开国元勋没有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和耻辱与不幸纠缠不清。与同时代的政治家们相比,汉密尔顿的青年时代也因此多了几分神秘感。在不削弱对他那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描写的同时,我尽力地搜集了有关汉密尔顿的种种轶事,以塑造出一个较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个睿智的男人既迷人又冲动,既浪漫又诙谐,既活泼又顽固,没有哪个传记作家能够抵挡住诱惑,不去剖析汉密尔顿的精神世界。汉密尔顿尽管天赋异秉,但他长期被自己的暴躁与自负所困扰,他总是满腹牢骚又无比好斗。他从来没有摆脱过人们对他人品的责难,他的机智更是经常被激动的情绪打败,使自己丧失最基本的判断力,以至于他最热情的追随者们都常常为此而目瞪口呆。一方面,他确实是个能够广交朋友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与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门罗和伯尔这一干人等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所展现出的巨大才华,使他一生中的其他角色黯然失色:小职员、大学生、青年诗人、随笔作家、炮兵上尉、华盛顿的战时副官、战场上的英雄、国会议员、废奴主义者、纽约银行的创始人、州议员、制宪会议成员、纽约州宪法批准大会会员、演说家、律师、雄辩者、教育家、《纽约晚报》的庇护者、外交政策理论家、陆军少将……毫无疑问,是他直接促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党派——联邦党(Federalists)的诞生,并且充当了该党的重要智囊。在华盛顿和亚当斯执政时期的连续4届总统选举中,他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16年中,美国的政治架构经他之手确立,当时的所有重大事件,背后也都有他的影子。
早几代的传记作家所能依赖的主要是汉密尔顿留下来的汗牛充栋的著作。在1961年到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哈罗德·C.希莱特(Harold C. Syrett)和他带领的了不起的编辑队伍整理出版了一部多达27卷的汉密尔顿个人与政治论文集。小朱利乌斯·戈贝尔(Julius Goebel, Jr.)和他的团队又在这已经不堪重负的书架上增加了5卷汉密尔顿所著的有关法律和商业的文集,让整套文集加起来超过了2.2万页。这些全面细致的汉密尔顿文集已经不仅仅是汉密尔顿生前作品的毫无遗漏的汇编了,它是学者的大餐,除了汉密尔顿个人的作品,还添加了丰富的专家评论和汉密尔顿时代的报纸摘要、信件和日记。还没有哪个传记作家能够完全消化如此的饕餮盛宴。我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除了阅读以上的文献外,还大量阅读了已经公开的档案文件,以及将近50篇尚未公之于众的珍贵的汉密尔顿的作品。为了将汉密尔顿的青年时代整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我还阅读了苏格兰、英格兰、丹麦和加勒比海上八个群岛的有关记录,更不用说大量的国内文献了。我希望,经过我的手描绘出的汉密尔顿一生的画像,将是栩栩如生的,即便对那些已经熟读汉密尔顿时代文献的人来说,亦能让他们惊羡不已。
这是一个回顾汉密尔顿——这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先知的一生的好机会。如果说杰斐逊极大地丰富了政治民主的观念的话,汉密尔顿则对经济机会有更敏感的嗅觉。汉密尔顿是未来——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信使。我们已经抛弃了那混合着温情脉脉的关于平均地权的动听宣传与冷冰冰真实存在的蓄奴制的杰斐逊式民主,生活在一个贸易、工业、股票市场和银行业高度繁荣的汉密尔顿所设想的世界(坚定的废奴主义也是他的经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未来联邦政府的形态和权力的设想上,汉密尔顿也是无可置疑的预言家。在杰斐逊和麦迪逊鼓吹“立法权”是民意最完美的表达的时候,汉密尔顿却赞成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执行机构、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专业化的武装力量——中央银行和完善的金融体系。现在的我们毋庸置疑的是汉密尔顿所设想的那个美国的继承人,对他的这一遗产的批判,在许多方面,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