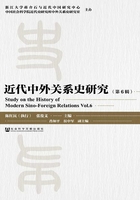
中外关系史专题
“华夷变态”后日本对清观的演变
摘要: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的认识从其入关定鼎中原起至台湾郑氏势力降服为止有很大的转变。以往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出发构建的幕府对清观主要侧重于其以己为华以清为夷的“华夷变态”意识的生成过程。此种叙述方式,往往将江户日本的“华夷变态”观放置于自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开始到近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向大陆扩张的长时段脉络中来加以考察。如此,近代日本入侵中国历史渊源便浮出水面,其一以贯之觊觎中国的思想主线更发人警惕。但是,清初至日本明治维新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中日虽未建立外交关系,但相安无事保持和平近300年,在这期间,日本幕府的对清观有过何种转变?本稿利用清初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史料“唐船风说书”对传入日本的清朝信息以及日本由此信息所建构的对清认识进行考察。“三藩之乱”平定后,台湾郑氏随即降清,海内一统,朝鲜、琉球等入贡臣服清朝,而赴日华人海商亦极言清朝社会之安宁、康熙之圣贤,在此种论述中,清朝获得与明朝同等或超出的“华”的地位,而日本幕府人士亦深受影响。
关键词:江户幕府 对清观 唐船风说书 华夷意识
一 问题的提起
19世纪后半期以来,日本在亚洲肆意扩张,将战争强加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人民,直至“二战”结束。有关近代中日之间的战争纠葛,迄今的研究积累已极为深厚。近年来学界力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注重引入长时段视角,探讨近代中日关系问题时将视线推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或“近代”以前),不再纠结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迟速”,致力于发掘“日本自身发育谱系的长时段演变特征和中日两国间的前近代消长轨迹” 的研究方向逐渐获得了发言权。
的研究方向逐渐获得了发言权。
在此种视角下,日本围绕朝鲜半岛经同中国几次大规模冲突后,已成为东亚地区唯一可与大陆政权进行公开抗衡的国家,传统东亚关系体系已从中国“一极卓立”向“两极对立”的局面转移 。日本很早就开始使用中国华夷秩序的理论装置
。日本很早就开始使用中国华夷秩序的理论装置 进行自身“日式华夷秩序”的构建,其目标由争取“对华平等”发展为“中华日本,对夷优位”,最终要达到“中华取代,天下一统”。
进行自身“日式华夷秩序”的构建,其目标由争取“对华平等”发展为“中华日本,对夷优位”,最终要达到“中华取代,天下一统”。 明清鼎革之前,其“华夷秩序”还基本上遵循“文野”程度的评判规则,且划分之区域亦仅限于他们国内或周边地区
明清鼎革之前,其“华夷秩序”还基本上遵循“文野”程度的评判规则,且划分之区域亦仅限于他们国内或周边地区 ,但明清鼎革为东亚华夷体系的震荡提供了契机,在南明乞师者和明朝遗民的影响、刺激下,日本刻意夸大清朝对于明朝的改变(“华夷变态”),并由此摆脱了自身“夷狄”的身份,提升了自身的地位,最后实现了中日两国之间“微妙的地位对调”,同时顺势增大了对琉球等地“藩属”的力度。
,但明清鼎革为东亚华夷体系的震荡提供了契机,在南明乞师者和明朝遗民的影响、刺激下,日本刻意夸大清朝对于明朝的改变(“华夷变态”),并由此摆脱了自身“夷狄”的身份,提升了自身的地位,最后实现了中日两国之间“微妙的地位对调”,同时顺势增大了对琉球等地“藩属”的力度。
由此出发,可以认为,近代日本对中琉朝等国的侵略和吞并,也应置于明清鼎革后以“中华”自居的日本,谋求取代中国中心进而达到东亚“一极卓立”的武装突进的延长线上来考察。而在“征韩论”倡导者西乡隆盛出生地萨摩藩的两乡中教育中有关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内容,无疑对西乡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丰臣秀吉侵朝的历史记忆,也为明治以来日本推进“八纮一宇”的野心提供了先例与行动的楷模,从丰臣秀吉到田中义一,通过朝鲜占据中国进而称霸世界,构成了一个“首尾连贯的日本课题”。
以上关于中日关系史的长时段考察,从政治思想史的分野出发为我们展现了更加宏大的画面,其跨越时空的论述也有着较强的理论性。但是,在论述“(日本)剑指东亚的侵略行动,定调于丰臣秀吉,承绍于明治天皇,膨胀于昭和时代” 时,如何说明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清朝、江户幕府及李氏朝鲜之间延续近三个世纪的和平状态?幕府对于明清鼎革(“华夷变态”)的刻意夸张,自说自话是否真的可以为日式“华夷秩序”提供有力支撑?抑或幕府有着对清朝更直接、现实的认识?解决这些疑问,需要我们先回到“华夷变态”所产生的历史场景对之做更细致的探讨。
时,如何说明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清朝、江户幕府及李氏朝鲜之间延续近三个世纪的和平状态?幕府对于明清鼎革(“华夷变态”)的刻意夸张,自说自话是否真的可以为日式“华夷秩序”提供有力支撑?抑或幕府有着对清朝更直接、现实的认识?解决这些疑问,需要我们先回到“华夷变态”所产生的历史场景对之做更细致的探讨。
1674年为“三藩之乱”爆发的次年,江户幕府儒官林春胜(1618~1680)接到吴三桂和郑经的讨清檄文,面对大陆云谲波诡的局势,担负幕府外交顾问的林氏亦深感有必要整理相关的海外信息。他搜集梳理了家藏的中国关系文书后,开始将由长崎送来江户的“唐船风说书”(以下简称“风说书”)续加其上辑为册子,因“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纔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注1故命名为《华夷变态》。注2此即“华夷变态”之由来。那么,“华夷变态”之说产生之前,幕府人士如何看待清朝?“三藩之乱”平定之后,他们对清朝的观感是否有变?本稿拟在讨论《华夷变态》所收风说书的基础上,对江户幕府人士之清朝观做一概观,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上述中日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提出浅见。
注1榎一雄 “華夷変態” 序、東京:東方書店、1981、頁1;以下只注书名和页码。
“華夷変態” 序、東京:東方書店、1981、頁1;以下只注书名和页码。
注2有关《华夷变态》的书志学信息及相关研究现状可参见拙稿‘日本 “華夷変態”研究
“華夷変態”研究 進展
進展 成果’、“満族史研究” 第12号、2013。
成果’、“満族史研究” 第12号、2013。
二 “三藩之乱”前幕府的清朝观
《华夷变态》所收《大明兵乱传闻自长崎注进》[落款日期为正保元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八月四日]中首次出现被记作“鞑靼人”的清朝。其中记载吴三桂与“鞑靼人”合谋,引“鞑靼之军兵”攻入北京。 相关研究显示,此年3月17日崇祯自尽,4月李自成招抚吴三桂不果发兵攻击,而吴三桂即投向清朝并与其合兵反攻北京,5月2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城。
相关研究显示,此年3月17日崇祯自尽,4月李自成招抚吴三桂不果发兵攻击,而吴三桂即投向清朝并与其合兵反攻北京,5月2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城。 清朝进入北京3个月之后北京两易其手的局面就被传入日本。而此时“清”的国号显然未曾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被认可。巧合的是,清军进入北京城的1644年5月,日本越前国三国湊(福井县坂井郡三国町)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人因风从日本海漂流至“鞑靼国”(珲春附近),登岸后漂流的日本人中有43人于6月17日被当地清人所诱杀,剩余15人则在8月末被转送至盛京,其后随同清人入关到达北京。1645年11月,此15人跟随清朝册封朝鲜世子的使团赴朝,次年经朝鲜东莱府、日本对马岛于6月16日抵达大阪。回到日本后,15人中的国田兵右卫门、宇野与三郎被召至江户,幕府当局在询问他们漂流清朝的见闻后编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后记成书日期为正保三年(1646)八月十三日]。注3从本书书名及内容,江户幕府当局内部有关此一漂流事件的记录,以及日本派向朝鲜答谢使所持“书契”中均可看出,虽然顺治帝有意通过送还漂流日本人表现其作为中华皇帝“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的盛德,并期望日本能够藉此“偏服”
清朝进入北京3个月之后北京两易其手的局面就被传入日本。而此时“清”的国号显然未曾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被认可。巧合的是,清军进入北京城的1644年5月,日本越前国三国湊(福井县坂井郡三国町)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人因风从日本海漂流至“鞑靼国”(珲春附近),登岸后漂流的日本人中有43人于6月17日被当地清人所诱杀,剩余15人则在8月末被转送至盛京,其后随同清人入关到达北京。1645年11月,此15人跟随清朝册封朝鲜世子的使团赴朝,次年经朝鲜东莱府、日本对马岛于6月16日抵达大阪。回到日本后,15人中的国田兵右卫门、宇野与三郎被召至江户,幕府当局在询问他们漂流清朝的见闻后编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后记成书日期为正保三年(1646)八月十三日]。注3从本书书名及内容,江户幕府当局内部有关此一漂流事件的记录,以及日本派向朝鲜答谢使所持“书契”中均可看出,虽然顺治帝有意通过送还漂流日本人表现其作为中华皇帝“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的盛德,并期望日本能够藉此“偏服” ,但此时日本对清仍以“鞑靼”相称。
,但此时日本对清仍以“鞑靼”相称。
注3園田一亀“韃靼漂流記 研究”、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総局庶務課、1939。杉山清彦‘“韃靼漂流記”
研究”、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総局庶務課、1939。杉山清彦‘“韃靼漂流記” 故郷
故郷 訪
訪 —越前三国湊訪問記—’、“満族史研究”第3号、2007、頁157。
—越前三国湊訪問記—’、“満族史研究”第3号、2007、頁157。
当然,通过朝鲜、还日漂民、赴日华商等渠道,幕府十分清楚清朝的年号及国号,来自朝鲜东莱府使的信息称“清人”攻取北京、南京后,“凡明朝各津各浦,参用清汉人,依仿旧制,即合蒙古,又取清朝,其地民众寡可以想知”。 而《华夷变态》内也明确记载:“明年乙酉(1645)春,吴三桂借鞑靼兵击退李自成夺回北京。三桂赴陕西逐自成,鞑靼径夺北京,改元顺清(治),号大清国。”
而《华夷变态》内也明确记载:“明年乙酉(1645)春,吴三桂借鞑靼兵击退李自成夺回北京。三桂赴陕西逐自成,鞑靼径夺北京,改元顺清(治),号大清国。” 清朝继承明朝旧制,并在其内部使用汉人的情形早为幕府所知,清朝国号等也被明记,但“清朝”的使用未能普遍。
清朝继承明朝旧制,并在其内部使用汉人的情形早为幕府所知,清朝国号等也被明记,但“清朝”的使用未能普遍。
清朝进入北京后,南明朝廷随后在南方组建。为抵抗清军计,自日本正保二年(1645)到贞享三年(1686),南明及郑氏势力共进行了16次日本“乞师”及6次“乞资”。注4其赴日乞师人士携带之书简内更渲染了清朝作为夷狄的行径。隆武朝水师总兵官崔芝于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12月派参将林高赴日乞师,在其作于12月12日,抬头为“大明国钦命总督水师便宜行事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泣血稽颡奏”的对日“奏文”中,对明清交替的表述如右:“我大明一统开基,递传三百余纪,列后延祚,相承一十六君,主圣臣忠,父慈子孝,敦睦之风,久播于来享来王之国,仁让之声,奚止于我疆我土之封。去岁甲申,数奇阳九,逆闯披猖,天催地缺,蠢尔鞑虏乘机恣毒,羶污我陵庙,侵凌我境土,戕害我生灵,迁移我重器,天怒人怨,恶贯罪盈。” 大明礼仪之邦与“鞑虏”的狡诈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崔芝以后,南明方面屡次请援,当然,其对于清朝的描述如“类同禽兽,不识礼仪文字”
大明礼仪之邦与“鞑虏”的狡诈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崔芝以后,南明方面屡次请援,当然,其对于清朝的描述如“类同禽兽,不识礼仪文字” “丑虏豺狼成性,亦欲生吞贵国(琉球)而甘心也”
“丑虏豺狼成性,亦欲生吞贵国(琉球)而甘心也” 等,与上述朝鲜方面清朝继承明朝旧制,且汉人亦加入其中的描述大相径庭。
等,与上述朝鲜方面清朝继承明朝旧制,且汉人亦加入其中的描述大相径庭。
注4中村久四郎‘明末 日本乞師及
日本乞師及 乞資’、“史学雑誌”第26巻第5号、第6号、1915。
乞資’、“史学雑誌”第26巻第5号、第6号、1915。
正保三年(顺治三年,1646)春,长崎地方官(奉行)山崎权八郎奉幕府之命对林高做了如下答复:“因大明反乱,来请助兵及军器之事,俱与众阁老言,而阁老曰,日本与大明及有百年之数,并无往来,所以日本之人,不往唐山,而唐山之船虽来日本,贸易者只是密通之说。” 自16世纪中期日本绝贡明朝至明清鼎革已及百年,而江户幕府至1630年代始即厉行“锁国”
自16世纪中期日本绝贡明朝至明清鼎革已及百年,而江户幕府至1630年代始即厉行“锁国” ,是以幕府以此为借口回绝南明乞师要求,我们也可从文中的“大明”和“唐山”一窥幕府对于明清鼎革初期中国的态度。
,是以幕府以此为借口回绝南明乞师要求,我们也可从文中的“大明”和“唐山”一窥幕府对于明清鼎革初期中国的态度。
与上述朝鲜称“清”不同,庆安二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经萨摩藩传来了琉球方面得到的大陆消息,在直至1653年才向清朝请封的琉球人眼中 ,此时清朝仍被称为“鞑靼”“鞑人”。值得注意的是,萨摩藩还有意向琉球人探听了清军马步兵组成、兵器粮草、作战特点等情况。
,此时清朝仍被称为“鞑靼”“鞑人”。值得注意的是,萨摩藩还有意向琉球人探听了清军马步兵组成、兵器粮草、作战特点等情况。
清军入北京城后,在大陆广大的区域内,反清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抵抗。 1637年已臣服清朝的朝鲜虽然已改用清朝国号,但在深受南明乞师人士影响的日本,以及稍后才朝贡清朝的琉球的记述中,至少清朝的国号还未被使用,仍处于被认知为“鞑靼”的境地。
1637年已臣服清朝的朝鲜虽然已改用清朝国号,但在深受南明乞师人士影响的日本,以及稍后才朝贡清朝的琉球的记述中,至少清朝的国号还未被使用,仍处于被认知为“鞑靼”的境地。
与清朝仍被日本称为“鞑靼”相应,明清鼎革后日本“日式华夷秩序”的论者特别看重南明及郑氏向日本的乞师。他们认为,南明人士将清朝与元朝的对接、对清朝残暴的宣扬一度激发了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出兵中国的野心,而明朝来使向日本称臣自小、对日本过分的抬高又使日人自觉获得了“华”的身份,1715年3月幕府实施的“正德新例”更固化了日清地位的逆转,而同年11月于大阪上演的近松门左卫门《国姓爷合战》则给了日本民众对于清朝的优越感。 在这种讨论中,不仅忽略了应对南明乞师要求的幕府一开始就不打算出兵,其暧昧的态度仅为敷衍国内老臣及浪人势力,以维系幕府“武威”体面的实情注5,而且也遗漏了对自南明朝廷覆灭至康熙统一台湾扫除海陆两方反对势力期间及以后的考察。以下本稿另起一章,对“三藩之乱”期间幕府清朝观的转变做一梳理。
在这种讨论中,不仅忽略了应对南明乞师要求的幕府一开始就不打算出兵,其暧昧的态度仅为敷衍国内老臣及浪人势力,以维系幕府“武威”体面的实情注5,而且也遗漏了对自南明朝廷覆灭至康熙统一台湾扫除海陆两方反对势力期间及以后的考察。以下本稿另起一章,对“三藩之乱”期间幕府清朝观的转变做一梳理。
注5小宮木代良‘明末清初日本乞師’ 家光政権
家光政権 対応——正保三年一月十二日付板倉重宗書状
対応——正保三年一月十二日付板倉重宗書状 検討
検討 中心
中心 ’、“九州史学”第97号、1990。
’、“九州史学”第97号、1990。
三 “三藩之乱”与幕府的对清认识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起兵反清,耿精忠、尚之信等随之呼应,“三藩之乱”爆发注6。吴三桂及郑经的讨清檄文由延宝二年(康熙十三年,1674)二番福州船携来日本并于六月三日送抵江户,其中吴三桂檄文内言:“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辽(僚),斗宵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山惨水愁,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鬻官卖爵,仕怨于朝,苛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途,徭役频兴,工怨于肆”。 而郑经檄文则云:“中国之视夷狄,犹峨冠之视残履,故资冠于履,则莫不腕(惋)忿,沦夏于夷(下划线为作者所加,下同),则孰不感媿……是以犬豕余孽,辄干闰位,遂使我明三百年之天下,一旦胥沦为夷狄……狡虏徒以诈力夺我天下,窃据之后,为虐益深,丞婬之丑,上及骨肉杀戮之惨,下逮狗彘,官方贪婪,役赋繁重,历观胡元之政,未有败坏如今日之甚者。”
而郑经檄文则云:“中国之视夷狄,犹峨冠之视残履,故资冠于履,则莫不腕(惋)忿,沦夏于夷(下划线为作者所加,下同),则孰不感媿……是以犬豕余孽,辄干闰位,遂使我明三百年之天下,一旦胥沦为夷狄……狡虏徒以诈力夺我天下,窃据之后,为虐益深,丞婬之丑,上及骨肉杀戮之惨,下逮狗彘,官方贪婪,役赋繁重,历观胡元之政,未有败坏如今日之甚者。” 此时距清朝入关已近30年,吴、郑均将矛头对准清朝的夷狄出身以及统治的暴虐。夷狄出身是以狡诈,为虐是为必然,由此中国“沦夏于夷”,“胥沦为夷狄”。
此时距清朝入关已近30年,吴、郑均将矛头对准清朝的夷狄出身以及统治的暴虐。夷狄出身是以狡诈,为虐是为必然,由此中国“沦夏于夷”,“胥沦为夷狄”。
注6详见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另见拙稿‘唐船風説書 見
見 鄭経
鄭経 ‘西征’、“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42号、頁144-173、2014。
‘西征’、“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42号、頁144-173、2014。
《华夷变态》编者林春胜6月4日接到此檄文,四天后,他始起念编纂《华夷变态》,并论述其编纂缘由如右:“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纔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福漳商船来往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之。吾家无不与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号华夷变态。顷间(闻)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其胜败不可知焉。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 此中林氏关于“华夷变态”的论述显然受到郑经檄文中“沦夏于夷”表述的影响,在吴郑檄文的鼓动下,深具儒学修养的林氏亦对“明朝”衣冠的恢复给予了直白的同情。
此中林氏关于“华夷变态”的论述显然受到郑经檄文中“沦夏于夷”表述的影响,在吴郑檄文的鼓动下,深具儒学修养的林氏亦对“明朝”衣冠的恢复给予了直白的同情。
除此檄文外,《华夷变态》所收署名“明遗民何倩甫”的《大明论》,以及“明遗民林上珍”的《清朝有国论》内,亦称清朝为“虏”,为“伪朝”“胡元丑类” ,居于日本的明朝遗民的主张亦不能不给日本朝野人士以强烈的影响。但是,与这些檄文及遗民士人文章内称清为虏不同,在长崎送至江户的风说书中开始频繁出现“大清”“清朝”的表述,清朝统治30年里,来日海商似乎逐渐习惯了清朝的称谓,在他们的论述里,“三藩之乱”之初乃是明清间的战争。注7以下取延宝二年至四年风说书中对清朝的表述列表如下(详见表1)。
,居于日本的明朝遗民的主张亦不能不给日本朝野人士以强烈的影响。但是,与这些檄文及遗民士人文章内称清为虏不同,在长崎送至江户的风说书中开始频繁出现“大清”“清朝”的表述,清朝统治30年里,来日海商似乎逐渐习惯了清朝的称谓,在他们的论述里,“三藩之乱”之初乃是明清间的战争。注7以下取延宝二年至四年风说书中对清朝的表述列表如下(详见表1)。
注7川胜守先生也注意到“鞑靼”“鞑靼人”的称谓在《唐船风说》书中逐渐减少的情形,并且认为这种倾向在康熙十九年(1680)左右开始显著。但以上统计可见,“三藩之乱”爆发之初(康熙十三年,1674)“清”的称谓已然占据多数。参见川勝守“日本近世 東
東 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頁234。
世界”、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頁234。
表1 “三藩之乱”期间风说书内的清朝称谓

从表1可以看到,与“三藩之乱”之前相比,风说书内称清朝、大清的情形已占绝对多数,甚至林春胜自身所做的中国势力分布图中亦不称“鞑靼”“鞑虏”或“夷狄”,而用“清国”标记。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来自朝鲜的消息反而指称清朝为“鞑靼”,“三藩之乱”爆发后,朝鲜内部有呼应三藩反攻清朝的议论注8,可否认为,此称谓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国内的形势。
注8神田信夫‘三藩 乱
乱 朝鮮’、“骏台史学”第1号、1951;葛兆光:《乱臣、英雄抑或叛贼?——从清初朝鲜对吴三桂的各种评价说起》,《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春之卷。
朝鮮’、“骏台史学”第1号、1951;葛兆光:《乱臣、英雄抑或叛贼?——从清初朝鲜对吴三桂的各种评价说起》,《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春之卷。
与此相对,上节所述琉球称清朝为“鞑靼”的情形发生逆转,虽然福建耿精忠曾就反清事宜积极联络琉球 ,但琉球改称“大清国”的事实证明了耿氏的失败。康熙十六年(1677)七月二十一日清朝福建布政使咨文引用琉球中山王世子前发咨文内云:“照得甲寅(1674)五月内,前年在闽贡使趋回本国,切切告称,福建靖藩主叛君猾夏,无名出师,伏思我祖先王蒙清朝高恩,封立藩王,是以与举国臣民,即虑朝廷惊动,切恐天下烦扰,本欲飞越而同心戮力,恨奈海山万里,不能如意耳。”
,但琉球改称“大清国”的事实证明了耿氏的失败。康熙十六年(1677)七月二十一日清朝福建布政使咨文引用琉球中山王世子前发咨文内云:“照得甲寅(1674)五月内,前年在闽贡使趋回本国,切切告称,福建靖藩主叛君猾夏,无名出师,伏思我祖先王蒙清朝高恩,封立藩王,是以与举国臣民,即虑朝廷惊动,切恐天下烦扰,本欲飞越而同心戮力,恨奈海山万里,不能如意耳。” 在这里,汉人后裔的耿精忠反而成了“猾夏”的对象,很显然,在琉球人此文中,清朝已经完全具备了“中华”的资格。当然,耿精忠已于前年(康熙十五年,1676)10月复投降清朝,并于1682年被凌迟处死。
在这里,汉人后裔的耿精忠反而成了“猾夏”的对象,很显然,在琉球人此文中,清朝已经完全具备了“中华”的资格。当然,耿精忠已于前年(康熙十五年,1676)10月复投降清朝,并于1682年被凌迟处死。
延宝六年(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十三日,林春胜接到了由东京船(越南北部)带来的吴三桂篡称皇帝的风说书 ,半月后的7月30日,林氏口述一文,对自己曾给予殷切期望的吴三桂、郑经等反清势力进行了辛辣的批判:“若其(三桂称帝)果然,则三十年来之素心,至是而见,而非忠义,而篡夺也。盖彼亦效曹操、朱温之迹,而有刘裕衰暮之叹,而不克终而然乎……又闻吴郑之外,如福建耿氏及孙将军、平南王,各割据一方,然始与吴郑相应,又降鞑寇。吴郑则蜂蚁之类,不足算也。”注9虽然清朝仍是“鞑寇”,但林氏期待以华变夷的主力——吴郑至此亦失去“华”的身份,沦为夷狄不如的“蜂蚁”。“华夷变态”得以成立的前提,已由创造出这一概念的林氏亲自否定。可以认为,原本意义上的“华夷变态”,因为“华”的不在已失去其现时性的思想价值,其后风说书逐渐向记载赴日商船运营状况的“崎港商说”性质转变的事实也印证了此处的判断。
,半月后的7月30日,林氏口述一文,对自己曾给予殷切期望的吴三桂、郑经等反清势力进行了辛辣的批判:“若其(三桂称帝)果然,则三十年来之素心,至是而见,而非忠义,而篡夺也。盖彼亦效曹操、朱温之迹,而有刘裕衰暮之叹,而不克终而然乎……又闻吴郑之外,如福建耿氏及孙将军、平南王,各割据一方,然始与吴郑相应,又降鞑寇。吴郑则蜂蚁之类,不足算也。”注9虽然清朝仍是“鞑寇”,但林氏期待以华变夷的主力——吴郑至此亦失去“华”的身份,沦为夷狄不如的“蜂蚁”。“华夷变态”得以成立的前提,已由创造出这一概念的林氏亲自否定。可以认为,原本意义上的“华夷变态”,因为“华”的不在已失去其现时性的思想价值,其后风说书逐渐向记载赴日商船运营状况的“崎港商说”性质转变的事实也印证了此处的判断。
注9林春勝‘呉鄭論’、“鵞峯林学士文集”上、第48巻、東京: 社、1997、頁509-510。
社、1997、頁509-510。
四 台湾郑氏降清后“唐船风说书”中对清朝的描述
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于1681年以吴三桂孙吴世璠的自绝而失败,此前的1680年,渡海西征的郑经已经在清朝海陆大军的压迫下放弃厦门回到台湾。注10此后清朝战和两手并用,在澎湖海战后终于逼迫郑经之子郑克塽投降。 由表2可知,就在清郑战事正酣的1682年、1683年,从台湾出发的华人海商亦未曾称呼清朝为“鞑虏”,而来自大陆的海商则共称清朝之安宁。
由表2可知,就在清郑战事正酣的1682年、1683年,从台湾出发的华人海商亦未曾称呼清朝为“鞑虏”,而来自大陆的海商则共称清朝之安宁。
注10拙稿‘海澄攻防戦(1678~1680) 清朝
清朝 鄭氏勢力’、“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43号、2015。
鄭氏勢力’、“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43号、2015。
表2 台湾降服前夕风说书关于清朝之称谓

清朝收复台湾一个月后,天和三年(康熙二十二,1683)九月九日入长崎港的二十七番南京船(山东诸城出港)“风说书”云:“大清各地一统,如今为政有道,诸方安宁,近年得享太平。各地官员有清廉之风,以至万民之下均习正道,天下无有怪异之风闻,人民仰慕大清之心与大明治平之时相同。因此诸地商买繁盛,米谷颇廉,大清安堵。” 从1640年代即笼罩在人民头上的战争阴云终于散去,达成海陆一统的大清至少在海商心中(虽然此时尚禁海,此海商为走私者)获得了与大明同等的地位。
从1640年代即笼罩在人民头上的战争阴云终于散去,达成海陆一统的大清至少在海商心中(虽然此时尚禁海,此海商为走私者)获得了与大明同等的地位。
贞享元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七月十七日八番厦门船报告康熙宽宏以待郑氏一族的信息后,林氏感慨“文武诸官、贵贱上下均感贤君之仁德” ,极力称赞康熙帝之仁德。而同年十二月四日二十四番南京船华商亦报告:“大清十五省自东宁降后各地一统,十五省共得安宁,为数十年来未有之事。地方米谷廉价,万民安堵。”
,极力称赞康熙帝之仁德。而同年十二月四日二十四番南京船华商亦报告:“大清十五省自东宁降后各地一统,十五省共得安宁,为数十年来未有之事。地方米谷廉价,万民安堵。” 福建江浙沿海均称治世。
福建江浙沿海均称治世。
台湾收复后,康熙帝即于当年启程赴山东江浙南巡 ,其南巡情形亦被海商竞相报告日方。
,其南巡情形亦被海商竞相报告日方。
贞享二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七日一番福州船华商在报告“大清十五省一统安宁,即山海之端亦不复闻贼徒”之后,对康熙帝南巡的情况做了生动的描述:“街旁屋中老若之民,为拜望龙颜而俯身途中,即发敕命于耆老,言康熙帝即朕,准尔随意拜望。白发老民以为幸事,争先奉拜,诚古今稀有之事也。” 康熙帝准许民众于路途直接拜谒,其形象亲民注11,与狡诈之鞑虏大相径庭。其不但乐于接触民众,而且在赋税免除方面亦极为大方,二月八日记录的二番南京船“风说书”亦对康熙南巡做了详细的描述。其中提到康熙帝在参拜孔子圣庙且叮嘱延续孔庙的祭祀后宣布免去山东全省赋税和抵达南京苏州后亦免去江浙三分之一赋税之事。由此“各地人民感激之情前代未闻,都鄙咸称圣君”。
康熙帝准许民众于路途直接拜谒,其形象亲民注11,与狡诈之鞑虏大相径庭。其不但乐于接触民众,而且在赋税免除方面亦极为大方,二月八日记录的二番南京船“风说书”亦对康熙南巡做了详细的描述。其中提到康熙帝在参拜孔子圣庙且叮嘱延续孔庙的祭祀后宣布免去山东全省赋税和抵达南京苏州后亦免去江浙三分之一赋税之事。由此“各地人民感激之情前代未闻,都鄙咸称圣君”。 延续前朝孔子祭祀,实行赋税减免政策的康熙被称为“圣君”。
延续前朝孔子祭祀,实行赋税减免政策的康熙被称为“圣君”。
注11岸本美绪提到清朝1680年代的江南政策时指出:清朝在一扫作为社会内部自立一极的土豪势力之同时,净化官府并使其服从于皇帝的一元化支配,尝试通过将民众舆论纠合于一君万民的德治主义来恢复社会秩序。岸本美緒“明清交替 江南社会”、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頁20。从“唐船风说书”来看,清朝纠合民众舆论的此种意图得到了实现,并且德治主义的宣传还通过海商传至海外,一定程度上对淡化清朝原本夷狄身份起到作用。
江南社会”、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頁20。从“唐船风说书”来看,清朝纠合民众舆论的此种意图得到了实现,并且德治主义的宣传还通过海商传至海外,一定程度上对淡化清朝原本夷狄身份起到作用。
此种情形下,将康熙帝及清朝称为鞑靼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贞享二年三月十八日八番南京船“风说书”如此供述:“康熙帝之本国为东鞑靼,鞑靼地分东西,原本西为大国而东为小国。康熙帝之皇父即东鞑靼之国王,因攻取大明时幸得西鞑靼之援军,是以向西鞑靼年纳谢金三万六千贯,数十年来未辍。但去年西鞑靼发兵突袭东鞑靼,消息传至北京,康熙帝即从苏州还驾。” 同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三番厦门船“风说书”云:“当年五月,北京康熙帝派户部之官一人,另名为笔帖式的鞑靼官员二人来福建。”
同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三番厦门船“风说书”云:“当年五月,北京康熙帝派户部之官一人,另名为笔帖式的鞑靼官员二人来福建。” 从以上两则史料可以看出,鞑靼已经成为特指,是“大清十五省”之外的满洲或蒙古地方的代称,在描述“满人”时,可能因为唐通事照顾了幕府官员的习惯而特地使用“鞑靼人”这一说法。
从以上两则史料可以看出,鞑靼已经成为特指,是“大清十五省”之外的满洲或蒙古地方的代称,在描述“满人”时,可能因为唐通事照顾了幕府官员的习惯而特地使用“鞑靼人”这一说法。
本稿第二节已经提到朝鲜曾报告清朝参用满汉人的信息,贞享四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十八日,二番南京船华商也就汉官的选拔报告如右:“大清情形与往日无异,各地太平。帝都北京更为安宁,虽至两三年前高官权柄尽操康熙帝之本国鞑靼人之手,但近年中华之官清廉声著,诸高官掌权者内中华之人亦多被选,由此清官日多,山海共闻太平。” 清朝朝廷官员多以清廉之汉官充任,且圣君康熙多用汉官,此种复合型的朝廷构造则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用“鞑靼”来形容了。
清朝朝廷官员多以清廉之汉官充任,且圣君康熙多用汉官,此种复合型的朝廷构造则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用“鞑靼”来形容了。
贞享三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二十八日,八十九番福州船客商云:“大清十五省静谧无事,北京康熙帝万几之暇与近侍之臣亦仅以诗词歌赋为慰,军兴之务皆无,万民亦得以共享太平之景象。福州之本省福建虽与北京路途遥远,但仰仗朝廷圣化,官民勤于己业,安稳度日。” 上至都城,下至福建边海,狡计用兵之事尽去,诗词歌赋复盛,是以贞享四年三月一日二十二番南京船客商也极力称赞清与明之无异:“大清十五省如今之安宁太平,尽与前代大明开基之时至万历时节相同,各地上下贵贱同称平治,此节如先入港之船报告无误。尤其康熙帝是为贤君,天下政道专事仁慈,万民乐业。加之太皇太后七旬有余,度量宏厚,辅助贤君成就如此盛世。”
上至都城,下至福建边海,狡计用兵之事尽去,诗词歌赋复盛,是以贞享四年三月一日二十二番南京船客商也极力称赞清与明之无异:“大清十五省如今之安宁太平,尽与前代大明开基之时至万历时节相同,各地上下贵贱同称平治,此节如先入港之船报告无误。尤其康熙帝是为贤君,天下政道专事仁慈,万民乐业。加之太皇太后七旬有余,度量宏厚,辅助贤君成就如此盛世。” 台湾降服四年后,清朝之治世几与明朝最好的时期相媲美,在海商异口同声的赞美声中,“明清鼎革=华夷变态”的林氏之判断已然被推翻。
台湾降服四年后,清朝之治世几与明朝最好的时期相媲美,在海商异口同声的赞美声中,“明清鼎革=华夷变态”的林氏之判断已然被推翻。
上述风说,亦有可能是南京海商对日人对于清人偏见的一种辩解,不知道长崎的唐通事和江户幕府相关人士看到此种说法会做何感想,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与同时期许多关于清朝安宁太平的风说一起被送往江户幕府,并被记录和认知,在清朝印刷的书籍还没有被大量运往日本之时 ,作为日人了解大陆情形最重要的渠道,它不可能不对幕府的清朝观产生影响。
,作为日人了解大陆情形最重要的渠道,它不可能不对幕府的清朝观产生影响。
以上对郑氏降清后“风说书”中有关清朝的描述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综合海商传给日本的信息,我们可以为清朝、康熙等做一番立体的复原。清朝一统后各地太平安宁,刀兵不兴,盗贼绝迹,人心纯正,民众安居乐业;朝廷治道以文治为本,尊崇儒道,登用汉官,吏员勤廉奉公;康熙帝诸事从汉俗,礼敬孔教,亲民仁厚,堪称圣贤;太皇太后慈悲为怀,专事辅佐,保朝廷安泰。这些论述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刚从战争带来的残破中复苏的人们,可能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面向日人的有意识的夸耀,也并非毫无可能。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获取此种信息的幕府人士再要把清朝以夷狄对待的话,都要面临如何说服自己的问题。“华夷变态”至此俨然成为中华引入满洲因素后蜕变为另一更“中华”的过程。正是在此基础上,幕府第四代将军和他以后的几代幕府将军都十分尊重中国,称其为“上国”,称康熙帝为“上国圣人”, 1719年清顺治帝颁布的《六谕》经琉球传入日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阅后十分欣赏和重视,命荻生徂来附以训点,经室鸠巢译成日文,以《六谕衍义》之名向全国发行。还命令把康熙的训谕《十六条》,以《圣谕广训》之名付梓刊行。1788年又把雍正帝对《十六条》训谕的敷衍译文附于书后再版,并称颂这些圣谕“为万世不易的金言”。注12
注12冯佐哲:《清代前期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第66页。另参见川勝守“日本近世 東
東 世界”、頁187-218、231-242。
世界”、頁187-218、231-242。
结语
本稿内容可做小结如右:清朝入关至“三藩之乱”爆发期间,日本因传统观念及乞师南明人士、遗民等的影响,以清朝为夷狄,称其为“鞑靼”“鞑虏”。“三藩之乱”爆发后,幕府内部人士亦将明清鼎革定位为“华夷变态”,并对吴三桂、郑经等恢复明朝“华夏”给予深切同情。但随后三藩之间的内讧和叛服无常以及吴三桂的篡称帝位,使林氏等日本人深为失望,“华”的缺位使“华夷变态”之说已不能立足,“风说书”中“鞑靼”亦渐为“大清”所替换。郑氏台湾降清后海内一统,朝鲜、琉球等入贡臣服,而赴日华人海商亦极言清朝社会之安宁、官员之勤廉、康熙之圣贤,在此种论述中,清朝获得与明朝同等或超出的“华”的地位,而日本幕府人士亦深受影响。
在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中,必然要对很多历史细节加以舍弃,清朝与江户幕府在官方互不接触,但在有管理地开放民间商业交流的“沉默外交”注13体制下,相安无事近250年,这种默然的、没有发生可值得记述的大事件的历史就容易被忽视,最后丰臣秀吉则跨越江户时代与明治、昭和“接统”。在此语境中,“华夷变态”也生发出不同的意味,并在近代被石原道博等人所恶用 。本稿认为,应让“华夷变态”回到它所产生的历史场景进行定位,并在此基础之上再来探讨中日关系长时段的演变,不仅要聚焦于日本“雄飞”大陆野心的思想谱系,还要探求清朝幕府何以能够在地域理念互斥的情况下相安无事,只有如此,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和有益。
。本稿认为,应让“华夷变态”回到它所产生的历史场景进行定位,并在此基础之上再来探讨中日关系长时段的演变,不仅要聚焦于日本“雄飞”大陆野心的思想谱系,还要探求清朝幕府何以能够在地域理念互斥的情况下相安无事,只有如此,研究才能更加全面和有益。
注13岩井茂樹‘清代 互市
互市 “沈黙外交”’、夫馬進
“沈黙外交”’、夫馬進 “中国東
“中国東 外交交流史
外交交流史 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358-377;岩井茂樹‘‘華夷変態’後
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358-377;岩井茂樹‘‘華夷変態’後 国際社会’、村井章介·石井正敏·荒野泰典
国際社会’、村井章介·石井正敏·荒野泰典 “日本
“日本 対外関係6近世的世界
対外関係6近世的世界 成熟”、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頁44-68;岩井茂樹‘清代中国
成熟”、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頁44-68;岩井茂樹‘清代中国 国際交易
国際交易 海防—信牌問題
海防—信牌問題 南洋海禁案
南洋海禁案 ’、井上徹
’、井上徹 “海域交流
“海域交流 政治権力
政治権力 対応”、東京:汲古書院、2011、頁189-218。
対応”、東京:汲古書院、2011、頁189-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