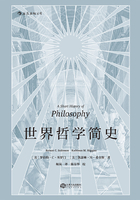
艰难时期: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日益成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对抗,不只是柏拉图的学园与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之间的对抗(当时这两座学园都已经传给了其他学者),而且还有竞相出现的新学派之间的对抗。尽管有“学园”背景,许多哲学主要关切的仍是如何生活这个人类的基本问题。不可否认,柏拉图的许多追随者从事关于数的本性和几何学(以及他的形式论)的重要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则显示了对逻辑和科学的各种兴趣。但我们在此不会追溯这些发展。相反,我们将集中于哲学家在应对日益艰难的时代所采取的不同方式,这个时代的艰难包括希腊城市——国家的解体、野心勃勃的君主之间毫无意义的战争、埃及的迫害和屠杀、罗马对希腊的蹂躏,以及罗马帝国众所周知的堕落和衰败。
柏拉图的学园持续了好几百年,在哲学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胜利和死亡,博大精深的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滋养了它们的城邦世界突然终结了。“政治”的哲学走向了终结。许多希腊科学从南方迁移到亚历山大和帕加马的港口。在亚里士多德死后发展起来的哲学,出乎意料地摆脱了他的影响,尽管柏拉图(当然还有苏格拉底)影响下的“学园派”仍是哲学中的重要力量。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拒斥了柏拉图(实际上他们深受柏拉图影响)和亚里士多德,而提倡更加唯物主义的世界概念。不过,宇宙论不是他们的主要关切所在。在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死后(分别死于公元前 323 年和公元前 322 年)的“希腊化”世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伦理学问题。①这对于“学派”的剧增也很重要,而这种剧增现象支配了整个中世纪的哲学,甚至影响到了当代哲学。因此,哲学对美好生活的寻求,也成了团体活动。或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希腊——罗马式的世界中,哲学也逐渐成为了“大众”的事业。
希腊化时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的世界大同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一点部分归功于希腊的强制统一以及对埃及和波斯的征服。希腊化世界(或多或少)是单一的世界,与之后的罗马帝国没有什么两样。特别要提及的是位于尼罗河口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Ptolemy,亚历山大手下的大将)掌管了埃及,随后发展成了文化和哲学中心。由于亚历山大里亚有座伟大的图书馆,希腊以及希伯来的经典文献得到了保存和研究。但是,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喜忧参半。在托勒密一世的统治下,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文化的主要堡垒,但在公元前 2 世纪快要结束之际,在托勒密九世(希腊人给他取的绰号是“大肚子”)的统治下,地中海周边的科学家、诗人和学者遭到了系列迫害和屠杀。最终,就像希腊征服了埃及,罗马征服了希腊和希腊文化。
在亚历山大里亚,东方的宗教相互交融,先是影响了希腊人的思想,接着又影响了罗马人的思想。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人和犹太人的交汇之地。哲学家斐洛(Philo)是第一批将经典的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先知的旧约教义结合的人,从而为基督教铺好了道路。希腊圣经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创造。甚至有狂热的哲学家竟然声称,柏拉图与摩西有同样的哲学理念。从这种文化汇流中涌现出各种形而上学思想,后来形成为中世纪神学。
不过,回到雅典,希腊化哲学促进了学派的繁荣,其中包括伊壁鸠鲁,他是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的信徒,也是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建者。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有纵情享乐之名,但他自己强烈反对这个称号。今天,所谓伊壁鸠主义者就是沉浸于感官快乐的人,这些人奢侈甚至放纵。这完全偏离了原意。事实上,伊壁鸠鲁离群索居,他学派的成员通常避免参与到同时代的激烈辩论当中。他们真正笃信的是心灵的平静。伊壁鸠鲁认为,追求快乐和感官的愉悦很“自然”。(他没有像某些犬儒派那样鄙视或谴责享乐,不过,他也没有鼓励享乐,更没有把享乐提升为生活的目的。)他主要关切的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宁静(不动心,ataraxia)。伊壁鸠鲁说,贤人甚至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也不会恐惧生活。伊壁鸠鲁声称,真正的贤人哪怕身受折磨也能获得幸福。他坚持认为,痛苦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按照伊壁鸠鲁的说法,死亡无非是构成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原子的分离而已。这样看来,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对于那些害怕诸神对他们的行迹加以审判和惩罚而恐惧的人,伊壁鸠鲁向他们保证,诸神根本不关心我们。然而,人们不应该因此认为伊壁鸠鲁厌倦生活,是纯粹的犬儒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确实主张,快乐是轻松的,我们应享受快乐。他为德性辩护,但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把它确立为生活的至高目的。德性不过是达到心灵平静的手段而已。通常,有德性的人很少有敌人,也不必担心受到指控和逮捕,因而总的来说没什么可恐惧的。
首先,伊壁鸠鲁与早他四十年的亚里士多德类似,认为友谊是美好生活的关键。实际上,在古代伦理学向我们今天的伦理学的转变中,最为显著却未受注意的是,友谊在论述美好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消失。今天,哲学家大量谈论的是道德、公共善和契约的神圣性。更为粗俗的哲学家则谈论财富和权力。他们几乎不会谈论朋友的重要性。人们可能认为,现代哲学家较倾向于简单地认为友谊理所当然,不值得进行哲学上的关切,但是,这恰恰是启示性的。在伊壁鸠鲁看来,友谊是体面生活的核心,或许正是这点而不是其他让伊壁鸠鲁受到尊崇,被认为是哲学家。后来,在罗马,伊壁鸠鲁学派成为两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之一,甚至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黯然失色。(另一种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我们马上就会论及。)
在公元前 1 世纪活动的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成了伊壁鸠鲁最忠诚、最著名的信徒(因为只有他的作品保存了下来)。他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尽管常常主要被解读为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原子论的某种版本),但他更深层的意图则是重新定义不动心这种“稳定、甜蜜的伊壁鸠鲁式宁静”并为之辩护,尤其是反驳迷信以及对诸神不必要的恐惧。不过,无论是伊壁鸠鲁还是卢克莱修,都没有否定诸神的存在。实际上,伊壁鸠鲁认为诸神的存在显而易见,卢克莱修甚至宣称诸神会在梦里造访我们。但是,根据他们的叙述,诸神的真正生活安详宁静,没有恐惧,不受人类行为打扰,也不关心人类事务。不动心,而不是爱管闲事的宙斯和赫拉(或朱庇特和朱诺,他们在罗马的对应神祇),才是诸神真正神圣的生活。
希腊化时期第二个大的哲学派别是斯多葛学派,它是希腊罗马哲学中最成功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哲学运动。有些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不久就出现了,著名的有斯多葛学派的芝诺(Zeno,约公元前 335—前 263,不要与巴门尼德的学生、爱利亚的芝诺混同),接着就是克吕西普 (Chrysippus,公元前 280—前 206 )。晚期的斯多葛学派则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期和瓦解过程中宣扬自己的学说。“生活的是艰难的”,他们的这个论点不仅影响了那些落魄的人,比如奴隶爱比克泰德(约 55—约 135),甚至影响到了那些处于权力顶峰的人。实际上,有个斯多葛学派成员是罗马的皇帝,即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
斯多葛学派的特点是对理性几近狂热的信仰。特别是,他们强化了古已有之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对抗。②柏拉图区分了灵魂的不同部分(欲望部分、激情部分和理性部分),亚里士多德也明显区分了理性和情感。不过,苏格拉底曾警告他的追随者不要让情感遮蔽他们的理性,而柏拉图则赞扬灵魂三个部分的完美和谐。亚里士多德把情感与理性视为同等重要,认为它是德性、品格和美好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他说,受到挑衅而不愤怒的人是“傻子”。)但是,随着斯多葛学派的兴起,理性和情感分道扬镳。
斯多葛学派认为,情感是非理性判断,是让我们感到沮丧和不幸福的东西。正如几个世纪之前、几千公里外的东方佛陀教导的那样:减少欲望就会减少痛苦。爱比克泰德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不要求事情如你所愿那般发生,而要让事情自行发生,这样你就会生活幸福。”③
斯多葛学派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处混乱世界,这是虚荣、残酷和丑恶横行的世界。然而,他们相信宇宙是理性,只是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非理性的或荒谬的。他们也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认为它是“神圣的火花”,能够使我们看透人类关切的残酷和卑琐愚蠢,从而理解更大的合理性。
克吕西普通过重提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观念,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只关心它所谓的原则性原因(形式因或目的因)——也就是说,我们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在我们自身之中、在我们的品格中找到。我们应该忽略那些外在于我们的纯粹偶然的原因(动力因)。一般来说,斯多葛学派宣扬我们应“按照自然”生活,不过,如今自然被认为“与理性一致”,而不是与我们的情感一致。实际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理想可以概括为“不动心”(apatheia)。因此,他们拒绝人类的虚荣和骄傲。他们教导说,愤怒毫无意义,只能自我毁灭,爱甚至友谊都是危险之物,贤哲只需要有限的财物,不应惧怕悲惨和死亡。
与注重精神的希腊人相比,务实的罗马人不怎么待见哲学,因此哲学家在这个时期比较遭罪。罗马重要哲学家塞涅卡(Seneca)的悲惨命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危险时代的政治家。在疯狂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的统治下,他只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才勉强逃脱了死刑,他还陷入了与克劳迪乌斯的严重麻烦(塞涅卡无情地嘲笑了后者自以为的神圣性)。然而,在性情乖张的腐化皇帝尼禄统治下任职时,塞涅卡(因所谓的谋反)被勒令自杀,然后他照办了。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悲剧和不义而产生的,因此,它的持续不变的主题是强调通过理性超然于生活的荒谬的重要性。
斯多葛主义是极端的哲学,但在艰难的时代里有助于许多灵魂的安顿。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它成了极为盛行的哲学。实际上,斯多葛学派为禁欲主义所作的辩护,以及它们关于看似非理性的世界中包含更大的合理性的洞见,后来为早期的基督徒所继承,成了基督教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最后,还有更为极端的哲学派别,即怀疑论,它从古希腊的皮浪(Pyrrho,约公元前 360—约前 272)流传到罗马的塞克图斯·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3 世纪)。皮浪宣称,避免信仰是通往宁静的必经之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宁静[不动心]的观念可能来源于印度。)无疑,正如好几代怀疑论者,恩披里柯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皮浪如何差点掉落悬崖,在马群和战车中行走,又是如何饮食毫无规律、毫不在意,他之所以还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朋友和学生的警觉。(倘若他真的活到了九十岁,这些故事无疑可以说是假的。)当然,皮浪并没有费心写下任何东西。(哲学家在实践中与自己相矛盾的程度是有所限制的。)这种徒劳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塞克图斯·恩披里柯是虽不算雄辩但充满活力的作家,是强有力的辩证法学家,据说,他还是优秀的医生。他极少下断言,但对所有人和事都进行冷酷无情的质疑。(类似于苏格拉底,怀疑论者发现,这种做法在论辩中有巨大的优势,即无需断言任何东西,同时却可以要求他人提供充足的证明和证据。)从柏拉图的老学园开始,早期的怀疑论者反对斯多葛学派(他们称这个学派的人为“教条主义者”),主张所有信仰,包括对理性的信仰,都是不满和不和谐的根源。与打着怀疑论旗号的现代运动不同,古代的怀疑论者关切的几乎完全是伦理学,而不是知识及其确证的可能性。
无论关于信仰的本性和确证有什么样的论证,怀疑主义首先是生活哲学。它首要关切的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即有没有这种生活方式,人们藉此可以应对这个世界常见的残酷、悲剧和不公正。怀疑论者主张,悬置信仰(悬搁)首先是治疗形式,是让自己超脱的方式,是宁静之道——即免于恐惧的安静和自由。因此,它完全不同于现代盛行的怀疑主义。现代怀疑主义仍存在于大学生活和各种书籍之中,被认为是关切信念之确证的令人困扰却又显然不可解决的悖论,但是,它几乎不关注这些问题的实践意味。在古代的怀疑论者看来,普遍的怀疑是智慧,是合理的生活方式。那种纯粹出于理智的怀疑主义观念,尤其是当它与教条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念相互联系,在他们看来是伪善和荒谬的。
怀疑主义的传统,尤其是作为斯多葛学派的对立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时期柏拉图学园的领导者。早在公元前 3 世纪初,他们就通过扩展苏格拉底的怀疑论(人不知道或者无法知道任何事情)的内涵,发动了对斯多葛学派的知识论的全面攻击。学园追求的既有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也有苏格拉底的方法。
或许,这种苏格拉底方法最有名的提倡者,是罗马政治家、演说家马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 106—前 43)。尽管他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发现了许多值得欣赏的东西(有时甚至从那里借用了不少东西,相反,他在伊壁鸠鲁学派那里发现了许多令人嘲笑的东西),但考虑自己在公共争论中的角色,④他觉得怀疑论者称许的那种对不同观点的质疑,既有吸引力,又很实用。因此,毫不奇怪,他成了修辞学和我们今天所谓的 “应用伦理学”的拥护者,所谓“应用伦理学”,就是处理政治和日常事务的方法。(如果你正在售卖的房子屋顶漏水,你有义务告知买方吗?)类似于其他怀疑论者,他发起了一场严肃的运动,常用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没有阐述任何哲学“体系”。因此,他是决疑术(把特定情境下做出具体论证时用到的所有原理搜集起来)的发明者,决疑术就像它之前对应的“诡辩术”,长时间以来都名声不佳。
尽管如此,在最好的苏格拉底方法的学园传统中,他们仍把知识确立为终极理想(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柏拉图的形式论开始慢慢得到复兴)。“学园派”认为斯多葛学派(以及伊壁鸠鲁学派)是“教条主义者”。实际上,尽管内部有各种纷争,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说都有显而易见的连续性。不过,这种“教条”也为人们得到慰藉提供了来源,即认为信仰、自足与命运相伴而行、密不可分,而且,在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斯多葛主义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后来成了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看法。
相应地,怀疑主义的强烈反对者是希腊医生盖伦(Galen,约 129—约 199)。(怀疑论者塞克图斯·恩披里柯也是医生——哲学家。)除了在医术和医学理论上有诸多贡献,盖伦还常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社会现象。他抱怨道,既然教师一开始就剥夺了学生的教育基础,即一个有所知的教师,那么教师又能如何进行教育呢?不过,他也质疑斯多葛学派强有力的观点,认为他们过分强调情感和品格的意愿方面。他论证道,既然情感更多是生理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想要人对他的激情负责就是误导性的说法。比如,当人们观察小孩子的行为,会禁不住被小孩很早就确立品格意识打动。人有多少选择,他应如何生活,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范围是有限的。在最惨然辉煌的哲学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这样的常识之音、实践之声。哲学在人们之间的交流中繁荣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