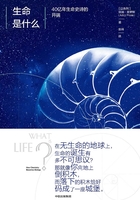
序
我整个下午都在津津有味地思考生命。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觉,生命是多么奇妙的事物!你知道吗,它和世间其他事物是如此不同,希望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
——佩勒姆·格伦维尔·沃德豪斯
(P. G. Wodehouse)
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一些基本问题,数千年来,它们一直困扰并折磨着人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探索,即对生命体与无生命物体之间关系的追问。无论我们怎么强调确切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都不会言过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将揭示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而且将影响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理解。宇宙是不是像人择原理(anthropic principle) 的支持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过精密的调控支持着生命体的运作呢?又或者,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不是更接近哥白尼的(Copernican)看法呢?用知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话来说,“人类不过是生活在一颗中等大小行星上的化学废料”。我们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两种观点差别更大的看法了。
的支持者所指出的那样,通过精密的调控支持着生命体的运作呢?又或者,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不是更接近哥白尼的(Copernican)看法呢?用知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话来说,“人类不过是生活在一颗中等大小行星上的化学废料”。我们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两种观点差别更大的看法了。
20世纪40年代,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撰写了一本标题引人注目的书——《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该书在一开头便谈到了这个问题,薛定谔写道:
在一个有机体的空间范围内,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该如何用物理和化学来描述?初步的答案……可以概括如下:当今的物理和化学虽然在描述这些事件上无能为力,但并不代表这样的事件不能被这些科学所描述。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这些年来伴随着诺贝尔奖获奖名单不断加长,人类在分子生物学领域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困扰于薛定谔那简单而直接的问题,它的确让人感到困惑。20世纪顶尖的生物学家卡尔·乌斯(Carl Woese)甚至声称,当前生物学所处的状态正类似于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在20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埃尔温·薛定谔和其他伟大的物理学家还没有完成对物理学的变革,而现在,生物学的变革也还没有完全实现。这确实是一个颇为激进的看法!不过令人失望的是,现代生物学仿佛心满意足地漫步于当前机械式的研究道路上,大多数从业人员对于要求重新审视学科的尖锐呼声,不是无知无觉就是漠不关心。
没错,身处于现代的我们明确地知道生命冲力(élan vital) 是不存在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一样,都由没有生物活性的“死”分子构成,但是这些分子在一曲完整的“生命大合奏”中相互作用的独特方式,形成了十分独特的结果——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生命体的诞生。尽管半个世纪以来分子生物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它与没有生命的世界有何关联,又是如何出现的。诚然,半个世纪以来为了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人们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那通往“应许之地”的大门却仿佛依然遥不可及。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地平线处那象征着绿洲的棕榈树在闪烁着微光,当这一切仿佛触手可及的时候,这景象又消失了,徒留我们去体会对未知世界难耐的饥渴和无法满足的冲动。
是不存在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一样,都由没有生物活性的“死”分子构成,但是这些分子在一曲完整的“生命大合奏”中相互作用的独特方式,形成了十分独特的结果——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生命体的诞生。尽管半个世纪以来分子生物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我们依然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它与没有生命的世界有何关联,又是如何出现的。诚然,半个世纪以来为了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人们投入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那通往“应许之地”的大门却仿佛依然遥不可及。就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一样,地平线处那象征着绿洲的棕榈树在闪烁着微光,当这一切仿佛触手可及的时候,这景象又消失了,徒留我们去体会对未知世界难耐的饥渴和无法满足的冲动。
所以,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持久且令人不安的困境?为了简单地阐明问题所在,请思考下面这个虚构的场景:你行走在一片原野上,这时你忽然看到了一台冰箱。这台冰箱功能完好,里面还放着几瓶冰镇啤酒。不过,一台位于原野中央且没有与任何外界能量源相连接的冰箱是如何运作的,它又如何维持内部的低温呢?它为什么会在那里,又是怎么到那里去的?你更仔细地去观察,终于发现冰箱顶部有一块与电池相连的太阳能板,太阳能板给维持冰箱正常运作的压缩机提供所需的能量。于是冰箱运作的谜题解开了。冰箱通过光伏板获取太阳能,因此太阳就是使冰箱运作的能量源。这能量使得压缩机能够将制冷剂泵为吸收了冰箱内热量的高温蒸汽,这由冷到热的过程与自然状态下的热量流动过程恰好相反。所以,尽管自然的规律是让冰柜内外的温度趋于平衡,但这个我们称作“冰箱”的物体通过一个功能性的设计,让我们能将饮食储藏在宜人的低温环境下。
但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冰箱会出现在那里。是谁把它放在那儿的?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现在如果我告诉你没有人把冰箱放在那里,这冰箱是通过自然的力量自发产生的,你或许会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多么荒谬!这不可能!自然不是这么运作的!大自然不会自发地生成高度组织化、远离平衡态且具有目的性的实体,比如冰箱、汽车、电脑等。这些物体都是人类设计的产品,它们刻意且具有目的性。大自然如果真的具有某种倾向的话,则倾向于将系统推向平衡态,推向无序和混乱而不是秩序和功用——果真如此吗?
简单的事实就是,哪怕是像细菌细胞一样最基本的生命系统,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远离平衡态的功能性系统,这系统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说和一个冰箱的运作方式类似,但是其复杂性却高了好几个数量级。冰箱充其量不过涉及数十个元件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而在一个细菌细胞中则存在成千上万个不同分子和分子聚合物之间的互动,有的分子本身就具有惊人的复杂性。这一切都发生在数千个同步进行的化学反应网络内。在冰箱的例子中,冰箱的功能显而易见是通过将热量从低温的内部泵到高温的外部,从而保证冰箱中的啤酒和其他东西处于低温的状态。但具有有序复杂性的细菌细胞又有什么功能呢?简单来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它的行为来判断它的功用,就像我们通过观察冰箱的运作从而发现其用处一样,通过研究细胞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功能或者说目的。那么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什么结果呢?每一个活细胞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工厂,正如任何一个人造的工厂一样,它需要与能量源和能源产生器相连接来保证其运行。一旦能量源被切断,工厂将立刻停止运行。这个迷你工厂通过利用能源产生器产生的能量,将原材料转化为许多功能性元件,这些元件将被组装起来,用于生产工厂的产品。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纳米级别细胞工厂都生产些什么呢?更多的细胞!每个细胞到头来都是一个为了生产更多细胞的高度组织化的工厂!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就曾富有诗意地描述过这个事实:“每个细胞的梦想都是变成两个细胞。”
关于生命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此,正如我们会觉得冷藏室、集能设备、电池、压缩机和制冷剂等部件能自发地组装成一台功能正常的电冰箱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即使所有的部件都已经齐备,一个自发形成的高度组织化、远离平衡态的微型化学工厂同样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个体不会自发形成,一些基本的物理学法则也反复说明着同样的道理。系统倾向于朝着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发展,而不是秩序和功用。也难怪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如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玻尔、薛定谔等都觉得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生物学和物理学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互相矛盾,难怪智能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 的鼓吹者们能到处兜售他们的观点。
的鼓吹者们能到处兜售他们的观点。
活细胞的存在本身所包含的悖论就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研究生命的出现这一问题并不像追溯某个家族的源流那样,它不是个人在历史兴趣下展开的隐秘活动。只有解释了生命的产生背后存在的悖论,我们才能理解生命是什么。也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为这被称作“生命”的化学系统的产生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本书的目的是重新审视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并证明我们能够勾勒出那控制着所有生命的出现、存在和本质的基本法则。有赖于当前化学界新领域的出现,即君特·冯·凯德罗夫斯基(Günter von Kiedrowski)提出的“系统化学”(Systems Chemistry) ,本书将描述我们如何连接起生物与化学之间的断层,而作为生物学基本范式的达尔文主义,不过是自然力量的广泛物理化学特征在生物学上的体现。我试图融合生物学与化学的野心主要基于一个看法:我认为自然中存在一种被长期忽略的稳定性,我将这种稳定性称为动态动力学稳定性(dynamic kinetic stability,DKS)。如果将这种形式的稳定性糅合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中,可以产生一个囊括了生物和前生物系统的广义进化论(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有趣的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自己早已意识到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生命法则。他在一封给乔治·沃利克(George Wallich)的信中写道:
,本书将描述我们如何连接起生物与化学之间的断层,而作为生物学基本范式的达尔文主义,不过是自然力量的广泛物理化学特征在生物学上的体现。我试图融合生物学与化学的野心主要基于一个看法:我认为自然中存在一种被长期忽略的稳定性,我将这种稳定性称为动态动力学稳定性(dynamic kinetic stability,DKS)。如果将这种形式的稳定性糅合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中,可以产生一个囊括了生物和前生物系统的广义进化论(general theory of evolution)。有趣的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自己早已意识到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生命法则。他在一封给乔治·沃利克(George Wallich)的信中写道:
我相信我曾经说过(但我找不到原文),根据连续性原理,在未来,生命的法则可能会被证明是某种普适规律的结果或者一部分。
这本书试图说明,查尔斯·达尔文的远见卓识是正确的,并且这种理论现在已经开始成形。我将论证,在物理与生物之间起到桥梁作用的科学——化学——能够回答这些有趣的问题,即便这答案还不够完备。对生命是什么的深刻理解,除了能回答我们是谁、是什么的问题之外,更将给我们带来对宇宙本质及其基本法则的洞见。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从许多人的反馈和交流中获益。我特别希望感谢让·昂格贝尔(Jan Engberts)、乔尔·哈普(Joel Harp)、斯伯伦·奥托(Sijbren Otto)和里奥·拉多姆(Leo Radom)为这本书的初稿提出的详细建议和批评。我还要感谢米切尔·格斯(Mitchell Guss)、杰拉尔德·乔伊斯(Gerald Joyce)、埃利奥·马蒂亚(Elio Mattia)、埃莉诺·奥尼尔(Elinor O’Neill)、戴维·奥尼尔(David O’Neill)和彼得·斯特拉热夫斯基(Peter Strazewski)为本书做出的总体评价,还有戈嫩·阿什克纳西(Gonen Ashkenasy)、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君特·冯·凯德罗夫斯基、肯·克拉亚夫德(Ken Kraaijeveld)、普里·洛佩斯—加西亚(Puri Lopez-Garcia)、梅厄·拉艾(Meir Lahav)、米凯尔·迈勒(Michael Meijler)、凯帕·鲁伊斯—米拉索(Kepa Ruiz-Mirazo)、罗伯特·帕斯卡尔(Robert Pascal)、厄尔什·绍特马里(Eörs Szathmáry)、伊曼纽尔·坦嫩鲍姆(Emmanuel Tannenbaum)和纳撒尼尔·瓦格纳(Nathaniel Wagner)所贡献的珍贵讨论,这些讨论结果对我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还有我的妻子奈拉(Nella),我们之间的讨论、她敏锐的眼光和观点都极大地影响了这本书。最后,我特别希望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拉塔·梅农(Latha Menon),她对科学深刻的理解和出色的编辑能力,保证了这本书不会被不必要的生物学术语所淹没,她为这本书的最终成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书中所有的讹误完全由我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