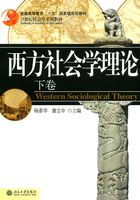
第四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结构理论
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内部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于个人的有机整体,是传统功能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观点。不过,在帕森斯以前,功能主义传统的社会学家们大都把社会结构当作一种完全独立和超越于个人行动之外的客观实在来加以研究,无视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此不同,帕森斯则企图将韦伯关于社会结构不过是个人社会行动之集合的思想与传统功能主义关于社会结构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特性之有机体的思想结合起来,以使传统功能主义的社会结构观更为完善。帕森斯首先将“行动”与“体系”相联结,提出了“行动体系”的概念,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AGIL四功能模式作为分析行动体系之结构的基本工具。按照这个模式,人类是生活在由许多“单位行动”联结而成的行动体系当中,行动体系则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系统,每一层次都具有四种基本的功能要求,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为了满足这四种基本的功能要求,行动体系就必须分化为四个相应的子系统,以分别执行四种系统功能;行动体系首先分化为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四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进一步分化为四个子系统(如社会系统又分化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社区四个子系统),如此一级级分化下去;行动体系各层次的四个功能子系统之间不仅是一种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控制等级关系。根据这种描述,社会系统既是一个由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特性的有机体系,同时又只不过是整个行动体系的一部分;它由人类的“单位行动”所构成,又与行动体系的其他部分(有机体、人格与文化系统)相互区别、相互联结,共同型塑了人类行动本身。帕森斯的“行动体系”概念,以及他用来分析行动体系的四功能分析模式,既表达了社会结构的行动性质,又表达了行动的结构—功能性质。不过,在帕森斯的著作中,他更为强调的实际上是行动的结构性质(强调行动受其结构制约的一面)和行动结构的功能特性(行动体系是一个功能协调的合意系统)。帕森斯著作的这一方面后来受到了来自微观社会学(互动论、交换论等)与冲突社会学两方面的攻击。微观社会学批评帕森斯过于强调了行动对结构的受动性,忽视了行动之间的冲突和行动体系的强制性。对帕森斯行动体系理论的这两个缺陷进行修正,成为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生长点。作为“功能主义”者,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多数沿袭了帕森斯关于行动体系的概念以及他的四功能分析模式;但作为“新”功能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罗西、亚历山大、芒奇、艾森斯塔德等则吸收了微观社会学与冲突社会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对帕森斯的行动结构理论及其分析模式作了一系列的修正和改进。
亚历山大区分了行动与行动的环境两个方面,提出AGIL四功能分析模式不能用于分析行动自身,而只能用来分析行动的环境。与帕森斯不同,他认为具体的行动是不能被分析性地割裂为不同的系统要素的。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等并非是作为行动本身的要素,而只是作为行动的环境因素进入行动过程当中的。因此这些系统也只是作为具体行动的一种外部环境来对行动产生影响的。作为具体行动的外部环境,它们为行动提供真实的行动目标、手段、社区支持、规则、意义框架和心理条件等。这些环境要素既是具体行动赖以展开的前提条件,同时又是具体行动的产物。行动者在它们提供的限制范围内展开行动,同时又不断地突破这种限制,创造新的行动环境。因此行动并非只是简单地受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这些环境因素的规制,行动与环境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构造的 。
。
罗西则对帕森斯AGIL四功能模式中蕴涵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进行了批评,提出要对四功能模式进行“辩证再解释”。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帕森斯的“文化决定论”。“因为,在我看来,行动的四个子系统或更精确地说是四功能范式的组成部分处于辩证地构成的互动之中”、“四个子系统通过它的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差异而相互建构。一方面,每个子系统都必须保持其分析特征从而使其在组织焦点上与其他子系统相区别,但同时任何子系统的存在又是以其他子系统的相互对立为条件的。就此而言,子系统又是相互建构的” 。例如,“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的相互渗透是指,除非参与一个社会系统,否则人格系统无法存在。……反过来,社会系统无不产生于社会成员的人格所由构成的行动系统诸部分的整合”
。例如,“社会系统和人格系统的相互渗透是指,除非参与一个社会系统,否则人格系统无法存在。……反过来,社会系统无不产生于社会成员的人格所由构成的行动系统诸部分的整合” ;同样,尽管只有参与文化系统之中,人格系统才能存在,但文化系统也只有当它可以内化于人格系统时才能存在。因此,行动体系的四功能部分之间不是一种机械的控制等级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相互建构关系。这种辩证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四功能部分之间(尤其是行动体系的集体组成部分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与个体组成部分有机体系统和人格系统两大部分之间)造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辩证张力。这种辩证张力的存在使得行动体系的结构既带有部分决定论的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行动者所改变。
;同样,尽管只有参与文化系统之中,人格系统才能存在,但文化系统也只有当它可以内化于人格系统时才能存在。因此,行动体系的四功能部分之间不是一种机械的控制等级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相互建构关系。这种辩证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四功能部分之间(尤其是行动体系的集体组成部分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与个体组成部分有机体系统和人格系统两大部分之间)造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辩证张力。这种辩证张力的存在使得行动体系的结构既带有部分决定论的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行动者所改变。
芒奇也通过将“符号的复杂性”与“行动的偶然性”两个因素引入AGIL,从而对AGIL模式作出了重大的推进,使得帕森斯的AGIL四功能模式与微观社会学对行动者主观意义及行动偶然性的强调能够结合起来。他提出行动总是发生于一个可由“符号的复杂性”与“行动的偶然性”这两个维度来加以刻画的空间之中。首先,人类行动是一种符号控制下的有意义的行动,指导人类行动的这些符号其数目与相互依赖性(也即其复杂性)在不同的行动过程中是各个不同、变化不定的。其次,人类行动是一种符号控制下的有意义的行动,这个特征本身就蕴涵了人类行动的偶然性。人类行动潜在的可能性空间是随控制它的符号系统的不同而不同的。越是开放的符号系统,其涵盖的可能性空间就越大,它控制之下的人类行动的偶然性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将这两个基本维度相交叉,可以将人类的全部行动空间划分为四个在“符号复杂性”与“行动偶然性”方面互不相同的行动领域。这四个行动领域与帕森斯的AGIL四功能领域正好是对应的。在执行系统适应功能的行动领域内,行动具备高度符号复杂性和高度偶然性;在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的行动领域内,行动具备高度的符号复杂性和低度的偶然性;在执行整合功能的行动领域内,行动同时具备低的符号复杂性和低的偶然性;在执行模式维持功能的行动领域内,行动则具备低的符号复杂性和高的偶然性 。由于“符号复杂性”与“行动偶然性”这两个行动维度的引入,帕森斯AGIL四功能分析模式的决定论色彩大大降低了,行动在结构中的自由度大为拓展,在功能主义范围内来对行动主体的能动性进行考察便具有了可能。
。由于“符号复杂性”与“行动偶然性”这两个行动维度的引入,帕森斯AGIL四功能分析模式的决定论色彩大大降低了,行动在结构中的自由度大为拓展,在功能主义范围内来对行动主体的能动性进行考察便具有了可能。
如果说上述几位学者主要是通过吸收微观社会学的一些有关思想来对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修正,那么艾森斯塔德则是通过吸收冲突社会学的一些有关思想对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重要的补充。艾森斯塔德对功能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冲突社会学中的利益群体、利益群体结构以及群体冲突的概念引入了功能主义理论。艾森斯塔德将社会系统的不同功能需求与具体社会群体的利益联结起来,指出社会系统的不同功能部分同时也是有着不同利益和目标的社会群体,它们在履行着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在追求着自身的利益,为控制更多的权力与资源而努力。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功能关系结构,而且也是一种利益关系结构;社会的结构—功能分化过程同时也是社会的阶级或阶层分化过程 。由于社会的各个群体在利益与目标上存在着差别,因此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合意系统,社会的结合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努力在这种带有一定程度强制性质的社会结合中占据更好的甚至主导的或统治的地位,是各个利益群体的行动目标之一。通过把功能关系结构的概念与利益关系结构的概念相联结,艾森斯塔德把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结构—功能关系的强调与冲突社会学对社会利益—强制关系的强调协调了起来,弥补了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忽视社会强制性质的缺陷。
。由于社会的各个群体在利益与目标上存在着差别,因此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合意系统,社会的结合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努力在这种带有一定程度强制性质的社会结合中占据更好的甚至主导的或统治的地位,是各个利益群体的行动目标之一。通过把功能关系结构的概念与利益关系结构的概念相联结,艾森斯塔德把结构功能主义对社会结构—功能关系的强调与冲突社会学对社会利益—强制关系的强调协调了起来,弥补了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忽视社会强制性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