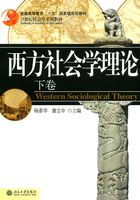
第三章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J.Habermas)的批判理论在近二十年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显学,其学说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罕有比拟的。但颇为悖论的是,哈氏的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跟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主导思潮相违背。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可以说是对现代人影响力最大的两股相辅相成的思潮。这些学术思潮跟20世纪下半期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甚至人类日常生活上的理念和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相互影响。特别是近年来流行的“文化多元论”,似乎更是把学术层面的理念和在社会、政治,以及日常生活层次等事项联结起来。当然,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论,跟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关系十分复杂,不能作简单的化约。然而,所有这些理论和情境都是在传递着一个信息,这再不是一个有绝对和普遍的准则去评估和指引人类行为的年代。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气候里提出来。哈氏的理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其中最受争议的地方是他企图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基础”(normative foundation)来描述、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的结构。
“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是哈贝马斯学说的中心概念,并且是哈氏用来支持其理论的普遍性的主要论旨。然而,恰恰是这个概念引来不同学派的强烈的批评。哈氏用以支持和证实其沟通理性的论据相当复杂,牵涉不同学科和层次上的分析。由纵贯的角度着眼,他跟随帕森斯早期的研究路向,试图从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来指出沟通理性或沟通行动论的可能性。其中对他这方面的理论影响特别深的,是韦伯的西方理性化发展理论,其次是涂尔干、米德以及帕森斯和马克思有关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在横贯的层面上,哈贝马斯引用了“日常语言学派”(ordinary language approach)的分析,建立他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理论,同时也跟随皮亚杰和柯尔柏格的结构发展心理学,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和证实西方理性化的进程,是具有一种进化色彩的发展方向。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可以说是他在这方面理论的最完备及最有系统的论述。本章主要是透过这本书介绍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由于哈氏的理论相当艰涩难懂,因此在下文里,在有必要时会引入他较早期的论点,并且加上本章作者的进一步演绎和解说
,可以说是他在这方面理论的最完备及最有系统的论述。本章主要是透过这本书介绍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由于哈氏的理论相当艰涩难懂,因此在下文里,在有必要时会引入他较早期的论点,并且加上本章作者的进一步演绎和解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