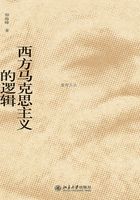
第一章 物化、总体性与社会存在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上,卢卡奇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奠基者,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构成了后来者的理论尺度 。在这本著作中,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以一种从主体—客体出发的总体性辩证方法,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晚年,他重新讨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力图从对《资本论》的理解中重新建构马克思的哲学框架。这部未竟之作,对于今天讨论马克思的哲学理念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鉴于卢卡奇的历史贡献,帕森斯说:“卢卡奇被公认为本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
。在这本著作中,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以一种从主体—客体出发的总体性辩证方法,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在晚年,他重新讨论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力图从对《资本论》的理解中重新建构马克思的哲学框架。这部未竟之作,对于今天讨论马克思的哲学理念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鉴于卢卡奇的历史贡献,帕森斯说:“卢卡奇被公认为本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哲学家之一。” 对卢卡奇思想的讨论,也是我们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入口。
对卢卡奇思想的讨论,也是我们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入口。
第一节 精神世界的分裂与对总体性的渴望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青年卢卡奇的代表著作。在写作这本著作之前,青年卢卡奇经历了从新康德主义到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想转变。在转向新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对精神世界的分裂的考察与对总体性的渴望构成了他的思想的重要主题。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在重新阅读马克思著作的过程中,卢卡奇实现了自身思想的理论提升与逻辑建构。鉴于卢卡奇思想发展的这一阶段在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本节就从青年卢卡奇的思想转变谈起。
1.青年卢卡奇思想的总体进程
1885年卢卡奇出生于布达佩斯,是银行家约瑟夫·卢卡奇(犹太人)的次子。当时匈牙利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国王住在维也纳。虽然处于上层阶层,但青年卢卡奇对流行于其中的民族主义和官场习惯都非常反感。在社会团体中,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也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挑战者。在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发展中,一些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的知识界杂志,如1908年创刊的《西方》对他影响很大,从这家杂志的名称可以看出,它反对匈牙利的民族沙文主义,赞成放眼西方。卢卡奇于1908—1917年期间经常为这家杂志撰稿,这些文稿后来形成为《心灵与形式》一书。另外,如《二十世纪》这一杂志对卢卡奇也很重要,他青年时期的许多文章都发表于此。
1902到1906年,根据父亲的意愿,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学,在此期间他非常喜欢戏剧。1906年开始在国外学习,并转向自己感兴趣的社会学和哲学。1906—1907年,他已经开始运用社会学思想分析戏剧并写成了《近代戏剧发展史》。当时德国社会学的两大巨匠之一的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柏林执教,1909—1910年卢卡奇参加齐美尔的讨论班。齐美尔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运用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来分析问题,提出了物化理论(reification),以批判当时发生于生产力与技术层面的物化,并认为只有艺术才能为走出这种物化提供可能性。1912—1915年,卢卡奇来到海森堡,在这里遇到德国社会学的另一巨匠韦伯(Max Weber)。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表明,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工具理性的发展为目的的,这使得价值理性衰落了,人陷入到了工具合理性的“铁笼”之中。虽然韦伯不是这种“铁笼”的辩护者,并认为应该以价值理性来批判这种工具合理性,但他也认为这种合理性实际上是无法逃避的。虽然深受韦伯影响,但这次使卢卡奇留在海森堡的原因却是对哲学的兴趣,因为海德堡是新康德主义的重镇之一,主导者是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Rickert)。他听了这些人的课,与另一位新康德主义者拉斯克(Emil Lask)结成好友,并在新康德主义思想影响下写成了《美学》。
从价值理论与艺术解放思想出发,卢卡奇关注的是世界的分裂与精神的危机,力图从个人的一种艺术感受中寻求解决危机的方式。随着狄尔泰对青年黑格尔的讨论进入到卢卡奇的理论视野,他认识到问题在于如何超越这种分裂,实现一种总体上的解放,从而进入到新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发展阶段。在狄尔泰看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摧毁了精神观看者的梦幻并揭示了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可以合法地使用先天的概念,从而解决了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黑格尔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将世界历史放到理性的自我理解之中,精神的外化在历史的过程中能够重新得到统一。但狄尔泰反对黑格尔的普遍主体理论,他认为“不存在一种普遍的主体,而只存在历史的个人。意义的理想性不可归入某个先验的主体,而是从生命的历史实在性产生的。” 通过这种转换,狄尔泰认为个体的生命体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卢卡奇,并于1916年写下了《小说理论》。正是在这篇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对物化世界的批判与对总体性的渴望。从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发展来看,《心灵与形式》是他受新康德主义思想影响时期的重要作品,《小说理论》则是他从新黑格尔主义出发建构自己理论的一次尝试。
通过这种转换,狄尔泰认为个体的生命体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卢卡奇,并于1916年写下了《小说理论》。正是在这篇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对物化世界的批判与对总体性的渴望。从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发展来看,《心灵与形式》是他受新康德主义思想影响时期的重要作品,《小说理论》则是他从新黑格尔主义出发建构自己理论的一次尝试。
2.精神世界的分裂与异化:《心灵与形式》
《心灵与形式》是1911年出版的著作,由10篇文学评论组成。在这篇文献中,卢卡奇提出了一种现代社会人的存在困境的悲观世界观:即在现代社会,人处于分裂的存在状态,人被上帝抛弃,也被人抛弃。这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观念。
在这篇文献中,卢卡奇区分了评论家与创作家。在他看来,创作家只关注生命的创造性表达,这种表达与事物的真理可以无关,而评论家必须表达有关事物的真理,要有对形式所包含的精神的感受。什么是形式呢?卢卡奇认为:对评论家来说,决定性的时刻即是感受和体验到获得一种形式的时刻;它是“外在和内在、灵魂和形式相统一的神秘时刻。”因而,情感和形式是密切相关的。评论家关注存在的生命,关心形式所体现的一种世界观、一种生命的观念,但他却是以一种嘲讽的方式来完成这一点,这是评论家与创作家在关注生命时的重要区别。卢卡奇把论说文等同于评论作品,评论家以嘲讽的方式来写论说文,这是因为评论家谈论生命的根本问题,但却带着这样一种口吻,仿佛他谈论的只是画像或书本。 比如绘画,有风景画或肖像画,对于创作家来说,我们不会去问他画的东西是否为真,但对于评论家来说,他总会问是否相像,这里就体现了评论家与创作家的区别,虽然评论家与创作家都关注生命,但他们关注的方式并不相同,前者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命,后者关注的是通过作品呈现出来的生命。在论说文关注生命的时候,永恒的形式构成了生命的最高法则。在这里能看出新康德主义形式先验的理念对卢卡奇的影响。
比如绘画,有风景画或肖像画,对于创作家来说,我们不会去问他画的东西是否为真,但对于评论家来说,他总会问是否相像,这里就体现了评论家与创作家的区别,虽然评论家与创作家都关注生命,但他们关注的方式并不相同,前者关注的是现实的生命,后者关注的是通过作品呈现出来的生命。在论说文关注生命的时候,永恒的形式构成了生命的最高法则。在这里能看出新康德主义形式先验的理念对卢卡奇的影响。
论说文是一种广义的文艺评论,也是一种艺术作品。在卢卡奇这里,艺术与科学是有区别的:“科学以其内容影响我们,而艺术则以其形式影响我们;科学提供给我们事实及其关联,而艺术给我们的则是心灵和命运。两条道路在这里发生了分野;这里不存在替代和过渡。……只有当某物将其所有的内容都消解在形式之中,并由此变成纯粹的艺术的时候,它才不再是多余的;这时,它过去的科学性便被人们完全遗忘,再也没有意义了。” 卢卡奇之所以强调论说文的形式一面,有其自己的理论意图。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二元论的社会,生活与活着,在哲学中就是概念与具体之间的对立,在表达上就是“表象”和“意义”的对立,“其中的一个原则是创造表象的,另一个原则是生成意义的;对于第一个原则来说,只有事物是存在的,对于另一个原则而言,只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概念和价值是存在的。”
卢卡奇之所以强调论说文的形式一面,有其自己的理论意图。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二元论的社会,生活与活着,在哲学中就是概念与具体之间的对立,在表达上就是“表象”和“意义”的对立,“其中的一个原则是创造表象的,另一个原则是生成意义的;对于第一个原则来说,只有事物是存在的,对于另一个原则而言,只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概念和价值是存在的。” 。对立的双方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但又都不是真正的现实,这种分离使意义被表象所遮蔽,只有超越于表象之上的光线才能穿透表象并使意义最终得以显现出来,这正是评论家的任务。在他看来,评论家所需要的是体验生活的形式,在这种体验中包含着活生生的心灵现实,但这种现实在直接生活的表象中是无从发现的,它只能在这种体验中被读出来,生活本身也是这样通过体验的图式而被赋予了意义,因此只有评论家才实现了表象与意义的统一。“批评家的命运时刻,是事物变为形式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形式之或远或近的所有感情和体验都接收了形式,被融化、压缩为形式。这是内部和外部、心灵和形式联合的神秘时刻。”
。对立的双方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但又都不是真正的现实,这种分离使意义被表象所遮蔽,只有超越于表象之上的光线才能穿透表象并使意义最终得以显现出来,这正是评论家的任务。在他看来,评论家所需要的是体验生活的形式,在这种体验中包含着活生生的心灵现实,但这种现实在直接生活的表象中是无从发现的,它只能在这种体验中被读出来,生活本身也是这样通过体验的图式而被赋予了意义,因此只有评论家才实现了表象与意义的统一。“批评家的命运时刻,是事物变为形式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形式之或远或近的所有感情和体验都接收了形式,被融化、压缩为形式。这是内部和外部、心灵和形式联合的神秘时刻。”
在对形式的追求中,卢卡奇所梦想的仍然是那个遥远的希腊。“希腊人感觉每一样可用的形式对他们都是一个现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事物而不是一种抽象。” 但这种感觉在今天已不再是真实的存在,论说文所体现的是追求这样一种感觉的努力。如果把真实的存在看做是一个真正的终点,那么论说文就是对这一终点目标的接近,在论说文的批评过程中,终点不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成了一个有待被征服的高峰,通过论说文,人们最后要达到的是对生命赋形的永恒价值。“因为在有待于被发现的价值系统里,我们所说的渴望因要被满足而被取消;但是,这个渴望胜过了等待满足的某些东西,它是拥有一个价值和它自己存在的心灵事实:对待生活总体的一种原发性的根深蒂固的态度,一个最后的不能再缩小的体验可能性范畴。因此,它不但要被满足(因此被取消),而且要被赋形,这不仅能够真正释放其最深层的本质之物,而且能将现在不可分割的实体放置到永恒的价值之中。这就是论说文所做的事。”
但这种感觉在今天已不再是真实的存在,论说文所体现的是追求这样一种感觉的努力。如果把真实的存在看做是一个真正的终点,那么论说文就是对这一终点目标的接近,在论说文的批评过程中,终点不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成了一个有待被征服的高峰,通过论说文,人们最后要达到的是对生命赋形的永恒价值。“因为在有待于被发现的价值系统里,我们所说的渴望因要被满足而被取消;但是,这个渴望胜过了等待满足的某些东西,它是拥有一个价值和它自己存在的心灵事实:对待生活总体的一种原发性的根深蒂固的态度,一个最后的不能再缩小的体验可能性范畴。因此,它不但要被满足(因此被取消),而且要被赋形,这不仅能够真正释放其最深层的本质之物,而且能将现在不可分割的实体放置到永恒的价值之中。这就是论说文所做的事。” 论说文虽然不是一件艺术品,但它与艺术一样追求形式,追求对生活的赋形。他认为这是超越当下分裂的重要途径。这种超越分裂的思想在《小说理论》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论说文虽然不是一件艺术品,但它与艺术一样追求形式,追求对生活的赋形。他认为这是超越当下分裂的重要途径。这种超越分裂的思想在《小说理论》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3.《小说理论》中的总体性理念
《小说理论》体现了卢卡奇从康德走向黑格尔的理论转换。这本书的写作源自于对一战中狂热的战争情绪的担忧和绝望。卢卡奇认为不管是俄国战败还是德国战败,他都能接受,但问题在于“谁将把我们从西方文明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如果最终的胜利属于当时的德国,对我而言,这不啻于噩梦般的可怕前景。)” 在这本书中,他从永恒形式走向了美学范畴的历史化理解,正如黑格尔把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看做是精神的不同形式表现一样,卢卡奇也以这样的方式来评论作品。相对于《心灵与形式》中所强调的形式的永恒价值的特性,《小说理论》中的卢卡奇强调要使形式服从于一种历史哲学的辩证法,形式问题之所以被突现出来,是因为存在于赋形主体的先验结构与存在于外部世界被创造的形式之间的平行关系被破坏了。因此,生活意义的内在性的丧失,对应于与这种意义相应的外部世界的灾难性丧失,在这时,我们不能只是希望通过回归内在性而渴望获得统一,因为内在性的本真性恰恰消失了。在这样的分析思路中不难看出黑格尔的影子。正是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总体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在他关于史诗的评论中可见一斑。
在这本书中,他从永恒形式走向了美学范畴的历史化理解,正如黑格尔把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看做是精神的不同形式表现一样,卢卡奇也以这样的方式来评论作品。相对于《心灵与形式》中所强调的形式的永恒价值的特性,《小说理论》中的卢卡奇强调要使形式服从于一种历史哲学的辩证法,形式问题之所以被突现出来,是因为存在于赋形主体的先验结构与存在于外部世界被创造的形式之间的平行关系被破坏了。因此,生活意义的内在性的丧失,对应于与这种意义相应的外部世界的灾难性丧失,在这时,我们不能只是希望通过回归内在性而渴望获得统一,因为内在性的本真性恰恰消失了。在这样的分析思路中不难看出黑格尔的影子。正是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总体性”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在他关于史诗的评论中可见一斑。
卢卡奇把史诗看做是“总体性”的体现,史诗中的主体都是经验的主体,但这并不是现代艺术中所谓的赋形的主体。在史诗那里,主体把其内在先验性和内在性不可分割的统一在一起,这种内在的先验性正是对世界总体性内容的真实展示。
这本书的开头一段文字是非常优美的:“在那幸福的年代里,星空就是人们能走的和即将要走的路的地图,在星光朗照之下,道路清晰可辨。那时的一切既可令人感到新奇,又让人觉得熟悉;既险象环生,却又为他们所掌握。世界虽然广阔无垠,但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因为心灵深处燃烧的火焰和头上璀璨之星辰拥有共同的本性。尽管世界与自我、星光和火焰显然彼此不太相同,但却不会永远地形同路人,因为火焰是所有星光的心灵,而所有的火焰也都披上了星光的霓裳。所以,心灵的每个行动都是富有深意的,在这二元性中也都是完满的:对感觉中的意义和对各种感觉而言,它都是完满的;完满是因为心灵行动之时是蛰居不出的;完满是因为心灵的行动在脱离心灵之后,自成一家,并以自己的中心为圆心画了一个封闭的圈。‘哲学犯了思乡病,’诺瓦利斯说,‘不论在哪里它都迫切地想回家。’所以,哲学——无论是生活形式的哲学,还是决定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哲学——总是要表征为‘内’与‘外’的断裂、自我与世界的本质区别,以及心灵与行为的失调。所以说,幸福的年代是没有哲学的,要不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年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共同享有每一种哲学都向往的乌托邦宗旨。” 在这样的时代,心灵没有内外之分,既不会迷失自我,也不会想要去寻找自我,这样的年代就是史诗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充盈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二分的裂变,在希腊人较小的形而上的生活圈子里,人与世界构成了一个总体;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大了,但同时也消除了人们赖以生活的基础——总体性。什么是总体性呢?卢卡奇认为:第一,总体性意味着存在于它自身之内的东西是完整的;第二,总体性是每个个别现象的根本实在;第三,总体性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一切都发生于它之中,没有任何东西被它排斥在外;第四,总体性内部的一切都趋向完美成熟,每一存在都按其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责任,美是可见世界的意义。这样的世界才是总体性的世界,希腊的世界,即荷马史诗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总体性在这里具有乌托邦的意味。
在这样的时代,心灵没有内外之分,既不会迷失自我,也不会想要去寻找自我,这样的年代就是史诗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充盈的关系,而不是一种二分的裂变,在希腊人较小的形而上的生活圈子里,人与世界构成了一个总体;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大了,但同时也消除了人们赖以生活的基础——总体性。什么是总体性呢?卢卡奇认为:第一,总体性意味着存在于它自身之内的东西是完整的;第二,总体性是每个个别现象的根本实在;第三,总体性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一切都发生于它之中,没有任何东西被它排斥在外;第四,总体性内部的一切都趋向完美成熟,每一存在都按其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责任,美是可见世界的意义。这样的世界才是总体性的世界,希腊的世界,即荷马史诗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总体性在这里具有乌托邦的意味。
当史诗被悲剧替代时,这个完整的世界就已经分裂,生命的本质就已经在内损。史诗回答的问题是“生活如何变为本质?”,而悲剧回答的问题是“本质如何变得鲜活?”。在悲剧这里,生活已经离开了本质,悲剧的时刻就是发现生活经验的无意义的时刻,但这一发现的主人公不再是荷马史诗中的平常人,而是被神化了的英雄,在常人被这种无意义的生活所吞没的地方,只有英雄才能发现事情的真相。但同样是悲剧,卢卡奇认为古希腊的悲剧与近代的悲剧还是存在着区别。在古希腊时代,生活意义的沉沦把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转移到了另一个领域中去了,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和他的本质保持一种相近性,所有的人都在相同的本质高度内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的悲剧具有向史诗靠拢的特性。而在近代悲剧中,本质的重新获得有赖于人与生活的总体对抗并在对抗中取得胜利,这时人也就成为一个走在钢丝上的孤独者,这是一种对生活的失望。这种失望也表明了总体性的消失。近代的这种悲剧构成了从史诗向小说的过渡。
总体性世界的消失,产生的是碎片化的世界和孤独的个人,本真性不再存在于生活之中,定在的“实然”与存在的“应然”之间分裂了,“应然”被指向一种超验的存在,不管这个超验的存在是一种偶像化的实体,还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它都指向经验自我的外部。卢卡奇认为这些是在荷马之后的现代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他称小说的这种特性为“外延的总体性”。卢卡奇认为,史诗有两种形式,一是荷马的史诗,另一种就是与伟大的史诗处于同一家族来揭示外延总体性的小说。在小说产生时,生活的内在性已经成为问题,生活的外延总体性也不再直接存在,但这个时代还拥有一种总体性的信念。当总体性成为个体的先行决定的先验性结构时,总体性令人望眼欲穿,小说的主人公就成为探索这种总体性的主人。所以卢卡奇说:“史诗为从自身出发的封闭的生活总体性赋形,小说则以赋形的方式揭示并构建了隐藏着的生活总体性。客体的给定结构——对于诸如此类的事物的探索不过是从主体的角度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全部客观生活也好,它与主体的关系也罢,都不是天然和谐的——道出了赋形的信念:历史情况所负载的一切分歧和破裂都被放置到赋形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也不应用写作手段伪饰起来。因此,小说中决定形式的基本信念被客体化为小说主人公们的心理:他们是探索者。” 小说的要素是抽象的,作者将自己的愿望看做是唯一真实存在的思乡之情,这种抽象又体现在以事实的现存和承受力量为基础的社会构成物的特定存在上,通过赋形,小说想追求一种总体性,但这种总体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存在的总体,而是那个总体的一个主观方面。同时,小说的赋形过程具有双重危险:或者是将世界的脆弱性一面彰显出来,这时形式所追求的意义的内在性也就变得很无望;或者对总体性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世界的脆弱性被遮蔽了,形式中不安全的和谐也被取消了,小说世界封闭了自己,这就是一种主观的总体性的表现。小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家”,但实际上却掩饰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真实存在状态。“卢卡奇说,史诗时代尚没有任何精神世界的概念,或者任何心灵的自身探索的概念,这个事实便是它的特点。它还是这样一个时代,神对于人是熟悉和亲密的,同样又是难以理解的,正如父亲对于婴孩一样。现代人生活在大大拓展了的界域的同时,也在自我和世界之间投下了一道鸿沟,这在史诗时代是不存在的。我们已丧失了希腊人生活作为总体性的意义:无所不包的总体性,再也说不出在它外面还有任何更高的实在。总而言之,现代人不像荷马时代的人,他们对天地万物是陌生的;而表达这种‘超自然的无家可归’的文学形式就是小说。”
小说的要素是抽象的,作者将自己的愿望看做是唯一真实存在的思乡之情,这种抽象又体现在以事实的现存和承受力量为基础的社会构成物的特定存在上,通过赋形,小说想追求一种总体性,但这种总体不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存在的总体,而是那个总体的一个主观方面。同时,小说的赋形过程具有双重危险:或者是将世界的脆弱性一面彰显出来,这时形式所追求的意义的内在性也就变得很无望;或者对总体性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世界的脆弱性被遮蔽了,形式中不安全的和谐也被取消了,小说世界封闭了自己,这就是一种主观的总体性的表现。小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家”,但实际上却掩饰了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真实存在状态。“卢卡奇说,史诗时代尚没有任何精神世界的概念,或者任何心灵的自身探索的概念,这个事实便是它的特点。它还是这样一个时代,神对于人是熟悉和亲密的,同样又是难以理解的,正如父亲对于婴孩一样。现代人生活在大大拓展了的界域的同时,也在自我和世界之间投下了一道鸿沟,这在史诗时代是不存在的。我们已丧失了希腊人生活作为总体性的意义:无所不包的总体性,再也说不出在它外面还有任何更高的实在。总而言之,现代人不像荷马时代的人,他们对天地万物是陌生的;而表达这种‘超自然的无家可归’的文学形式就是小说。”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史诗的虚假替代品。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史诗的虚假替代品。
卢卡奇将小说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抽象理想主义小说,这以《唐·吉诃德》为代表。在卢卡奇看来,在荷马史诗中,人与世界之间具有一种距离感,但这种距离感并不意味着人的无能,人在神的指引下虽然谦卑,但最终还是能够取得成功。在现代心灵中,这种距离感没有了,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对象。这时,人们一方面能真正地触及外部对象,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又必然是主观的,并在外部对象中实现自己。在内在性体验缺失的时候,心灵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行动,并从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寻找确证。这种行动指向外部,处于这种生活中的人必然处于一连串的不间断的自我选择的冒险中。他无法回归内在的体验,只能通过冒险发现那个生活的世界,即一个貌似的世界,并将之看做是一个本真的世界,就像唐·吉诃德所做的一样。卢卡奇认为,塞万提斯写出的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在这个时代,人已变得非常孤独,只有在漂泊不居的心灵内部才能找到意义和实体。同时,对中世纪世界观念的批判,使现实世界从彼岸的“真实存在”中挣脱出来,其内在的无意义也随之暴露出来。过去通过乌托邦而联系着的有力量的存在,如今被降格为单纯的存在。这种存在“变得空前巨大,正引发一场针对那正在上升尚不能把握的、无力自我暴露和向世界渗透的力量之雷霆万钧、乍看却似乎漫无目的的斗争。……塞万提斯,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率真而忠诚的爱国者,创造性地揭示了精灵性难题的这个最深刻的本质:当通往先验家园的路不再畅通的时候,最纯粹的英雄主义必然会变得荒诞不经,最坚定的信念也必然会变得疯狂:现实不必再与最真的或最英雄主义的主观明证相符。” 这就是反讽得以产生的历史基础,这种讽刺性的结果使主人公受到一种异己历史的掌握,越是这时,就越需要冒险,通过纯粹的行动使异化的心灵暂时地宁静下来。但也可以是另一种方式,即主人公总是在冒险中获得成功,但每次成功后取得的东西在主人公看来恰恰是没有意义的,总是弃之如敝屣。
这就是反讽得以产生的历史基础,这种讽刺性的结果使主人公受到一种异己历史的掌握,越是这时,就越需要冒险,通过纯粹的行动使异化的心灵暂时地宁静下来。但也可以是另一种方式,即主人公总是在冒险中获得成功,但每次成功后取得的东西在主人公看来恰恰是没有意义的,总是弃之如敝屣。
第二种类型是幻灭的浪漫主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这一类型的小说。理想主义越是向外扩张,越是会产生一种幻灭感。“当一个过分的、面向外部世界的、无法阻挡的活动成为抽象理想主义的心理结构的标识时,就留下了一个更为消极的趋势;这是一个宁可逃避外在的冲突和斗争而不愿接受它们的趋势;一个只愿意在心灵内部解决所有跟心灵相关的问题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外在的物质生活过程和主人公的活动过程不再重要,因为主人公在内心中形成了对现实的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判断,当主人公无法在外部世界中达到自己的主体想象时,这种超越的力量就会回转向心灵自身,从而放弃面对外部世界的斗争而满足于绝望的自卫,这时,个人的内在重要性就达到了历史性的制高点。与上述那种抽象的理想主义不同,这种内在性不再依赖于外在的先验世界,而是将价值承载于自身,存在的价值也似乎只有在主体的体验以及对个体心灵的意义中,才能获得其合法性的基础。这是在外在的主体性失败之后产生的浪漫主义,而且这种失败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在这种失败中,“理念和现实之间最大的差异是时间:作为持续存在的时间的流程。主体性之最深刻、最感耻辱的无能,并不是存在于它与无理念的形象及其人类代表的斗争之中,而是存在于它不能抵挡滞重但持续的时间的流程,存在于它必须从艰难赢得的高峰缓慢而无可遏制地下滑;存在于时间——这不可理喻的、在无形中运动不止的实体——逐渐地夺走了主体所拥有的一切,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将异质的内容强加于它。”
在这种情况下,外在的物质生活过程和主人公的活动过程不再重要,因为主人公在内心中形成了对现实的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判断,当主人公无法在外部世界中达到自己的主体想象时,这种超越的力量就会回转向心灵自身,从而放弃面对外部世界的斗争而满足于绝望的自卫,这时,个人的内在重要性就达到了历史性的制高点。与上述那种抽象的理想主义不同,这种内在性不再依赖于外在的先验世界,而是将价值承载于自身,存在的价值也似乎只有在主体的体验以及对个体心灵的意义中,才能获得其合法性的基础。这是在外在的主体性失败之后产生的浪漫主义,而且这种失败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在这种失败中,“理念和现实之间最大的差异是时间:作为持续存在的时间的流程。主体性之最深刻、最感耻辱的无能,并不是存在于它与无理念的形象及其人类代表的斗争之中,而是存在于它不能抵挡滞重但持续的时间的流程,存在于它必须从艰难赢得的高峰缓慢而无可遏制地下滑;存在于时间——这不可理喻的、在无形中运动不止的实体——逐渐地夺走了主体所拥有的一切,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将异质的内容强加于它。” 这是从外在的冒险回归内心的价值追求,但人与世界的分离是持续存在的。在他看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描述的正是这一过程。
这是从外在的冒险回归内心的价值追求,但人与世界的分离是持续存在的。在他看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描述的正是这一过程。
第三种类型是对上述两种类型的综合,其主题是成问题的个人在经验理想的引导下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和解,这是一种成长教育类的小说,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就是这一类型。主人公不得已接受了社会的生活形式,把自己封闭起来,让只能在心灵深处实现自己的东西保存在心灵深处,从而与这个社会达成了和解。在这类小说中,主人公不再有前两类小说主人公所具有孤独感,主人公的归宿是对世界的顺从,而不是对世界的抗议。把心灵不能在世界上实现的东西,归之于心灵本身的虚弱。通过这样一种和解,主人公获得了一种宁静感。这当然还不是真正的和解,而是一种压抑之下的和解,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后的升华,以实现心灵与外部环境的统一。
第四种类型就是以托尔斯泰为主要代表的超越性的小说。在这种小说中,作者创造出一个超越于当下生活的乌托邦式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了日常的世俗生活,心灵的乌托邦指向了一开始就无法实现的目标。托尔斯泰试图通过爱情与婚姻来调解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种调解最终以失败而结束。但就在这种失败中,总存在着灵光闪现的“伟大的时刻”,即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死亡时刻。“伟大时刻在一刹那间照亮了一个本质生活,照亮了一个富含意义的过程……” 安娜正是在死亡的那一刻,从世俗生活中超越出来并获得了和解。这是另一种总体性的渴望。卢卡奇称这种小说最接近于史诗,但同时也表明,这种小说只是史诗的一个要素,因为史诗是无法重新恢复的。
安娜正是在死亡的那一刻,从世俗生活中超越出来并获得了和解。这是另一种总体性的渴望。卢卡奇称这种小说最接近于史诗,但同时也表明,这种小说只是史诗的一个要素,因为史诗是无法重新恢复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人的本真性在生活世界中已经失落,现代写作游走于一地鸡毛式的文字游戏之中,“本真性就飘荡在它的上方,即使我们看见了这种本真性,悲剧人物之间纯粹心灵的相互认同也不能达及”,当一种形而上的目的被界定为生活的追求之后,意义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之根。“在目的没有直接被给定之处,那心灵只是在道成肉身的过程中于人群中遭遇到的作为自己行动的看台和基础的结构,它在超人的、应有的必然性中失去了自己的明显根基”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隔离了,现代史诗中的个人与小说中的主人翁,都与外部世界相隔膜,对总体性的渴望也意味着对生命本真性的渴求。正是在这一主题上,有人认为卢卡奇影响了海德格尔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隔离了,现代史诗中的个人与小说中的主人翁,都与外部世界相隔膜,对总体性的渴望也意味着对生命本真性的渴求。正是在这一主题上,有人认为卢卡奇影响了海德格尔 。
。
综合《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我们看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两个重要主题——物化与总体性——已经出现,前者是对世界的批判分析,后者是对超越物化的可能性道路的探索。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入,关于物化的历史批判以及超越这种物化情境的无产阶级总体性意识的建构,成为卢卡奇的思考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