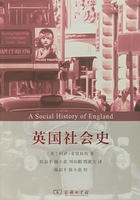
第一章 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古迹是磨损了的历史,或者是从时间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一些历史残迹。
——弗朗西斯·培根:《学问的进步》,1605年
对古文物感兴趣是一种令人着迷的特质。这种兴趣是不受地区和时代限制的。它可以通过历史联系而加强或专注于任何特殊对象而呈地方化;不过,要对它进行最充分的阐述……那是无边无际的。
——威廉·卡德沃思:《布雷福德的古文物收藏家》,1879年
史前史研究的是基本事物,它让一个孩子去思考什么是生命的基本需要,它展示出常见事物的古代起源。
——蒂娜·波特韦·多布森:《学校的史前史教学》,1928年
史前史的传统观点如今在每一点上都是矛盾的。
——科林·伦弗鲁:《文明之前》,1973年
英国是个小国,它的面积仅相当于美国的六十分之一,然而它却是旧世界的中心。当美洲殖民地人民在1776年宣布独立的时候,他们为他们崭新的大陆感到骄傲。与此相反,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正如对中国人而言一样,古老是一种资产,而不是负债;远古的时代可能是最美妙的时代。
英国乡间景观千姿百态,犹如英国社会历史层次的丰富多彩。英国的景观固然反映出这个岛国地质结构的复杂和气候的多样性,但也反映出许多别的东西。某些在20世纪显得十分蛮荒的地带,像多塞特郡那满目凄凉、石楠丛生的荒野,在英国历史上却是很早就被开发的地区。“英国绿色的宜人的土地”,正如18世纪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所称赞的那样,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它遍布各地如同黑暗的魔鬼磨坊的产物。英国被海洋包围着,所以英国的每个地方,不管它多么遥远荒僻,离海洋却十分接近,这一点对英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永恒的意义,就像高山或沙漠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意义一样,但是英国的海岸也发生了变化。不管事件的发生是使人麻木还是震惊,大自然所造化的山陵或是峡谷、湖泊或是沼泽,灌木或是森林总是使英国人感到宽慰或鼓舞,那种害怕大自然受到威胁的担忧可能仍然是很强的,因为“这是生养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土地。”对土地的忠诚,也都跟醉心于当地的景色有关,而大自然和文化(这个词源于土地)两者,在英国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通过帝国的建立而产生的不列颠的成就和问题,其范围要比英格兰本身的成就和问题要广,而且它们是与其他发展中的社会和文化的成就和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正是这个事实激励着许多外国探索者远涉重洋来访问英国,否则他们准会待在家中或附近的地方。对于他们——对英国人自己也一样——仅有探索没有解释是不够的。即便无简单答案可循,当代探索者至少会提出问题。最显而易见的两个问题是:“英国人为什么能完成他们所完成的一切?”“英国人为什么以及如何变成他们今天这副模样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往往要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一位法国(而不是英国)社会史学家、伟大的马克·布洛赫曾经写道:“完全以其前一个时代为模式而形成的社会,它的社会结构将必然是可以任意改变的。”特里维廉的《英国社会史》回溯到“乔叟的英国”,因为只是在这个时期“英国作为有特色的民族才开始出现,而英语,其本身就反映出许多社会变化的历史,也正在开始成为它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是,有许多理由使我们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远古时期的历史所集中研究的是人与自然,骨头与岩石,海岛与大陆,地理与地质。它的研究对象——用一本1928年出版的史前史教师手册的话说——都是“基本的事物”。在这本手册中,强调的是它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而不怎么强调可资利用的证据的局限性;对于为什么儿童应当学习史前史,它提出了完全不同但十分吸引人的理由。因为儿童本身处于“原始状态”,“原始事物”对他们就会具有吸引力。
到1928年前后,时间尺度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那时候开始,除了出现用以测定年代的新体系之外,还发现了新的遗物,加之对各种可用证物进行评估的新方法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这使得原来的结论迅速过时了。通过20世纪后期的时空观(这种时空观与以前若干世纪的大不一样,它是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现在我们向后推进并接触到我们最遥远的祖先了。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跨越时代进行探索时可以忽视过去的历史探索者所走过的历程,因为社会历史学家对社会史的了解,有许多不仅来自新近的解说,而且还来自那些已经陈旧过时、为人所抛弃的历史解释。这也不意味着当我们自己在历史中漫游,寻求“人的理性的历史”的时候,所有的惊奇都会消逝。事实上,我们很快意识到,对往昔历史的追踪要比到一个陌生的大陆去游历更让人感到神妙莫测。有许多东西我们还无法解释,例如,巨石阵注1虽然最近经过重新考察,重新确定了年代,但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它让20世纪晚期的“旅行者”和18世纪的考古学家同样地着迷。
18世纪和19世纪的探索者是第一批去延长自然与人类历史时间跨度的人,他们还试图更系统地整理它。他们对前所未有的物质进步颇感自豪,经过激烈的辩论,他们愿意放弃陈旧的思想方法。他们惊异地发现煤块,对他们来说煤是财富和权力的源泉,是从石炭纪的森林变来的,那些森林在数百万年以前在这个岛上曾经非常繁茂。事实上,正是特里维廉家族的一位先人在诺森伯里亚沿海一带的煤田里发现了深深地埋在那里的20棵笔直的树木。因为修建铁路和挖掘排水隧道而进行的施工,导致了其他重要发现。如同20世纪后期在修建公路时的情况一样。
怀着一种惊恐交加的心情,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还注意到,久已绝迹的动物,诸如高大的爬行动物、巨大的哺乳动物等等(它们的模型曾在锡德纳姆的水晶宫花园和1881年开馆的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了出来),曾经在这个岛上游荡。他们当中一些人还花了大量时间收集燧石并把它们加以分类,但往往难以分清哪些是自然形成的,哪些是人类的工具。他们那时候当然不懂花粉或骨骼分析或放射性碳素断代法等科学方法,但是当尚不存在这些手段的时候,根据遗留下来的文物,他们还是井井有条地把史前时期划分成若干阶段。对考古学来说这是一个外行人也热衷考古的时代,然而,毕竟是出来看热闹的多,研究价目表的买主多,而真正从事野外挖掘的人少。
地质分期为人类历史的分期提供了指导。不列颠岛是地质学家的自然博物馆,就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和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们一样,必须把整个不列颠岛而不仅仅是英格兰作为他们的研究单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地质学家发现了代表地球发展历史各个重要时期的石样,并为它们取了带有不列颠乡土气息的名字。因此,遂有寒武纪的叫法,名字来源于威尔士的坎布里亚,这个年代延续了大约1亿年;另外一个较短较早的年代称之为泥盆纪,因为那是羊齿植物和鱼类的时代,延续了大约6000万年。还有奥陶纪和志留纪,这些不太通俗的称谓来自古代不列颠部落的名字。
从以上这种命名中,我们不但可以知道地球形成本身的历史,同样可以,甚至更多地了解到了19世纪的社会和思想的历史。在这个神秘的故事中,有两点充满了矛盾,在当时似乎也颇为重要。不列颠岛的形成是由于宇宙间的剧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天翻地覆的环境变化,而与此同时人类历史却比较平静,而且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正是那些使地质学和生物学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却颇以英国历史中鲜有革命而自豪,他们想不到某些20世纪晚期的社会史学家却认为,革命的极少发生对英国有害。
第二点也包含着某种似是而非的悖论。对维多利亚时代人来说,不列颠的性格似乎是由于其岛国的状态决定的,然而现在已经揭示了当人类历史开始的时候,不列颠尚不是个游离于大陆之外的孤岛,而是大陆的一部分。在十分久远的年代里,成群结队的猎人为了追逐猎物跨过了当时尚未沉入水中的大陆架地区来到了如今被称为英格兰的地方。事实上,英格兰与大陆的分离还不到9000年,并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看来奇怪的是,曾经一度存在于英格兰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天然桥梁,和人类交流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的繁忙的19世纪时期不列颠与大陆之间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比较起来,竟显得更为渺茫难寻。
因而,在19世纪,其实对于今天也一样,要想毫无阻碍地把地球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联结起来,是不容易的。虽然,如同一位19世纪作家所说那样,“原始人类的唯一值得信赖的编年史是记载在大自然这本大书里面”,这本大书到头来却被证明是既不容易让人读懂又并非完全可靠。1912年在苏塞克斯“发现”的所谓皮尔丹人头盖骨,曾经被认为是英国人类早期发展的独一无二的证据,结果证明是件伪造的东西。与此相类似的,某些过去生活方式的异想天开的实物再现,像1888年在萨默塞特“发现”的格拉斯顿伯里湖村,显然包含着滑稽的成分。只有通过最近研究中的惊人进步,某些进步体现在实验手段上,才能对大自然这部大书重新加以解释。量化分析已经变得十分精细:对骨骼化石的研究不仅可以追根溯源而且可以揭示出各种疾病;在格拉斯顿伯里附近的萨默塞特岩层的探索者,现在从泥炭中收集的不仅是燧石还有古代花粉。人们正试图解释变化的顺序。同时还有新的发现,例如1992年在瑞士的一个冰川里发现的埋在冰里面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
在科学的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前,对早期不列颠的理解的关键似乎是对生活在世界上其他部分的民族有更充分的了解。奥斯伯特·盖伊·斯坦霍普·克劳福德是将空中摄影新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的先驱,也是创刊于1927年的《古物》杂志的创办人。他曾经写道:“考古学不过是人类学的过去式”。人类学的许多内容都是进化论的,有其19世纪的渊源。据称,从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可以追溯出人类的共同进化顺序,开始时是狩猎者,然后逐渐进化到食物采集者、农民、金属制造工人和“祭司”:结果,所涉及的不仅是物质文化,还有群体“心理”的问题。在1928年的《手册》成文时,各学校曾使用了一套很著名的关于史前史的丛书,其中皮克和弗勒介绍了这套丛书所包括的一系列“类型”,这些类型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但可以通过“时间走廊”加以辨别。第一卷叫作《类人猿与人》,出版于1927年;第二卷叫做《狩猎者与艺术家》(在史前时期的洞穴中有些极为有趣的很古老的动物画,尽管在英格兰很少见到);第三卷是《农民与陶匠》(对考古学家来说,有关陶器的证据极为重要,那些盆盆罐罐往往比人还要紧);第四卷是最后一卷,叫做《祭司与国王》(该书认为,宗教与领导阶层的出现是出于社会结构的需求,前者是圣灵的宝剑,后者是真正的武器,两者都是可以经受考验的)。
当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断延伸时间跨度的同时,却如同铁路和远洋轮船一样在缩小空间距离:他们相信人类在基本的方面是一样的,而最早的英国社会史,现在只是被看作一个具体的例子而已,因此,通过归纳和演绎、推理,至少可以部分地勾画出来。例如,当中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女性形象、男性生殖器的遗迹在诺福克郡的格拉姆斯燧石矿井中发现以后,人们就认为它们可能是,实际上也确实是,与一种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有关,那就是对大地女神的崇拜。
然而,19世纪对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的命名,开始是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继而是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金属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依据的主要是人们所使用的物质材料和方式而不是他们的价值。史前史这个术语在英国首先于1851年,即万国工业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内(在迁往锡德纳姆之前)的水晶宫举办的那一年使用,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既然可以把各国在19世纪的产品集中起来来证明物质上的进步,难道就不可以把人类过去各个不同阶段的产品收集起来加以陈列并分期吗?到1851年的时候,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分期在英国就已经被接受,尽管当时有人批评说不能拿“对待物理科学的办法来对待历史,把它的研究对象按属种类加以安排”,然而这种分期已成难更改。
最终,经过几十年的发掘、收集和研究,在分类上进行了大量的完善和改进,而且越来越强调这样一点,即认为若把一个阶段跟另一个阶段截然分开,那是危险的。然而,已经形成的框架仍然留传下来。除此之外,正像地质阶段的命名反映出不列颠的影响,在地质样品收集的命名上则反映了欧洲大陆的影响。例如,“奥瑞纳克期”就得名于法国的奥瑞纳克山洞及其奇妙的原始艺术;因而在英国德比郡的克里斯威尔峭壁(那里的一个山洞在很久以后才被人们神奇地称为罗宾汉山洞,另一座则被称为格兰第大妈注2的客厅)发现的遗迹,就被纳入“奥瑞纳克期”。这种追求事物之间的关联与一致性的做法,简直是“不屈不挠”的。
为了说明在冰期消融以后英国文化与欧洲的亲密关系,许多考古学家求助于所谓“入侵说”。按照这种说法,社会变迁的动力要么来自人群的移动(迁徙说),要么来自艺术和技术的转移(文化接触说),再从不列颠是一个岛屿的情况来看,前一种说法占了上风。这个过程开始于所有早期的环境变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即农业的出现,它可追溯到近东地区这个起源中心,在那里人工种植的小麦和大麦,伴随着驯化动物向西向北扩展开来。正如戈登·柴尔德所说:欧洲的野蛮是被“东方文明”所“熏陶”的;虽然不列颠处于这种开化过程的边缘地区,但由于它拥有出海口和半岛,这个边缘地带对于外界的人的进入是有吸引力的。柴尔德曾经做了许多工作使史前“文化”概念深入人心,他强调在整个史前史时期的舞台上起作用的不是个别人,而是群体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各群体的“分化、迁徙和相互作用”都充满着有趣的情节。在这方面,他写作的笔调很像是一位社会史学家,而且他写的《不列颠群岛的史前社会》比特里维廉的《英国社会史》还早一年出版。在其晚年,柴尔德还认为史前史学家企图从考古学遗迹中提炼出“一种文字出现以前的替代物来替代一般的政治军事史,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化,是迁徙而不是战场。”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虽然一度令人振奋,如今看来却有局限性,尽管“文化”这个概念(包括人、器物和“精神”)仍然存在,事实上还很牢固。而迁徙作为我们这个世纪中的一个主要主题,仍然是探索铁器时代的人口分布、器物和精神传播的关键。这种传播范围跨越欧洲,从现代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的“模式遗迹”直到罗马人到来之前500年的不列颠。随着对越来越多来自不列颠的材料的系统研究,通过对一处处遗址、一个个地区的研究,人们已经把重点转移到对当地环境的适应上,不论哪个时期都是如此。此外,柴尔德的“取代战斗”这种提法似乎也容易使人误解。就像现代社会史学家再也不能像特里维廉试图避开政治那样,在谈及史前时代故事的时候也不能避开战争。手斧,这是留存下来的最早一种器物,其用途并不单纯;它的使用年代可以追溯到间冰期的“旧石器时代”,在斯旺斯库姆的泰晤士河河段的沙砾层中就曾发现这种器物和与它在一起的人头骨碎片。20世纪的一位小说家约翰·福尔斯非常聪明地提出:“如果说石器时代最好的工具是用来与木头和石头打交道的话,青铜时代最精良的工具却是为了杀戮或征服人类”。远古时代存在暴力,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在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西南部一个长长的坟堆里发现一具成年人的骷髅,在它的一侧有一枚树叶形状的燧石箭头。在科茨沃尔德边上的维奇伍德森林中有一座埋有20个人的长房子样的坟墓,其中一个埋葬者是被箭射死的,箭头从下方穿透右肋,嵌在脊骨中。任何时期的社会史都必须是既能包罗万象又能体察入微,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人们的威望和权力问题。
20世纪后期发生的“分期革命”已经迫使人们对时间和空间重新进行检验。因此,由于以农业发展为依据的新石器时代的概念已经被推到更久远的年代,不列颠外围的岛屿,包括在最北边的那些,在考古说明中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英格兰本土像巨石阵那些久为大家所熟知的地方,已经具有了新的意义。巨石阵Ⅰ的确很古老,而巨石阵Ⅱ则被认为是在圣经旧约中的亚伯拉罕在世时才修建的。西欧各国(包括英格兰西部)的巨石则直到19世纪才被归纳到一起,但现在已被确认为比希腊的迈锡尼文化还要古老。在不列颠群岛许多地方都有环形的石林圈或直立的巨石。
许多不同的科学不仅对新的年代学做出了贡献,对于非文字记载的历史的解释也发挥了作用,因为后来通过放射性碳重新确定年代(这项发明使威拉德·利比获得1960年诺贝尔奖)所引起的分期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新问题。随着猜测的大量消失,推理的范围扩大了。因而某些考古学家企图把推理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他们认为,考古学家提出或回答问题应该根据资料。然而,不管多么困难甚至众说纷纭,人们总是试图进行概括,像史前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需要系统的研究:生活资料、技术、社会组织、贸易与交通通讯、文化和人口统计学(人口分析)。

这六个特性与其在后来的社会中一样,显然是互相依存的。例如,生活资料明显地影响人口,反之亦然。同样地,技术与社会组织互相影响:技术决定农作方法,因此影响到生活资料,而社会组织显然与贸易与交通以及文化都有关联。即便实证资料尚属支离破碎,但仍然可以把上述那些特征一一分辨清楚并以模型的形式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总是有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的工作,我们今天可以描绘出的某些社会画面尽管仍然粗糙并有待于修改,但也远比那些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营地和湖边村落的陈旧得已经褪色的图画更有说服力。
生活资料问题对于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考古学家总是一点一滴地寻找有关史前时代食物的材料。新石器时代,从依靠狩猎转变为发展以谷物为主的农业和家畜饲养,但这并不意味着狩猎的结束。居处虽有篝火保护,也很难说得上绝对安全。不过这种转变意味着食物必须贮存起来,地界必须划分出来,而且家族的世系变得重要起来。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土地的使用和沿海资源利用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已得出一份十分复杂的年表,它与人口流动有关系,与社会组织的强度也有关系,某些地区由于地力耗尽而被放弃,另一些地区则被开垦出来。在更为集中的研究中,最近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弄清了史前时代的饮食构成,它既包括鱼类,也包括肉类和蔬菜。不同的遗址显示了不同类型的遗迹。
与生活资料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也牵涉到后世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满足了直接需要以后,由于粮食的剩余带来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农业剩余。这是由于偶然性引起的意外收获呢还是有意造成的?没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人脱离采集食物的工作,要建成巨石阵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块巨石的重量都在三十五吨左右,需要六七百人用皮绳拖起搬运。在涉及坎布里亚巨石群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计算。数世纪以来,坎布里亚的地理条件存在许多障碍,既不利于粮食生产(有效的自给农业),也不便于交通。那么,脱离粮食生产的人口是如何获得的?这些巨石又是怎么搬运的呢?
每一种技术过程,包括搬运石头在内,都可以从对用于特定建筑的工具和材料进行研究中推断出来。特别是,使用青铜器可以办到用燧石所无法完成的事情,而使用铁器又可成就用黄铜器所无力完成之事。不过,这些材料的使用也有可能是互补的;至于另外两种材质——木头和皮革,在一般情况下难以保存下来,然而,它们在技术上得到了使用。
要弄清技术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往往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推测。然而,似乎可以令人信服地提出:4000年前在威塞克斯的坟堆(这是单葬坟堆而不是公葬坟堆)的数量的显著增加以及在那个地方大量发现的早期青铜时代的遗迹,可以说明当时人口有所增加,而且也比先前的社会较为注重等级。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着手恢复过去的整个结构,正如科林·伦弗鲁所做的那样。伦弗鲁曾经注意到,当时人们逐渐地不那么强调去动员人力来从事公共工程,例如修建西尔伯里山那样的欧洲最大的人工墓冢,但却是越来越强调个人、财产以及首领和小首领的威信。炫耀性的消费迹象也处处可见。此外,还有必要进行补遗。在弄清社会组织方面,有许多证据是跟死亡或至少是跟葬礼的方式有关,而不是跟生活的方式有关。这一点在远远靠后的历史时代里,包括维多利亚时代在内,都可以得到证实。
文化具有一系列的象征,这些象征最终要通过“艺术”和“宗教”(往往是通过人工制造的实物)来说明。因此,对于文化作用的研究,很受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关注。但是,现存的东西看来很少有完整的。就英国情况而言,如果与东方国家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它的考据是很零碎的。英国只有很少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尽管在克里斯威尔峭壁中发现了雕刻着一个马头的骨片并在德比郡的另一个岩洞里发现一段刻有一条鱼的图案的象牙尖。此外,还发现了一些较晚时期的小型生殖器崇拜物,它们说明了文化和生殖之间的联系。然而,考据的稀缺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概括出人们在宗教态度上有巨大的转变:俯视大地让位于仰望天空。
对物体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行追踪,往往可以推知人们对宗教的态度以及宗教仪式的传播情况。例如,手斧可以在举行仪式时使用,如同中世纪和现代的权杖一样。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可能更容易辨别。例如,陶器的流通方式可以通过车子的轨迹进行判断。很明显,在罗马入侵时期,贸易和交通都是比较发达的。事实上,早在这以前,罗马人和希腊人都已经知道康沃尔是个出产贵金属的地方。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时尚的变化:2500年前人们的长袍改用别针来代替扣子,可以用来跟两个世纪前人们把鞋扣改为鞋带进行对比。
对于社会史学家来说,人口学是最富有挑战意味的研究领域之一,由于人口统计资料作为该学科本身的需要进行收集,在历史上开始得很晚(英格兰直到1801年才进行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于那些遥远的年代的人口情况,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主题。然而,一切社会史都必须以人口统计和经济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18世纪(即在足够的数据被收集之前)就曾对人口增长情况进行过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讨论,这次讨论第一次指向了社会的六个基本特性,而其中概述了文化和史前社会的关系。这些特性不是构成一个序列,而是形成一个循环。
就史前史而言,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主要还是极力运用他们的才智去估计某些特定地点的居民人数、年龄及性别情况,或是提出在不同时期的人口压力的变化情况以及所考察的居民是否是新迁入者。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一些,随着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的改变以及好奇心的增长,我们对人口的估算方法也有所变化。模拟操作重现了人们在当时所能获得的食物的条件下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更富有启发性的方法仍然是把从后来的人口和生存模式中所获得的知识应用于史前时代。人们还雄心勃勃地试图测定各地和英国的人口总数。据推测,在上部旧石器时代,人口在250人至5000人之间;在狩猎时代的高峰,人口在3000人至2万人之间(这时期人口的增减也许有相当大的波动);在新石器时代,人口在1万人至4万人之间;在青铜时代,人口在2万人至10万人之间;在铁器时代,人口在5万人至50万人之间。
这些有争议的估计数字固然很吸引人,然而,如果能够对每个特定的遗址的生活方式进行回顾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当今的考察者可以把离伦敦15英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从国外往返的希思罗机场作为考察的起点。当20世纪40年代在这里修建机场跑道时,发掘出距今2400年的考古遗迹,随后确定出该机场是修建在一个铁器时代的遗址上(其中还有一个神庙)。当时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并信仰宗教的人民,在大约500年以后罗马人进入不列颠岛时,曾经抗击过罗马人。当然,在他们之前还有过许多其他的居民,也有一些居民则是比他们晚来得多。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曾写道:“谁是不列颠的最早的居民?他们是土著人民还是移民?这始终不清楚。”不过,他又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补充说:“必须记住,我们正在跟野蛮人打交道。”
在距离伦敦更远些的另一个遗址,即托基附近的肯特洞穴,发掘出一个猎人的主要营地,这个营地大约一直使用到距今1.4万年前;在那里出土的东西非常丰富,包括毛猛犸象和犀牛的骨骼,狼、鬣狗和熊(主要是熊)的遗骸,有趣的是,还包括后来在英国社会史上起重要作用的马的残骸。花粉分析则提示我们在当时曾有过青草和草本植物,生长着柳和桧,偶尔还有松以及橡、椴等树木;人工制品则有矛头、刀片和骨针等。
早期的猎人不一定住在洞穴里,但是他们却对当地的材料加以有效地利用,其中包括骨头。例如,在斯塔卡尔(离约克郡的斯卡博罗不远)发现的一个较晚的猎人营地里(如今已看不到),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在距离营地一个小时的步行距离内找到,除了当时可能用来从燧石上打火的二硫化铁外(这种东西在外表上很像从南约克郡煤田上找到的样品)。在这些猎人的世界里,火和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的世界,在水平上则又与猎人世界不同。在6000年前(海岛形成以后)跨海来到这里以后,新石器时代的男人和女人们清除了灌木丛和树林,开辟了牧场来饲养动物,种植谷物,并且住进可以取暖的房屋。他们可能是乘坐皮筏过来的,定居下来以后,便开采燧石并烤制陶器。从事这些活动,要求人们在本能和经验之间取得一种新的平衡,同时还给人们的工作以新的推动力。一些考古学家们甚至谈到石斧“工厂”的问题。新石器时代的人身材矮小,很少有人的身高在5.5英尺以上,尽管他们都善于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这些人以群定居,每一群的规模要大于单个的家庭,对其形成过程我们知之甚少,同时我们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了解不多。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们留下了不朽的遗迹。
在这方面,威尔特郡的遗存甚丰。温德米尔希尔就是位于威尔特郡的一个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用堤道围起的营地,它离埃夫伯里的巨石圈只有1.5英里,而与巨石阵相距也只有11英里。它的遗存是如此丰富,以致使乔治·马尔科姆·扬这位20世纪的文化史学家宣称:这个地区散发着的对遥远的过去的沉思意识,要比英格兰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强。扬称史学家为“连贯古今的高级牧师”,他认为如果顺着里奇韦(一条古道,现在M4公路经过此道)做一次穿越威尔特郡丘陵地区的旅行,就等于“沿着300代人的足迹所作的一次漫步”。
威尔特郡的这部分地区之所以对社会史学家有吸引力,不仅是由于它体现了英国遥远的过去,而且还由于作为历史的角色的自然本身也同样地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意识。然而,人们不应当被它今日的那种孤寂的景象(除去冬至或夏至时分)所迷惑。要知道,在新石器时代和在铁器时代的后期阶段,这里是属于国内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此外,科茨沃尔德、德比郡的山丘和约克郡的荒原也都是如此,因为所有这些地方都属于石灰石地带,土层很薄,用那个时期的工具来耕作,要比在河谷上比较肥沃的深土地带来得容易。
威尔特郡的历史有那么多的层次,以致难以把不同世代的人们所从事的工作辨认清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巨石阵(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大废墟,离希思罗机场60英里)的建设至少有五个阶段,而它的最后一个阶段跟第一个阶段相距的时间,和我们现在与朦胧难辨的公元7世纪之间相距的时间一样长。我们还知道,巨石阵的最早的建设者至少是在罗马人到来之前1800年就开始动工的。看来,他们是下定决心让他们的工程万古长存的,正如一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它孤独地屹立在历史上,如同它孤独地屹立在这块大平原上一样。”
毫无疑问,不同世代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对巨石阵所作的不同解释,大多以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情况为依据,而远远没有反映出历代建设者的工作状况。在12世纪,一位编年史家,蒙默思的杰弗里认为,巨石阵只不过是在7个世纪之前建造起来的,这样就把巨石阵列为和万斯代克(一个原长达50英里的大型壕沟)同时期的工程;在17世纪,人们则把巨石阵跟德鲁伊(凯尔特人的祭司的统称)、即曾跟罗马人进行对抗的当时的“教士们”联系在一起;而到了20世纪,巨石阵不仅与“旅游者”而且与科学家和计算机联系了起来。在这当中,18世纪的一位热心于考古学的先驱者——威廉·斯蒂克利,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巨石阵的构想“给常人的头脑带来可以想象的最大愉快”。
巨石阵以及其他一些遗址,之所以不断地使人迷惑不解,主要不在于投入这项建设工程所花费的大量的有组织劳动(80块极其贵重的青石看来主要通过水路从135英里外的威尔士彭布罗克郡运来),而在于这个工程的用途是什么。巨石阵Ⅰ大约建于4500年至5000年以前,它具有天文学和考古学上的价值。巨石阵Ⅱ也是如此。无论是把这个遗址称为“由矗立的巨石堆砌而成的几何学”的亚历山大·托姆,还是写了《巨石阵谜解》的杰拉尔德·斯坦利·霍金斯,都在对这个遗址的布局和方位进行仔细研究后提出:它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的兴趣,显然在于测量时间和预测季节的转换。巨石阵Ⅱ是从莱茵河流域迁来的所谓“宽口陶器人”的创作,他们是在公元前超过1000多年前最后一批大规模流入英格兰定居的民族。他们的名称取自于他们制作的宽口陶器,此外,他们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他们把死者单独地埋葬在圆形冢内(这是一项发明),虽然他们也实行火葬。他们对当地原有的居民也许更多地是实行融合,而不是征服。近来有人提出怀疑,即怀疑他们当时能否达到创造这样一种杰出的文化的水平。
巨石阵Ⅲ的结构则有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当时人们从马尔博罗运去了一种天然的沙石(沙鹿仙或称砂岩原砾)。人们把这组巨石阵跟后来的所谓“贵族的”威塞克斯文化联系在一起。当时,葬礼已经比较讲究,陪葬品也比较多,而且,墓冢往往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片片的墓地。这个时期遗留下来许多有意思的物品,包括铜器、金器、青铜器,以及在妇女墓冢中发现的彩釉陶珠和一种蓝颜色的玻璃状粘贴(人们甚或认为,在妇女的墓冢中发现很丰富的陪葬品,也许意味着在宽口陶器时代以后妇女地位的提高)。至于说,这些遗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反映这种文化的全貌,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同样有争议的问题还有,这些遗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明当时人们依赖于技术的改进(如加工工具)和以爱尔兰黄金作为后盾的贸易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当时经济上的收获所依靠的并非技术的改进和贸易的发展,而是在远为高度发达的农牧业的基础上取得的。巨石阵的一位新近的发掘者,理查德·约翰·科普兰·阿特金森宣称:我们现在已经有证据说明,当时之所以能够修建像巨石阵这种规模的工程,是“由于政治权力的集中——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一个唯一能够凭一己之力即可为修建这种工程创造并保持必要的条件的人手里。”
这里所谈到的“政治权力”,纯属推测而已,事实上,我们也满可以用“强制”或“宗教”来取代“政治”这个字眼。有一点看来很清楚,就是在那个时代随着金属的采掘、合成、铸造和分配,社会的专业分工比较细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弄不清楚,例如,有关巨石阵和其他巨石圈的维护以及为何放弃原在巨石阵工程周围进行的主要工程,都使人感到神秘莫测。
用“青铜时代晚期”这个标签来概括铁器时代之前的那段时期,或是概括罗马人来到之前的1000年间所包含的各个时期,都是完全不够充分的。虽然,我们可以从收藏的大量青铜器中追溯到青铜本身用作装饰或武器的变化过程,但我们尚不清楚的是,社会变化——例如聚落形态或者景观外观的变化,与青铜在不同阶段的使用情况,究竟有多少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近来人们强调指出了一些社会变化:好的耕地比较值钱了,而且出现了比较复杂的迁移模式。不过,由于现存的考据很少,所以我们所知道的也极其有限。对于在多塞特发现的与众不同且连续不断的德弗莱尔-里姆伯里文化(它在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000年间繁荣起来)所作的考古发掘,使我们了解到在铁器时代之前那些不规则的小块锄耕地已经消失,代之而出现的是被称为“凯尔特田野”的方块犁耕地,而且当时已经出现了“畜牧场”和“贮藏窖”。在遥远的英格兰北部,已经建立起带有中间立柱的有屋顶的圆形房屋;而在东部,有证据说明当时在芬斯地区注3已对边际土地进行了开垦。在罗马入侵的8个世纪以前,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看来是在不断地增长,但过了两个世纪以后便又再度萎缩。还有,看来在当时的社会中暴力现象有所增加,这也许是由于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对土地的压力所致。在武器制造方面,古老的长剑已被青铜时代的双刃重剑所取代,这种剑既能砍又能刺。毫不足奇,当时也有了青铜盾,而马具则进一步讲究起来,笼头已包括缰绳、马嚼子、缰绳环等物。当时,山堡也已出现。
在英格兰,铁制兵器和工具的生产的历史开始于罗马入侵的600年以前。有些兵器装饰得很漂亮,这说明在当时的社会里战斗是很普遍的。制铁技术是从欧洲大陆传入的,当时的技术水平至少可以和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相匹比,尽管人们对于这种技术是否由岛外移民“强加”给本土居民还不断有争论,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时的社会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在约克郡东部的考古发现是很重要的,它说明在罗马入侵的500年以前就存在外国的直接影响。在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游牧人民看来喜欢住在带围栏的小型宅地里,而在中部和东部,人们则喜欢空旷、无围栏的村落和星星散散的农场;不过在南部,工事坚固的山堡则形成铁器时代的一种特色。在那里至少有3000个各式各样的山堡,其中一些——如在多塞特的最著名的梅登堡——则高踞在一些老旧建筑之上。许多山堡至今仍历历在目。
若干世纪以前,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已经在梅登堡建立起一个带有堤道的营地,这个营地在铁器时代大大地改进了:增加了一道壕沟,加高了护墙。其中一道建在斜坡上的主要护墙,从墙顶到沟底的高度已达83英尺(当时还是使用投石器和铁剑的时代)。一些大型山堡的内部,看来当时已具有城镇的样子:有道路、圆形房屋以及贮藏谷物用的地窖,它们可能建得非常稠密。正是在这些年代里,马已被钉上铁蹄,并且开始从动物中脱颖而出。离里奇韦不远的一个白垩山坡——乌芬顿的大型白马图像,也可能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据估计,这个图像还是后来在许多山坡上出现的白马图像的始祖(它们大多数是在过去200年间完成创作的)。马的图像还出现在铁器时代的水桶和钱币上。当时的马四肢苗条,体高约11.2至12.2掌注4,它被用来驾驶战车,这时的战车终于配备了带轮辐的铁轮。当时使用牛来犁地,并且使用交叉十字犁来翻土。人们已经使用铁斧来清理林地。这个时代的宗教及流畅的曲线艺术与傍依溪流和林木的圣地有着联系。这时候的经济已远比先前的时代为复杂,铸币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我们离罗马入侵的时期越近,所能掌握的考古学证据也就越多,虽然这些证据还是零碎不全。这些证据说明,当时存在着比家族要大的“部族”单位,它们有各自的“王者”领袖。在这些部族中,特里诺万提斯人住在泰晤士河的东北部,杜洛特里格斯人和杜姆诺尼人住在西南部,布里甘特人则分布在奔宁山区的许多地方以及相邻的英格兰北部的平原上。我们可以在若干地区追溯到单独的宅地和集结的住地的分布情况,同时还可以考察到铁器时代的农业情况,其耕作业以小麦和大麦为主,其畜牧业则以绵羊为主,农牧业都紧密地与各种有效的耕作方式联系在一起,包括牲口繁殖、施肥和种子的认真保存等。
一般来说,工艺技术的变化要比先前的时期更大。在罗马人到来之前的一个世纪,陶器已经采用快转轮进行生产,而且已经有了粗陶器和细陶器之分。纺织机使用上了骨制的和陶制的锭盘,或是像先前的时代一样,使用石制的锭盘;但编织这时已经使用以黏土压重并带有骨质精梳的直立式织布机来进行。至于铁这种金属——该时代即因其得名——可能是在碗状熔炉中冶炼出来的。在这个时代里,消费看来已经划分为社会等级,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奢侈品的名目增加了。从其他地区进口了葡萄酒,随之而来的往往还有精美的酒具。此外,还有精工镶嵌的胸针,在坟墓中还能发现镜子和武器等物品。在罗马人到来的那个世纪中,镜子的设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主要的港口是汉吉斯伯里赫德,它位于基督教堂港的南边。
然而,没有文字的历史仍然充满着神秘。究竟当时有多少迁入者?尤利乌斯·恺撒认为这些人是跨越海峡的比利其人。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的?发明创新是否依靠移民?英格兰南部这个特别为罗马人所熟悉的地区的发展,究竟跟内陆以及北部或东部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最早铸造的硬币全都是不适合普通人用于交换的金币?这些金币是否专门用来进贡或是还有其他什么用途?妇女在经济中起什么作用?孩子们是怎样养育成长的?
至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开始于跟罗马人遭遇的那个“部族”社会,这个社会的文化后来被称为凯尔特文化,跟这种文化相联系的有具有特色的方形犁耕地及其他种种东西。事实上,从古代的渊源来看,以任何一种特殊方式把“凯尔特”这个词跟英格兰联系在一起,都是缺乏根据的。只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学者们才推断出,盖尔语和威尔士语源自于一度曾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定居的古代凯尔特人的语言。
在英格兰的康沃尔这个地方,当时人们还讲一种凯尔特人的语言;直到今天,英国的许多河流和溪流仍然以凯尔特语命名,诸如艾尔河、艾文河、迪河、德尔文特河、默西河、塞文河以及泰晤士河。利兹是用凯尔特语命名的最大的现代化城市,还有像萨尼特、怀特(在怀特岛上)和克雷文(约克郡的一个美丽的丘原村落)这些地方,其名称都源自于凯尔特语。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自然和语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一直保存下来。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我们能够画出一张凯尔特人时代的英格兰地图,但除了上述的以外,很少有其他来自那个遥远时期的凯尔特语的词汇进入我们的语言,并在许多世纪中跟我们共存。在我们最熟悉的寥寥无几的词中有“ass”(驴子)和“combe”,后一词是小峡谷的意思,它跟地图的联系要比跟词典的联系更多。至于通过法语和爱尔兰语间接地进入英语的凯尔特词汇,则比以上列举的多得多。然而,一些作者认为,在英国的传统中具有一种老的凯尔特情结。正如一位出生在康沃尔的20世纪的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所说:“19世纪的史学家们惯于把我们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其实我们是地地道道的盎格鲁-凯尔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