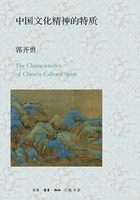
道家的理想人格与超越精神
我们从杜甫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儒家的忧患和民间的疾苦。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体会到道家放达、超越的精神和智慧,对理想人格的追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1章,以下只注某章。)这里涉及“道”与“名”,“道”与“有”“无”,“道”与万物的关系。“徼”指边界,即事物间的界限,也可引申为端倪。“玄”谓幽深难测。“道”是整体性的,它在本质上既不可分割,也不可界定、言说。“道”是无限的,不可以用有限的感观、知性、名言去感觉、界说或限制。可以言说、表述的“道”与“名”,不是永恒的“道”与“名”。“无名”是万物的本始、源泉;“有名”是各种现象、事物的开端。这表明“道”也是先于语言概念的。无欲之人才能体悟“道”的奥秘,利欲之人只能认识事物的边界或表层。“道”与“无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名称,都叫作“玄”。“无名”是无形无限的宇宙本体,“有名”是有形有限的现象世界。通过两者之间的变化,人们可以探索深彻幽微的宇宙本体和奥妙无穷的现象世界的门户。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道家的道体具有超越性、绝对性、普遍性、无限性、圆满性、空灵性。道家之“无”在哲学上具有无限的意义。道家之“道”是有与无、神虚与形实的整合。“有”指的是有形、有限的东西,指的是现实性、相对性、多样性;而“无”则是指无形、无限的东西,指的是理想性、绝对性、统一性。“有”是多,“无”是一;“有”是实有,“无”是空灵;“有”是变,“无”是不变;“有”是内在性,“无”是超越性。
“道”又被形象化地比喻为“谷”“谷神”“玄牝”,“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6章)。“道”如山谷一样。山谷是空虚的,唯其如此,才能永远存在并具有神妙莫测的功能。“牝”是雌性牲畜的生殖器,泛指雌性。玄牝,意为万物最早的始祖,也即“道”。“谷”“牝”的门户,是天地的发生、发源之地,绵绵不绝好像存在着,其作用无穷无尽。
“道”的展开,走向并落实到现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2章)道产生原始混沌的气体。原始混沌的气体又产生阴阳两种气。阴阳两种气产生中和之气。中和之气则产生万物。万物各自具有阴阳二气,阴气阳气相互摇荡就成为和气。“和”是气的流通状态。
道家道论认为,不仅宇宙之有、现象世界、人文世界及其差异变化,即存在的终极根源在寂然至无的世界,不仅洞见、察识富有万物、雷厉风行的殊相世界,需要主体摆脱诸相的束缚,脱然离系,直探万有的深渊,而且习气的系缚、外物的追索、小有的执着,会导致吾身主宰的沉沦、吾与宇宙同体境界的消亡。因此,老子主张“挫锐解纷”“和光同尘”“谷神不死”“复归其根”“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无为而无不为”“无用而无不用”。这些话语论证滞留物用、执着有为对于心体的遮蔽,论证摄心归寂、内自反观、炯然明觉、澄然虚静的意义,着重强调了人生向道德和超越境界的升华。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40章)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发展,是“道”的运动;柔弱,是“道”的作用。举凡自然、社会、人生,各种事物现象,无不向相反的方向运行。既如此,柔弱往往会走向雄强,生命渐渐会走向死亡。老子看到了事物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状况。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章)人们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善之所以为善,那也就知道丑恶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先后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存在,相辅相成,相互应和。“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39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22章)受得住委屈,才能保全;经得起弯曲,才能伸直;洼下去,反而能盈满;凋敝了,反而能新生;少取,反而能多得;多得,反而迷惑。《老子》书中特别注意物极必反的现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58章);“物壮则老”(30章);“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44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76章)
老子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极限,主张提前预测设计,避免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防患于未然,因而提出了“不争”“贵柔”“守雌”“安于卑下”的原则。他主张向水的品格学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8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正言若反。(78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28章)
柔弱之水可以冲决坚强之石,弱可以胜强,柔可以克刚,新生的、弱小的事物能够战胜腐朽的、强大的事物。老子看到强大了就接近死亡,刚强会带来挫折,荣誉会招致毁辱,因此安于柔弱、居下、卑辱。他提出“去甚、去奢、去泰”(29章)的主张。老子所谓“玄德”和“常德”,即深远、永恒的本性,如山谷、沟溪、赤子,乃在于它具有超越性和本真性,即超越了一定社会的等级秩序、道德准则和善恶是非,摆脱了人为的沾染,真正回复到人的本然的纯粹的性状,这才是人应持守的本性或品德。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48章)减损知、欲、有为,才能照见大道。“损”,是修养的工夫,是一个过程。“损”就是做减法。我们面对一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进而层层追寻真理的内在意蕴。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是剥落了层层偏见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最后豁然贯通在我们内在的精神生命中。“无为而无不为”,即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所以老子强调学习要做加法,求道则要做减法,减掉世俗看重的身份地位、功名利禄,减损又减损,一直到无为。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妄作妄为。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6章)意思是说,致力于“虚”要经常要彻底,也就是不要让太多现存的、人云亦云的知识、规范、利害、技巧等充塞了头脑,要用否定的方式排除这些东西,激活自己的头脑,使自己保持灵性、敏锐,有自己独立运思的空间。“守中”也是“守虚”、致虚。“守静”即保持闲静的、心平气和的状态,排除物欲引起的思虑之纷扰,实实在在地、专心地保持宁静。这也是随时排斥外在之物的追逐,排斥利欲争斗等引起心思的波动。“观复”,即善于体验万物都要回复到古朴的老根,回复到生命的起点以及回归故乡与故园的规律。“观”就是整体的直观、洞悉,身心合一地去体验、体察、观照。“复”就是返回到根,返回到“道”。体悟到“道”的流行及伴随“道”之流行的“物”的运行这一常则的,才能叫“明”(大智慧)。反之,不识常道,轻举妄动的,必然有灾凶。“常”是常识、真相、规律,我们只有“知常”,才有大聪明,才有宽容之心,才能知道天下的公道,这才是与道相符的心态,一生才不会有危险。体悟了“道”的秉性常则,就有博大宽容的心态,可以包容一切,如此才能做到廓然大公,治理天下,与天合德。与“道”符合才能长久,终身无虞。通过“致虚”“守静”到极致的修养工夫,人们达到与万物同体融合、平等观照的大智慧,即与“道”合一的境界。我们平常太忙,有太多的活动,要守守静,反思反省;有太多的实务,要守守虚,多思考问题。动静互涵,虚实相济,这也是道家修炼的功夫。我们也要学会调节生命,不能一根筋地往前走。道家的玄观,启发我们超越现实,透视无穷。
道家强调无用之用;儒家强调有用之用。儒家之“有”“用”,即建构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道家之“无”“用”,则要从人文世界中超越出来,回归到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道家的逍遥无待之游,是自我真实的自由人格之体现,以“适己性”“与物化”为特征;儒家的刚健自强之道,是自我真实的创造精神之体现,以“人文化成”为特征。古代的智慧强调民族、文化的可大可久,讲究空间的无限性与时间的延续性,强调对生态的保护。儒释道三教都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涵。太过强势,太过占有,太多的有为,往往适得其反。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是互补的。孔子为了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了道德的理念、社会的理想而拼搏奋斗。而老子可以洞见这个世界深邃的问题,减损自己的功名利禄,达到大有为而不是盲目有为的状态,才能无所不为,才能洞悟道的本体。老子讲无为而治,以正道治国。因为什么都要政府管,是很难的,政府无穷大,也是有问题的。
道家之“无”在政治论、道德论、道德境界及超越境界的慧识方面是值得发掘的。尽管道家以虚无为本,柔弱为用,削弱了“有”之层面(人文、客观现实世界)的能动建构,但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我们对于道家破除、超脱有相的执着,荡涤杂染,消解声色犬马、功名利禄的系缚,顺人之本性,养心之清静方面,则不能不加以肯定。虚、无、静、寂,凝敛内在生命的深度,除祛逐物之累,正是道家修养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无为”“无欲”“无私”“无争”,救治生命本能的盲目冲动,平衡由于人的自然本性和外物追逐引起的精神散乱,也是道家道德哲学的基本内容。而道家澄心凝思的玄观,老子“涤除玄览(鉴)”的空灵智慧意在启发我们超越现实,透悟无穷,然后再去接纳现实世界相依相待、迁流不息、瞬息万变、复杂多样的生活,以开放的心灵破除执着,创造生命。因此,他与孔子儒家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按照老子的道德理想、道德境界、人生智慧和人格修养论,他推崇的美德: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贵柔守雌、慈俭谦退、知足常乐、致虚守静、清静无为、返璞归真。老子以此为至圣与大仁。这是老子对人生的感悟,特别是对春秋末年贵族阶级奢侈生活的批判,对贵族社会财产与权力争夺的沉思,对财产与权力崇拜和骄奢淫逸的警告。老子通过冷静观照,提示了淡泊宁静的生活旨趣,看到逞强、富贵、繁华、暴利、暴力、权势、浓烈的欲望、奢侈、腐化、夸财斗富、居功自恃、骄横等的负面。故老子的解构与孔子的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
庄子及其学派提出了“逍遥无待之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论。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庄子》内篇中的《大宗师》《齐物论》《逍遥游》三篇文章的主旨,一般认为这是庄子的代表作。
《大宗师》指“道”或“大道”。大是赞美之词,宗即宗主,师就是学习、效法。篇名即表达了“以道为师”的思想。也就是说,宇宙中可以作为宗主师法者,唯有“大道”。既然道的生命是无限的,那么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万物的生命也是无限的。所谓生死,不过如昼夜的更替,我们不必好昼而恶夜,因而无须乐生而悲死。这才算领悟了生命的大道,也可以说是解放了为形躯所限的“小我”,而成为与变化同体的“大我”了。
“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该篇假借孔子与颜回的对话,通过颜回之口表达修养工夫。“坐忘”即通过暂时与俗情世界绝缘,忘却知识、智力、礼乐、仁义,甚至我们的形躯,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坐忘”的要点是超脱认知心,即利害计较、主客对立、分别妄执,认为这些东西(包括仁义礼乐)妨碍了自由心灵,妨碍了灵台明觉,即心对道的体悟与回归。《大宗师》作者认为,真人或圣人体道,三天便能“外天下”(遗弃世故),七天可以“外物”(心不为物役),九天可以“外生”(忘我)。然后能“朝彻”(物我双忘,则慧照豁然,如朝阳初起),能“见独”(体验独立无对的道本体),然后进入所谓无古今、无生死、无烦恼的宁静意境。庄子的意思是去心知之执,解情识之结,破生死之惑,顺其自然,不事人为,以便与道同体,与天同性,与命同化。与“坐忘”相联系的另一种实践工夫是“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此处也是假孔颜对话,托孔子之口表述作者之意。以耳来感应,可能执定于耳闻,不如听之以心。以心来感应,期待与心境相符,尽管上了一层,仍不如听之以气。气无处不在,广大流通,虚而无碍,应而无藏。所以,心志专一,以气来感应,全气才能致虚,致虚才能合于道妙。虚灵之心能应万物。心斋就是空掉或者洗汰掉附着在内心里的经验、成见、认知、情感、欲望与价值判断,自虚其心,恢复灵台明觉的工夫。
《齐物论》与《大宗师》相辅相成,互为表里。《齐物论》表述了庄周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强调自然与人是有机的生命统一体,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齐物”的意思即是“物齐”或“‘物论’齐”,即把形色性质不同之物、不同之论,把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不和谐的现实世界种种的差别、“不齐”,视之为无差别的“齐一”。这就要求我们以不齐为齐一,即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接受、面对真实生活的同时,调整身心,超越俗世,解脱烦恼。此篇希望人们不必执定于有条件、有限制的地籁、人籁之声,而要倾听那自然和谐、无声之声、众声之源的“天籁”,以消解彼此的隔膜、是非和有限的身生命与有限的时空、价值、知性、名言、概念、识见及烦、畏乃至生死的系缚,从有限进入无限之域。庄子反对唯我独尊,不承认有绝对的宇宙中心,反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主张破除成见,善于站在别人的立场,更换视域去理解别人,而不以己意强加于人。《齐物论》有“吾丧我”之说。“丧我”与“心斋”“坐忘”意思相近,“形若槁木”即“堕肢体”,“心若死灰”即“黜聪明”,也就是消解掉由形躯、心智引来的种种纠缠、束缚。“丧我”的另一层意思是消解掉“意、必、固、我”,消解掉自己对自己的执着,走出自我,走向他者,容纳他人他物,与万物相通。与“心斋”“坐忘”一样,人们通过“丧我”工夫最后要达到“物我两忘”的地步,即超越的精神境界,以便与“道”相契合。
《逍遥游》把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当作最高的境界来追求,认为只有忘绝现实,超脱于物,才是真正的逍遥。本篇宗旨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作者指出,“逍遥”的境界是“无所待”的,即不依赖外在条件、他力的。大鹏神鸟虽可以击水三千,背云气,负苍天,飘然远行,翱翔九万里,然而却仍有所待,仍要依凭扶摇(飙风)羊角(旋风)而后始可飞腾。有的人才智足以胜任一方官吏,行为足以称誉一乡一地,德性足以使一君一国信服,按儒家、墨家的观点,可称得起是德才兼备的人,但庄子认为他们时时刻刻追求如何效一官,比一乡,合一君,信一国,仍有所待。宋荣子略胜一筹。宋荣子能做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已属不易,然而他能“存我”而未能“忘我”,更未能物我兼忘,仍不是最高境界。列子略胜一筹。列子日行八百,任意而适,无所不顺,更不多见,但他仍有所待。他御风而行,飘飘然有出尘之概,可是没有风他就无能为力了,仍不能谓为逍遥之游。有比列子境界更高的人,他们顺万物本性,使物物各遂其性,没有丝毫的造作,随大自然的变化而变化,物来顺应,与大化为一,即与道为一。如此,随健行不息的大道而游,还有什么可待的呢?因其“无所待”才能达到至人、神人、圣人的逍遥极境。这个境界就是庄子的“道体”,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是道体的化身。庄子的人生最高境界,正是期盼“与道同体”而解脱自在。“各适己性”的自由观的前提是“与物同化”的平等观。逍遥无待之游的基础正是天籁齐物之论。章太炎《齐物论释》从庄子“以不齐为齐”的思想中,阐发“自由平等”的观念。“以不齐为齐”,即任万物万事各得其所,存其不齐,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体自身具有的价值标准。这与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正好相通。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人格。儒家心目中的圣人或圣王,有着内圣与外王两面的辉煌。虽然“内圣外王”一说出自《庄子·天下》,然而后来却成为儒家的人格标准。内圣指自我德性修养,外王指政治实践及功业。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因此,儒家人格理想不仅是个体善的修炼,更重要的是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是济世救民。儒家的人格特性包括如下内容:自强不息,意气风发,认真不苟,发愤忘食,兼善天下,关怀他人,系念民间疾苦,知其不可而为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立德、立功、立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等。儒者对国事民瘼有真诚的关怀,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业,即使遭到贬谪也以深沉的忧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兴亡。儒家也有其超越精神,穷居陋巷,自得其乐,安贫乐道。孟子讲的“君子三乐”,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理性之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育之乐,正表现了儒者的情怀。
道家庄子的真人、圣人、神人、至人、天人的理想人格,与儒家有别,其特性是:一任自然,遂性率真;与风情俗世、社会热潮、政权架构、达官显贵保持距离;独善其身,白首松云,超然物外,恬淡怡乐。这是庄子和道家的神韵情采。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相比较,道家凸显的是超越和放达,即不是积极肯定、参与、改造现实,而是以保持距离的心态,否定、扬弃、超越现实。对于权力结构的压制,儒家是积极地抗争,道家则是消极地不合作。
庄子之真人、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与道同体,因而都具有超越、逍遥、放达、解脱的秉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无穷、无限的境界。这深刻地表达了人类崇高的理想追求与向往。这种自然无为、逍遥天放之境,看似玄秘莫测,但实际上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每一时代的类的人、群体的人,尤其是个体的人,虽生活在俗世、现实之中,仍总要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即空灵净洁的世界。任何现实的人都有理想,都有真、善、美的追求,而道家的理想境界,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合一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