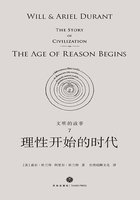
第三章 | 派那西斯山坡(1558—1603)
书
此时书籍数不胜数,日见增多。巴纳比·里奇(Barnaby Rich)于1600年写道:“这个时代的最大通病之一,就是全世界书的印行数目一直增多,大家难以消化这么多的无聊事。因为它们每天都在生产,然后传于全世界。”伯顿也说(1628年):“我们已由于这么多的书而引起分歧纷扰,我们受这些书的压迫,我们的眼睛疼痛了,手指也翻痛了。”但这二人都写书。
贵族阶级知书达理,在物质上赞助那些献书助兴的作者。塞西尔、莱斯特、西德尼、雷利、埃塞克斯、南安普敦、彭布罗克伯爵及夫人都是很好的赞助人,他们在英国贵族与作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查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讲学以后,仍然存在。发行人给予作者每小册约40先令,每部书约5镑。两三位作者试图专以摇笔杆为生,“文人”这种绝望的职业,此时已在英国成形。很多富有人家有私人图书馆,公立图书馆还很少见。1596年自加的斯返国途中,埃塞克斯暂时在葡萄牙的法罗(Faro)一地逗留,并尽取主教杰罗姆·奥索利亚斯(Jerome Osorius)的图书馆藏书。他把这些书赠予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爵士,博氏又将之藏起,后来遗赠给牛津大学(1598年)的博德利图书馆。
受到国家法律和群众兴趣的控制,书商是在焦虑中求生存发展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共有250个书商,因为此时印刷和卖书仍然是同一种生意,他们多数自营印刷。伊丽莎白时代晚期,印刷和发行两个行业才分开。发行人、印刷人及卖书人联合组成“印书公司”(Stationers' Company,1557年),印刷品在这个行会登记就有版权,不过版权不是保护作者,而是仅保护发行人。通常该公司登记的只是取得合法印刷执照的那些出版物,凡是著作、印刷、贩卖或持有损害女王或政府书籍的,印刷或进口异端书籍或教皇圣谕或教书的,或持有主张教皇权力优于英国国教书籍的,均犯重罪。违反这种禁令而受刑者不算少数。印书公司获得授权可以搜查印刷厂,可以焚毁无照的印刷品和拘禁其发行人。伊丽莎白时代的出版检查较宗教改革以前的任何时代都要严厉,文艺仍然欣欣向荣,就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出版危机反而使智慧更加敏锐。
学者很少,这是一个创造而非批评的时代,在炽热的神学变革年代,人文主义的洪流已经枯竭了。多数的历史学家仍是编年史家,以年代来做不同的历史叙述。不过,理查德·诺里斯(Richard Knolles)的《土耳其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1603年)是一部比较优秀的作品,很令伯夫利欣赏。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编年史》(Chronicles,1577年)供给莎士比亚英国历朝帝王的史实,因而其声名意想不到地大为增加。约翰·斯托(John Stow)的《英国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1580年)具有“某种智慧的色彩,劝人为善,及对那些不适当的事情产生强烈的憎恨感”,其中的学识却贫乏得可悲,其文章具有引人沉沉欲睡的特性。其《伦敦观测》(Survey of London,1598年)一书显得较有学问,但并未使他赚到更多钱。到了老年,他甚至穷得要发给他乞讨许可证。威廉·卡姆登在其《大不列颠》(Britannia,1582年)一书中,以流利的拉丁文描述英格兰的地理、景观及古物。《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Rerum Anglicarum et Hibernicarum Annales Regnante Elizabetha,1615—1627年)一书是基于小心研究原始文件而写成的。卡姆登一味增加伟大女王的荣光,推许斯宾塞,忽视莎士比亚,赞赏罗杰·阿谢姆,但令人痛心的是,这样好的一个学者,竟因喜爱赌博和斗鸡致死,死时一贫如洗。
阿谢姆曾任“血腥玛丽”的国务大臣、伊丽莎白的家庭教师,死时(1568年)曾留下英国最著名的教育论文《教师》。主要论述拉丁文的教学,但另以雄浑淳朴的英语,吁请以基督的仁慈教育取代伊顿学院严厉的手段。他曾提到一次与伊丽莎白政府要员吃饭时,话题转到鞭打教育的情形,并说塞西尔赞成采取较温和的方法。而理查·沙克维尔(Richard Sackville)爵士私自对阿谢姆供认,“一位好笑(愚蠢)的教师……使我为了恐惧鞭打,再也不爱读书了”。
学者最主要的成就是使外国的思想灌输到英国人的心智中。16世纪末,希腊、罗马、意大利、法国等国作品的译文,形成一股浪潮并横扫了整个英国。荷马史诗要等到1611年才由乔治·查普曼加以翻译。当时缺少希腊戏剧英文译本,也许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采取浪漫派形式而非古典派形式的主因,但是已有下述作品译本:西俄克里图斯(Theokritus)的《田园诗》,穆塞俄斯(Musaeus)的《海洛与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埃皮克泰图斯(Epictetus)的《手册》(Enchiridion),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与政治》(Ethics and Politics),色诺芬的《居鲁士劝学录》(Cyropaedia)和《国家经济学》(Oeconomicus),狄摩西尼和伊索克拉底的《演讲集》,希罗多德、波力比阿、狄奥多鲁斯·西库拉斯(Diodorus Siculus)、约瑟夫斯(Josephus)及亚比安(Appian)等5人的历史著作,赫里奥多拉斯(Heliodorus)和朗戈斯(Longus)的小说,托马斯·诺思爵士(Thomas North)将阿米奥(Amyot)所译的普鲁塔克的《传记》(Lives)法文翻译本,转译成生动的英文本。译自拉丁文者有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马希尔(Martial)、卢肯(Lucan)等人的作品,也有普劳图斯、泰伦斯及塞涅卡的剧本,李维、萨卢斯蒂、塔西佗及苏多尼乌斯(Suetonius)等人的历史作品。译自意大利的有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薄伽丘的《菲洛科珀和菲亚玛塔》(Filocopo and Fiammetta,但是1620年以前未将《十日谈》译成英文)、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历史集》、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奥尔兰多》(The Orlandos)、卡斯底里欧内的《廷臣》(Libro del Cortegiano)、塔索(Tasso)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The Gerusalemme Liberata)和《阿明塔》(Aminta)、瓜里尼(Guarini)的《菲都牧师》(Pastor Fido),班戴洛(Bandello)及其他作者的寓言小说,后来集入威廉·班特(Welliam Painter)的《欢乐之宫内》(Palace of Pleasure, 1566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迟至1640年才译成英文,可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都很熟悉。哈维说,剑桥大学中,“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和阿奎那的理论,因受学生骚动的影响……在校园中完全被摒弃了”,被马基雅维利和让·博丹(Jean Bodin)的学说取代。译自西班牙的有最长的爱情故事《阿玛迪斯·高拉》(Amadis de Gaula)、第一本描写恶汉的小说《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第一本古典乡土作品蒙特梅尔(Montemayor)所著的《戴安娜》(The Diana),取自法国的最佳战利品是普莱亚迪(Pleiade)的诗、蒙田的散文,均由弗洛里欧译成英文(1603年)。
这些译文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影响甚巨。模仿古典作品开始——继续了两个世纪——阻碍英国诗和散文的发展。多数令人追念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均熟知法文,因此翻译并非必要。意大利吸引着英国,英国的田园派仿自桑纳扎罗(Sannazaro)、塔索及里尼,英国十四行诗仿自彼特拉克,英国小说仿自薄伽丘和寓言小说。这些作品供给马洛、莎士比亚、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约翰·福特(John Ford)等人著作的材料,并使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都以意大利城镇为背景。排斥宗教改革的意大利,不谈宗教改革而排斥旧神学,甚至基督教的伦理观也受扬弃。伊丽莎白的宗教独自摇摆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知抉择之际,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却已不顾宗教的纷争,径自恢复文艺复兴的精神与活力。有一段时期,意大利受到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而一蹶不振,只好将文艺复兴的火炬传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
智慧之战
在伊丽莎白朝的狂欢时代,诗与散文像一股狂流倾泻而出。我们已知200位伊丽莎白时代诗人的大名,但直到斯宾塞著《仙后》,只有散文受到当时英国人的注意。
约翰·李利于1579年著有富于想象的《尤弗伊斯》(Euphues)一书,或称《智慧的解剖》(The Anatomy of Wit),首先受到英国人的注意。李利表现的主题是通过教育、经验、旅行和谆谆诱导,即可产生明智善性的人物。尤弗伊斯(意为“良言”)是一位雅典青年,其出外冒险的故事,供给讨论教育、礼节、友谊、爱情及无神论的讲坛。这本书非常畅销,应归功于其特殊的体裁——对照格、头韵、直喻法、双关语、对称子句、古典叙述、想象的交互使用。这种体裁像暴风一样地扫过伊丽莎白的宫廷,流行达一个世纪之久。如:
这位英勇的年轻人,机智胜于财富,而财富又超过智慧,自视其快活不亚于任何人,以为其诚实远优于所有人,因而他自以为适合做任何事情,结果几乎终日无所事事。
李利文章的弊病,究竟是仿自意大利人马里尼(Marini)、西班牙人盖瓦拉(Guevara)或佛兰德斯的韵文家,至今尚无定论。无论如何,李利乐于接受这些影响,然后又影响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人。它破坏了莎士比亚早期的戏剧格调,影响了培根的论文集和语言的发展。
这是一个注意用词的时代,剑桥大学教师哈维发挥其全部影响力,试图使英国的诗由重视重音和韵律转向重视基于音节长短的古典脚韵。受其鼓励,西德尼和斯宾塞在伦敦成立文艺俱乐部,称为最高法院(The Areopagus)。有一段时间,该俱乐部力图迫使伊丽莎白时代的活力转入维吉尔形式的著作。纳什故意模仿哈维“跳跃式的”六步韵,讥为完全与宫廷文学脱离。哈维卖弄学问、谴责纳什之友格林的无德时,他成为笔战的目标。这次论战带给英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尖酸谩骂的各种方法。
格林的一生是自维庸(Villon)至魏尔伦(Verlaine)止,上千种波希米亚人浪漫无行的文艺生涯的缩影。他与哈维、纳什和马洛一样,都是剑桥大学的学者。在那里,他与一群和他一样“荒唐的滑稽人”过从甚密,他和他们一起“消耗了青春的花朵”。
我沉浸于骄傲中。狎妓是我每日的运动,酩酊大醉是我唯一的嗜好……到此为止我对上帝一无所求,所以我很少想到上帝,反而喜欢拿上帝的名字来骂人和亵渎……假如我在世之时一直有欲望的存在,我就很满足,只有等死后再让我改变也罢……我畏惧法官审判的程度与我恐惧上帝的审判并无轩轾。
他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旅行,他说他在那里“看到和做的恶事令人作呕而不愿说出”。返国后他成为伦敦酒店的常客,红发、针须、丝袜,还带贴身卫士。他结婚后,温柔地述说婚姻的忠诚与快乐。不久他就为了情妇而遗弃自己的发妻,在情妇身上花的却是发妻的财产。从亲身体验的第一手资料中,他写了《诈欺集团的惊人发现》(A Notable Discovery of Cozenage,1591年),描述黑社会的欺诈手段,并警告进入伦敦的乡下人注意骗子、玩假牌者、扒手、老千及妓女的诈欺手段。因此,黑社会想要取其生命。令人惊奇的是虽一直过着邪恶的生活,他竟还有时间写下12部小说(尤弗伊斯体裁)、35本小册及许多成功的剧本,笔调具有新闻记者的迅速和活力。其精力和收入锐减之时,他才发现德行也有相当道理,因而就像他作恶一样,他以过人的雄辩畅述他的忏悔。1591年,其《再见愚蠢》(Farewell to Folly)一书出版。1592年,他编写两篇相当重要的文章,一是《关于一个暴发户马屁精的妙语》(A Quip for an Upstart Courtier),攻击哈维;二是《格林的小智慧》(Greene's Groatsworth of Wit Bought with a Million of Repentance),攻击莎士比亚,并吁请其腐化的同伙——显然是指马洛、皮尔(Peele)和纳什——改过迁善,敬神忏悔。1592年9月2日,他向受其遗弃的发妻请求付给一位鞋匠10镑,因为若没有他的照顾,“我已在街头中逝世了”。第二天,在这位鞋匠的家里,他告别了人间——据哈维说,是死于“吃了太多的腌青鱼和莱茵河流域的酒”。其女房东赞赏其诗,宽恕其债务,在其头上戴上桂冠,并替他妥为安葬。
伊丽莎白时代的散文家中,格林之友纳什的口舌最不饶人,拥有广大的读者。他是副牧师之子,讨厌俗礼的拘束,剑桥毕业后住在伦敦的波希米亚浪人区,撰文为生,学到能够“信笔疾书自成文章”。其《不幸的旅客》(The Unfortunate Traveller)及《杰克·威尔顿传》(The Life of Jack Wilton,1594年),奠定了英国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基础。格林死后,哈维在《四字经》(Four Letters)中攻击格林和纳什,纳什也连续发表小册反击哈维,而至《与你同赴萨弗伦·沃尔登》(Have with You to Saffron Walden,1596年)一文发表时达到高潮:
读者,开心吧!因为在我身上不缺令你们开心的事……这或将使我倒霉,但我将使他被嘘出这所大学……我要扔掉他。我把他揪上剑桥最主要学院的舞台上时,你们会给我什么呢?
哈维面对这种攻击仍然幸存下来,活得比那群波希米亚无行文人长,他死于1630年,享年83岁。纳什续完成其友马洛的戏剧《狄多》(Dido),与本·琼森合著《狗岛》(The Isle of Dogs,1597年),后以引诱罪被起诉,终而默默无闻地消沉下去。34岁(1601年)即英年早逝,这也是他短暂生命的巅峰时期。
菲利普·西德尼(1554—1585)
远离那疯狂的一群,西德尼平静地更早走到生命的尽头。伦敦国家人像画廊(The National Partrait Gallery of London)中陈列的西德尼像,似乎脆弱得不像一个男人:瘦削的脸,褐色的头发。兰古特(Languet)说他“一点也没有健康的样子”,艾布雷说他“极为漂亮”, “不像个男性,但是……具有大勇”。某些腹中有牢骚的人,认为他有一点自负,并觉得他在过分追求完美。唯其英雄式的结局终使大家原谅他的德行。
其母玛丽·达德利夫人(Lady Mary Dudley),是爱德华六世时掌政的诺森伯兰公爵的女儿,有此母亲谁不骄傲;其父亨利·西德尼爵士是威尔士首席贵族和爱尔兰第三任贵族代表,有此父亲谁不骄傲;得以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为其教父,并因而得其基督教教名,谁不骄傲呢?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部分时间是住在宽敞的彭夏斯特大厦(Penshurst),有橡木横梁,有天花板、画墙及水晶吊灯,是当时留下的最漂亮古迹。他年仅9岁即受封为世俗教区长,年俸60镑。10岁进入什鲁斯伯里学校,该校距其父任威尔士首席贵族的官邸勒德洛(Ludlow)堡不远。亨利·西德尼爵士不时写信给这位11岁的小童,信中充满了可爱的智慧之语。
菲利普用力甚勤,收效也大,成为其叔莱斯特及其父之友塞西尔的宠儿。在牛津大学3年后,他奉派赴巴黎担任英国使馆的小职员。查理九世宫廷曾殷切予以招待,他也目睹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他悠然自在,环游法国、荷兰、德国、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兰克福,他与胡格诺教派的学术领袖兰古特订下生死之交;在威尼斯,保罗·韦罗内塞(Paolo Veronese)曾替他绘像;在帕多瓦,他接受了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的传统。回到英国,他受到宫廷的欢迎,而且在两年内一直是女王的舞伴。有一阵子,因反对女王与艾列森的婚姻而失宠。他具有骑士高贵的各种特性——重视门第、马上比武的技巧与勇武、宫廷礼仪、谨守信誉及为爱情滔滔雄辩。他研读卡斯底里欧内的《廷臣》,试图模仿那位绅士哲学家所谓的理想绅士的典型,而其他人又模仿西德尼的举止行为。斯宾塞称他是“贵族和骑士的领袖”。
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以往贵族蔑视文艺,现在却开始写诗,并允许诗人附骥于门下。西德尼虽然并不很富裕,却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文学赞助人。他曾协助卡姆登、哈克路特(Hakluyt)、纳什、多恩、丹尼尔、本·琼森,尤其是斯宾塞。斯宾塞极为感激他的协助,誉之为“博学者的希望和年轻诗人的赞助人”。很反常的是,戈森竟赠给西德尼《恶行学校》一书,该书题旨称他是“令人欣然的抨击诗人、音乐家、演奏者、说笑话者及王国的那群像毛虫的无赖”。西德尼起而应付挑战,写下第一本伊丽莎白时代的古典作品《诗之辩护》(The Defence of Poesy)。
依据亚里士多德和意大利评论家的先导,他将诗下定义为:“一种模仿的艺术……表达、模仿或想象……一种能以言词表达的图像”,要达到“教育和娱乐的目的”,他将道德置于艺术之上,认为艺术应借图像为例教人以德:
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前者通过箴言,后者通过范例,而达成其目标;是这两种人,若无此二者,则工作势将停顿下来。因为哲学家以锋利的论证定下了空洞的(道德)规范,很难加以解释,而且太含糊难以把握,所以除他以外找不到指点迷津的人,直到他进入老年为止,或在他找到可以坦诚一吐的事实之前,就会追随他。因为其知识建基于抽象和空泛的理论基础上,因此可以了解其理论的人就感到高兴了……反之,历史学家缺乏格言,注意的不是应该如何,而是已经如何……所举和范例并无必然如果,因而这就是收效较少的理论。现在无匹敌的诗人却表现了这两种东西,因为无论哲学家说该做什么,诗人都会提供已经做到的哲学家要求的那个人的完美图像,因而他就是以特殊范例来表达一般的观念。我之所以说完美的图像,是因为他随心灵的力量产生了影像,那是哲学家仅能以语言加以描述的,然而这类描述无法像诗人那样推敲深入或拥有其人的影像。
依据西德尼的观点,诗是包含各种想象性的文学在内——戏剧、诗及想象的散文。“并不是押韵及诗化便是诗;一个人的作品虽未诗化,然其本质可能仍是诗,也可能作品诗化了,而创作的却不是诗。”
他在箴言之上加上范例。1580年,著作《诗之辩护》的那年,他开始写《彭布罗克伯爵夫人桃园赋》(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伯爵夫人是其妹,为英国最受喜爱的夫人之一。她生于1561年,比菲利普小7岁,曾经接受各类教育,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而其魅力一直不衰。她成为伊丽莎白王室的一员,女王出巡时例必由她陪同。其叔莱斯特预付给她部分嫁妆,她才得以嫁给彭布罗克伯爵亨利。据艾布雷的说法,“她很淫荡”,另有情人取代其夫。但西德尼仍然很崇拜她,应其请求写下了《彭布罗克伯爵夫人桃园赋》。
模仿桑纳扎罗的《桃园赋》(Arcadia,1504年),西德尼这篇散文冗长而轻松地幻想了一个有勇敢君王、漂亮公主、高贵骑士、神秘的化装及诱人景色的世界:“乌拉妮娅的可爱,是这个世界所能表现的最伟大的事”,然而如此的赞赏也仅能表现其万一而已;帕拉底亚斯“富有敏锐的机智,不会故炫其才,高尚纯正的思想寓于谦虚之心中;虽能滔滔雄辩,但谈吐温婉,言语甚为缓和;举止高贵,虽在困境亦如此”。显然,西德尼曾读过《尤弗伊斯》一书。故事本身是爱情的迷宫:皮洛克里斯伪装成妇人去接近美丽的菲洛可丽,令他感到挫败的是她竟爱他如同姐姐,而其父却爱上了他,误认他是女人,其母也爱上了他,认为他是男人。不过,故事的结局完全不违反上帝的十诫。西德尼根本未把这本书当作一回事,他从未校正原稿,临死前嘱咐将之销毁。但仍然被保存下来,重新编辑、出版(1590年),而且在10年内为伊丽莎白时代散文中最受欢迎的著作。
在写作这部罗曼史和《诗之辩护》中、在担任外交官和士兵生涯中,他编写了一连串十四行诗,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先河。要写这些诗,以有失恋的经验为宜。在第一任埃塞克斯伯爵的女儿佩尼鲁普·德弗罗(Penelope Devereux)身上,他找到了失恋的感觉。她把他的呻吟和歌颂当作正当的游戏,最终嫁给男爵里奇(1581年)。西德尼继续写十四行诗向她倾诉,甚至在她与沃尔辛厄姆结婚后仍是如此。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很少会为这种“诗的破格”(Poetic License)而震惊,没有人认为男人写十四行诗应以妻子为对象,做妻子的大方到足可使诗人安心写作。一连串的十四行诗在西德尼死后印行成书(1591年),题名为《爱星者与星星》(Astrophel and Stella)。该诗集模仿彼特拉克的体裁,奇怪的是这里的劳拉也有类似德弗罗的眼睛、头发、眉毛、双颊、皮肤和嘴唇。西德尼相当了解,他的热情本身就是一种写诗的手法。他曾写道:“假如我是一位情妇,十四行诗诗人永远不会令我相信他们爱我。”一经被视为美好的游戏,这些十四行诗立即成为莎士比亚以前的最佳作品,甚至月亮都害相思病:
哦!月亮,以何等悲伤的脚步,你攀上了云空,
多么沉寂,多么沉郁的面容!
啊!也许天堂亦不例外,
那忙碌的射手也试着射出爱情的箭?
的确,倘若那对渴望爱情的熟悉双目,
断定了爱已发生,了解了爱人的状况,
我就可从你的神色中看出,你动情的风姿,
对我,与卿相同,从你的情况即可了然。
那么,月亮呀!即使只为了友谊,也请告诉我,
除了缺少机智外,那里是否有永恒的爱?
在那里美丽是否与此地一样可傲?
它们是否比爱情更被喜爱,但是
那些爱人是否蔑视拥有那类喜爱的人?
他们是否把德行称为忘恩负义呢?
1585年,伊丽莎白派遣西德尼协助荷兰叛军反抗西班牙。虽然尚未满31岁,他已受封为总督。由于士兵的俸给均是贬值的货币,他要求小气的女王供应更多的补给和较佳的待遇,因而得罪了她。他率领士兵攻占亚塞(Axel,1586年7月6日),并身先士卒,在最前线作战。在聚特芬战役(9月22日)中,他表现得太勇敢了。其坐骑在战役中被杀,西德尼迅即跃上另一匹马,冲杀至敌阵内。敌阵中一颗步枪子弹射入他的大腿骨中。坐马失去控制,奔回莱斯特阵内。 西德尼立即被送回阿纳姆(Arnhem)的民房内安置。在25天中,他被那些无能的外科医生害得很苦,最后引起伤口化脓腐烂,10月17日这位“当代伟人”(斯宾塞挽语)去世。临死那天他说:“对这个世界性的帝国我不改我的乐观。”其灵柩带回伦敦时,葬礼的隆重为英国在纳尔逊之前未曾见。
西德尼立即被送回阿纳姆(Arnhem)的民房内安置。在25天中,他被那些无能的外科医生害得很苦,最后引起伤口化脓腐烂,10月17日这位“当代伟人”(斯宾塞挽语)去世。临死那天他说:“对这个世界性的帝国我不改我的乐观。”其灵柩带回伦敦时,葬礼的隆重为英国在纳尔逊之前未曾见。
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
斯宾塞说:“西德尼逝矣,逝者是我的朋友,逝去的是活在世上的欢乐。”斯宾塞之所以有勇气写诗,应归功于西德尼的鼓励。斯宾塞不幸生为织工之子,只是贵族斯宾塞家的远亲,当然谈不上有显达的机会。依赖慈善机构的奖学金,他才能在麦钱特·泰勒伊斯学校就读,然后至剑桥彭布罗克学院读书,仍须半工半读,自付膳宿费。16岁时,他开始写诗——甚至开始出版。哈维试图使他以古典形式和主题写诗,斯宾塞最初谦逊地取悦于他,但不久就反对接受这种限制,因为接受这类限制必须把不合己意的脚韵放在诗中。1579年,他把《仙后》的首部示于哈维,哈维不喜欢其中包含的中古寓言式的故事,也不欣赏其中精美的形式,他劝告斯宾塞放弃这种设计,但斯宾塞继续写下去。
暴躁好战的哈维替斯宾塞找到一个在莱斯特伯爵手下的职业。在那里,他认识了西德尼,很喜欢这个人,作《牧羊人的日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1579年)献赠予他。该诗形式仿自西俄克里图斯的作品,但依据流行历书的安排,照每年各季节分配牧羊人科林·克劳特(Colin Clout)的工作。其主题是描写牧羊人科林·克劳特单恋残忍的罗莎琳德(Rosalind)的故事。这算不上值得推介的作品,幸有西德尼的赞扬,斯宾塞才赢得一些喝彩。为了谋生,诗人接受新任爱尔兰贵族代表格雷爵士亚瑟的秘书一职。随之出征,目睹格雷在斯梅里克屠杀投降的爱尔兰人和西班牙人,也无异议。经过7年替爱尔兰的英国政府服务后,他从没收的爱尔兰叛军财产中取得位于马洛与利麦立克(Limerick)之间的基尔科曼(Kilcolman)城堡及3000英亩的土地。
在该地,斯宾塞定居下来,成为垦殖的乡绅,写作精美的诗。为了悼念西德尼的逝世,他写下流畅冗长的挽歌《阿斯特斐尔》(Astrophel,1586年)。之后他又更新、加长《仙后》一诗。胸中热情澎湃,他于1589年渡海返回英国,由雷利推介觐见女皇,并呈献该诗前三册给她,“这三本书将随女王的声名永存”。为赢取普遍的欢迎,他在该诗集的序中献赠颂诗于彭布罗克伯爵夫人、卡鲁夫人、哈顿爵士、雷利爵士、伯夫利爵士、沃尔辛厄姆爵士、汉士顿爵士、布克哈斯特爵士、格雷爵士、霍华德爵士、埃塞克斯伯爵、诺森伯兰伯爵、牛津伯爵、奥蒙德尔伯爵、昆布兰伯爵等人。伯夫利伯爵与莱斯特斗争不已,攻击斯宾塞是一位无聊诗人,但许多人称他是自乔叟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女王心情愉快,答应每年给他50镑养老金,财务大臣伯夫利爵士却故意延缓支付。斯宾塞曾经期望得到实质的收获,现在失望了,只好回到爱尔兰的城堡,在蛮荒、仇恨和恐惧中,过着写作那部理想史诗的生活。
他曾打算把这部史诗写成12册。1590年印行3本,1596年印行另外3本,自此以后即无进展。即使如此,《仙后》比《伊利亚特》长两倍、比《失乐园》长3倍。每册是一个寓言故事——谈到神圣、戒酒、贞操、友谊、正义、礼仪,全书旨在通过既有的范例的教训,“剖画一个有德行有纪律的绅士或高贵的人”。这就与西德尼把诗当作通过想象的范例表现道德的观念完全相符了。因为非常注意礼仪,斯宾塞的著作很少谈到肉欲享受的问题。有一次他偶然目及“雪白的胸脯,袒露着等待糟蹋”,他却高傲地走过,置之不理。通过6篇诗,他高唱骑士爱情的高调,即是对美丽妇人的无私的服务。
对我们这些忘了骑士精神、讨厌骑士和惑于寓言故事的人来说,《仙后》最初读起来觉得清新可喜,却因太长而无法竟篇。书中的政论被该时代人所喜欢或厌恶,对于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书中轻描淡写的神学之战对于我们而言不能引起震动,其故事至多是对维吉尔、阿里奥斯托及塔索等人的模仿而已。在人为的奇想、笨拙的倒置法、虚伪的仿古和求新及未受阿里奥斯托微笑影响的罗曼蒂克夸张方面,世界文学史上找不到超过美丽的《仙后》的诗篇。约翰·济慈(John Keats)和雪莱(Percy Shelly)喜欢斯宾塞,尊他为“诗人中的诗人”(The Poet's Poet)。为何?是不是因为其形式上某种美感可以弥补中古的荒诞不经,还是某种绮丽的文笔可以美化其中的失真?斯宾塞的新九行诗是一种麻烦的体例。斯宾塞的诗虽极圆融,如行云流水,而常使我们感到讶异,但是有多少次他竟为了韵律而牺牲内容!
他曾经中断《仙后》的写作,改写一些短诗,也许那才是他成名的主因。其《小爱人》(Amoretti)十四行诗(1594年)也许是彼特拉克派的奇想,或是其长年追求伊丽莎白·波丽(Elizabeth Boyle)的反映。他于1594年娶了她,在其最佳的诗作《结婚曲》(Epithamium)中咏颂其结婚的快乐。他毫不自私地让我们分享她的魅力:
告诉我,商人的女儿,以前你曾否见过
如此漂亮的女人,在你们的镇上,
如此甜美、可人,温柔似她,
美貌兼备德行,便益增风采。
她善良的眼睛似青玉般明亮,
前额似象牙般白净,
她的双颊像太阳晒红的苹果,
嘴唇似樱桃般诱人欲尝,
她的胸脯像碗明净的乳酪,
乳头就像含苞待放的百合,
她的雪颈似大理石般光洁,
而她的胴体就像一座美丽的宫殿……
婚礼和欢宴过后,他敦请客人立即离开:
现在该停止了,少女们,欢乐已经过去,
你们整日的欢乐已经足够,
现在白昼已逝,夜晚也近尾声。
如今该将新娘送到新郎怀中……
她躺在床上;
躺在百合和紫罗兰的旁边,
丝帘低垂,
香气迷人的花帷床单和棉被……
但愿此夜只有沉静寂然,
没有暴风或伤心的争吵,
别像耶夫与美丽的艾尔可梅娜躺在一起……
让少女与少年停止歌唱,
不让森林回答他们,也不让他们的回声响过天空。
还有女孩完成终身大事比这更富情调吗?
斯宾塞这些奔放的感情,尽情表现于《四首赞美诗》(Four Hymns)中,尊重人间的爱、人间的美、天上的爱及天上的美,仿自柏拉图、费西诺及卡斯底里欧内,开济慈的《恩底弥翁》(Endymion)一诗的先河。他忏悔作了“许多首色情短诗”,而愿通过可爱的胴体,使其灵魂找到超俗的美,那是程度不同的隐藏于人间诸物之中的。
爱尔兰人的痛苦遭遇不啻一座活火山,斯宾塞住在那可以说每天都接近死亡边缘。就在怨恨积成的火山再次爆发之前,他写了一篇好散文(因为只有诗人才写得出好的散文)《爱尔兰现状之我见》(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主张英国方面适当增加经费和军队,以期完全征服爱尔兰。1598年10月,曼斯特失地的爱尔兰人如火如荼地起来抗暴,驱逐英国殖民者,并烧毁基尔科曼城堡。斯宾塞夫妇在千钧一发中死里逃生,逃回英国。3月后,其财产和热情均已消耗殆尽,诗人终于魂归道山(1599年)。不久注定随其逝世的埃塞克斯爵士为他收埋礼葬,贵族和诗人列队送他出殡,并在威斯敏斯特的墓上献花和致挽词。
现在整个英国竞相写作十四行诗,一时成为风尚,足与戏剧相比——形式上大体颇为精良,只是主题与用词多是陈旧套语;均致少女或其赞助人,并惋惜她们的过分拘谨,劝请她们在美丽褪色之前要善加利用;有时候新颖的旋律闯入心扉,男人答应其情妇在迅急的结合当中给予小孩以为报酬。每位诗人找到一位劳拉——或丹尼尔笔下的迪莉娅,托马斯·洛吉笔下的菲利普斯,康斯特布尔笔下的黛安娜,富尔克·格雷维尔笔下的卡利尔。当中最著名的十四行诗人是塞缪尔·丹尼尔,本·琼森虽是粗野工人,然非“未成熟之人”,称之为“诚实的人,惜非诗人”。米歇尔·杜雷顿(Michael Drayton)的《珀伽索斯集》(Pegasus)具有散文式的诗脚,在各种诗型中特立独行,其中一首十四行诗却有清新的旋律,通过向情妇道别,激使她不再小气——“因为已无他法可想了,过来,让我们吻别吧!”
总而言之,除了戏剧外,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较法国落后一个世代之久。散文极有活力、易变,常常纠缠混乱,屡有冗词,多幻想,有时却有高贵的风格和感人至深的韵律,只是未产生像拉伯雷或蒙田这类文学家。在诗歌方面,除了《结婚曲》和《仙后》外,均胆怯地模仿外国的作品。斯宾塞在欧陆从未拥有读者,但龙沙(Ronsard)在英国也未得到读者拥护。诗可以解释语言,我们可以感到其中有一种一般言语听不到的音乐在跃动。民谣较之宫廷诗歌更易获得一般百姓的注意与喜好,它们贴在酒家或酒店的墙上,街头巷尾均有人高唱和出售,兰德尔(Randall)爵士诗集中的挽歌至今使我们感动。也许受了这些民间流行诗歌的影响,而不是受了十四行诗诗人的高明技巧的感化,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才懂得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
戏剧舞台
英国文学在乔叟与斯宾塞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干旱期,为何一朝之间竟出现了莎士比亚呢?因为财富的增加,因为长期有利的和平时期,及刺激人心、终获胜利的战争,因为外国文学和出外旅行扩大了英国人的眼界。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教给英国人喜剧的艺术,塞涅卡则教以悲剧的技巧。意大利演员曾在英国公演(1577年起)。英国人曾经作了1000次的演出实验。1592年至1642年,英国共有435出喜剧上演。闹剧和幕间插剧演变成喜剧,由于一度神圣的神话如今失去了信仰根据,神秘剧和伦理剧转为世俗的悲剧取代。1553年,尼古拉斯·尤达尔(Nicholas Udall)创作《拉尔夫·劳埃斯特·道埃斯特》(Ralph Roister Doister),这是英国第一部古典喜剧。1561年,中寺法学院的律师演出《戈布达克》(Gorboduc)一剧,这是英国第一部古典悲剧。
有一段时间,传自罗马的形式似乎注定成为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典型。大学学者如哈维、律师兼诗人如乔治·加斯科因(George Gascoyne)、古典学派人如西德尼,都主张遵守戏剧三一论(The Three Unities in a Play):剧中只能有一种行动或情节,情节只能发生于一个地方,发生的时间最长以一天为限。就我们所知,三一论首由洛多维科·卡斯特尔韦特罗(Lodovico Castelvetro,1570年)于一篇《亚里士多德〈诗论〉的评论》中力倡。亚里士多德本人仅主张情节的统一:情节应在“太阳单一旋转的范围内”,但他又增加了另一种可以称为“语调统一”的主张——喜剧是“低级人民的象征”,就不应与“代表英雄行动”的悲剧混在一剧中。西德尼在《诗之辩护》一文中,采纳卡斯特尔韦特罗的戏剧三一理论,并有力而富于幽默地将之应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且要强售其强制性的地理学:
亚洲是一边,非洲又是另一边,另外又有许多地方归属不同的王国统治,一个剧作家处身其中,首应说明他站在哪一边……现在他们是更为自由了,因为两名王亲恋爱变成常事,经过许多接触她就有了孩子,那是个很漂亮的男孩,他……又成长为壮男,又坠入情网,又会生小孩,而这些只是两个小时中的事而已。
法国采纳古典主义,并产生拉辛(Racine)这位大作家;英国却屏弃古典主义,其悲剧表现了浪漫的自由和自然主义的色彩,因而产生了莎士比亚。法国文艺复兴的理想是秩序、理性、均衡、仪礼;英国则是自由、意志、幽默、生命。伊丽莎白时代的听众,包括了贵族、中产阶级、低级人士等,兴趣广泛并经常变换口味,他们需要的是行动,而非隐藏行动的冗长报告;他们喜欢大笑,根本不在乎掘墓工人与王子在一起讨论哲学;他们有一种奔放的想象力,在一种符号的召唤或在一行字的暗示下,曾由此处跳跃至另一处,甚而跃过了整个大陆。伊丽莎白的戏剧表现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不是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语或波旁王室的法语,因而那是一种自然的艺术,反之学自外国的艺术即无英语根基可言。
英国的戏剧发展至马洛和莎士比亚戏剧之前,必须先打另一场硬战。初期的清教徒运动拒斥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舞台,视之为异教、猥亵及渎神的大本营。它谴责听众有妇女和妓女在内,并攻击妓院靠近戏院旁边。1577年,约翰·诺思布鲁克(John Northbrooke)撰文强烈谴责“赌博、跳舞、戏剧和插剧”,他写道:
我确信除了戏剧与戏院外,撒旦找不到更快的方式和更适当的学校,以满足教人放纵其欲望,及驱使男男女女陷入性欲和邪恶卖娼的淫欲罗网内。因此,政府有必要比照青楼妓院,禁止并解散那些场所和演员。
戈森的《恶行学校》较为温和,承认某种戏剧和演员可以“不加谴责”,但答复他时,戈森立即又放弃原有的立场。在《演员五错》(Players Confuted in Five Actions)中,他竟将戏剧描写成“邪恶行为、暴动及通奸的粮食”,演员则是“邪恶的主人,教人放纵的老师”。批评者从喜剧中看到的是邪恶和流氓行为的写照,从悲剧中看到的是刺激谋杀、阴谋和反叛的各类例子。伊丽莎白即位初期,星期天通常是演戏的日子。戏剧开始是以吹号通知的,犹如教堂钟声召唤人们参加下午祈祷一样。教士难过地发现其会众逃避礼拜,拥挤到戏院去了。一位传道士问道:“一出肮脏的戏剧,在号角的吹动下,立可召集1000人,不是远较1小时的钟声召集100人来参与布道会快得多吗?”而诺思布鲁克更强调:“假如你想学……骗自己的丈夫,或丈夫骗妻子,怎样当妓女……怎样拍马屁,说谎……谋杀……渎神……唱色情歌曲……难道在这类插剧中你还学不会怎样付之实行吗?”
戏剧家写了许多小册子反击,并在戏剧中取笑清教徒,如马尔沃里奥(Malvolio)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即是。剧中托比·贝尔奇(Toby Belch)爵士问小丑道:“你难道不知道,因为你自负的德行,这世界就要没有饼和酒了吗?”小丑答道:“是的,依照圣安妮的意思,姜汁酒也会烫嘴哩!”剧作家,甚至莎士比亚亦然,继续在剧中加上暴力、强奸、乱伦、通奸和卖娼。莎士比亚《伯里克利》(Pericles)剧中的一幕,妓院老板抱怨他的人“断断续续地行动,差不多已经腐化了”。
伦敦市政府——某些人是清教徒——认为清教徒的主张较为正确。1574年,市议会禁止上演未经检查许可的戏剧,因而莎士比亚戏剧中有一句“艺术已经政府封了口”。幸亏伊丽莎白及其枢密院喜欢戏剧,有许多贵族与演员来往,因而受到皇家的保护和松弛的检查,才有7家剧团获得许可在城中演出。
1576年以前,戏剧主要是在旅舍庭院中临时搭台上演的。1576年,詹姆士·伯比奇(James Burbage)建造了英国第一家永久剧院,它仅简单地称为剧院。为免受伦敦地方官吏的管辖,它正好坐落在该城之外肖雷迪奇(Shoreditch)郊区内。不久,别的剧院也兴起了:帘幕戏院(The curtain,约1577年)、皮影戏(Blackfriars)剧院、好运剧院(Fortune,1599年)等。1599年,伯比奇的儿子理查和卡思伯特拆毁其父的剧院,改在索思沃克建立著名的球形(Globe)剧院,正好在泰晤士河的另一边。外面是八角形,内部可能是圆形。因此,莎士比亚称之为“这座木头圆屋”(this wooden O)。1623年以前,伦敦的剧院都是木制的,多数是角形剧场,内部数重环形楼座可以容纳2000名观众,并容许另外1000名站在舞台周围空地观看。这些就是低级观众,哈姆雷特斥责他们的“愚蠢的行为和喧闹”。1599年,立位的价格是1便士,楼座价格为2至3便士,在舞台上的座位稍为贵些。舞台是一座宽敞的高台,自一壁延伸至院子中心;后面是更衣室,在那里演员换上戏服,舞台管理人则操纵剧院的道具,包括墓碑、头骨、黄杨树、玫瑰丛、珠宝箱、窗帘、大锅、梯子、武器、工具、小瓶的血及一些断首;设有机关可以使男神和女神自空中飘然而降,或使鬼和女巫从舞台上飞升而逝;拉一拉绳子就会有雨自空中落下,“双层带”(Double Girts)会使太阳悬在空中。这些道具可以弥补布景的不足,但公开和未加帘幕的舞台是无法尽速改变布景的,这样情节变换都在观众面前为之,而观众感到自己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观众不是整个景象中微不足道的人物。商人出卖烟草、苹果、硬果和小册子给观众,到了后来,假使我们可以相信清教徒威廉·佩赖恩(William Prynne)的话,商人还售给女人烟斗。有相当多的妇人去看戏,虽然教会宣称男女混杂而坐会引起诱惑,但仍阻挡不了她们。有时候——阶级之间的战争会影响戏剧的进行——低级的观众把残余零食丢向舞台上的花花公子。要了解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我们要谨记那些观众的特征:具有喜欢爱情故事的情绪,想要小丑与国王在一起演出的强烈幽默感,喜欢修辞的浮夸作风,欣赏暴力演出的激情,以及几近三边形的舞台导致剧中人的自言自语和偏向一边的表演。
此时,演员人数多如过江之鲤,每逢佳节,几乎任何城镇都可发现巡回演出的戏子,在城中广场、酒店院落、马房、大厦或在教堂落成仪式中演出戏剧。莎士比亚时代尚无女演员,只有由男孩来扮演女人的角色。贵族化的公学中,学生排演戏剧被当作训练的一部分。这些青年演员剧团与成人剧团竞争,在私人剧院上演戏剧并争取观众。莎士比亚对这种竞争颇有意见,1626年以后这类竞争才告消失。
为避免被视为浪人,这些成人演员在富有的贵族的照顾和保护下组成剧团——这些贵族有莱斯特、塞瑟克斯、沃里克、牛津、埃塞克斯。海军大臣有一剧团,张伯伦爵士也有一剧团。演员在贵族家里演出时,才由其宠主供养,此外他们必须依靠剧团的分红为生。红利不是公平分享,经理取得1/3,主要演员又取去其余大部分。最著名的明星理查德·伯比奇每年收入为300镑,其对手爱德华·艾伦(Edward Allen)竟出资创建伦敦的戴维克学院(Dulwich College)。舞台名角受到公众的崇拜,并拥有很多情妇。约翰·麦宁汉在1602年3月的日记中记下一段有名的故事:
有一次,伯比奇演出《理查三世》一剧时,有一位市民因为太喜欢他了,在离开剧院之前,约他当天晚上以理查三世的名义与她幽会。莎士比亚偷听了这件事,就先去她家,在伯比奇到达以前照约行事,很受她的款待。然后,门房消息到来,称理查三世已到达,莎士比亚即叫人告诉他,威廉大帝在理查三世之前,即已捷足先登了。
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
剧作家不如演员混得那样得意,他们把全部剧作以4至8镑的价格售给剧团,他们对原稿未保留任何权利,而且通常剧团不准将剧作出版,以免被敌对剧团窃用。有时候一位速记人员在戏剧演出中,会把全剧记录下来,印刷商即据此记录盗印篡改版本,作者除了会得高血压外什么也得不到。这类版本并不会永远冠上作者的名字,因而某些剧本,如《法弗舍姆的阿尔丁》(Arden of Faversham,1592年)之类,历经数世纪始终佚其作者之名。
1590年以后,英国舞台上演了许多相当重要的戏剧,一时显得生气蓬勃,虽然当时只有少数戏剧演出达一天以上。李利在喜剧中加上可爱的抒情诗,其剧中可爱的小精灵的魅力为后来《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开道。格林的《僧侣培根和邦吉》(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1589年)是关于奇异魔术的故事,可能受到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影响。托马斯·吉德的《西班牙悲剧》(Spanish Tragedy,约1589年)谈到杀人的血腥故事,终场几无活人。该剧的成功鼓励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竟与将军和医生一比流血多少。就像《哈姆雷特》一样,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复仇者和戏中戏(A Play within a Play)。
马洛只比莎士比亚早两个月受洗。因他是坎特伯雷鞋匠之子,若不是大主教巴尔克给他奖学金,他可能无法上大学。在大学期间,被沃尔辛厄姆聘为间谍,探查反对女王的阴谋。他研究古典作品,使其神学主张一直不曾落实,他熟习马基雅维利思想,则使其怀疑主义转为讽世。在取得硕士学位移居伦敦后,他与托马斯·吉德共居一室,参加雷利的自由思想集团。政府密探理查·巴尼斯(Richard Barnes)向女王报告(1593年6月3日),说马洛曾经宣称:“宗教的开始是要使人们恐惧……基督是私生子……假如有什么好宗教的话,那么只有天主教了,因为该教事神而多礼……新教徒均是假道学的蠢货……《新约》的内容不干不净。”巴尼斯又说:“这位马洛……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劝人相信无神论,要他们别怕精灵鬼怪,完全轻蔑上帝及其使徒。”更严重的是,巴尼斯(1594年因为犯了“不名誉”的罪行被绞)强调马洛卫护同性恋一事。格林临终诉请其朋友改邪归正时,将马洛描写成从事渎神和无神论者。而托马斯·吉德于1593年5月12日被捕时也承认(受到刑讯)马洛“无宗教观念,纵酒无度,残忍”,惯于“冒渎圣经”、“讥嘲祈祷”。
远在这些报告送达政府以前,马洛就已经写作并上演雷霆万钧的戏剧,剧中暗示其不信仰上帝。显然,《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是在大学时写的,完成于毕业之年,其中的高超知识、美及力量都显示诗人的浮士德脾气:
我们的灵魂,它的能力足可理解,
世界上伟大的建筑,及
测量每个行星的轨道,
至今仍在追求无限的知识,
永远无止无息地向前迈进,
让我们尽情善用我才,永远自强不息
直到我们最成熟的果实终于丰收。
关于帖木耳(Timur)的两出剧都很粗糙而且不够成熟,造型太简单化了——每一个人一种个性。帖木耳大帝本来应以其权力自傲,可是实际表现的这种傲气却不是胜利帝王沉静自若的自信,而是大学生充满未消化的新奇感的那种自负。故事中血流成河,不时发生各类不太可能的事件。其风格似乎显得太过夸张。然而,这部戏剧为什么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上大获成功呢?或许是它表现暴力、流血和夸张,但是,我们相信也是为了它的表现异端与雄辩。这里面包含比伊丽莎白时代任何戏剧更大胆的思想、更深刻的偶像、转折更适当的语句。里面有许多为本·琼森赞扬的“有力诗篇”,还有精致优美的文句,斯温伯恩(Swinburne)推许为同类作品的杰作。
马洛受到喝彩的鼓励,尽其精力写下其最伟大的戏剧《浮士德博士》。中古伦理学也许已知“知识的快乐是一种苦中作乐”,及“智慧越高悲伤越多”,因此将过分的求知欲视为大罪。但中古人类的热切抵拒这类禁忌,甚至诉之魔术和撒旦以追求自然奥秘和大能。马洛剧中的浮士德是维滕贝格著名的博学医生,他忧虑其知识有限,梦想魔术会使他成为全能:
在寂静的两极之间移动的万物
将听从我的指挥……
我可使精灵替我带来我喜欢的东西,
替我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并从事危险的工作;
我要驱使他们去印度寻金,
在大洋中搜寻东方的珍珠,
并搜遍新世界的每个角落,
找寻异果和珍馐;
我要驱使他们为我念哲学,
告诉我外国帝王的秘密。
在其吁请下,靡菲斯特出现了,答应若他肯把灵魂售给卢西弗(Lucifer),就可给他24年年限的快乐与权力。浮士德同意了,并从伤腕中取血签立契约。他第一件要求是与德国最漂亮的少女结婚,“因为我极放纵好色”。但是靡菲斯特劝他别做结婚打算,反要他选择一群妓女。浮士德向他要特洛伊的海伦,果然她来了,他为之狂喜不已:
这就是引来千艘战舰出征的红颜,
焚毁高耸的特洛伊城堡的人吗?
甜蜜的海伦呀!给我一吻永生……
哦!你比夜晚的天空还要美丽
群星的美尽集于你的一身……
最后一场戏特别有力:他绝望地诉之上帝,求其慈悲永远的处罚——“让浮士德在地狱中度过1000年,10万年,最后才获救吧!”——在午夜的闪击、黑云密布及怒吼中,浮士德就此消失了。合唱团唱出其墓志铭,也唱出了马洛的墓志铭:
可以长得挺直的树干今已断矣,
阿波罗的桂枝如今付之一炬。
在这几幕剧中,马洛可能已经清算了他自己对知识、美及权力的热情。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悲剧净化作用清算作者之处多、读者之处少。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约1589年)一剧中,其权力意愿表现为贪财的形式,并在序曲中由一位“马基雅维利信徒”强为辩解:
恨我最深的人就是羡慕我的人。
虽然有人公开抨击我的书,
但他们都会阅读,为了取得
彼得的宝座;而他们把我丢开时,
已经中了我攀升的花毒。
我把宗教看作小孩的玩具,
相信除了无知以外世上没有罪恶。
贷款人巴拉巴斯(Barabas)代表了另一种特性,即他的贪婪使他怨恨任何阻碍他得利之人,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讽刺罪恶:
我在佛罗伦萨学会吻我的手,
他们叫我是狗,我只是双肩一耸,
像赤脚和尚一样低肩垂首,
希望看到他们在厩房中忍受饥饿。
注视着他的珠宝,他面对“有这样无限财富的一个小房间”而感到战栗不已。他女儿取回他失去的钱袋,他以凡是无情高利贷放款人都会有的感情冲动,高声叫道:“哦!我的好女儿,我的黄金,我的财富,我的幸福!”这剧中有一种力量,几近狂暴,一种尖锐的描述和强有力的文辞,使马洛不时可以进逼莎士比亚而无愧色。
在《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1592年)一剧中,他更接近莎翁。这位加冕不久的年轻国王,邀请其“希腊朋友”格夫斯顿(Gaveston)来宫,并赐予他官职和财富,受忽视的贵族逐走爱德华。他退而研修哲学,呼唤其仅存的同志说:
来吧,斯宾塞,来吧,巴德克,与我同坐。
现在我们探讨那个哲学,
在我们驰名的艺术养成所中
可以沉浸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海中。
从这出结构严谨的戏剧中,从敏感、富于想象及威力万钧的诗篇中,从各种不同但一贯刻画的角色中,因具有年轻人的单纯和善意而值得原谅的这位国王中,可以看出这幕剧与一年后的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一剧,已十分相近。
假如他已成熟,这位27岁的青年剧作家会有怎样的成就?在那个年纪,莎士比亚只写了一些无价值的戏剧,如《徒劳的爱》、《维罗纳二位绅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及《错误的笑剧》(A Comedy of Errors)。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中,马洛学会使每一幕剧都有井然有序的剧情。在《爱德华二世》中,他学会使角色不只包含一种个性。在一年或两年内,他可能清除剧中的过分夸张和通俗,他可能达到更广博的哲学水准,更能同情人类相信神话与其弱点。他的缺点是缺少幽默感。在其戏剧中缺少开心的大笑,偶有喜剧也不像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样,可以在悲剧中表现应有的功能——在听众被引进更大的悲剧之前,松弛紧张的神经。他会欣赏女人的胴体美,但不知欣赏其温柔、关怀和优雅。在他的剧中没有生动的女性角色,即使在尚未完成的《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 Queen of Carthage)中,也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其诗篇。有时剧中的演说家会压倒诗人,滔滔不绝地作“一个伟大和雷霆万钧的演说”。但在许多幕戏中,都流动着富有生动想象和情调的诗句,致使人们误以为这些诗句是莎士比亚幻想的清流。马洛的无韵诗已经被证明是英国戏剧的推动力,有时固然甚为单调,但通常韵节鲜明而富于变化,极为自然。
他自己的“悲剧史”,现在突告落幕。1593年5月30日,3名政府密探,英格拉姆·佛瑞哲(Ingram Frizer)、尼古拉斯·史凯利(Nicholas Skeres)、罗伯特·布雷(Robert Poley)与诗人一起——也许他仍是间谍——在伦敦数英里外的戴佛(Deptford)酒店中吃饭。根据验尸官威廉·丹比(William Danby)的报告,佛瑞哲与马洛相骂,原因是他们对支付饭钱,“无法取得协议”。马洛从佛瑞哲皮带上取下小刀,刺他一刀,伤口很小并无大碍。佛瑞哲反抓住马洛的手,把武器对着他,“然后当场给马洛右眼致命的一击,伤痕深达两寸……马洛立告死亡”,刀叶插入脑中。佛瑞哲被捕,辩称自卫杀人,一个月后即获释放。马洛于6月1日葬于今已不知其名的墓中,死时只有29岁。
除了《迦太基女王狄多》一剧外,他还留下两个优秀的作品。《海洛与利安德》是浪漫派作品,采用英雄双行体,表现的是穆塞俄斯述说的、5世纪一位青年为了守约游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故事。《热情牧羊人致其爱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是伊丽莎白时代伟大的情诗之一。莎士比亚在《温莎的欢乐夫人》(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第3章第1节中,使伊凡爵士(Hugh Evans)吟出该诗的片断,并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第4章第5节中亲切地加以引述,表达他对马洛相当的感激:
死亡的牧羊人,如今我才发现你力量的所在,
谁会去爱第一眼看去就不顺眼的人呢?
在这样短暂的生命中,马洛的贡献相当大。他使无韵诗(Blank Verse)成为易作且有力的辞章,他使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免受古典主义者和清教徒的影响,他使思想剧和英国历史剧有了确定的形式。他影响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和《理查二世》的情诗,及其夸张的遣词倾向。通过马洛、吉德、洛吉、格林和皮尔,窍门已经开了,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形式、结构、风格、材料都已确定了。莎士比亚的产生不是一种奇迹,而是集前人之大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