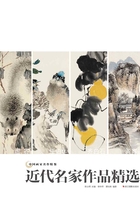
我以丹青书丹心
——虚谷、任伯年、齐白石、黄宾虹艺术赏析
歌行
在中国近现代繁星满布的艺术天空里,有四颗璀璨的明星在其中散发出尤为夺目的光辉——虚谷、任伯年、齐白石和黄宾虹(按出生年份先后排序),即使在动荡变革的时代大环境之下,他们仍坚持以杰出的艺术禀赋、经久的艺术锤炼、高蹈的艺术追求和独特的艺术创见,丰富了中国画的内涵,扩展了中国艺术的外延。
虚谷:一拳打破去来今
虚谷曾是清廷一将官,因不愿奉命攻打太平天国而出家为僧,“意有感触,遂披缁入山”,但他“不茹素,不礼佛”,也“从不卓锡僧寺”,唯以书画自娱。
虚谷寓居上海城西关帝庙,与任伯年、胡公寿过从甚密,且多有合作。任伯年对虚谷的人品、画艺极为推崇,尊称后者为“道兄我师”,伯年为虚谷摹过像,也题过字。
同样,虚谷对任伯年出众的艺术才华也十分钦佩。1887年,虚谷为任伯年作《山阴草堂图卷》,“山阴草堂”乃任伯年之画室住所,此画蕴含对山阴草堂“有仙则名”的褒扬之意。虚谷还为任伯年所画《高邕之像》轴作长款题跋。
两人在人物画上时有合作,如虚谷画《月楼小像轴》(1878)、《高邕之像轴》(已佚),均由任伯年“补景”。
在当时繁华开放的大都会上海,虚谷与胡公寿、任伯年、高邕之、蒲华、吴昌硕、张熊、王礼等人之间志同道合、英雄相惜,兼得商贾士绅的鼎力支持,形成了“海上画派”欣欣向荣、兼收并蓄的生动画面。
在诸位海上画家中,虚谷以其冷逸清雅、虚静隽永的风格独树一帜。
这种冷逸与奇峭,与虚谷的用笔有一定关系。书画界一般以中锋用笔为常规,而虚谷却独独青睐用“断笔”“战笔”。“断笔”,顾名可思义,而“战笔”是指行笔缓慢而中指略微抖动的笔法,这种对中锋、侧锋、逆锋的交替使用,令线条断续顿挫,而气韵不断。画面中产生毛、涩、苍浑的线条,可谓草草写意,生动超逸,于笔墨间呈现出一种拙味,一种禅意。
在用色上,虚谷大胆突破了传统的“随类赋彩”模式,敷色淡雅,清润和谐。他善于在色纸古今笺上使用白粉,使笔下的白色荷花、仙鹤羽毛、粉绿兰花等显得栩栩如生。虚谷画桃,不画“三千年结实”透熟的寿桃,却采用冷色调勾画青涩、硬实的桃。桃叶则以侧锋横笔写就,造型交代自由、简练,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增添了作品的冷隽、沉静之感。
虚谷的画章法独特,经营位置巧妙。画山水——荒寒而简远,平淡而萧疏,能在尺幅之间收尽千里之景;画花鸟——不拘陈规,取势大胆,小中见大,意趣非凡;画人物——惜墨如金,大片空白,意境空灵,立体感十足。

虚谷·松鼠红叶

虚谷·竹林白条鱼

虚谷·湖中风味
立轴《兰花》,兰花兰叶取斜势自左向下伸出,上下占据约八分之七的画幅,剩余的空白处画了三朵落花,右边题有跋语“落花水面皆文章”。全画未出现山石和流水,却令观者仿佛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花香,听到了潺潺流动的水声,足见画家的匠心独运。
对飞鸟游鱼、瓜果蔬植的变异处理,是虚谷的一大创造。他笔下的金鱼,眼睛是方的,身体也是方的,这是他“宁方不作圆”的画法,他没画长尾巴,却能表现出金鱼逆流而行的姿态,出人意料而妙趣横生。
论画,可论笔墨、线条、设色、构图等,然虚谷的画中最不能令人忽略的,则是他的性情心境。有一幅画面上是树枝和水中畅快游动的鱼,虚谷在画上题了“水面风波鱼不知”,一语道尽江湖险恶。虚谷历经人间沧桑,满腹隐痛无处诉说,只好寄情翰墨,言有尽而意无穷。
他的作品,多有掩盖不了的冷寂孤独感。《松鹤杞菊图》中,修长的松鹤独立孤松下,一脚着地,一脚蜷缩,头颅低垂,目光呆滞,菊花低伏,草丛枯萎,一股萧索、冷清的气息扑面而来。对此,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有意无意地给出了解答:“但愿终生伴此石,何愁迟暮老风尘。茫茫本是知音少,自赏孤芳自写真。”知音本就难觅,孤芳自赏又如何?
虚谷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对生活的探索和感悟是艺术发展的源泉,他笔下的一枝一叶、花木禽鱼,无不给人清新的形式美,这是画家师法传统和师法造化的造诣所在。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与其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密不可分。他在一幅画竹图中提到,“其本清虚,其性刚直”,这正是他艺术生涯的总结,也是其人格的真实写照。
任伯年:笔无常法,别出新机
与虚谷一样,任伯年亦是“海上画派”的佼佼者。
伯年居沪上,间接、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艺术、思想的影响。对此,沈之瑜在《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中写道:“任伯年有一个朋友刘德斋,是上海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土山湾所办图画馆的主任,两人来往密切。刘德斋的西洋画素描基础很厚,对任伯年的写生素养有一定影响。任伯年每当外出,必备一手折,见有可取之景物,即以铅笔勾录。这种铅笔速写的方法、习惯,与同刘德斋的交往不无关系。”
少时,任伯年已显示出过人的默记、造型能力,至此,又与西方科学的写生方法相结合,在创作人物肖像时,更加得心应手。
其人物肖像画重视“神”的表现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在平时与人交往时,留心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神态表情,下笔即一气呵成,栩栩如生,形神兼备。
《玩鸟人》画面中,留着长辫子、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一手执鹅毛扇,一手斜托鸟笼,任伯年在扇柄上端用石绿点染出一块明亮的翡翠,巧妙暗示了人物的富有。同时,玩鸟人嘴角略微上扬,眼缝细长,面带笑容,显出商人洋洋自得之状。他没有勾画人物的皱纹和骨骼的起伏,正是表现人物的丰腴与富态。这幅画生动反映了当时城市中上层阶级的物质的富裕与精神的空虚,隐含着一丝画家的嘲讽和轻蔑。
在画法上,任伯年开拓了传统的表现技法,以没骨法为基础,舍弃渲染,以线条为主宰,稍加淡墨、淡色或笔皴擦。任伯年在行笔、转笔、入笔处强调粗细、顿挫、节奏等的笔墨变化,而线条则注重简洁、干湿、刚柔、快慢的变化,始终以造型为中心。在色彩运用上,他大胆打破了传统绘画“水墨为上”的理论观念,以色代墨,融西法色彩学于中国画中,明暗对比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取向,既符合生活真实,又略作艺术夸张,有时还像泼墨一样运用泼彩。在构图上,任伯年往往匠心独运,不步前人,“煞费构思,及捉笔,则疾如风雨”。他善于将人物放在典型环境中进行刻画,以景托人,人景呼应。
《松荫高士图》,松树和石坡占据了大部分画面,而高士却仅有一小点,但人们观画,第一眼还是被高士所吸引,这是任伯年在构图上运用了焦点透视和躲藏的关系,同时,人物的服饰色彩也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种不拘传统、别出心裁的构图方式,带给人全新的审美体验。

任伯年·苏武牧羊
任伯年也大大扩展了人物画的题材范围,上至历史神话人物,下至民间贩夫走卒,皆可入画。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作品被人诟病为“俗”。其实,格调高低,不仅仅在于题材,更在于是否有画家独立的创作思想。
任伯年早年以画人物为主,到了艺术成熟期,花鸟画远比人物画多。

任伯年·哺育小鸟·花鸟册八开之一
任伯年的花鸟画,笔墨流畅,色彩明丽,水色交融。如画紫藤,任意由淡紫色水、色、粉浓淡交融,层次却非常清晰,无拖泥带水之处。任伯年作花鸟画,落笔极快,用色如墨,笔笔到位,不重复涂抹,这种由“工”发展到“写”的写意没骨法,可说是任伯年花鸟画的独特风貌。
任伯年善于将观察人物的方法延伸到花鸟画摹写中,结合西方的写生法与中国的默记法,将西方的色彩学与中国传统的赋彩法融合起来。他虽继承传统,但在艺术技巧、造型语言、笔墨技法等方面,更受到近代社会人们审美取向的影响,加上对西方绘画精神的融会贯通,无疑令任伯年的花鸟画较之前人有更大进步。
任伯年的山水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不及他的人物画和花鸟画,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其以卖画为生计,一生中大部分作品应买画者喜好创作,而无太多时间和精力去真山真水中“师法造化”,这无疑是一大缺憾。
在其一生短短的五十六年里,他为世人留下了数以千计的绘画作品,对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画家》杂志认为:“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凡·高相若,在十九世纪为最具创造性的宗师。”
徐悲鸿在《任伯年评传》中将任伯年推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并以“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一句表达对任伯年的艺术成就的推崇与遗憾。
齐白石:胸中山水奇天下

齐白石·葫芦图

齐白石·老当益壮
齐白石书画生涯凡七十载。在其各类作品中,所绘花鸟鱼虫最多最优,成就最高,这一点为世人及业界所公认。二十七岁时,他拜胡沁园为师学工笔花鸟,这是他进入中国画领域的起点,从工笔线描入门绘事,奠定了他之后作画以形写神、以象取意的扎实基础。
梅和菊是齐白石描绘最多的传统花卉题材。他在《红梅》画上题诗:“风神宜雪宜霜,为汝清吟心狂。如此寒香冷艳,我非铁石心肠。”齐白石画梅,不仅因对梅花品格的欣赏,在面对舆论对其画作的批判非难之际,他几乎已将梅视为知己。他在《梅花》画上题款“吾友梅花,知我只有梅花”,在《十二月三十日看梅》诗中又写道:“飞馋说尽群非我,只有梅花辨得清。”联系他当时的境遇,这些诗句表达其确信有能鉴识其作品价值的伯乐存在,历史最终会给出公正的评价。
在齐白石心中,菊花具有圣洁感。他画《白菊》,题诗有“翠云裁作叶,白玉截成花”;画黄、白亮色菊花,题有“黄金填作色,白玉截成花”,将其色其质比作世间最为珍贵的黄金与白玉。
《秋趣图》立轴,以竹架下盛开的墨叶红菊为主体,又自上而下画了低飞的蜻蜓、攀上竹竿的蝉虫、趴在地上的大蟋蟀等,一旁则是养蟋蟀的带盖瓦盆,上面横放一根细细的逗蟀草。作品野趣横生,表现了秋高气爽时节院落内生机盎然的景象。齐白石的作品中常可以看到,花卉果蔬用意笔水墨挥洒而就,虫鸟却画得精细工整,也就带来了全图的“工致气”,这是齐白石花鸟画的技术功力特色,也是他能达到事半功倍艺术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齐白石所绘的花鸟鱼虫作品,描绘对象多样,表现题材丰富,那些为传统文人画家所不屑的对象——白菜、胡萝卜、茄子、香菇、青蛙、蝌蚪、虾、蝉、蚂蚱等,都成了他笔下妙趣横生的新题材。
齐白石的山水画启蒙于他的师父胡沁园之友谭荔生。在学山水画的过程中,齐白石一是学习临摹他推崇的前人佳作,二是实地观察真山真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齐白石的山水画品格简朴,空灵中蕴含着意境和勃勃生气,在情感的浓郁、豁达中袒露纯真又隐含睿智,而山水画画面特有的形制、强烈的黑白对比,不仅显示出笔墨的苍劲老辣,更形成了犷悍的力度感,渗透出富有魅力的形式美。这与清代“四王”传统的密体山水、模式化山水确实拉开了很大距离。
《渔村夕照》一图,画面三分之二为前景河面,以淡墨渴笔写波纹,波纹有远近不一的纵深感;上端三分之一以浓墨粗笔勾画山峦、垂柳、屋宇与渔舟,地面施淡墨,红日施饱和洋红,天际染淡洋红,渲染黄昏氛围,题款画龙点睛:“网干酒罢洗脚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大白话将屋内捕鱼人平凡而充实的日常生活描绘得情趣无穷。
“与众不同,画格很高”,这是陈师曾最早给齐白石山水画的高度评价。
相较而言,人物画在齐白石的绘画创作中次要一些,数量也少。学界普遍认同其人物画,一是重寓意,二是重童趣,前者体现画家世事洞明的睿智,后者则流露出其纯真的本性。
齐白石曾经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道:“作画先阅古人真迹过多,然后脱去前人习气,别造画格。乃前人所不为者,虽没齿无人知,自问无愧也。”对后来模仿者,他亦以“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一语提点。由此可见,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家的个性和创造力,求新求变,不落窠臼,最终成就了他在近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的辉煌。
黄宾虹:泼将水墨见精神
黄宾虹出身于书香门第,六岁时师从陈崇光学花鸟,到晚年高寿仍非常勤奋,锲而不舍。五十岁以前,他驰纵百家,追溯唐宋,反复临摹古人而又一扫前人因袭模仿的风气,其后饱游饫看,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上泰山,又登五岭、雁荡,畅游巴蜀,积累了大量的速写墨稿。他以“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求修养之高,无以言境界”自勉,积贮丘壑,开阔胸怀。

黄宾虹·雁宕三折瀑
七十岁后融会贯通,卓然成一代名家。八十岁以后,黄宾虹所画的山川气势磅礴,水墨淋漓,浑厚华滋,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他的山水画成就达到了最高峰。
笔法是中国画线条艺术的精髓,黄宾虹讲求中锋用笔,“用笔之法,书画同源”。他重视收笔回转,勾的线条顺笔为之,勒的线条逆笔为之。锋宜藏不宜露,更不能在画中露出气力。线条起讫要明确,意到笔到。一勾一勒,除了画出地貌山岗外形,还要写出山川气势。

黄宾虹·春满湖山
关于用笔,黄宾虹有五字诀,他说:“用笔宜于平、留、圆、重、变五字用功,能平而后能圆,能重而后能留,能平、留、圆、重,而后能变。”“平”是如锥画沙,“留”是如屋漏痕,“圆”是如折钗股,“重”是如高山坠石,“变”是运笔要左右回顾,上下呼应,按照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平、留、圆、重诸法,在变化中寻求画面的统一性。
墨法是中国画水色气韵的灵魂。黄宾虹认为“笔力是气,墨彩是韵”,要使画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关键在于用墨,对此黄宾虹总结了历代画家墨法精华并结合自己一生的艺术探索和实践,归纳出了浓、淡、泼、破、积、焦、宿的“七墨”法。
一墨融万彩之变,水墨的简洁朴素与韵味无限是最契合文人雅士的审美取向的。黄宾虹作画用墨甚多。他晚年的作品常以水运墨,或以水混墨,通常以浓墨、焦墨、宿墨反复施加、点染,最后再用花青、石绿、赭石等色及淡墨反复晕染,其用墨之重古今罕见。他的画乍看之下满纸笔墨,然而细观之下,层次变化非常丰富,使他的山水画整体呈现出一派浑厚华滋的艺术效果,又常于一片黑墨中间留出一点空白,不仅使这片墨色富于变化,而且使整个画面都灵动起来,达到他所言“一点之光通体皆灵”的奇妙作用。
石涛在题画诗中说“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揭示了中国画用墨的本质所在。“五笔七墨”法虽不是黄宾虹首创,却是他首先将这一套方法归纳成了系统理论,在实践中发挥到极致、臻于化境,并为开创中国画笔墨境界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影响深远。
黄宾虹认为作画在意不在貌,不应重外观之美,而应力求内部充实,追求“内美”,他不着力讲求意境,而是以游戏笔墨为尚,曾言“中国绘画舍笔墨无他”,秉持着“山水画乃写自然之性,亦写吾人之心”的创作理念,在重构自然河山的精神指引下,“道与艺合”,手画心迹,将似与不似、不齐之齐的美感发挥到了极致,令人叹为观止。
黄宾虹的山水画近视无物,而远观则甚为真实,达到了既抽象又具象的艺术高度,究其原因,在于其胸次高旷,学识渊博,对画理、画法研究极深,从观察自然山川,到构思、布局、作画,都能辩证地看问题,因此能在画面上制造出很多矛盾,而又使之归于统一。
集古今诸家之大成,在此基础上又有独创的风格,黄宾虹的画品格多变,有的雄浑高古,有的典雅含蓄,有的疏野豪放,有的超逸洗练,但都能归于自然流动,使所画皆妙极而神化,足可雄视百代,照耀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