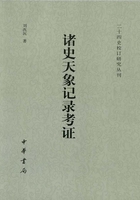
前言
(一)古代天象记录及其校勘
出于迷信占验和科学研究的双重目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天象观测极为重视,在历代官方史书中留下大量系统的实时天象记录。这些天象记录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延续时间之长,堪称世界之最。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历史学、科技史和现代科学研究,例如利用各种天象记录研究夏商周年代(1),利用超新星记录研究恒星演化(2)等等。
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大多有天文志(或天象志、司天考、五行志),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系统地记载当时发生的天象事件。除天文志外,历代本纪中也有不少天象记录。本纪中记录的数量通常远少于天文志,但日食记载相当完整,彗星和“太白昼见”较受重视。此外,历法志中偶有比较详细的日食月食记录,用于检验历法精度;一些天象记录,也被归入五行志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的天象记录,是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主体,此外只有极少量殷商甲骨和先秦文献的早期记录、极少量与“二十四史”同期的文献记录以及明代以后较大量的其他官方记录和地方志记录。
在某些时期,天象记录的篇幅甚至超过记载全国大事的本纪。例如《宋史》神宗熙宁一至十年,本纪共有1.1万字,天文志中这一时期的天象记录就有1.6万字。又如《元史·顺帝纪》,全卷纪事约450条,天象记录就占了40%。可见古人对天象的重视。
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形式简略而公式化,通常包括年号、年、月、干支日、天象,例如《汉书·武帝纪》:“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在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校勘记中,各史对天象记录的处理不同。最仔细的当属《元史》:可以看出,对日干支的存否以及在月中的相对位置作了全面的检验;对志、纪的天象记录作了认真对比(《元史》本纪天象记录特别多,与天文志几乎一一对应);一些相异的记录还利用天文学常识,甚至粗略的计算判断正误。其他大多数史书都对天象记录作了干支检验、他书比对等一定程度的校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出校的标准不一。例如有的仅仅日期干支错就出校(没有别的考证),但同一卷中,别的许多干支错却没有出校。
随着现代天文学、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些天象记录的多数,都可以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加以验算,恢复出“历史的真相”。点校本校勘记中提出的许多疑问,也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能够检验的天象包括日食、月食、月五星列宿掩犯等;不可检验的记录主要有流星陨星、客星、日月晕、太阳黑子等(彗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计算,但历史记录的认证比较困难)。例如《宋史·天文志》共载有日期、现象俱备的天象记录7991条,其中可以计算验证的5661条,不可计算的2330条(3)。两千年来的日、月、行星位置,现代天文计算精度可以达到0.1°左右,满足肉眼观测的极限。但对于早期日食(例如汉代以前),特定地点能否看到全食,还有一定误差。
本书所作计算,是利用自编的计算机程序,作各种可能性的搜索。读者若需检验,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天文计算的商业软件。宁晓玉等比对了多种专业和商业软件,推荐SkyMap作为古代天象记录研究的工具(4)。用天文软件考证古代天象记录,或许会发展成一项大众参与的学术游戏。
利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对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系统检验,始自朱文鑫。他利用Oppolzer的日食典(5)对《春秋》和“二十四史”中的日食记录进行了全面考证(6)。由于计算能力的限制,其考证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值得改进(7)。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天文史界和古籍界投入大量人力,对中国古代天象记录进行了全面整理,尤其是对各地地方志中的天象记录进行了全面搜索,其中部分成果收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8)。日本学者斋藤国治也曾对中国五代以前的天象记录进行了全面检验(9)。
笔者应用现代天文学计算方法对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天文志(天象志、司天考、五行志)和本纪中可以计算的天象记录进行了全面的检验。在错误的记录中,超过半数可以考出其原来面貌。这些错误往往是由于传抄过程中文字的形似、音近,或月份、年份的脱漏造成。这些“可考”的记录及考证结果收于本书。日食在古代受到特别的重视,因此某些年代错误而无考,甚至正确的日食记录(如春秋时期),也收入本书。此外,还包括少量注释条目。
书中每个条目首先列出天象记录的原文,然后是相应检验和考证,最后是简短结论。书中条目的顺序,按照中华书局点校本的页码排列(极少数需要归并的例外)。本书中各节内的分类,多取自原文。但有些原文缺,或多项合并,则是笔者所立。
检验天象记录的第一步,是将原文“年号、年、月、干支日”表达的日期转化为公历年月日和阴历日期。由于干支有60种,每个月只有29天或30天,如果文献流传过程发生日期错误(年、月、干、支中的某个字错),一部分错误的日期就会呈现“该月无该干支”(或称干支不存,或干支错)的情况。如果这样的日期错误是随机发生的,“干支不存”应该占全部日期错误的一半。
本书日历换算主要参考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10)。陈《表》源自宋代刘羲叟(司马光《通鉴目录》)和清代汪曰桢(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的工作,是根据诸史历法志重建的历代日历。在古代碑刻、简牍中,均发现不少陈《表》与实行历不合的例子(11)。笔者在天象记录检验中也发现一些不合的例子(12),在本书中列出。
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绝大多数记有年、月、干支日。极少数干支日脱漏的,只要记录清楚,类型合适,前后记载密集互证,也可以可靠地推算出具体日期。这种情况,本书部分收录。
本书所用公历日期,在圆括号内以阿拉伯数字表达,按国内外史学界的通用方法,1582年10月5日以后为格里历,10月5日以前为儒略历。计算所得的天象时刻,为东8区时,即“北京时间”。
(二)天体、天象及其记录
(1)恒星
恒星距离遥远,看起来它们的相互位置似乎是固定不变的。西方古人按照亮度给恒星分为等级,称为星等。最亮的一批恒星为1等,肉眼可见最暗的6等。按现代精确的定义,每相差1等,亮度相差2.5倍。全天肉眼可见的恒星,大约6000颗。中国传统恒星分为283官1464颗,《晋书·天文志》、《宋史·天文志》有详细的描述。其中的二十八宿(28个星官)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天空位置的参考系,日月行星和其他恒星的位置,以二十八宿距星(每个星官都有一颗标志星,称为距星)为标准来度量。二十八宿形成带状环绕天球,它们依次分为四组,自西向东:
东方苍龙:角(左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斗(南斗)、牛(牵牛)、女(婺女/须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觜觹)、参;
南方朱雀: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
用二十八宿的28颗距星分别连接天球南北极,将全天划分为28个长条区域,就像花皮西瓜的花纹那样,每颗恒星都属于其中一宿。天体的球面位置用“入宿度”和“去极度”来表达,类似于现代天文学中的赤经、赤纬。为了满足太阳日行一度的观念,中国古代定义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这与现代度量的“°”相当接近,在历法计算和仪器(例如浑仪)观测中,使用这种计量单位。在任意方向的角度估计时,“丈、尺、寸”常被用到,尤其在天象记录中。研究显示,一尺相当于一度(13)。
中国古代星官内的具体恒星,缺乏完整的系统命名。除少数恒星如轩辕大星、心前星、房上相外,多数恒星的指示,用东西南北、第一第二来形容,而不是严格的定义。例如南斗的同一颗星,时而是西第三星,时而是东第四星。至于当今用数字表达的中国星名体系(例如轩辕十四、毕宿五等),则是迟至清代才开始应用的。
恒星的视运动具有周日和周年的规律,被古人用来测定季节,观象授时(《礼记·月令》)。由于太阳、月亮和行星只在黄道附近运动,所以黄道带恒星大量出现在月五星掩犯记录中。彗星、流星、客星记录则会参考更多的恒星。中国古代对恒星亮度不够重视,虽然提到大星小星,但没有建立起亮度等级,所关注的恒星也不是由亮及暗。一些似见非见的暗星被特别关注(例如5.4等的鬼西南、6等的天理四星),一些较亮的3等星却从不提及。这与中国传统恒星的星占目的有关。
图1“黄道带星图”,一长条的星图分为6幅。其中的中国星名大量出现在天象记录中。图中所注中国星名,是伊世同根据清初文献整理的(14)。此前的传统星官,有少许不同,例如哭星、积薪、日星等。方框内的星座名称以及星旁的希腊字母,是现代国际通用星名。二十八宿是许多天象记录确定位置的参考。其中一些宿不在黄道星图中,特将它们的方向注在图的边上,以显示该宿的范围。星图所用坐标,为2000历元的黄经黄纬。


图1 黄道带星图。
在恒星中,只有“老人星见”(或称寿星)作为一类天象,被长期系统地记载。作为恒星,它的出现有着很简单的规律。作为“异像”而记载,是由于它靠近南天极,在西安—洛阳—开封—南京一线,它只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出现在南方接近地平线的低空,加之气象干扰,不易见到(在北京,老人星完全看不到;在广东,见到它则是很普通的事)。老人星是各类天象中少有的“吉兆”,历代往往在每年初见时举行祭典。
(2)日月
太阳在黄道上从西向东顺行,每年行一周,日行约1°。月亮也是从西向东顺行,每月行一周,日行约13°,沿黄道附近约5°范围。
月行速,日行迟,每月会合一次,是为朔。如果朔时月亮恰好接近黄道,月面掠过日面,就发生日食。日面直径被遮挡的比例称为食分(例如日面直径被遮挡50%称为食分0.50)。每次日食,各地见食情况(时刻、食分)不同。据笔者统计,全球平均每世纪发生日食238次;其中以北京—西安—南京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核心地区能看到的45次。对于某一地点而言,平均2.56年发生一次日食,230年发生一次日全食(15)。古代日食记录是当代天文学家研究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主要依据,历来备受重视(16)。
月亮行至与太阳相背的位置称为望。如果望时月亮恰好接近黄道,月面进入地球的影子,就发生月食。月面直径被遮挡的比例称为食分。每次月食,各地见到的食分相同,但月亮的天空位置不同,如果月亮还没升出地平,该地就看不到该次月食了。全球平均每世纪发生月食154次,对于某一地点而言,可以看到的超过其中半数。此外,月亮进入地球半影时,发生半影月食。通常认为,半影月食肉眼不可见。
由于星占和科学的双重原因,日食在中国古代受到特别重视。日期确凿、系列完整的日食记录从春秋直至清末(仅战国至秦比较薄弱),而且多记在本纪之中。日食记录大多十分简略,但也偶有详情(17)。明中叶以后的地方志中,出现了日全食在各地的生动记载(18)。
相比之下,月食比较不受重视。尽管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屡有月食记载,但较完整的月食系列记录迟至南北朝才出现,远在其他常见天象之后。
月掩犯行星、恒星,是中国古代数量最多的一类天象记录。除了掩(奄、食)、犯外,偶尔也使用凌、乘、逾等词。据笔者研究,“犯”的定义范围为1°(19)。“掩”的含义本身是清楚的,但由于月亮盘面明亮,暗弱的恒星往往只是被月亮的光芒掩盖。因而在本书的检验中,掩、犯没有严格区分。犯的记录,月面与被犯天体不超过2°者,都算作正确(它们只是不精确,不是错误的)。由于月亮位置计算受地球自转参数的影响,中国古代月掩犯记录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20)。
月晕是气象问题,但多数记录了月晕某星,可以判断正误。这样的记录很粗略,只可判误,不能考正。
中国古代虽然定义子夜为日期分界,但凌晨的观测往往记前半夜的日期(21)。因此,一次月犯某星,不管是所记日期的当天凌晨、当天前半夜还是次日凌晨成立,都属于正确。
(3)行星
古人称恒星为经星,行星为纬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分别称为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或镇星)。从现有文献看不出哪套称谓在先,但在“二十四史”中普遍使用后者。行星在黄道附近运行,通常自西向东,称为顺行。每个行星又都会有时自东向西,称为逆行。从顺行转为逆行,或从逆行转为顺行时,称为“留”,古时称“守”。留的时候,行星运动缓慢。行星的运动和现象与它和太阳的相对位置密切相关,相对于太阳周而复始,称为会合周期。
在地球轨道内侧的水星、金星称为内行星。它们的会合周期分别为116天、584天。在地球上看,内行星(水星、金星)总是在太阳的两侧摇摆。或者傍晚出现在西边天空,称为昏星;或者清晨出现在东边天空,称为晨星;或者离太阳太近而隐没不见,称为伏。内行星与太阳视角距(夹角)最远的时候称为大距,这时最容易看到。金星平均大距46°,又特别明亮,所以它可见时期很长,伏的时期比较短。水星大距18°—28°,又比金星暗,所以水星伏多见少,每年只有几次、每次几天,能在晨曦或昏影中依稀见到。因此在对水星记录的检验中,不但要计算其所掩犯是否正确,而且要特别注意是否在水星可见期(具体界限是日落/日出时地平仰角超过10°)。
在地球轨道外侧的火星、木星、土星称为外行星。它们的会合周期分别为780天、399天和378天。外行星的一个会合周期从“合”开始,这时伏于日光,顺行。此后,行星凌晨出现在东方。继续顺行,距太阳越来越远,直到超过半个天球,由顺行转为逆行(留)。逆行的中点是“冲”,此时行星、地球、太阳成一条线,行星距离地球最近,最明亮,整夜可见。冲后继续逆行,留,转而顺行,再行半个多天球,夕见西方,逐渐被太阳赶上,伏,合日。外行星都容易见到,它们伏的时期不长。
行星动态也是记录数量最多的天象之一。行星掩、犯的定义和月亮一样,但由于行星的圆面实在太小,历史记录的几十次行星掩星,也只能是“光芒相掩”(22)。常见的行星记录还有合、聚、留几种。
现代天文学定义“合”为两个天体(日月行星)运动中,赤经或黄经相等的时刻(这时两者并不一定很接近)。但古代常记录三个或更多行星相合,其含义则是在同一“宿”中(《宋史·天文志》两星相合也是同宿的意思)。这种情况,“聚”用得更多。但四星、五星相聚十分少见,许多记录并不限于同一宿。
“守”,在古代用来表达一个运动天体(行星、彗星)或新出现的天体(新星、超新星)长时间(例如好几天或更久)驻留在某恒星旁边。行星的“守”,就是现代天文学的“留”,本书中常称为“留守”。守的距离要求不像犯那么严,往往相距好几度,甚至只要在该星宿留,就称为守该宿,例如“荧惑守心”(23)。
太白昼见是数量较多的一类天象记录(还有少量岁星昼见),它在本纪中出现较多,可见受到重视。金星或木星能否昼见,实际上反映的是天气(大气透明度)问题。许多记录了太白昼见于某宿,则可以计算检验。这样的记载位置粗略,只可判误,不能考正。
(4)其他天体与天象
彗星的明显特征是模糊的彗头带着尾巴,亮度和尾巴长度不断变化,快速掠过广大的天区,历时几天至几个月。接近太阳时彗星最亮、尾巴最长。彗星的尾巴总是背向太阳。彗星的形象变化多端,因而在古代,根据其形状而有多种名称。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二十多种彗星的图像和名称(24)。历代天象记录中,彗星常被称为彗星、星孛、长星、蚩尤旗,也常被泛称为“客星”,而与新星、超新星混淆。如果记录描述客星移动、有尾或明显模糊,则可以确定为彗星。
精确测定一颗彗星在三个不同时刻的位置,就可以确定它的轨道,从而计算出它过去、将来的位置。有一部分彗星是周期性,可以回归的。这样,就可以计算它许多年前光临地球的时间和位置,与历史记录对比,甚至改进彗星长期运动的理论,哈雷彗星便是著名的例子(25)。但由于大多数彗星不能回归,历史记录难以证认和位置记录粗疏,难以靠计算方法来普遍检验古代彗星记录的正误。
新星和超新星是突然爆发的天体,持续可见的时间从几天到一年以上。这类天体在中国古代的可能记录约有130项(26),常被称为客星、景星、周伯、含誉,甚至星孛。由于此类记录在天体演化研究中起到特殊的作用,备受中外天文学界关注。
流星、流星雨和陨星的古代记录非常多。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志记录了各地不同的流陨事件,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地点的实况。这对于太阳系小天体的研究具有潜力,有待开发。流星、彗星和新星、超新星是现象完全不同的天象,但许多古代记录缺少动态描述,以至难以分辨。
“天变、日变、月变”常常囊括性质完全不同的许多天象。其中太阳黑子记录是研究太阳长期活动规律的有用资料;“白虹贯日”、“日珥”并非现代天文学所称日珥、“日晕”、“日晖气”、“日赤无光”等属于大气现象;夜间发生的“天开裂”、各色云气可能是极光,反映了太阳活动。
以上这些天象记录,都难以用天文计算方法检验。
(三)天象记录错误的常见类型及原因
错误的记录,经过考证往往能发现其原貌,我们称之为“可考”。“可考”记录大约占错误记录的一半。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例子。
(1)字形近似:
《魏书·天象志二》: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乙巳,月犯毕。
十一月无乙巳。十一月十一己巳(491.12.27),月犯毕大星。“乙巳”当为“己巳”。
(2)发音近似:
《宋史·天文志六》:乾道四年十一月戊申,(月)犯荧惑。
十一月无戊申。十一月十一戊辰(1168.12.11),月犯火星。“戊申”当为“戊辰”。
(3)月份错误:
《南齐书·天文志下》:永明二年四月丙申,太白从行犯东井钺星。
四月无丙申。五月廿四丙申(484.7.3),金星顺行犯东井钺星。“四月”当为“五月”。
(4)月份或日期脱漏:
《宋史·天文志八》:景德二年八月丁丑,(荧惑)犯轩辕大星。甲戌,犯左执法。
八月初一丁丑,火星犯轩辕大星不误。但八月无甲戌。九月廿九甲戌(1005.11.3),火星犯左执法。“九月”脱。
(5)误置:
《宋史·天文志八》:乾道二年五月己未,(填星)掩狗国星。
五月十七己未(1166.6.16),土星天象不合。月亮几掩狗国星。史书编纂整理过程中,将月犯列舍误置于填星。
(6)差一日:
《晋书·天文志下》:永和六年六月己丑,月犯昴。
六月二十己丑,天象不合。次日廿一(350.8.10),月犯昴。这种差一天的记录,我们归为“可考”,本书收录百余条。
归纳常见的错例,可以看出几大类错误的原因。
(1)传抄错误。与史书其他内容不同,天象记录的关键词干支和数字,一旦抄错,就难有改正的机会。乙—己、二—三、戌—辰这样的形似,申—辰、丑—酉这样的音似很容易混淆。干支两字中的后一个字,错的可能性很大,笔者在检验天象记录,输入计算机时,也常犯这样的错误。传抄中另一类常见的错误是脱漏。年份、月份脱漏通过计算验证容易确证,尤其是年月下系有多个记录,可以互相支持。日期脱漏,虽然往往能找出适合的日期,但这样的考证比较薄弱,本书中只是部分收录。古籍中的小字注,本不打断原文的时间顺序。传抄中小字变大字,成了正文,原文的时间顺序被扰乱,造成月份辨别不出。这种情况,在《魏书》、《宋史》的天文志中屡见。
(2)编纂错误。天象记录往往存于《实录》之类的编年史中,与其他事件混在一起。编纂《天文志》时,从中摘出。在这类编年史中,年号、年、月,通常只出现一次。当一条记录需要摘出时,与天象记录文字本身接近的只有干支日。月、年、年号都需要向前搜索。这一过程很容易发生错误。最容易发生的错误就是误用前面的月份(尤其是文本中该月月首没有换行)。这样的困难,在我们今天阅读诸史本纪时,同样存在。在《实录》之类的编年史中摘录天象记录,有时甚至向前查索干支日也会错误,这样就会误用前一天,甚至前几天的日期(27)。
由于天文志编者专业知识欠缺,在总结简化改写的过程中可能会表达错误。在明代天文志和实录的对比中屡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将“守”、“入”、“在”写成“犯”)。另一类编纂错误,可能发生在天象记录分类的过程中。
(3)原始错误。还有一些类型的错误,显然并不是编纂和流传过程产生的,我们称之为原始错误。例如掩犯记录,定义在1°之内,2°之内可以算作误差。可是少数“犯”的记录,天体之间的距离达到2°—5°,除了上述改写错误外,也可能是原始记录就这样粗疏。此外,观测者认错星的可能性也有,宋代有几例相当明显。
此外,有少量天象被记在次日或先一日,当属于史官误记。这种记录在唐代、宋代较多,可能与当时天象观测奏报的程序有关,也可能如前文所述摘录时取错日期。
(4)自东汉开始,常有这样一些日食记录,经计算当天确有日食发生,但中国地区不可能看见。这样的记录显然是不精确的计算结果。当时已有常规的日食预报,指导皇帝在日食时举行祭典。由于计算不准,实际上未见到日食,原始文献中会记下“当食不食”、“阴云不见”等等词语,但在编纂史书时往往省略掉了。自宋代以后,月食记录也出现类似情况。这种记录作为一类“可考错误”收入本书。
一些迹象显示,最原始的记载可能使用日序纪日(例如初一、十五),行星名称可能也是金、木、水、火、土,编纂史书时才统一改为干支纪日和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填星。这可以解释某些传抄错误发生的原因。例如辰星误为荧惑,字形并不相似,但它可能原本是从水星误为火星,字形相似。又如“十二”、“十三”字形相似,相邻的干支字形就不相似了。
《明史·天文志》的天象记录很可能直接摘自《明实录》。天文志的错误记录,大多可在实录中找到正确的原文。对比两者,对于理解天象记录错误的发生过程,很有启发。
应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后,天象记录中发现的问题成几十倍地增长。除了可以考证复原的天象记录集中于本书以外,发现的多数问题不可能显示。本书附录特以《魏书·天象志》三、四这两卷为例,对此问题加以说明。
笔者在对各代天象记录进行全面考证的同时,也对其类型、特征、数量、分布等做了统计分析,撰写并先后发表了《南北朝日月食记录》(《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3期)、《南北朝天象记录的统计分析》(同上,2013年第5期)、《隋唐五代日月食记录》(《时间频率学报》2013年第2期)、《隋唐五代天象记录统计分析》(同上,2013年第3期)、《宋史天文志天象记录统计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史元史天象记录统计分析》(《时间频率学报》2013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未刊稿《春秋至晋代的日食记录》、《汉魏晋天象记录统计分析》,可为本书读者提供参考。
刘次沅2010年8月初稿
2013年12月定稿
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
(1) 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 参见Stephenson F R,Green DA:Historical Supernovae and their Remna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 刘次沅:《宋史天文志天象记录统计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14页。
(4) 参见宁晓玉、刘次沅:《适用于古天文研究的计算机软件》《时间频率学报》2006年第1期,66页。
(5) OPPOLZER T.R.,Canon der Finsternisse.Vienna: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1887.
(6) 参见朱文鑫:《历代日食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7) 参见刘次沅:《朱文鑫〈历代日食考〉研究》,《时间频率学报》2008年第l期,73—80页。
(8) 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8年。
(9) 参见斋藤国治、小泽贤二:《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东京:雄山阁,1992年。
(10)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下称“陈《表》”。
(11) 参见黄一农:《中国史历表朔闰订正举隅——以唐〈麟德历〉行用时期为例》,《汉学研究》1992年第2辑,305页;罗见今、关守义:《敦煌居延汉简中与朔闰表不合诸简考释》,《文史》2000年第1辑(总第50辑),57页。
(12) 参见刘次沅:《二十四史天象记录与陈垣历表的朔闰差异》,《时间频率学报》2012年第1期,50页。
(13) 参见刘次沅:《中国古代天象记录中的尺寸丈单位含义初探》,《天文学报》1987年第4期,397页。
(14) 伊世同:《全天星图2000.0》,北京:地图出版社,1984年。
(15) 参见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16) 参见Stephenson F R.Historical Eclipses and Earth's Ro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7) 参见刘次沅:《中国古代常规日食记录的整理分析》,《时间频率学报》2006年第2期,151页。
(18) 参见马莉萍:《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121页。
(19) 参见刘次沅:《中国古代月掩犯资料的统计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298页。
(20) 参见吴守贤、刘次沅:《由中国古代月掩犯记录得到的地球自转长期变化》,《天文学报》1993年第I期,80页。
(21) 参见江涛:《论我国史籍中记录下半夜观测时所用的日期》,《天文学报》1980年第4期,323页。
(22) 参见刘次沅、P.K.Seidelmann:《二十四史行星掩星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128页。
(23) 参见刘次沅、吴立旻:《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507页。
(24) 参见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1982年第2期。
(25) 参见庄威凤:《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中国科技出版社,2009年,147—162页。
(26) 参见席泽宗:《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庄威凤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2009年,66—109页。
(27) 参见刘次沅、马莉萍:《明代月食记录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