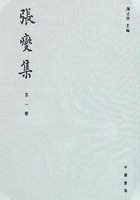
前言
張燮,字紹和,號汰沃,别號海濱逸史、逸史、岐海逸民、石隱主人、霏雲主人、汰沃子、蓬蒿長、石户農等,明代龍溪錦江(今福建省龍海市石碼鎮)人。萬曆元年生,萬曆二十二年鄉試中舉,此後屢困科場,恬然自處,居家著述,以舉人終身。崇禎十三年卒,享年六十八歲。入祀鄉賢祠。張燮出生名宦之家,其父張廷榜,字登材,人號春宇先生,自號丹霞一拙,又號霞南釣叟,萬曆二年進士,授仙源令,擢貳潤州守,署吴江令,後蒙冤罷歸,終老山林。伯父張廷棟,人號吉宇先生,萬曆八年進士,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後先奉使諸藩,贈餉一無所受’,卒於官。
張燮自幼秉承家風,博覽群書,精通經史,尤工詩文,《大清一統志》謂其‘嗜學,有文名’,以‘博學’知名于時。與蔣孟育、高克正、林茂桂、王志遠、鄭懷魁、陳翼飛合稱‘龍溪七才子’。與林茂桂、戴燝、蔣孟育、鄭懷魁、高克正、徐鑾、陳翼飛、陳範、汪有洵、鄭瓚思、吴宷、曹學佺及其父張廷榜諸人結霞中詩社,鼓倡文風于東南。閩南文壇一時蔚起,爲中原所矚目,而張燮是其中之佼佼者。
張燮一生‘淹貫史籍,沉酣學海’,且勤於筆耕,撰著宏富。陳繼儒曾謂‘閩中著述三家,侯官曹學佺、晋江何喬遠、龍溪張燮也’。黄道周亦稱張燮‘尚友三千年,著書四百卷’,在上崇禎皇帝的奏疏中曾自稱‘雅尚高致,博學多通,足備顧問,則臣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黄宗羲也嘗贊張燮‘其文波瀾壯闊而佐以色澤,萬曆間一作手也’。可惜的是,張燮逢世末戰亂,朝代更迭,故其著作多有散佚。據明末清初黄虞稷《千頃堂書目》載,張燮著述有《偶記》十卷、《鏡古録》三卷、《邇言原始》四卷、《采亹緒言》一卷、《北游稿》一卷、《藏真館集》四卷、《霏雲居集》五十四卷、《霏雲居續集》六十六卷、《群玉樓集》八十四卷、《東西洋考》十二卷,及輯《漢魏七十二家集》三百五十一卷等。據方志及公私藏書目録,尚有《游泉詩》(不分卷)、《居家必備》九十五卷、《初唐四子集》四十八卷、崇禎《漳州府志》三十八卷、崇禎《海澄縣志》二十卷等,未付梓之《霏雲居三集》等。此外,爲其子張于壘編《麟角集》四卷、《山史》,校刻蔣孟育《恬庵遺稿》三十八卷、徐日久《五邊典則》二十四卷;輯而未刊《唐賢七十二家集》,擬纂《閩中藝文志》,惜未竟。然而,距張燮去世僅七十七年後修纂的清康熙《龍溪縣志》藝文著書總目中,竟不見其著述,在該志本傳中亦僅提及‘刻有《七十二家文選》行世’,不言及其他著述。至乾隆年間初刻的《明史·藝文志》中,張燮著述僅見《東西洋考》與《群玉樓集》,且云:‘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之。’可見,張燮的大部分著作,在清初已難得一見,或已殘缺矣。經多方搜索,現存張燮著作有:《霏雲居集》五十四卷(目録五卷)、《霏雲居續集》五十四卷(目録六卷)、《東西洋考》十二卷、《海澄縣志》二十卷、《群玉樓集》八十四卷(目録六卷),輯有《七十二家集》三百四十六卷《附録》七十二卷、《初唐四子集》(其中《駱賓王集》未刻)四十八卷。
張燮喜交友,與同郡名儒周起元、林釬、黄道周、戴燝,萬曆、崇禎間名士温體仁、錢謙益、阮大鋮等交往密切。又好游歷,足跡遍及閩中八郡和吴越三楚,黄道周稱其‘出覽天下名山’。游歷中,張燮遍交海内名流學者,如徐、陳繼儒、曹學佺、徐霞客、何喬遠、蔡獻臣等與之往來甚篤,多有唱和之作。因新作問序,以碑銘乞文,張燮皆禮無不答,故張燮詩文集中保存有大量的序、紀、傳、尺牘以及墓志銘、祭文,保存許多漳州先賢的傳略,爲研究晚明漳州歷史留下了豐富的史料。其詩文内容豐富,不乏生動的細節,活生生地記述了明末的社會風貌和文人名士的生活情趣,從中可以獲得明代後期閩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歷史信息。張燮文思敏捷,文筆細膩而感情真摯,行文流暢,不失雅氣;嵌入典故,却不艱澀,給人以淋漓盡致的快感。其詩風格清雅纖秀,直抒胸臆,或寄托訴求,或抒發憂愁,或慰藉友人。然也多有贈别應酬、宴集吟唱、流連光景之詠誦。何喬遠頗自豪地説:‘吾閩有紹和,差爲武夷君吐氣!’張燮一生困頓,有着底層民衆的生活體驗,故其詩文中亦常常流露出對普通民衆的人文關懷。
張燮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明代晚期,是時,明處於内憂外患的漩渦中,東南有倭寇之害,東北有後金之窺,西南有播州之役。張燮以一個文人的視角,突出表現了對邊塞、海防等國家大事的關注。其《防海事宜序》云:‘今中朝局面,與嘉靖時又别一番。棄遼以飽虜,而又竭天下以奉遼。萬一海氛震裂,濁水靡旗,蘭皋失嶮,安能復以併力望援于他邦。惟是海國諸臣,早營家計,以自全其門户耳。’又曾嘆道‘方此北憂奴而西憂黔’,胸中常以國事爲己任。張燮喪子之後,在給好友蔡敬夫的信中,充分地表達了他憂國憂民的心境:‘燮每嘆今日之慘,已不减遼蜀間人,且遼蜀之慘,通國均受,弟却以衰宗,獨蒙斯毒,私心愈以不甘。然今遠夷突據海上,狎視内地,如走窔奥,又恐遼蜀之漸已成,復何策禦之乎!’張燮敏鋭地指出:‘從前遼事之誤,病在視賊太難,而膽先怯;黔事之誤,病在視賊太易,而慮鮮周。’因此,張燮在詩文集中不乏對‘建酋’侵邊的描述,如《遼師失利四首》,刻畫了邊關將士同仇敵愾、視死如歸的忠貞義節;努爾哈赤侵擾明朝疆域,氣勢凶悍,張燮稱其軍爲‘妖’,爲‘胡’,爲‘奴虜’,等等。因此,清修《四庫全書》時,張燮部分著作如《霏雲居續集》,因‘有指斥之語’而被列入《軍機處奏准全毁書目》,此亦爲張燮詩文不能傳世之因由。正如安平秋、章培恒主編的《中國禁書大觀》所述:‘《霏雲居續集》雖然多抒文人墨客的優游之情、閒澹之意,但仍以其抗奴滅酋的實在心跡,成爲清代禁毁書目的内容之一。’
整個晚明,是東南沿海的多事之秋,萬曆中期,倭寇之亂平息之後,又遭逢荷蘭的騷擾。張燮在《南中丞勒凱編序》云:‘閩以南瀕海,往歲苦倭。乃和蘭之夷,最晚出而遞爲梗,詭言請市,奪我彭湖,率意闌入,殺掠無算。彼俎我爲魚肉,而將吏望鋒先奔;彼弄我如嬰兒,而所司用款自誤。盤踞于兹,遂深歲月。’在《紅夷行》序文中亦云:‘紅夷自稱和蘭國,乘巨艦據我彭湖,出入鷺門、圭嶼。久之,海濱一帶無復寧宇。官以款自愚,夷玩我股掌之上,益肆哮吼。幽人徙避無處。’這種動蕩的社會狀態,逼得張燮萌生移居南京的想法,在給友人的信中説:‘今海上紅夷已成剥膚之勢,意欲携幼兒依仲先于吴門,令掃齋後片榻待我。’只是到了南京後不久,因周起元陷東林黨案,得罪魏忠賢,被革職回海澄,張燮才隨之回漳州。
然而,張燮並非是鼠目寸光的閉關自守者,而是睁開眼睛觀望大海遠處。閩南倭寇之禍,自嘉靖二十八年起,至隆慶三年止,大凡二十餘年,經歷這場曠時日久的戰亂,國庫耗殆,民生凋敝。因此,朝廷爲增加税收,停止‘海禁’,以增加財政收入,何喬遠曾上疏云:‘臣閩人也,敢言海事。竊見閩地窄狹,田疇不廣,又無水道可通舟楫上吴越間爲商賈,止有販海一路可以資生。萬曆間開洋市於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税二萬餘兩。’另一方面也以此蘇活民生,‘吕宋諸夷之販,則官爲之給引置榷,亦開一面之網……然向惟漳民爲盛’,這一政策促使海上貿易風生水起,假資借貸,而販者比比。張燮説:‘以夷爲市,子母既贏,因而機械百變,此漳與四方之所異也。’因東南亞國家‘皆好服用中國綾緞雜繒’,‘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悉得價可二三百兩。而江西之瓷器、福建之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而吕宋‘其國有銀山出銀,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暹羅、柬埔寨、越南産有我們需求的蘇木、胡椒、犀牛、象牙、沉檀、片腦諸物,月港之海商將之進出口,期間賺取的利潤自然十分豐厚。此亦爲今所謂‘海上絲綢之路’。
海外貿易有力地促進閩南一帶的經濟繁榮,這可從當時的奢靡之風窺見一斑。金門籍名宦蔡獻臣在萬曆四十六年編撰的《同安縣志》裏説:‘同安風俗之蠹者,其一曰賭,其二曰侈。’對‘侈’的描述,令人刮目相看。當時着衣帽‘往時市肆紬緞紗羅絶少,今則蘇緞、潞綢、杭貨、福機行市,無所不有者。往時惟有方巾、園帽二種,今則唐巾、雲巾、帽巾無人不用。瓦楞或用縐紗瓣幅,甚至奴隸之輩,亦頂唐巾朝履者’。佩帶首飾‘舊惟金面銀裏,今則有並裏用金者。舊惟真珠假石,今則不惟買珠於粤,而且市石於滇,沽玉瑙于燕者’。飲食宴席‘物必珍貴,具必鳳甌,品必數十,飲必丙夜’,其他弱冠生朝,演戲招賓,祖父忌祭,牌枚行酒,無所不有。每年迎神賽會,坊隅庵院神佛,必出像割香一番,‘而崇奉尤多,迎賽尤盛者,竟不知其何神也。’婚姻嫁娶,禮尚往來,也極盡豪華精美。張燮也説漳州‘世重福田,每梵宫有所修葺,金錢之施,不呼而滿’,於是他認爲‘若夫行樂公子,閑身少年,鬥雞走馬,吹竹鳴絲,聯手醉歡,遨神遼曠,雖妨本業,然亦足鼓吹盛世,點綴豐年,不容此無以見太平已’。經濟的繁榮也引發文化的興盛,時‘閩之中,無諸則有瑶華社,蒲陽則有西園社,泉中則有泉山社,漳中則有霞中社,無殊皆與更唱迭酬,過往而不休’。在此背景下,當時頗有見地的漳州府及海澄縣地方官認爲必須‘進而問徼外風土諸種種異’,於是特邀請博物善屬辭的張燮參咨搜稽,編撰《東西洋考》十二卷。海澄月港是明晚期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東西洋考》是一部明末漳州地區海外貿易的‘通商指南’,該書記載了十六世紀東南亞各國歷史和物産,保存了大量明代後期漳州地區與東南亞貿易和商品經濟發展的資料,對有關航海的技術知識和地理知識(如航程、航路、針路、水深、氣象、潮汐等)都有詳細記載。最可貴的是作者大量地使用了當時政府的邸報、檔案,查閲了前人留下的歷史文獻,如鄭和下西洋的有關資料,還有采訪航海商人、舟師得來的實際見聞等第一手資料。本書還是我國與西方接觸的最早資料之一。《東西洋考》一經出版,同時代就予以很高的評價。張維樞贊之:‘《洋考》寧直夷之董狐,是泉貨盈縮之源,而徹桑綢户、經國雄邊之算也。胸中蓋具有全海焉。覺張博望、郭守敬輩猶未爲大經濟,識者必采而資海籌矣!’周起元稱此書‘收千古歸之筆端,補前人所未備’,蔡獻臣亦稱‘《洋考》見惠,如讀《山海經》,博學多奇,自足傳信’。可以説,《東西洋考》是我們今天研究中外關係史、航海史、華僑史以及閩南文化的重要參考書。
張燮性高潔,雖優游於江南名士之中,却超然於其時訐忤不息的黨争。天啟間,此時張燮聲望已遠播中土,何喬遠等疏薦之與修《神宗實録》,辭不赴,時下諸名士也多以書勸駕,張燮終不爲所動。故清光緒《漳州府志》寫道:‘遠近舉稱曰“徵君”,既而黨禍大作,徵君獨飄然幾先,衆比之申屠蟠、郭林宗云。’
張燮作爲晚明著名詩人、學者、著述家,博學工文,其地位和影響,近四百年來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研究,其著述也長期湮没無聞。當今人感謝萬曆舉人胡震亨編輯之《唐音統籤》,以及錢謙益收集之唐詩殘稿,爲康熙年間編纂完成《全唐詩》提供重要參考時,也應記住同時代的張燮獨力輯佚洋洋灑灑數百卷之《漢魏七十二家集》,使其時已難一睹的千年前作品得以流傳下來。歷史是有選擇性地記憶,有的人物在那個時代,或風光顯露,或平淡無聞,而歷史往往給予判然不同的記憶,此乃有其因緣際遇。齊弼在《國朝全閩詩序》中,不無感歎地説:‘予謂閩人不善爲名,故文采風流不足争衡上國,非獨地勢限之,亦緣無好事者流爲之搜采,時爲表章。’况張燮時運不濟,處于鼎革之際,文友凋零,後朝文網嚴苛,將之抹殺。清康熙《龍溪縣志·張燮傳》中感慨寫道:‘龍溪自唐宋以來,文學日興。明初,猶尚宋學,文多醇質。嘉隆以降,追西京矣。兵火屢痛,子孫遂不保其先人所著述,全集多不傳,然其散見於殘編者,吉光片羽,已足輝映十五城矣。’就這樣導致歷史冷漠地將之淡忘。
今見藏於海内外藏書單位的張燮詩文集有《霏雲居集》、《霏雲居續集》、《群玉樓集》等三種,前二種爲孤本,後一種僅見同刻兩部,若不加意存録,則其聲光無從窺尋。因古籍素無勾乙,加之版本不佳,且多有闕字,字多通假、異體、俗體,令今之讀者研習應用多有不便。有鑑於此,我們對《霏雲居集》、《霏雲居續集》及《群玉樓集》勉爲丹黄。整理所依據底本分别爲:《霏雲居集》五十四卷(目録五卷),明萬曆四十年刻本,《四庫禁毁書叢刊·補編》據首都圖書館藏本影印本;《霏雲居續集》五十四卷(缺卷二十五至卷三十。目録六卷),萬曆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本;《群玉樓集》八十四卷,崇禎十一年刻本,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本。需要説明的是,臺北‘中央圖書館’館藏《群玉樓集》缺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卷四十一且個别卷次字跡漫漶,我們據河南省圖書館藏本予以校補。僅對各集明顯錯字予以改正,不出校記。《東西洋考》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中華書局謝方先生點校出版,考慮到《東西洋考》的學術價值,是張燮海洋文化思想的集中體現,徵得中華書局和謝方先生同意,編入集中再版。全書定名爲《張燮集》。另有《漢魏七十二家集》、《初唐四子集》等多部張燮輯佚之著述,因非本人撰著,故不予收録。
《張燮集》之鈎考鉛黄由陳正統主持,自二〇一三年夏開始至二〇一五年夏付梓。今點斷一部從來没人整理過的近二百萬字的古籍,已非要之皓首青燈,‘韋編屢絶鐵硯穿,口誦手抄那計年’了,而是需得仰仗諸多熱心人士的襄助。《張燮集》的整理工作得到臺盟中央常務副主席、全國臺聯會會長汪毅夫的鼓勵,中共漳州市委書記陳家東、中共龍海市委書記張禎錦的高度重視並予有力支持。民盟福建省委會李明蓉、曉風書屋許志强、興證期貨公司王君恩多方提供幫助。在出版經費有所短缺時,福建融僑集團及時予以贊助。爲了確保書稿品質,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俞國林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中華書局資深編審沈錫麟先生、熊國禎先生對書稿進行審定。著名篆刻家陳金光先生爲本書治印。張燮晚年隱居的萬石山(石獅巖),爲今之七首巖寺,住持釋照光,慨然爲我們的整理工作提供僧舍。本集的編輯過程中,漳州市圖書館蔡宇飛、徐紅慧、歐裕南、陳潔如、黄瓊、吴津芸,漳州市政協海峽文史資料館閻銘及福建農林大學金山學院賴曉雨等同志參與全部文稿的録入與校對工作。臺灣金門大學葉鈞培先生爲我們提供臺北‘中央圖書館’館藏《群玉樓集》複印本,福建省圖書館館長鄭智明、特藏部副主任許建平,河南省圖書館古籍部主任周新鳳爲我們複製、查閲《群玉樓集》提供了及時高效的支持。在此,謹向他們和關心此項整理工作的社會賢達表示衷心的感謝!
因時間倉促,學識有限,疏誤在所難免,尚祈望諸先進撥冗匡謬,不吝賜玉。
陳正統
二〇一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