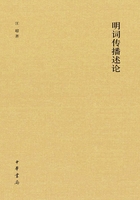
第一节 明代文学传播的社会环境
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指出影响传播的主要社会环境因素有四: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讯息因素。“如果上述因素呈现出良好的适宜和稳定状态,那么就会对大众传播活动起着促进、推动的作用;相反,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明代文学的传播自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朱元璋建立政权开始,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划时代的变化。在中华大地广袤的土地上不断萌生出新现象、新思潮、新文化,而这一切无不影响着有明一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
明代文学的传播自然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朱元璋建立政权开始,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划时代的变化。在中华大地广袤的土地上不断萌生出新现象、新思潮、新文化,而这一切无不影响着有明一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
一 政权稳定 交通畅达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蒙古人失其鼎,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即位,建号洪武,拉开了明王朝的序幕。明王朝的鱼鳞图册、废除宰相、大规模移民等等耳熟能详的典章故事让我们听到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最初的声音。尽管这个王朝外有倭寇侵袭,内有宦官专政,加上“问题皇帝”轮番登基 ,但由于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文官制度,国家机器依然能有条不紊地运转。明代近三百年,从朱棣兴兵到倭寇滋扰,从土木堡之变到大礼之议,从宁王叛乱到东林党祸,虽惊险不断,却少有政权不稳的情况。关于明代中央集权的巩固与统一,说者已众,无需赘言。政权的稳定为文学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适宜的大环境。
,但由于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文官制度,国家机器依然能有条不紊地运转。明代近三百年,从朱棣兴兵到倭寇滋扰,从土木堡之变到大礼之议,从宁王叛乱到东林党祸,虽惊险不断,却少有政权不稳的情况。关于明代中央集权的巩固与统一,说者已众,无需赘言。政权的稳定为文学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适宜的大环境。
国家统一,政权稳定,交通也随之畅达。不论是宦游,还是经商,或者是像徐霞客那样履迹遍及四方,交通永远是出行的基础,而良好的交通状况也是资讯传播的有利条件。明代两京至十三布政司有道路17条,两京至所属府道路11条,十三布政司至所属州府道路53条,江北水路干线44条,江南水路干线76条 。明代交通路程指南书籍及日用类书的《商旅门》中几乎都有全国州府图,交通线路说明等内容,有的还会详细告知途经地的特产、风景及注意事项,类似今天的旅行“小贴士”。其时出行者总不在少数,否则何以有数量如此众多,介绍如此详尽的旅行指南出现?而便捷的交通也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例如建阳崇化里书坊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建忠里洄潭“每月俱以四、九日集”,“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
。明代交通路程指南书籍及日用类书的《商旅门》中几乎都有全国州府图,交通线路说明等内容,有的还会详细告知途经地的特产、风景及注意事项,类似今天的旅行“小贴士”。其时出行者总不在少数,否则何以有数量如此众多,介绍如此详尽的旅行指南出现?而便捷的交通也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例如建阳崇化里书坊街,“每月俱以一、六日集”,建忠里洄潭“每月俱以四、九日集”,“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诸商皆集” ,其时该县每月有四日汇聚天下书商,进行图书贸易。试想,若非良好的交通条件,“天下诸商”如何能“皆集”于万山之中的建阳?而水网纵横的江南也有人为贩书而以舟载书,送书上门,时号“书船”
,其时该县每月有四日汇聚天下书商,进行图书贸易。试想,若非良好的交通条件,“天下诸商”如何能“皆集”于万山之中的建阳?而水网纵横的江南也有人为贩书而以舟载书,送书上门,时号“书船” 。便捷的交通让更多的百姓可以走出家门,明人外出经商、仕宦的途中消遣时间的通俗读物随之兴盛,娱乐书刊也是其中一种。娱乐书刊中的词作、词话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流传。良好的交通条件也间接促进着福建、江浙等地书籍流通的兴盛,自然也使词籍的流通更加顺畅。
。便捷的交通让更多的百姓可以走出家门,明人外出经商、仕宦的途中消遣时间的通俗读物随之兴盛,娱乐书刊也是其中一种。娱乐书刊中的词作、词话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流传。良好的交通条件也间接促进着福建、江浙等地书籍流通的兴盛,自然也使词籍的流通更加顺畅。
政权的稳定和交通的便捷也使国人与域外的频繁交流成为可能。明初郑和七下南洋,陈诚等人四使中亚,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地的官民也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原往来不断。“在朝鲜,自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存在大量的《朝天录》或《燕行录》,其数量应该在五百种上下。在越南,则有《北行纪略》、《北使通录》、《往津日记》、《北槎日记》、《北行丛记》等。” 其中亲眼目睹过大明都市的撰写者必然不少。国人也有出使朝鲜、越南并留下亲历记录的,如倪谦的《朝鲜纪事》、湛若水的《交南赋》。洪武二年(1369)至崇祯七年(1634),有明一代共向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遣使159次,其中朝鲜时代就达141次
其中亲眼目睹过大明都市的撰写者必然不少。国人也有出使朝鲜、越南并留下亲历记录的,如倪谦的《朝鲜纪事》、湛若水的《交南赋》。洪武二年(1369)至崇祯七年(1634),有明一代共向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和李氏朝鲜遣使159次,其中朝鲜时代就达141次 。中国使臣在出使活动中,也注重文化交流,与朝鲜国王、大臣多有唱和,李氏朝鲜于景泰元年(1450)至崇祯六年(1633)间将这些作品编印成24部《皇华集》传世。《皇华集》载有34首词,这些作品通过所在国的记载得以流传。双方首次以词唱和,是在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户部郎中祁顺出使朝鲜时,与朝鲜远接使、议政府左参赞、《东人诗话》的作者徐居正唱和。嘉靖十六年(1537)翰林院修撰龚用卿、嘉靖十八年工科给事中薛廷宠分别出使朝鲜,均在《皇华集》中留有词作。这些唱和也传回中国
。中国使臣在出使活动中,也注重文化交流,与朝鲜国王、大臣多有唱和,李氏朝鲜于景泰元年(1450)至崇祯六年(1633)间将这些作品编印成24部《皇华集》传世。《皇华集》载有34首词,这些作品通过所在国的记载得以流传。双方首次以词唱和,是在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户部郎中祁顺出使朝鲜时,与朝鲜远接使、议政府左参赞、《东人诗话》的作者徐居正唱和。嘉靖十六年(1537)翰林院修撰龚用卿、嘉靖十八年工科给事中薛廷宠分别出使朝鲜,均在《皇华集》中留有词作。这些唱和也传回中国 ,国家政权的稳定是这些国事活动雅重文艺的前提,而中朝文人在国事活动中的唱和具备人际传播的特质。
,国家政权的稳定是这些国事活动雅重文艺的前提,而中朝文人在国事活动中的唱和具备人际传播的特质。
不过,中朝的交往并不仅仅局限在官方,朝鲜词人的作品通过各种渠道流传至中国,也引起国人极大的兴趣,《古今词统》、《名媛诗归》、《花镜隽声》等总集中都收有朝鲜人的作品。明人编纂的《古今词统》就载有成氏、俞汝舟妻等朝鲜人的词作。《名媛诗归》、《花镜隽声》也收有许景樊等朝鲜人的作品,许氏即许筠的姐姐兰雪轩,是朝鲜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女作家。
在国内,交通的便捷同样促进了人口的流动,使得商业发达,城市发展,市民阶层随之愈发壮大。信息传播的便捷促进了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的流动也造成了语文统一的需要,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推广。
二 文教普及 语文统一
文学作品的传播有赖于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准备了受众条件。口传文学虽然对受众文化素养要求稍低,但作为影响文学史主潮的书面文学则必然要求受众能识文断句。民众能识字便是教育使然,当时文教之普及亦足可“度越汉唐”。
洪武二年(1369)十月,朱元璋诏谕臣下说:
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速行之 。
。
其中对人才的渴求,对教育的重视昭昭可见。身处当时的杨荣称颂道:“圣朝统一寰宇,自国都达于郡邑,皆建学立师,教育俊秀。仁义礼乐之化,旁洽海隅徼塞。人才之众,风俗之美,度越汉唐,而比隆虞周。猗欤盛哉!” 以当时实际观之,似非过誉。明代学校以北京、南京之国子监为首,地方州、府、县、卫、土司多设儒学,又有医学、阴阳学等专科教育,其时官方教育体系是完备的。前代相对落后的“海隅徼塞”也人文日新,例如琼州人邱濬《沁园春》词序有云:“服岭以南,由进士入官翰林者自予始。厥后二十五年,洗马叔厚以会元进。又十年,邦祥以探花进。甫三年,编修可大又以榜眼进。继此而又有编修伯诚者,源源而来。”
以当时实际观之,似非过誉。明代学校以北京、南京之国子监为首,地方州、府、县、卫、土司多设儒学,又有医学、阴阳学等专科教育,其时官方教育体系是完备的。前代相对落后的“海隅徼塞”也人文日新,例如琼州人邱濬《沁园春》词序有云:“服岭以南,由进士入官翰林者自予始。厥后二十五年,洗马叔厚以会元进。又十年,邦祥以探花进。甫三年,编修可大又以榜眼进。继此而又有编修伯诚者,源源而来。” 连原先教育落后的岭南地区都“源源而来”地涌现翰林,教育的地区差异较前代有所缩小。
连原先教育落后的岭南地区都“源源而来”地涌现翰林,教育的地区差异较前代有所缩小。
独立于官方学校之外的书院也是明代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明人亦以学校、书院并举。如天顺五年(1461)李贤《进<明一统志>表》就说:“书学校、书院以重育贤。” 全国各地书院林立,仅安徽一省就有一百余所书院
全国各地书院林立,仅安徽一省就有一百余所书院 ,而日渐兴盛的讲会活动也使书院成为民间新思潮的策源地
,而日渐兴盛的讲会活动也使书院成为民间新思潮的策源地 。万历三年(1575)勅谕:
。万历三年(1575)勅谕:
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堂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昔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迹,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 。
。
冠冕堂皇的言辞下所掩盖着的,大约正是对异乎官方意识形态之新思潮的担忧。但书院的兴起,确实为明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使当时教育更加普及。
据陈宝良先生推断,明代男性能读、写的比率在30%—45%之间,而女性识字率则为2%—10% 。这一推断应当是有道理的,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漂海南来,曾自浙江到北京,经辽东回到朝鲜,途经中国南北诸多地方。他对当时中国人文化水平的感性认识是:“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
。这一推断应当是有道理的,弘治元年(1488)朝鲜人崔溥漂海南来,曾自浙江到北京,经辽东回到朝鲜,途经中国南北诸多地方。他对当时中国人文化水平的感性认识是:“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闬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 这说明,明代相当数量的普通百姓能够读写文字,这些识文断字者正是文学作品潜在的阅读者。
这说明,明代相当数量的普通百姓能够读写文字,这些识文断字者正是文学作品潜在的阅读者。
虽然,由于理学本身的问题,科举教育也给文学传播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总体上说,明代教育的普及对文学传播是利大于弊的。教育的普及促使识字率的提高,识字率的提高扩大词作者和阅读者的基础,这为明代文学的传播准备了充分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但总体上说,明代教育的普及对文学传播是利大于弊的。教育的普及促使识字率的提高,识字率的提高扩大词作者和阅读者的基础,这为明代文学的传播准备了充分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明初,朝鲜人权近咏出“皇明四海车书同”(《代人赠段行人使还》),“山河万国同文日”(《代人送国子周典簿卓》)之类的诗句 。在域外士人看来,明代是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语言文字的统一,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统一的语言文字也正是信息传播的有利条件,而这也是朱元璋治国理念下的规划之一。汉字的统一早在秦朝即已完成,朱元璋登基后则注意统一语音,十六卷本的《洪武正韵》就是洪武八年(1375)乐韶凤、宋濂等人奉诏编成的。明太祖“以旧韵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在域外士人看来,明代是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语言文字的统一,正是其中的一部分。统一的语言文字也正是信息传播的有利条件,而这也是朱元璋治国理念下的规划之一。汉字的统一早在秦朝即已完成,朱元璋登基后则注意统一语音,十六卷本的《洪武正韵》就是洪武八年(1375)乐韶凤、宋濂等人奉诏编成的。明太祖“以旧韵起于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与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以中原雅音校正之”云云,实际上就是为国民的口头交流制定统一的语音规范。这也足见朱元璋本人对统一语音的重视。
。“以中原雅音校正之”云云,实际上就是为国民的口头交流制定统一的语音规范。这也足见朱元璋本人对统一语音的重视。
明人语音的统一并不仅仅停留于理论上,在现实生活中,明朝口语也是统一的。利玛窦说:“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Quon-hoa),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不过明人对官话的态度却因人而异,王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所谈皆前辈旧事,历历如贯珠,议论英发,音吐如钟”
不过明人对官话的态度却因人而异,王雅宜“不喜作乡语,每发口,必官话,所谈皆前辈旧事,历历如贯珠,议论英发,音吐如钟” 。而谢榛则认为“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
。而谢榛则认为“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 。尽管对语言的统一,明人自身也有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渔所谓“禁为乡土之言,使归《中原音韵》之正者是已”乃出于传播交流的需要
。尽管对语言的统一,明人自身也有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渔所谓“禁为乡土之言,使归《中原音韵》之正者是已”乃出于传播交流的需要 。
。
对语音统一的追求也影响到了明词。据说词韵最初起自宋代,有研究者认为《词林韵释》(又称《菉斐轩词林要韵》)即据南宋大晟乐府韵所编。然看法殊不相同,有人则以为其书是明人伪托 。明人所编词韵则有胡文焕《会文堂词韵》,只是当时影响并不很大。沈谦有《词韵略》,四库馆臣以为“词韵旧无成书,明沈谦始创其轮廓”
。明人所编词韵则有胡文焕《会文堂词韵》,只是当时影响并不很大。沈谦有《词韵略》,四库馆臣以为“词韵旧无成书,明沈谦始创其轮廓” 。邹祇谟称其“考据该洽”,“可为填词家之指南”
。邹祇谟称其“考据该洽”,“可为填词家之指南” 。虽然从创作实践上说,明人填词未必非按词韵选字不可,词韵书籍也要到清代才蔚为大观,但明人已然注意到词韵的使用。这对促进词作传播同样是具有影响的,以方言押韵的词作,在不同方言区的传播可能出现相应的阻滞。
。虽然从创作实践上说,明人填词未必非按词韵选字不可,词韵书籍也要到清代才蔚为大观,但明人已然注意到词韵的使用。这对促进词作传播同样是具有影响的,以方言押韵的词作,在不同方言区的传播可能出现相应的阻滞。
三 城市发达 经济繁荣
城市是一个区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它区别于散居的农村聚居形态,密集而流动的人口,繁荣的商业都是城市的典型特征之一。城市也是信息传播的集散地。相对于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城市与商品经济是有着天然联系的。刘石吉先生指出:“明清以来,江南许多市镇(甚至村集)均经历了‘都市化’的过程;而这种趋势又明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交互影响的关系。” 本就十分发达的苏州,到明代中晚期都市化程度更加发达,并带动了周边市镇的兴盛
本就十分发达的苏州,到明代中晚期都市化程度更加发达,并带动了周边市镇的兴盛 。唐寅《阊门即事》诗描述苏州的繁盛称:“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唐寅《阊门即事》诗描述苏州的繁盛称:“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翠袖三千”、“黄金百万”足见一时物质之富足,娱乐业之发达。颈联“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则是城市商业兴盛和外来人口众多的诗化表达。而王心一也从当地人的视角述说苏州商业的发达,道:“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
“翠袖三千”、“黄金百万”足见一时物质之富足,娱乐业之发达。颈联“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则是城市商业兴盛和外来人口众多的诗化表达。而王心一也从当地人的视角述说苏州商业的发达,道:“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
在中心城市影响下的市镇也是一样“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醒世恒言》提到盛泽镇:
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 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
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 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
。
而彼时的江南以手工业兴起的专业市镇实在也不少。不唯富庶的江南,就是边塞也有不少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城市。“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 ;又如肃州,“各类工匠搭有他们的店棚。他们的市场中有很多广场”;“甘州比肃州大得多,人口更稠密”
;又如肃州,“各类工匠搭有他们的店棚。他们的市场中有很多广场”;“甘州比肃州大得多,人口更稠密” 。商业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商业与城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对于文学来说,城市也是文学传播的最重要场域。方志远先生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戴健先生的《明代后期吴越城市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等均对此有所论述。词本就与商品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歌台舞榭、秦楼楚馆的城市元素正是唐宋词兴起最初的背景,王晓骊教授的《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曾谈到了这个问题,可以参考 。而明词传播也和城市密不可分,更与商品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试想:明代歌妓词人的生活背景就是城市;明代书坊也以金陵、杭州等地最密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环太湖地区也正是当时词学的中心。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桩哪一件是能脱离经济状况影响的?
。而明词传播也和城市密不可分,更与商品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试想:明代歌妓词人的生活背景就是城市;明代书坊也以金陵、杭州等地最密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环太湖地区也正是当时词学的中心。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一桩哪一件是能脱离经济状况影响的?
四 市民阶层兴起 通俗文化昌盛
城市的发展必然要聚集大量的人员与财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费随之兴盛,服务业、娱乐业趋于发达。明代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古代人口史的研究给出了相关的回答,或许这些回答并非最终答案,但也可了解明代城市人口的基本状况。“明初在洪武时期,以史籍所记人口再加上同数的妇女,人口亦应在1亿以上。”“明万历时(即公元1600年前后)人口当在2亿以上。” 有关明代城市人口的数量,曹树基先生认为明初民籍人口的约十分之一居住在城市,且“明代后期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可能超过明初”
有关明代城市人口的数量,曹树基先生认为明初民籍人口的约十分之一居住在城市,且“明代后期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不可能超过明初” 。则终明之世,城市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10%。综合王、曹之论推测,明代之城市人口总数在千万以上,而这些人口还不包括因为种种原因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例如遍布全国的商人,晋商、徽商、江右商帮自不必说,就是富庶的江南也吹起外出经商之风。吴县“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则终明之世,城市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10%。综合王、曹之论推测,明代之城市人口总数在千万以上,而这些人口还不包括因为种种原因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例如遍布全国的商人,晋商、徽商、江右商帮自不必说,就是富庶的江南也吹起外出经商之风。吴县“人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这些流动人口对城市发达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市民阶层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自由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各类城市贫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
。这些流动人口对城市发达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市民阶层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自由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各类城市贫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 这个阶层的兴起不仅仅是因为该阶层的人口基数已经达到千万以上,更因为他们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们已经成为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市民阶层的聚合力直接表现在了他们为维护本阶层权利而起的抗争。例如万历间因苏州税监孙隆大等议增织机税银引发的机户皆闭门罢织;松江董其昌父子侵暴乡民引发的“民抄董宦”等事件。而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直观地表现在通俗文化上。
这个阶层的兴起不仅仅是因为该阶层的人口基数已经达到千万以上,更因为他们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他们已经成为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市民阶层的聚合力直接表现在了他们为维护本阶层权利而起的抗争。例如万历间因苏州税监孙隆大等议增织机税银引发的机户皆闭门罢织;松江董其昌父子侵暴乡民引发的“民抄董宦”等事件。而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直观地表现在通俗文化上。
市民阶层的兴起,使得适应他们欣赏水平的文艺样式不断兴盛繁荣起来。当时之时调、俗曲亦如“有水井处皆歌”的柳词之于宋时。陈弘绪《寒夜录》引卓珂月语称《吴歌》、《挂枝儿》之类的俗调,为明代一绝 。其时“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其时“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 。其时兴起的戏曲和通俗小说也离不开市民阶层的喜闻乐见。清人所谓“花部”、“乱弹”的弋阳腔、海盐腔等在此时就甚有市场,王骥德曾叹道:“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
。其时兴起的戏曲和通俗小说也离不开市民阶层的喜闻乐见。清人所谓“花部”、“乱弹”的弋阳腔、海盐腔等在此时就甚有市场,王骥德曾叹道:“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 而专业的表演团队以之谋生的人数也在在不少,如明季张瀚所说:“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徘,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
而专业的表演团队以之谋生的人数也在在不少,如明季张瀚所说:“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徘,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 一时风气可知之矣。表演艺术是这样兴盛,通俗小说也毫不逊色。当时不少文士就加入到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搜集中,冯梦龙、凌蒙初、邓志谟等人都是显例。一些书坊还推出了适合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书刊,比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绣谷春容》等等。词在这种背景下传播,必然要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因此,“曲化”、“俗化”等“托体不尊”的问题就显得较为突出,但明词的这些特征也正是明词区别于前代词什之处。而通俗小说、戏曲的兴盛也为寄生于这两种文体中的词作提供了良好的传播途径。
一时风气可知之矣。表演艺术是这样兴盛,通俗小说也毫不逊色。当时不少文士就加入到了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搜集中,冯梦龙、凌蒙初、邓志谟等人都是显例。一些书坊还推出了适合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书刊,比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绣谷春容》等等。词在这种背景下传播,必然要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因此,“曲化”、“俗化”等“托体不尊”的问题就显得较为突出,但明词的这些特征也正是明词区别于前代词什之处。而通俗小说、戏曲的兴盛也为寄生于这两种文体中的词作提供了良好的传播途径。
五 思想自由 人欲觉醒
市民阶级的兴起,使得这股力量对社会思潮起到了一定的影响,社会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让人们对社会、人生有更多的判断能力,思想上更加自由开放;经济发达带来物质生活上的消费观念变迁,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物质欲念的觉醒。
明代初年,国家以理学为统一思想的利器,不遗余力地推动程朱理学的发展,奉之为圭臬。朱子曾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但是随着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兴起,反映该阶层主张的新思潮正如暗涌的地下长河,在程朱理学笼罩的地底激荡,新学派正不断酝酿。王阳明龙场悟道,发挥陆九渊“心即理也”的主张,反对“天理人欲”之说,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王门后学、“灶户”出身的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更升张“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大纛;至于“异端之尤”李贽,更明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但是随着明代中后期市民阶层的兴起,反映该阶层主张的新思潮正如暗涌的地下长河,在程朱理学笼罩的地底激荡,新学派正不断酝酿。王阳明龙场悟道,发挥陆九渊“心即理也”的主张,反对“天理人欲”之说,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王门后学、“灶户”出身的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更升张“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大纛;至于“异端之尤”李贽,更明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认为“穿衣吃饭”的“人欲”就是“人伦物理”,没有“衣”与“饭”,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罔论“人伦物理”了。可以说,明代中后期的新思潮是以要求思想解放、个性自由为宗尚的。思想的自由使得人们不必再汲汲于克制,因为在宋儒们那里,连诗歌都是被排斥的,以为会影响对“理”的寻绎。而到明代中后期,情欲的觉醒,使得“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反映这些思想的小说、戏曲和诗文可以四下传布。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存天理”与“去人欲”显然不能一统天下了,“人欲”作为一个话题复活了。人们敢于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以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
。李贽认为“穿衣吃饭”的“人欲”就是“人伦物理”,没有“衣”与“饭”,人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罔论“人伦物理”了。可以说,明代中后期的新思潮是以要求思想解放、个性自由为宗尚的。思想的自由使得人们不必再汲汲于克制,因为在宋儒们那里,连诗歌都是被排斥的,以为会影响对“理”的寻绎。而到明代中后期,情欲的觉醒,使得“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反映这些思想的小说、戏曲和诗文可以四下传布。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存天理”与“去人欲”显然不能一统天下了,“人欲”作为一个话题复活了。人们敢于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以致“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 。于是身处当时的文人看到了人们在生活需求上的变化,不时将他们生活的时代与前代生活对比,发出疑惑的声音。“国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
。于是身处当时的文人看到了人们在生活需求上的变化,不时将他们生活的时代与前代生活对比,发出疑惑的声音。“国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成化以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 何良俊感慨“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
何良俊感慨“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 。这些豪奢的生活也为市民阶层提供了更多的生活来源,陆楫就说:“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
。这些豪奢的生活也为市民阶层提供了更多的生活来源,陆楫就说:“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 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商业物流的发达,使得寻常人家也具备了一定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人欲觉醒的反映。而这在文学传播上,道理相近。人们对文学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物质生活已经有所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精神生活的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使得文学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人们对文学的消费又促进着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明代中后期,值得文学史大书特书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这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产品的丰富,商业物流的发达,使得寻常人家也具备了一定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人欲觉醒的反映。而这在文学传播上,道理相近。人们对文学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物质生活已经有所保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精神生活的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使得文学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人们对文学的消费又促进着文学的生产和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明代中后期,值得文学史大书特书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