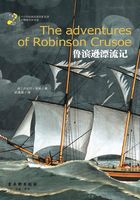
第5章 奴役和逃亡
当时那种邪恶的力量——它曾促使我离开了父亲,促使我产生发财的妄想,使我想入非非,不听一切的忠言,不听我父亲的恳求和命令——现在重新回到我的身上,使我看上了一种最不幸的事业,于是我上了一只开往非洲海岸的船,或者用一句水手们的习惯语:到几内亚去了。
在我一生的各次冒险中,我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以水手的身份去搭船,假如是那样,我的工作虽然比平常苦一点,至少可以学到一些管理前桅的技术和职责,即使将来不能做一个船主,至少也可以做一个大副。但是我是个背运的人,无论什么事,总是选择最坏的,在这件事上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口袋里既然有几个钱,身上又有一套好衣服,我每次总是像一个绅士似的去搭船,所以船上的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会做。
总算运气好,我在伦敦居然碰到了好人,对于我这样的放荡无知的年轻人,这实在是不常有的事,魔鬼对于这种人照例是一有机会便要替他安排下陷阱,但是这一次却不然。我一开头便结识了一个到过几内亚的船主,他在那边生意做得很成功,决定再去。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的谈话大概还不十分讨人厌。他听说我要到海外去见识见识,便对我说,假如我同他一块儿去,我可以不必出什么旅费,可以跟他一块儿吃饭,算作他的伙伴;如果我能带一点货,他将给我最大的便利,说不定还可以赚点钱。
我立刻接受了他的盛意,并且和这位船主做了亲密的朋友。这位船主是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我便带了一点货物,同他一船走了。由于这位船主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赚了不少钱,因为我按照船主的指示,带了一批玩物和其他零碎货物,大约值四十英镑,这四十英镑是我用通信的方式靠几位亲戚的帮助筹集出来的,我想他们送给我的钱,大概是从我父亲或者我母亲那里弄来的,作为给我第一次出门的资本。
在我一生所有的冒险中,只有这次还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完全是靠了我那位船主朋友的正直无私的帮助。同时,在他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些数学知识和航海的规程,学会了怎样记录航程,怎样观测天文,总之,我懂得了一个海员所应懂的一切。他很乐意教我,我也乐意学。简单一句话,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一个海员,又成了一个商人。这次出门,我带回了五磅零九盎司金沙,回来之后,我把它在伦敦换掉,差不多换了三百英镑。这回的成功使我更加野心勃勃,因而也使我的一生完全断送。
就是在这次航行中,也有我的不幸,特别是由于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岸一带,靠近北纬十五度,有时甚至在赤道上,我在那种炎热的气候之下得了热病,三天两头生病。
现在我已经勉强算作一个几内亚商人了。可是,不幸的事发生了:我那朋友回国不久便死了,他船上的大副做了船主。于是我便搭了他的船出发,决定再走一趟。然而这次航行是有史以来最不幸的航行。因为,我这回虽然只带了一百英镑新赚的钱,把其余的二百英镑通通存在我的一位寡妇朋友那里,可是,这次航行,我却碰到了许多严重的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正向加那利群岛[13]驶去的时候,或者也可以说,正在加那利群岛和非洲海岸之间航行的时候,有一天,天刚亮,突然有一只从塞拉[14]来的土耳其海盗船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了过来。我们最初尽量把帆扯得满满的,希望逃脱,后来看见海盗船愈追愈近,一定会在几小时之内追上我们,我们只好准备战斗,我们只有十二尊炮,而海盗却有十八尊。到了下午三点,它终于追上了我们。它本来想横冲到我们的船尾上,不想冲错了,却横冲到我们的后舷上,于是我们把八尊炮搬到这一边,一齐开火。他们一面还击,一面向后退,同时他们船上的二百来人也一齐用枪弹向我们射击。因为我们的人都隐蔽得很好,所以一个都没有伤到。它极力向我们进攻,我们也极力抵御,可是第二次它换了方向,朝我们另外一面的后舷攻过来,有六十个人冲上我们的甲板,把我们的桅索等通通砍断。我们用枪弹、刺刀、火药和其他武器向他们反击,把他们打退了两次。我现在不忍再细说这段可悲的故事,总之,末了我们的船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我们死了三个人,伤了八个,只好屈服下来,全部被他们掳到了塞拉,那是摩尔人的一个口岸。
我在那里所受的待遇,并没有我起初所料到的那样可怕,因为我并没像别的人一样,被带到皇帝的宫里去,而是被留在海盗船的船长家里,做了他的战利品,做了他的奴隶,因为我年轻伶俐,很合他的需要。由于这种环境的突然变化,由一个商人一下子变成了可怜的奴隶,我完全灰心丧气了。我回想到我父亲的预言,说我一定要受罪,谁也救不了我,觉得他的话果然应验。现在我的处境实在再糟不过了,因为我已经受到了天谴,永无出头之日了,可是,唉,这不过是我的苦难的一个开头罢了,诸位,谈到下文,自然就会知道。
却说我的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之后,我满以为他再出海的时候,也把我带去,那么迟早总有一天他会被一艘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战舰拿获,那时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了。但这个希望不久便成了泡影:因为他每逢出海的时候,总是把我留在岸上看守他的花园,在他的家里做些奴隶的苦工;等他从海上巡逻回来时,他又命令我睡在船舱里,替他看船。在这里,我整天净想着逃走的问题,以及采用什么办法实现它,可是总想不出一点稍有希望的办法。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我完全没有逃走的条件,因为我并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可以做同伴,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奴隶,没有任何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所以,前后两年之中,我虽然经常用幻想安慰自己,却没有一点希望使我的幻想得以实现。
大约过了两年,我的环境忽然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变化,使我头脑里重新浮起争取自由的老念头。原来我的主人这时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不大去做他的海上生意了,据说,这是由于没有钱。每星期当中,他经常有一两次,如果天气好的话,有时甚至两次以上——坐着大船上的舢板,到海口去捕鱼。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叫我和一个名叫马列司科的小孩替他摇船。我们很能得他的欢心,确实我的捕鱼技术也很高明。因此有时他也叫我和一个与他有亲族关系的摩尔人以及那个叫马列司科的小孩,三个人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
有一次,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早晨,我们到海上去打鱼,忽然海上起了大雾,我们离岸还不到一海里,就看不见岸了。我们也摸不清东西南北,整整划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我们不但没有朝岸上划,反而划到海里去了,离岸至少有两海里光景。随后,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冒了很大的危险(因为那天早晨风吹得很硬,而且我们都饿得要命),才划了回来。
我们的主人受了这次意外事件的警告,决定以后要更加慎重,刚好他有一只从我们英国大船上夺来的长艇,于是他决意以后出海打鱼的时候要带一个罗盘和一些粮食。他命令他船上的木匠——也是一个英国奴隶——在那长艇的中间装一个小舱,像驳船上的小舱的样子,舱后还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容一个人在那里掌舵,拉帆索;前面也要有一个地方,容一两个人在那里管理船帆。这长艇上所用的帆,是一种三角帆,帆杠横垂在舱顶上。舱房做得又小巧又严密,可以容得下他自己和一两个奴隶在里面睡觉,还可以摆得下一张吃饭的桌子,上面还有一些小抽屉,里面放着几瓶他爱喝的酒以及他的面包、米、咖啡。
我们经常坐这艘小艇去打鱼,我的主人因为我很会替他捕鱼,没有一次不带我去,有一次,他吩咐下来,要同两三位在本地有地位的摩尔人一同坐这只船到海上去闲游或者打鱼。为了款待他们,他大做准备,头一天晚上就派人把许多食品送到船上,同时他又吩咐我把他那大船上的三支短枪和火药预备好,因为除了捕鱼之外,他们还想打鸟。
我依照他的指示,把一切都预备停当,到了第二天早晨,小艇也洗净了,旗子也挂上了,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等候他的客人来到。不料到了后来,只有我主人一个人来到船上,对我说,他的客人因为突然有事,临时改期,命令我同那个摩尔人和那个小孩照平常一样出去替他打点鱼来,因为他的朋友当晚要来他家里吃晚饭。并且吩咐我,一打到鱼就送到他家里来。这些事,我都准备一一照办。
这时候,我那争取解放的老念头,突然又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一只小船可以随我支配了。于是,等我主人走后,我就大胆筹备起来,可是我所准备的不是打鱼,而是航行的事宜,虽然我既不知道,也没有考虑过要把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反正只要能逃开这个地方就行。
我的第一个步骤是找一个借口,叫那摩尔人弄些粮食到船上来。我告诉他,我们不应该擅自吃主人的面包。他说这话不错,于是便弄来一大筐本地饼干,又弄了三罐子淡水,搬到船上。我知道我主人装酒瓶的箱子放在什么地方,虽然,它是从英国人手里夺来的。我乘那摩尔人到岸上去的时候,把它搬到船上来,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看来就仿佛原来就在那里一样。同时我又搬了六十多磅蜜蜡到船上来,又搬了一包线,一把斧子,一把锯,一把锤子。这些东西后来对我非常有用,尤其是蜜蜡,可以做蜡烛用。接着我又想出另外一个花样,他也上了圈套。他的名字叫伊斯玛,但是人们都叫他摩雷。于是我对他说:“摩雷,我们东家的枪现在都在小艇上,你能弄一点火药和子弹来吗?我们也许可以打些水鸟呢,我知道他的火药都是藏在大船上。”他说:“好,我去弄点来。”果然他又拿了一个大皮袋来,里面装着一磅半以上的火药;另外又拿来一个大皮袋,里面装着五六磅鸟枪弹和一些子弹,通通放到船里,同时我又在舱里找到了我主人的火药,我把一个半空的大瓶子里的酒倒在另外一个瓶子里,把火药装在里面。各种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我们便开船到港外去打鱼。港口入口处的堡垒里的看守因为早已认识我们,也不来注意我们,我们出港不到一海里路光景,就下了帆,准备打鱼。不料这时风向是东北偏北,正与我的愿望相反,因为,假如刮南风,我就有把握开到西班牙海岸,至少也可以到西班牙加的斯湾。尽管这样,我决定不管风向如何,总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其余一切,都听天由命。
我们打了一会儿鱼,什么都没有打到,因为每逢有鱼上钩时,我总不把它钓起来,让那摩尔人看见。我便对那摩尔人说:“这样可不行,我们不能这样伺候我们的主人,我们得走远点。”他觉得我这个提议没有什么害处,也就同意了。他本来在艇头,就扯起帆,我就掌着舵,一口气把艇开到将近一海里以外,才把艇停住,假装捕鱼。我把舵交给那个小孩,跨到那摩尔人身边,做出要在他身后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冷不防用手把他拦腰一抱,一下子丢到海里。可是他立刻浮出了水面,因为他游起泳来活像一个软木塞,他大声叫着我,求我让他上来,说情愿随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在艇后面游得非常快,差不多快赶上了我的艇;因为这时没有什么风,我的艇走得很慢。于是我走到舱里,取了一支鸟枪出来,对准他说,我并没有害他的意思,只要他不捣乱,我决不会伤害他。我说:“你泅水的功夫很好,一定可以游到岸上去,再说今天海上没有一点风浪,只要你好好地游到岸上去,我也不来伤害你,可是你若一定靠拢我的艇,我就把你的脑袋打穿;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恢复我的自由了。”
这样,他便转过身去,向岸上游去了。我完全相信,他后来毫不费力就游到岸上,他是一个出色的游泳家。
我本来可以把这个摩尔人留在身边,而把小孩淹死,但是我不敢信任他。他走之后,我便对那小孩——他的名字叫佐立——说:“佐立,假使你对我忠实,我将来会使你成为一个大角色;假使你不凭着穆罕默德向我发誓,表示没有二心,我就把你也丢到海里。”那孩子对我笑嘻嘻的,发誓说他情愿对我忠实,随我走到天涯海角,他那种天真的神气,使我没法子不信任他。
当我的艇还在游泳的摩尔人的视线之内的时候,我把它逆着风向,一直向海里开去,目的是让他们断定我是向直布罗陀海峡驶去(任何有脑筋的人都会这样做的)。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向南方开去,向那最荒芜的海岸开去,那边全是黑人的部族,必然会用他们的独木船把我们包围起来,加以杀害,只要我们一登岸,就必然会给野兽或是更无情的野人吃掉。可是,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就改变了方向,一直向东南驶去,差不多向正东驶去,为的是沿着海岸走。
这时风势极好,海面上也平静,照这样走下去,我相信到了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再见陆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塞拉以南一百五十英里以外,远离摩洛哥皇帝或任何国王的领土了。
可是,我已经被摩尔人吓破了胆,生怕再落到他们手里,加之风势又顺,于是也不靠岸,也不下锚,一口气竟走了五天。这时风势渐渐转为南风了,我估计着假使他们有人在追我,这时也要罢手了,于是我便大着胆子靠了岸,在一个河口上抛了锚。至于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纬度,什么国家,什么河道上,我一概不知道。这时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同时我也不愿意看到什么人,因为我所需要的只是淡水。我们在傍晚驶入了河口,决定一等到天黑就游到岸上去,看看岸上的情形。但是刚到天黑,我们便听到无数不知道名目的野兽的可怕的狂吠声、咆哮声、呼啸声,把那可怜的孩子吓得半死,哀求我等到天亮再上岸去。我说:“好吧,佐立,我不去就是了,不过,说不定到了白天就要碰见人哩,他们对我们也许比狮子还要凶猛。”佐立笑着说:“那么,我们可以用枪打他们,把他们打跑。”我见佐立这样高兴,心里很满意,于是我从主人的酒箱里取了一杯酒给他喝,给他壮壮胆子。我觉得佐立的意见很好,就依了他,下了小锚,静静地躺了一晚上。老实说,我们整夜都没睡。因为在两三小时以后,便有一大群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巨大的野兽跑到海边来,在水里打滚、洗澡、冲凉,那种啸叫怒吼的声音,真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佐立非常害怕,我也是一样。尤其使我们害怕的是,我们听见有一头巨兽向我们的船边游了过来,我们看不出它的形状,但是从它喷水的声音,可以听出它是一头硕大而凶猛的野兽。佐立说是一头狮子,我想也许是。佐立哭叫着要我拔起锚来,把艇开走,我说:“不用,佐立,我们可以把锚索系上一个浮筒,放得长长的,把艇向海里移移,它们不会跟我们走得太远的。”我的话还没完,只见那东西已经离我们不到两桨来远了。我立刻走到舱里,拿起枪来,朝它放了一枪,于是它立刻转过身子,向着岸上游去了。
枪声一响,那些野兽因为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声音,便漫山遍野地狂呼怒吼起来,那种可怕的情形,简直不能描述。这使我不能不相信,除了晚上不能上岸外,白天怎样上去也是问题:因为假使我们落到野人手里,那与落入狮子和老虎手里一样糟,至少我们对于这两种危险是同样担心的。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非要上岸去从那里弄一点淡水不可,因为我们艇里连一磅水都没有了。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弄。佐立说,如果我让他带一个罐子上岸,他可以看看哪里有水,替我弄点来。我问他为什么要自己去,为什么不让我去,由他守在艇上。他回答的话是这样情深义厚,使我后来永远爱上了他。他说:“如果野人来了,他们把我吃掉,你走开。”我说:“让我们两个人都去吧,佐立,如果有野人来,我们就把他们打死,我们谁都不让他们吃掉。”于是我给佐立吃了一块面包干,又从酒箱里取了一杯酒给他喝,然后把我们的艇向岸上适当地推近一些,一齐踏水上岸,除了枪械和两个盛水的罐子外,什么都不带。
我不敢走得离艇太远,恐怕有什么野人坐独木船沿河而下;可是那孩子,他看见一英里以外有一块低地,就信步向那边走去。不一会儿,只见他飞也似的向我跑来,我以为他是在被野人追赶着,或是给什么野兽吓着了,急忙跑上去救他。可是当我走近他时,却看见他肩膀上背着个什么东西,形状像一只野兔,可是皮色不同,而且腿也比较长,原来是他打死的野味。我们都很高兴,因为这东西的肉一定很好吃。但佐立那么欢天喜地跑回来告诉我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他已经找到了很好的水,而没有看见野人。
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去找水。只要沿着小河向上走一点点路,等潮水退了,就可以找到淡水;就是潮来的时候,潮水也上涨不了多远。于是我们把所有的罐子都盛得满满的,又把杀了的野兔吃下去,准备继续前进。在那一带,我们始终没有发现人类的脚印。
我过去曾到这海岸来过一次,很清楚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15]都离此不远。但是现在既没有仪器可以测量出我们这时是在什么纬度,同时又不清楚或是记得这些群岛是在什么纬度,当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它们,或是在什么时候应该离开海岸,向它们驶去。不然的话,我一定很容易找到这些海岛。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继续沿着海岸走,一直走到有英国人做生意的地方,只要遇到一些来往的商船,就会被他们救起来,把我们带走。
依我的估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一定是在摩洛哥王国和黑人国土之间。这地方一向荒凉无人,只有野兽;黑人因为怕摩尔人,放弃了它向南迁去;摩尔人由于它是一片不毛之地,认为不值得居住。此外,这两个民族都舍弃了这块地方还有一个共同原因,那就是这里盘踞着无数的猛虎、狮子、豹子和其他的猛兽。摩尔人只把这里当作打猎的地方,每次来的时候,都像军队一样,有两三千人。真的,我们沿着海岸走了差不多有一百多英里,白天所看到的只是一片荒芜,毫无人烟,夜间所听到的只是野兽的咆哮和呼啸。
有一两次,在白天,我仿佛远远看到了加那利群岛上的泰德峰的山顶,很想冒险驶过去,但是试了两次,结果都被逆风顶回来,同时海上的风浪很大,小船也走不了。因此,我决定依照原来的计划,沿着海岸走。
我们离开了那个河口之后,有好几次不得不上岸取水。特别有一次,在大清早,我们来到一个小地角[16],下了锚。这时正在涨潮,我们想等潮水上来以后,再往里面走走。佐立的眼睛比我尖,这时低声叫了我一声,要我把艇开得离岸远一点,他说:“你看那小山下边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在那里睡觉哩。”我顺着他的手望去,果然看见了一个怪物:原来在岸上,在一片山影下,正躺着一头极大的狮子。我说:“佐立,你上岸去把它打死吧。”佐立显出很害怕的样子说:“我把它打死,它会一口把我吃掉的。”于是我也不再对他说什么,只叫他不要动。我把我们最大的一支枪拿在手里,装上大量的火药,又装了两颗大子弹,放在一旁;然后又把第二支枪里装上两颗子弹,再把第三支枪里装了五颗子弹。我拿起第一支枪,尽力瞄得准准的,向那狮子的头上开了一枪。不料它这时正用一只前腿挡着鼻子躺着,子弹打了过去,正打在它膝头上,把腿骨打断了。它猝然惊起,先是大声咆哮,等发觉腿已经断了,又跌倒下去,接着又用三条腿站起来,发出难听的吼叫声。我见自己没有打中它的头,不由吃了一惊。这时它仿佛要跑开,我急忙拿起第二支枪来对着它的头部又是一枪,只见它颓然倒了下来,轻轻吼了一声,一个劲儿在那里挣命。这时候佐立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坚决要我允许他上岸。我说:“好,去吧。”于是他便跳进水里,一只手举着一支小枪,一只手划着水,走到那东西的眼前,把枪口放在它的耳朵边上,向它的头部又开了一枪,结果了它的性命。
这件事,对于我们,只能算作一种游戏,因为不能带来食物。我觉得,为了这样一个无用的东西耗费了三份火药和弹丸,未免不上算。可是佐立说他一定要从它身上弄点东西下来,于是他走上艇来,叫我把斧子给他。我说:“做什么,佐立?”他说:“我要砍它的头。”可是他却砍不下来,结果只砍了一只脚下来,把它带回来,那真是一只大得可怕的脚。
我心里盘算,它的皮也许对我们有点什么用处,便决定想法子把它剥下来。于是佐立和我便跑过去剥皮。对于这件工作,佐立比我高明得多,我却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这工作足足费了我们一整天,才把它的皮剥了下来,拿来铺在我们的舱顶上。不到两天,太阳便把它完全晒干了,后来我便垫着它睡觉。
这次停泊之后,我们一连向南走了十多天,对于我们那日渐减少的粮食,吃得非常节省,除了不得已取淡水以外,很少靠岸。我的计划是要开到非洲海岸的冈比亚河或赛纳加尔河,这就是说,要到佛得角一带,希望能够在那里遇到欧洲商船。万一遇不到的话,我就不知道往哪里去好了,只有去找我那些群岛,或是死在黑人手里了。我知道所有的欧洲商船,无论是到几内亚去、到巴西去,或是到东印度群岛去,总要从这个海角或这些群岛经过。总之,我把我的整个命运都放在这个唯一的机会上,要是不能碰到船只,就只有死的份儿了。
我抱着这种决心走了十天,就开始看到有人烟的地方。有两三个地方,在我们经过时,可以看见一些人站在岸上望着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漆黑的,并且周身一丝不挂。有一次,我很想上岸和他们接近,但佐立却替我当顾问,对我说:“不要去,不要去。”我把船靠近岸走,想同他们谈话;他们也沿着岸跟着我跑了一程。我注意到他们手里并没有武器,只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竿!佐立说,这是一种标枪,他们可以把它掷得很远,并且每发必准!因此我只好离得远远的,尽量用手势同他们交谈,并且做出手势,向他们要东西吃。他们叫我把艇停住,表示要替我们取一点吃的东西来!于是我落了顶帆,把艇停住。这时他们当中有两个人向村子跑去,不到半点钟的工夫,又跑了回来,带来两块干肉,一些谷类,这大概是他们的土产,但我们对这两样都不认识。我们很愿意接受他们,但怎样去接受却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既不敢接近他们,他们也同样地怕我们。结果他们总算替我们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先把东西放在岸上,远远地躲开,一直等我们把东西拿到艇上来,才又走近我们。
我们做手势向他们致谢,因为我们拿不出东西来报答他们。可巧这时正有一个机会到来,使我们大大地还了他们的情。因为当我们正停在海边的时候,突然有两只很大的怪兽从山里冲到海边来,看那样子,仿佛是其中的一只正在追逐着另外一只。究竟它们是雌雄相逐、是相戏,还是相斗,我们也弄不清楚。同样,我们也摸不清这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呢,还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但是照情形看来,我想是后者的成分居多。因为,第一,这些残猛的兽类一般在白天不大出现;第二,我们看见那些黑人这时非常害怕,特别是女人们。除了那拿标枪的之外,其余的人都逃开了。可是那两只野兽跑到水边,并没有去袭击那些黑人,只是一齐跳到海里,游来游去,好像在游戏。后来,其中有一只出乎意料,竟跑到我们艇跟前来了。可是我早就准备好了,把我的枪装上了弹药,又叫佐立把另外的两支枪也装好了,等它走到射程以内的时候,我一枪打去,正打中它的头部。它立刻沉下去了,但马上又浮了起来,在水里上下翻腾,仿佛在做垂死的挣扎,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它拼命想往岸上游,但因为受到致命的伤,又被水所窒息,还没有泅到岸上就死了。
那些可怜的黑人听见我的枪声,看见火光的时候,那种惊慌失措的神情,真是再也形容不出来。有几个甚至吓得半死,一跤跌在地上。后来他们看见那怪兽已经死掉了,而且已经沉到水里去了,又见我向他们招手,叫他们到海边来,他们才壮起胆子,到海边上来搜寻那死兽。我根据它的血水,找到了它的下落,又拿一根绳子把它套住,把绳头递给那些黑人,叫他们去拖,他们把它拖到岸上,只见是一只很奇特的豹,满身黑斑,非常美丽。那些黑人一齐举起手来,表示他们的钦佩,想不出我是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死的。
另外一只怪兽,受了火光和枪声的惊吓,早已泅到岸上,一溜烟跑回山里去了。我离它很远,也看不出它到底是一只什么东西。我很快地看出那些黑人有意思要吃那豹子肉,因此乐得把它送给他们,作为人情。当我向他们打手势,表示他们可以把它拿去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感激,马上动起手来。他们虽然没有刀,却用一块削薄了的木片,一会儿工夫就把豹皮剥了下来,真比我们用刀子还要便当。他们送了一些肉给我们,我不要,做手势表示全部送给他们,不过表示要那张豹皮,他们立刻满不在乎地给了我。他们又弄了许多粮食给我,我虽然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但还是接受了。接着我又打着手势,向他们要水;我把一只罐子拿在手里,把它口向下翻过来,表示里面已经空了,希望把它装满。他们立刻把这意思通知他们的同伴,不久便有两个女人抬来了一个很大的泥缸(这泥缸,据我猜想,大概是用阳光焙制的),她们把这泥缸放在地上,照以前那样躲开,我叫佐立把我的三只水罐提到岸上,把它们通通装满。那些女人也跟男人一样,全部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杂七杂八的粮食,又有了清水,便离开了那些友好的黑人,一口气又走了十一天,没有靠一次岸。后来我看见离我四五海里[17]之外,有一片陆地,长长地伸到海里。这时风平浪静,我便离开海岸,绕着这小岛走。当我保持着离岸两海里的距离绕过这小岬以后,我又发现,岛的另外一边,海里也有陆地。于是我便断定这边是佛得角,而那边是佛得角群岛。但是,这些岛都离得很远,简直使我一筹莫展,因为如果遇见大风,那就连一个地方也走不到。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之下,我愁眉不展地走进舱房,坐了下来,让佐立去把舵。突然之间,那孩子叫了起来:“主人,主人,一只带帆的船!”原来这可怜的孩子吓昏了头,还以为是他东家派船来追我们了。但是我却很清楚,我们已经离得很远,他们是再也追不到了。我跳出舱一看,不但立刻看出是一只船,还看出它是一只到几内亚海岸装运黑人的葡萄牙船。可是,我再把它的行驶方向一看,便看出它是向另外的方向走的,并不打算靠近海岸。于是我拼命把艇向海里开去,决定尽可能同他们搭话。
我虽然把帆扯得满满地向前赴去,但不久就看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横插到他们的航路上去,不等我发信号,他们就要过去的。可是当我拼命扯满帆追了一程,正要绝望的时候,他们似乎已经用望远镜看见了我,并且看出我所开的是一个欧洲式的小艇,料定它是属于某一个失事的船只的,因此他们便落了帆,等我走近。这个举动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的艇上本来有我东家的旗帜,就把旗帜向他们摇了一摇,发出危急信号,又鸣了一响枪。这两个信号他们都看见了;因为他们后来对我说,他们虽然没有听见枪声,却看见了硝烟。他们看到信号,便停了船等我,又过了大约三小时,我才靠拢了他们的船。
他们用葡萄牙语,用西班牙语,用法语,问我是什么人,但是我通通不懂。末了船上有一个苏格兰水手过来,我告诉他我是英格兰人,刚刚从塞拉的摩尔人手里逃出来。于是他们便叫我上了船,把我和我的一切东西都收留下来。
谁都会相信,我从这样一种困苦绝望的处境里得到救援,该有怎样说不出来的喜悦,我立刻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船主,报答他救命之恩,但是他却慷慨地对我说,他什么都不要我的,等我到了巴西时,我所有的一切都要交还给我。“因为,”他说,“我救你的命,不过是希望将来有人救我的命,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碰到同样的情形哩。再说,我把你载到巴西之后,你离家乡那样远,如果我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拿去,你一定会挨饿的,那不等于我救了你的命,又害了你的命吗?不行,不行,英国先生,我把你载到那里去,完全是慈善性质,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在那里过活,做你回家的盘费。”
他不仅提出了这种慈善的建议,还一丝不苟地实践了他的建议。他下令给船员们,不准任何人动我的东西,后来索性把所有的东西收归他自己保管,开了一张清单给我,让我以后便于提取,甚至连我的三只瓦罐也不例外。
他看见我的小艇很好,便对我说,他很想把它买下来,放在船上使用,问我要多少钱,我对他说,他在各方面都对我这样慷慨,这只小艇我实在不好说价,随便他好了。于是他对我说,他先给我一张西班牙金币的期票,到巴西去取;如果到了那里,有人出更高的价,他一定照数补足。他又出了六十西班牙金币想买我的佐立,可是我不肯接受。我并不是不愿意把他卖给船主,而是因为他曾忠心地帮助我获得自由,现在我实在不愿再把他的自由出卖。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了他,他觉得很有道理,并且向我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同那孩子订一个契约,如果他信了基督教,十年以后就还他自由。我听见了这句话,同时又见佐立本人也情愿跟他,才把他让给船主了。
我们一路顺利地向巴西驶去,大约过了二十二天,便抵达了万圣湾。现在,我已经从最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解救,以后究竟怎么办,不得不加以考虑了。
那船主待我的好处,真是记不胜记。他不但不要我的船费,还用二十块威尼斯金币买了我的豹皮,用四十块威尼斯金币买了我的狮皮,又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如期交还给我。而且,凡是我愿意出售的东西,如酒箱、枪支和我制作蜡烛所剩的一块蜡之类,他都一一买去。简单一句话,我把我的货物一共变换了二百二十块西班牙金币,带着这笔钱,我在巴西上了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