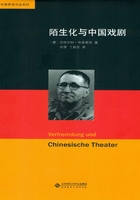
正文
在这篇文章里简短地论述一下中国古典戏剧中的陌生化效果的运用。这种效果终于在德国被采用乃是在尝试建立非亚里士多德式(不是建立在感情共鸣的基础上)的戏剧,亦即史诗剧的时候。这种尝试就是要在表演的时候,防止观众与剧中人物在感情上完全融合为一。接受或拒绝剧中的观点或情节应该是在观众的意识范围内进行,而不应像沿袭至今的情况那样,在观众的下意识范围内达到。
在往昔一年一度的民间集市的戏剧和绘画中,就已经可以看到这种使观众对被表现的事件感到陌生的原始阶段尝试。马戏团丑角演员的说话方式和全景的绘画手法就采用了这种陌生化的艺术手法。在德国的许多一年一度的集市中展出的《勇敢的卡尔在姆尔顿战役后的逃遁》的复制品的绘画手法是不足取的,但由于它采用陌生化的艺术手法(这点原画不如复制品),因而使人感到这种不足并非由于复制者才能的欠缺。正在逃跑的统帅,他的战马和随从以及田野风光都完全有意识地这样被描绘,令人对画中情景顿时产生发生了非常事件和大难临头的印象。画家虽有不足之处,但却出色地表现出了不期而遇的效果。惊异驾驭着他的画笔。
中国古典戏曲也很懂得这种陌生化效果,它很巧妙地运用这种手法。人们知道,中国古典戏曲大量使用象征手法。一位将军在肩膀上插着几面小旗,小旗多少象征着他率领多少军队。穷人的服装也是绸缎做的,但它却由各种不同颜色的大小绸块缝制而成,这些不规则的布块意味着补丁。各种性格通过一定的脸谱简单地勾画出来。双手的一定动作表演用力打开一扇门等。舞台在表演过程中保持原样不变,但在表演的同时却把道具搬了进来。所有这些久已闻名于世,然而几乎是无法照搬的。
要与一种习惯决裂而去整个采用另一种艺术表现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当人们在许多效果中要去研究其中一种的时候,这却是需要的。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在中国古典戏曲中是通过下面的方式达到的:
中国戏曲演员在表演时,除了围绕他的三堵墙之外,并不存在第四堵墙。他使人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的表演在被人观看。这种表演立即背离了欧洲舞台上的一种特定的幻觉。观众作为观察者对舞台上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产生视而不见的幻觉。欧洲舞台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丰富的技巧,把演员隐藏在四堵墙中,而各种场面安排又让观众看清楚,这种技巧就显得多余了。中国戏曲演员总是选择一个最能向观众表现自己的位置,就像卖艺人一般。另一个方法就是演员目视自己的动作。譬如,表现一朵云彩,演员表演它突然出现,由轻淡而发展成为浓厚,表演它的迅速的渐变过程,演员看着观众,仿佛问道: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但是演员同时看着自己手和脚的动作,这些动作起着描绘检验的作用,最后也许是在赞美。演员清晰的目光看着地面,舞台为他提供的艺术创造的空间内并不存在什么破坏演员想象力的东西。演员把表情(观察的表演)和动作(云彩的表演)区分开来,动作不因此而失真,因为演员的形体姿势反过来影响他的脸部表情,从而使演员获得他的全部表现力。这样,他就得到一种成功的有控制的表现力,一种完美的胜利!演员借助他的形体动作描绘出脸部表情。
演员力求使自己出现在观众面前时是陌生的,甚至使观众感到意外。他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是因为他用奇异的目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表演。这样一来,他所表演的东西就使人有点儿惊愕。这种艺术使平日司空见惯的事物从理所当然的范畴提高到新的境界。表演一位渔家姑娘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船。现在河流越来越湍急,掌握平衡越来越困难;眼前她来到一个河湾,小桨摇得稍微慢些,看,就是这样表演驾驶小舟的。然而,这个驾驶小舟的故事好像是有历史根源的,许多歌曲传诵着它,这不是一般的划船,而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故事。这个闻名的渔家姑娘的每一个动作都构成一幅画面,河流的每一个拐弯都是惊险的,人们甚至熟悉每一个经过的河湾。观众这种感情是由演员的姿势引起的,她就是使得驾舟表演获得名声的那个姑娘。这些场面让我们想起皮斯卡托[1]导演的《好兵帅克》中赶赴布德魏斯(即布迪尤维斯——译注)的行军。帅克三天三夜日顶太阳夜披月光赶赴前线的行军分明是难以实现的,这完全是历史地来看这次行军,作为一个事件,它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点上并不亚于拿破仑在1812年向俄国进军的场面。
演员在表演时的自我观察是一种艺术的和艺术化的自我疏远的动作,它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并十分出色地创造出二者之间的距离。但这绝不排斥观众的感受,观众对演员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观察者来感受的,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就这样被培养起来了。
中国戏曲演员的表演对西方演员来说会感到是很冷静的。这不是中国戏曲抛弃感情的表现!演员表演着饱含巨大热情的故事,但他的表演不流于狂热急躁。在表演人物内心深处激动的瞬间,演员的嘴唇咬着一绺发辫,颤动着。但这好像是一种程式惯例,缺乏奔放的感情。很明显这是在通过另一个人来重述一个事件,当然,这是一种艺术化的描绘。表演者表现出这个人已经脱离了自我,他显示出他的外部特征。这样恰如其分地表现的脱离自我,或许也有不合适的地方,那就是舞台所不需要的。无论如何,从大量的标志当中选择特殊的东西,显然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愤怒自然和不平有区别,憎恨和厌恶也不同,爱情和同情又是两回事,但这许多不同的感情动作都是简朴地表演出来的。演员表演时处于冷静状态,如上所述乃是由于演员与被表现的形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力求避免将自己的感情变为观众的感情。谁也没有受到他所表演的人物的强迫;坐着的不像是观众,却像是亲近的邻居。
西方的演员则用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地引导他的观众接近被表现的事件和被表现的人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演员让观众与自己的感情融合为一,并用尽他的一切力量将他本人尽量无保留地变成另一个人,即他所演的剧中人物。当这种毫无保留地变成另一个人的表演获得成功的时候,演员的艺术就差不多耗尽了。演员一旦变成了被表现的银行出纳员、医生或者将军,这样他所需要的艺术本领就像“生活当中”的银行出纳员、医生或将军那样少。这种毫无保留地变成另一个人的表演是非常艰苦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了一系列艺术方法,提出了整个体系,凭借他称之为创造情绪的这类东西,强制演员在每次演出中不断产生新的情绪。对一个演员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很难持久地作为另一个人来感觉。这样他很快就开始感到精疲力竭,而只能在一定的姿势、外部动作中和声调上去摹拟另一个人,这样一来,在观众中引起的效果就要可怕地被减弱了。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创造另一个人是—种“直觉”的,亦即一种模糊状态的行动,是在下意识中进行的;而下意识的控制作用是极其微弱的:这就是一种拙劣的记忆。
中国戏曲演员不存在这些困难,他抛弃这种完全的转化。从开始起他就控制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完全融合在一起。他用什么艺术手段做到这一点呢?他只需要一点儿幻想。他所表现的东西,即使对一个不善于思考的人也是值得一看的。有哪一位沿袭老一套的西方演员(这一个或另一个喜剧演员除外)能够像中国戏曲演员梅兰芳那样,穿着男装便服,在一间没有特殊灯光照明的房间里,在一群专家的围绕中间表演他的戏剧艺术的片断呢?譬如说,能够表演李尔王[2]分配遗产或奥赛罗[3]发现手帕吗?如果他那样做,将会产生像一年一度的集市上魔术师玩把戏的效果,没有一个人看过他一次魔术以后还想再看第二遍。他所表演的,仅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而已。催眠状态过后,剩下来的就是一些糟糕透顶无动于衷的表情,一种匆促掺拌起来的商品,在黑夜里售给匆匆赶路的顾客。当然,没有一个西方演员会这样把自己的货色陈列出来的。艺术的神圣在哪儿呢?是转化的神秘教义吗?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不自觉地做出来的,否则将会失去价值。与亚洲戏剧艺术相比,我们的艺术还被拘禁在僧侣的桎梏之中。诚然,我们的演员们越来越难于完成这种神秘的毫无保留的转化,他们的下意识的记忆将日益减弱。这样即使是一个秉有天赋的人,在损害直觉的情况下,作为阶级社会中一个成员,他也几乎不可能去吸取真理了。
要求演员每天晚上都产生某种感情冲动和情绪,这是艰难费力的,相反,让他表演人物的那些伴随着感情冲动而来,并能表现出感情冲动的外部标志,那就简单得多了。当然这不是要借用这种感情冲动去感染观众。陌生化效果不是出现在没有感情冲动的形式里,而是出现在感情冲动的形式中,感情冲动对被表现的人物是无需掩饰的。忧伤的凝视可使观众感到快乐,愤怒的目光也许让观众觉得憎恶。当我们在这里说感情冲动的外部标志的表演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这样的表演和这样的标志选择,感情冲动之所以产生感染作用,就是由于演员自身产生着表演的感情冲动,他正是在这种感情冲动中来表演这些外部标志。例如:通过声音的抑扬和呼吸的控制,同时紧缩颈部肌肉,这时血液冲上头部,演员就轻而易举地使自己产生了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出现效果的。相反,在另一种情况下倒会出现效果,当演员在特定的场合,不需要过渡,而用一种机械方法,用两只手把脸遮住,把手中藏着的白粉抹在险上,脸部立即变得极其苍白。这样,演员就把一个显然被抓住的事物本质诉诸于观众的视觉,他的恐怖随即在此处(由于这消息或这一发现)引起陌生化效果。这样的表演就更加健康一些,对于我们这样思考着的人显得更有价值一些。这种表演要求大量的人类知识、生活智慧并对社会重要的事物具有敏锐的理解能力。显然,这儿也要经历一个创造过程:这是一种更高的创造,因为它已提高到意识的范围里。
“陌生化效果”表演方法显然并不为矫揉造作的表演提供条件。人们绝不应把它理解为流行的风格化。恰巧相反,陌生化效果是和表演的轻松自然相联系的。只是当演员在检验自己表演的真实性的时候(这是一个必需的剖析,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其体系中为此费尽了心血),就不仅要依赖自己的“自然感觉”;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通过与现实的比较来纠正自己的表演(一个发怒的人真的是这样说话的吗?被遇见的那个人是这样坐到椅子上去的吗?),这就是说从外部,通过其他人物来纠正自己的动作。他这样表演,几乎在每句台词之后,观众都能产生判断,甚至每一个表情观众都能加以鉴别。
中国戏曲演员不是置身于神智恍惚的状态之中。他的表演可以在任一瞬间被打断。他不需要“从里面出来”。打断以后他可以从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表演下去。我们打扰他的地方,并不是“神秘创造的瞬间”。当他登上舞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创造的形象已经完成。在他表演的时候,改变他周围的环境,对他不会有什么妨碍。不停动作的两只手已足以使他在观众面前完成他的表演。当梅兰芳表演一位少女之死的场面的时候,一位坐在我旁侧的观众对表演者的一个动作发出惊讶的叫声。接着就有几个坐在我们面前的现众愤怒地转过头来,向他作嗤以示抗议。他们的感觉就像真的面对着一位贫穷的、正在死去的少女。他们这种态度对一场欧洲戏剧的演出也许是正确的,但对中国戏曲演出却是非常可笑的。陌生化效果对他们没有发生作用。
把中国戏曲中的陌生化效果作为一个可以移动的技巧(即与中国戏曲脱离的艺术概念)去认识,这不是简单的事。中国戏曲对于我们似乎出奇地矫揉造作,它表现人的热情是机械的,它对社会生活的解释是凝固而错误的,乍一看去,这种伟大的艺术对于现实主义和革命戏剧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吸取的东西。陌生化效果的动机和目的对我们都是奇异而又可疑的。
当我们欧洲人看中国人表演的时候,首先将遇到一个困难,就是要从他们的表演所引起的惊愕感情中解脱出来。人们必须明白,他们的表演在中国观众中也会引起陌生化效果。无须否认,更加困难的是,当中国戏曲演员创造出一个神秘的印象,而他却不想为我们揭开它的谜底。他从自然界的许多神秘中(特别是人的秘密),造成他自己的秘密,他不让你看出他是怎样把自然现象显示出来的;同时,即使他对自然界的现象还没有深入认识,他就被允许去显示自然了。我们站在一种原始技巧,一种科学初级阶段的艺术表现面前。中国戏曲演员像从魔术的符箓里获得他的陌生化效果。“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却仍然不可思议,知识是诡秘的东西,它在细心照料并从其秘密当中汲取好处的人的手中,就显得更加微小;然而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深入到自然现象里去,这种创造的才能就提出了问题,而在未来,研究家就得辛勤地去探索这些自然现象,并使它变成能够被人们理解和控制,通俗易懂的东西。对事物首先得具有探究的立场,事物之所以显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和不可掌握,原因即在于此。中国的戏曲演员使自己置身于惊愕状态之中,并去运用陌生化效果。认为“二乘二等于四”的公式是理所当然的人,不是一个数学家,他还是一个并不理解这个公式的人。当一个人第一次看见一根绳子吊着一盏灯在摇摆着的时候,他会惊奇地观看它,而且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感到非常奇怪。灯为什么摆动呢?为什么它偏偏这样摇摆而不那样摇摆呢?这种追问探索使他逐步接近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从而最后支配它。不要简单地张口叫喊:“你说的这种态度只适合于科学,而不适合于艺术。”为什么艺术就不能以它自己的方法,去探索为支配生活的伟大社会任务服务呢?
事实上,只有那些把这样一种技巧作为特定社会目标的需要的人们,才能够在研究中国戏曲的陌生化效果中获得益处。
新的德国戏剧的实验完全独立自主地发展着陌生化效果,到目前为止,它并未受到亚洲戏剧艺术的影响。
在德国的史诗戏剧中,不但通过演员来达到陌生化效果,而且通过音乐(合唱、歌曲)和布景(字幕、电影等)创造陌生化效果。它的目的主要是使被表现的事件历史化。在这方面可以做如下理解。
资产阶级戏剧把表现的对象变成没有时间性的东西。对人的表现则依赖所谓永恒的人性。借助故事的安排创造出一些“一般化”的环境,使各个时代各种肤色的人随便都能在这些环境中表现出来。一切事件都只是夸张的台词,在这种台词后面得出的“永恒”的回答,那就不可避免是习以为常的、自然的,同时也即是人性的回答。一个例子:黑人像白人一样地恋爱,一旦当他在故事中为情敌所迫,被白人陷害之后(据说他们在理论上能够把这个公式倒置过来),艺术的环境就创造出来了。特殊的不同的东西在台词中说明:回答是共同的,在回答里没有不同东西。这种见解可能承认历史的存在,但这是一种缺乏历史内容的见解。某些环境在变更,情势在变北,但人始终不变。历史只对情势发生作用,对人则不起作用。情势是孤立而不重要的,它纯粹只是作为机缘被理解,是一种可变的容量,一种独特的非人性的东西,它可以离开人而单独存在。情势作为一个封闭着的统一的东西出现在人的面前,人总是不可改变的,是一个固定的容量。对于人的理解就是情势的变化,对于情势的理解就是人的变化,这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对情势的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即具有历史性的思想。为了缩短历史哲学的浏览过程,举一例作为说明,舞台上表演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姑娘离开她的家到大城市去工作(皮斯卡托的《美洲的悲剧》)。对于资产阶级戏剧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显然,这是一个故事的开头,人们之所以要经历这件事,是为了了解下文,或者说是为了紧张地等待下文的发展。演员在这里几乎用不着进行幻想,就一定意义说,这个故事是很一般的,年轻姑娘找到了工作岗位(如果她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紧张起来)。这个事件只在这一点上是特殊的:这个姑娘走了(假如她留下来,后面的事情将不会发生)。家里让她走,这不是要探讨的事,这是可信的(动机是可信的)。但对历史化的戏剧来说,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日常发生着的事件最需要探讨,要全力研究它独有的特殊的东西。为什么这个家庭让一个成员离开它的庇护,今后她不再需要帮助,而能独立谋生了吗?她能够做到吗?作为家庭的一员,她学过什么东西,这能够帮助她获得生计吗?难道许多家庭都不能抚养自己的孩子吗?孩子成了家庭的累赘了吗?这难道是世界遵循的轨道,人们都奈何它不得吗?当果子熟透的时侯,它就从树上掉下来,这句话在这儿适用吗?是不是孩子们总有一天要去独立生活?每个时代都这样吗?是所有家庭都这样吗?是过去和现在都如此?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因为人是生物的缘故,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否都采取同样方式,出自同一原因,因而得到相同结果呢?这些就是演员需要回答的问题(或者是问题的一部分),假如他想把这个事件作为历史的不可重复的东西来表现,同时又想表达一种伦理习惯的话,就能启示人们去理解一个特定(短暂的)时代的社会的整体结构。这个事件要怎样表现才能显示出它的历史特征呢?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不幸时代的混乱状态引起人们的注意呢?当母亲在被劝告和道德要求下为女儿收拾一个很小的箱子的时候——应该怎样表现呢?这么多的要求和这样少的衣服?为终生着想的伦理要求,而面包却只能应付五个钟头?当母亲把小箱子递给女儿的时候,这位女演员应该怎样来说这句话,“就这样吧,我想这足够啦”,才能让它作为历史性的语言而被人们所理解呢?只有采用陌生化效果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位女演员不能把这句台词当作她个人的事情来说,她必须从批判的角度使人们明白她的意图,把这句话变成对社会的抗议。这种效果只能在长期钻研的基础上表达出来。在纽约一家很进步的犹太语剧院,我看过一出斯·奥尔尼茨(S.Ornitz)描写一位东城区[4]青年怎样成为一个非常腐化的律师的戏。这家剧院不会演这出戏。舞台上出现这样的场面:这个年轻律师坐在他屋子前面的街道上,接受各种关于法律事件的询问,收费极少。一个年轻妇女陪着一个被交通事故伤了脚的女人来了。但是在受伤者还没提出损伤赔偿要求的时候,事情就被草率地了结了。她绝望地指着她的脚大声喊道:“伤口已经好了!”这个剧院没有采用陌生化效果,无法在这个很不寻常的场面里把一个血腥时代的恐怖事件表现出来。观众中很少有人注意她,几乎没有—个人过后还能想起她的惊叫来。这个女演员的叫喊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正是在这个地方,这样一种控诉在贫苦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演员应该作为一个仿佛从地狱深处归来的受惊的使者,把这控诉告诉观众。为了这个目的,演员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技巧,将特定的社会状态的历史事实强调出来。这只有陌生化效果能够做到。没有这种效果,她就只能看见她怎样从容地完全变成舞台形象。在阐明一些新的艺术原则并创立一些新的表演方法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被历史时代更替所支配的任务出发,看到重新阐释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在出现。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受到检验,一切都应从社会的立场出发加以考察。在各种艺术效果里,一种新的戏剧为了完成它的社会批判作用和它对社会改造的历史记录任务,陌生化效果将是必要的。
[1] 即埃尔温·皮斯卡托尔(1893—1968),德国著名导演。1919年倡导政治性“时代戏剧”,20世纪20年代在柏林导演过许多进步剧本,当时影响很大。
[2] 指莎士比亚剧本《李尔王》中的主角李尔。
[3] 指莎士比亚剧本《奥赛罗》中的主角奥赛罗。
[4] 指纽约贫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