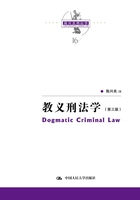
一、立法论的思考与司法论的思考
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一文中,对法学作了以下描述:
根据法学思想的原则,人们制定了精确的法典,它部分地受到逻辑力量的限制,部分地受到传统中既定法律规范的限制,当某些合法的规则和某些解释方法被认为有约束性时,法律思考就出现了。是否应当有法,以及人们是否应当恰当建立这些法律规范———这些问题是法学回答不了的。它只能声称:如果人们希望有这种结果,根据我们的法律思想规范,这种规范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合适手段。[1]
韦伯的上述论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法学思维方法论问题:关于法律的思维与根据法律的思维。这个问题,对于法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刑法学中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首先讨论刑法方法论之一:立法论的思考与司法论的思考。
立法论的思考是指关于法律(about law)的思考,而司法论的思考是指根据法律(by law)的思考。在上述两种思维过程中,法律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在立法论中,法律是思考的客体;而在司法论中,法律是思考的根据。当然,韦伯所说的法学,是指司法论,即法教义学。因为韦伯说那些是否应当有法,以及人们是否应当恰当遵守这些法律规范等问题,法学是回答不了的。这些问题都是关于法律的思考,属于法哲学的范畴,是对法的形而上的思考。
在刑法学中,可以分为立法论与司法论,而司法论也称为解释论。以此为标准,可以将刑法学分为立法的刑法学与司法的刑法学,前者是广义上的刑法学,后者是狭义上的刑法学。日本大谷实教授十分形象地把刑法解释学称为临床医学,而基础刑法学则是基础医学。当然,大谷实教授并没有进一步指出刑法解释学与基础刑法学的区别。[2]而且,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荣坚教授把自己的刑法体系书称为《基础刑法学》,而这恰恰是一部刑法解释学的著作。
我认为,刑法解释学与基础刑法学的区别,主要在于思维方法上的差异,即刑法解释学采用司法论思考方法,即根据法律的思考,而基础刑法学是采用立法论思考方法,即关于法律的思考。上述区分,究其根源来自休谟及康德的自为与当为、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区分论。根据休谟的观点,“是”与“不是”是一种事实判断,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而“应当”与“不应当”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两者应当严格加以区分,即,从“是”与“不是”的关系中不能推论出“应当”与“不应当”的关系。康德接受了休谟的这一思想,从中引申出事实科学与规范科学的区分:事实科学探讨的是自然法则,而规范科学探讨的是道德法则。自然法则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服从于实然律;道德法则是一个“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服从于应然律。可以说,立法论的思考是一个“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而司法论的思考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前者是对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评判,而后者则是以法律为逻辑起点的推理。应该说,这两种思考方法的规则是不同的,但我们往往混淆,即使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对于这两者都会混为一谈,更何况社会公众。
案例1—1 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
对于该案,检察机关以嫖宿幼女罪对冯支洋等人起诉,在媒体上被披露以后,引起轩然大波,许多网民认为对冯支洋等人的行为不应当定嫖宿幼女罪,而应当定奸淫幼女罪,因为奸淫幼女罪重于嫖宿幼女罪。甚至个别律师也主张定奸淫幼女罪。该案几经波折,于2009年7月24日作出了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冯支洋等人的行为构成嫖宿幼女罪,分别判处7年至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判决之后,我受邀就该判决撰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短文加以法理的阐述,意在疏导民意。我是从立法论与司法论相区别的角度切入的,因为社会公众并不关注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而只是用自己朴素的感情对判决作出评价,因而其结论有时会出现偏颇。对此,需要引入立法论与司法论的不同视角,为法院作一些解脱。我的短文刊登在2009年7月27日的《贵州日报》上,全文如下:
上述短文在新华网法制频道转载以后,被不少网站转载。我上网查看了一下网友的评论,虽然仍有个别谩骂性留言,但还是将人们的视线从司法转向立法。
不仅社会公众往往混淆立法论与司法论的思考,而且我们学者有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刑法知识论》一书中我曾说过以下这段话:
在一些刑法著作中,时常发生语境的转换,由此带来理论混乱。例如,为证明某一理论观点正确,常引用某一法条作为证据;为证明某一法条正确,又常引用某一理论观点作为证据。这种在理论与法条之间的灵活跳跃,完全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态度。问题在于:在刑法解释学的语境中,法律永远是正确的,需要通过理论去阐述法条。而在刑法法理学的语境中,法理是优先的,是法条存在的根据,因而可以评判法条。如果这两种语境错位,则只能使刑法法理学与刑法解释学两败俱伤。[3]
法教义学的逻辑前提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法律永远是正确的。由此可以引申出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对于这一法律格言,张明楷教授做过以下阐述: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Lex non debetesse ludibrio),而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不应受裁判(Non sunt judicondoe leges),而是裁判的标准,我并不倡导主张恶法亦法(Duralex,sed lex),但也不一概赞成非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Lex injusta non est lex),而是主张信仰法律,因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4]。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随意批评法律,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而应当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对于法学者如此,对于裁判者更应当如此。“裁判者只有适用法律的职务,却没有批评法律的权能。裁判者只能说这法律是怎样怎样,却不能主张法律应该是怎样;所以立法的良恶在原则上是不劳裁判者来批评的……要晓得法律的良与不良,是法律的改造问题,并不是法律的适用问题。”[5][6]
我注意到在该书第3页注①中,张明楷教授说:“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刑法学实际上演变为刑事立法学,而不是刑法解释学。”该书是1999年版的,过去十年是指从1989年到1999年这十年间。大家知道,我国1997年进行了刑法修改,从1989年以后我国刑法学基本上是以刑法的修改、完善为中心议题,从而形成了刑法立法学的研究局面,立法论思考大行其道,司法论思考受到遮蔽,刑法解释学没有更大进展。在2000年以后,我国才开始真正进行刑法解释学的研究。由此可见,刑法解释学是刑法学研究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刑法学就是刑法解释学。奥地利著名法学家凯尔森创立了纯粹法学派,其所谓纯粹法学就是采用司法论思考方法的法学,绝对排斥在法学中的形而上的思考。凯尔森指出:
纯粹法理论之旨趣唯在于认知其研究对策。换言之,其试图回答“何谓法律”或“法律从何而来”,而无意于对“法律应当如何”或“法律应如何制定”等问题作解释。本理论乃是法律科学而非法律政策。[7]
凯尔森之所谓法律科学与法律政策的区分,就相当于在刑法学中刑法解释学与其他刑法学的区别。刑法解释学,从字面上看,就是对刑法进行解释而形成的学问。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解释或者注释存在某种误解,因此,刑法解释学一词名声不太好。其实,在德国刑法学中另有一个概念,就是刑法教义学(也有翻译为刑法信条学的,我则称为教义刑法学),似乎更为恰当地揭示了这一学科的性质。德国学者考夫曼曾经对法哲学与法教义学作了区分,并阐述了法教义学的内容,指出:
法哲学并非法学,更非法律教义学。据康德,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解释理性的独特过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当做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法律教义学者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不是指法律教义学必然诱使无批判,但即便是在批判,如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审视,这总是在系统内部论证,并不触及现存的体制。在法律教义学的定式里,这种态度完全正确。只是当它把法哲学和法律理论的非教义学(超教义学)思维方式,当做不必要、“纯理论”甚至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拒绝时,危险便显示出来。[8]
考夫曼认为,法哲学与法教义学同样重要,不可互相取代,它们属于不同种类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教义或者信条呢?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里主要涉及教义与法律、信条与法条的关系。教义能否等同于法律?信条能否等同于法条?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
刑法信条学是研究刑法领域中各种法律规定和各种学术观点的解释、体系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学科。[9]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注①中,罗克辛对信条一词作了以下解释:
“信条(Dogma)”是一个希腊词,意思很多,例如“观点(Mein-ung)”,“指令(Verfügung)”,“理论原则(Lehrsatz)”。
由此可见,信条并不能等同于法律或者法条。教义学是一种对待法律的态度,就像对待宗教戒律一样来对待法律,因而它包含了对法律的信仰,摒除了对法律批评的可能性,例如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教义一词本身具有“先验”的特征。教义学还是一个以法律为逻辑起点演绎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它包含法律,并不限于法律。法律是其中的基本框架与脉络,通过教义学的方法,使之形成一个有血有肉的理论体系。因此,教义学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法学研究的成果。法官不仅受法律的约束,而且受教义学的约束。例如,德国学者温弗里德·哈斯穆尔提出了对法官通过法律教义学的约束的命题,指出:
这关涉到法律教义学,它在法学的支持下,将法官规则系统化,指出并修正了法官规则的概念,还在规则体系中学习了这一概念。在法律与案件判决间中等抽象程度上,法律教义学阐释了判决规则,当法律教义学被贯彻之时,它同样事实上约束着法官。法律教义学也不仅作为法律的具体化来理解,而且以它这方面根据法律的含义和法律的内容,建构自己(变化)的标准。它至少事实上实现了对法官的约束,这归功于它的稳定化和区别化功能:它使得问题变得可决定,途径为,它缩小了可能的判决选择的圈子,刻画了问题的特征,并将之系统化,确定了相关性,提供了论证模式。只有利用法律教义学的帮助工具,法官才能坚实地处理法律,才能察觉不同,并将法律分门别类。[10]
法教义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我认为是法律规范先天的不周延性、不圆满性与不明确性造成的。任何法律都是抽象的、概括的,当它适用于个案的时候,都难免会出现法律所不及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能为裁判提供所有规则,而只有法教义学才能承担这一职责。法教义学本身具有逻辑推理的含义,它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作为逻辑推理的起点,经过司法的推理活动,使法律更加周延、更加圆满、更加明确,从而满足司法对规则的需求。可以说,只知法律而不懂法教义学是无法承担司法职责的。法学教育就在于为法科学生提供法教义学知识,法科学生与其说是学习法律,不如说是学习法教义学方法。因此,法教义学对于法学教育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教义学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法律知识水平的标志之一。我认为,法教义学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一)拓展法律外延,为司法适用提供裁判规则
立法的主要使命是为司法提供裁判规则,然而由于立法的有限性与案件的具体性,立法难以独自地完成提供规则的职责。而法教义学可以在现有的、有限的法律基础上,采用适当的方法,无限地扩展法律的外延。在这个意义上说,法教义相对于立法的有形之法与有限之法而言,是无形之法,甚至是无限之法。法教义学为找法活动提供径路,是司法活动的有效工具。例如,我国刑法第196条第1款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其中第3项行为是“冒用他人信用卡”。该条第3款规定: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第264条是关于盗窃罪的规定,因此,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应以盗窃罪论处。在上述情形中,存在两个行为:一是盗窃信用卡,二是使用盗窃的信用卡,这也就是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根据刑法规定,对于上述情形,应定盗窃罪。刑法规定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定盗窃罪。那么,诈骗信用卡并使用的、抢劫信用卡并使用的、抢夺信用卡并使用的、捡拾信用卡并使用的,应当如何定罪?对此刑法并无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推而广之,因而得出诈骗信用卡并使用的、抢劫信用卡并使用的、抢夺信用卡并使用的、捡拾信用卡并使用的,都应当以信用卡取得行为定罪的结论。这表明,在我国刑法中信用卡作为一种财产凭证,是刑法关于侵犯财产罪的保护客体。但2008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规定:
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司法解释与上述教义学原理是相悖的,但法律与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的效力大于法教义学原理,因而,对于这种拾得他人信用卡使用的行为,应定信用卡诈骗罪,这是一个特别规定。以上就是一个法教义学的推理过程,通过这种逻辑推理活动,拓展了法律的外延,使法律规定更加周延。
(二)建构理论模型,为定罪活动创造工具理性
法律适用活动并不是在自动购货机上投入硬币获得商品这么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为体现司法思维的正确性,需要创制一些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当然不是法律规定的,但却是适用法律的必要工具。在刑法学中,以构成要件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就是一个定罪的理论模型。它是德国学者创造的刑法教义学的成果,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德国学者通过对犯罪论体系演变过程的叙述,作出了以下结论:
一个清楚的刑法信条学,对于理论、实践和法安全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信条学中,关键是要看到规定的真正对象所具有的结构和实质,因为借助单纯的理论虚构的形象或者关键词,人民并不能得出一般有效的结论。在这些结论从“行为刑法”和“罪责刑法”的基本原则中,模式性地为犯罪的一般案件,塑造由此产生的各种体系性结论时,就有可能在这个中心领域成为一种通用的刑法科学。这种刑法科学就可以为国内的立法者和法院阐明,应当如何合乎逻辑地看待总则的法律形象;并由此提供明确的和具有归类功能的概念。这样,通过科学地建立的方法,这种刑法科学就为法安全和正义作出了贡献。[11]
犯罪论体系为定罪活动提供了一整套严密的思维步骤,使依照刑法规定的定罪活动成为一种理性的思维活动。因为定罪问题在刑法中居于首要地位,所以,犯罪论体系的水平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刑法教义学水平的指数。在犯罪论体系中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构成要件、违法阻却、罪责等,都是刑法所没有规定的。刑法只是规定了行为、客体、结果、正当防卫、故意与过失等内容,而犯罪论体系将这些刑法规定在一个思想(idea)下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为定罪活动提供理性工具。
(三)设定教义规则,为价值判断发挥引导作用
法教义学对于法律本身不作价值判断,因而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是互相排斥的。其实不然,法教义规则天生就包含了价值判断,这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它是实现价值理性的所谓工具理性。当然,这种对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与对法律的价值判断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在论及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时,我国学者指出:
作为总结,在规则与价值判断的二元区分的必要性上,拉茨(Raz)的观点深值赞同:从价值判断到判决结论,需经过两层推理。第一层推理是通过立法或司法活动(考虑到判例法或权威判决之影响力)将价值判断转化为法律规范,并通过法教义学将这些规范整合为完整一致的体系;第二层次再经过法教义学将这些规范具体适用到案件审理中。法律义务本身便是其应当被遵守的唯一理由(exclusionary reasons),在此以外,法律适用者无须再搜寻其他理由。在此情形下,当然存在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裁判导致有违价值判断的可能,但必须要认识到“法律应当无条件遵守”的要求正是规则得以实行的基本条件,而且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12]
法律规定本身就是立法者的一种价值判断,即以规则作为一种价值内容的物质载体。因此,司法者依照法律规则处理个案,这种规则适用本身就是价值内容的实现。可以说,法律规则是在价值判断问题上所能达成的最大妥协和共识。因此,正如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也是最低限度的价值。当然,为了避免过于信赖法律规则所带来的对个别公正的破坏,立法者通过一般条款、例外条款、概然条款等方式,赋予司法者在一定限度内进行直接价值判断的权力。在这些情形中,法教义学能够起到重要引导作用,因为法教义学具有再创造(reproduc-tive)的功能,它可以使一般的价值内容实体化。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19~2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2版,黎宏译,11~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陈兴良:《刑法知识论》,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5]朱采真编:《现代法学通论》,93页,上海,世界书局,1935。
[6]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2版,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37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8][德]阿尔图·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穆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9][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11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0][德]阿尔图·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穆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284~28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1][德]汉斯·约阿希姆·希尔施:《关于德国现代刑法信条学的现状》,王世洲、苏颖霞译,载《北大德国研究》,第2卷,1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2]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载《中外法学》,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