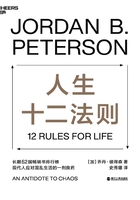
荒芜青春
那时我有个朋友,就叫他克里斯吧。克里斯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和我喜欢同一类型的科幻小说。他很有创造力,对电子元器件、机械和引擎都很感兴趣,是个天生的工程师,但家庭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克里斯的父母温和善良,姐妹们也很聪明,整个家庭看上去很正常,但克里斯好像在某个重要的层面被忽视了,所以他虽然聪明、充满好奇心,但内心充斥着愤怒、怨恨和绝望。
克里斯的那辆1972年产的蓝色福特皮卡可以说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这辆臭名昭著的皮卡车就像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外壳,它的每一寸都布满了因为各种事故和磕碰留下的凹痕,保险杠上的贴纸也很应景地写着:“警告!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放纵与狂欢!”这张贴纸和所有凹痕共同建构了一种强烈的荒谬感,而这一切绝非偶然。
每次克里斯出了车祸,他父亲都会把车修好,并且再另外给他买一些东西,但克里斯从不在乎。克里斯经常表达他对父子关系的不满,也许是他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因为精力不足而无法足够关注儿子,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父子关系恶化起来也说不定。
克里斯有个比他小两岁的表弟艾德。艾德是个聪明、机智、英俊并且讨人喜欢的孩子,如果你只见过12岁的他,那你一定会觉得这孩子会有很好的未来。但艾德一直在走下坡路,以至于最终陷入了一种从现实掉队的半游离状态。他不像克里斯那样易怒,但也同样充满了困惑。克里斯和艾德后来开始接触大麻,这并没有让他们的状况变好。
在漫漫长夜,我和克里斯、艾德还有其他小伙伴们会开着车四处游荡。我们穿过主街,沿着铁路大道一路再向北,路过高中,在小镇的北端转向西;或者沿着主街一直向北,到小镇北端后再向东转,如此不断重复着一样的路线。如果我们不在镇上开,那就会去乡间。一个世纪以前,测量员在这个约80万平方公里的荒原上规划了庞大的道路网络。往北每隔三公里,就能碰到一条自东向西无尽延伸的石子路;往西每隔两公里,也都能遇到一条自北向南的路。因此我们永远不缺可以用来打发时间的驾驶路线。
除了开车乱逛,我们的另一个消遣选择就是参加派对。一些年纪稍大的人会在家里举办派对,然后那里就会成为各种不请自来者的临时住所。喝了酒之后,有些本来就讨厌的人会变得更加面目可憎。如果某个孩子的父母临时出差,并且被开车乱逛的人注意到屋里灯火通明,屋外却没有大人的车的话,这个孩子的家也会成为派对的临时举办场所。有时候,这种派对的局面会失控,甚至还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不喜欢青少年们的派对,也毫不怀念那些黯淡的场景。在阴暗的灯光下,自我意识被缩到最小。吵闹的音乐让人无法交谈,不过本来也没什么好说的。派对上总是充斥着一种凄凉和压抑的感觉,每个人都在肆无忌惮地抽烟和酗酒,一切都显得漫无目的。不过有时候也会发生些事情,比如有一次,我的一个性格异常内向的同学,在喝醉之后拿着一把子弹上了膛的霰弹枪四处挥舞;另一次,那个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女孩轻蔑地羞辱了一个持刀威胁她的男孩;还有一次,一个朋友从树上摔了下来,一分钟之后他的傻瓜跟班又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没人知道自己在这些派对里要做什么。希望看到女啦啦队员?等待戈多?虽然大家更愿意看到前者,但后者似乎更接近现实。比较浪漫地说,如果无聊透顶的我们有得选,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过早地变得消极厌世、抗拒责任,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不够酷,我们也无法坚持参加成年人为我们组织的辩论社、航空青年团或学校体育队。我不知道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青少年生活是什么样的,1955年的小孩子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一个社团吗?至少20多年后的我们好像是不行的。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先锋们建议年轻人“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 。大多数人都做到了第一项和第三项,可并没能怎么做到第二项。
。大多数人都做到了第一项和第三项,可并没能怎么做到第二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