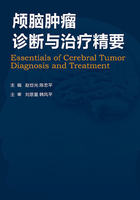
第十节 和脑肿瘤相关的癌易感综合征
有不到5%的脑肿瘤和一种罕见的易感综合征相关,此类脑瘤患者存在家族聚集性。这种聚集性可能是一种遗传畸变的家族传递,使得存在这种畸变的人更倾向于患脑瘤和其他外周神经肿瘤,也有可能是生殖细胞上出现新突变,并将之传递给后代。散发神经胶质瘤患者的直系家属同样患神经胶质瘤的风险也略高,然而这种风险并没有高到像乳腺癌那样具有显著性。尽管数量较少,学习这种癌易感综合征,并在临床、流行病、病理和分子水平对它进行分析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做能为我们补充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并因此为治疗大量的散发肿瘤患者提供帮助。它让我们可以研究队列,研究表观遗传因素对疾病模式的影响,它常常和散发的相应病例存在共同的分子变异,它还能帮助我们通过调整易感基因建立预临床试验的动物模型,从而开发新药和生物治疗方法等。下面我们将重点讨论一些这样易感综合征,以及它们和脑肿瘤之间的联系。
一、Ⅰ型多发性神经纤维瘤(NF- 1)
NF- 1是一种相对常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发生率大约是每3000~4000人中存在1例(Friedman,1999)。以一个新的NF- 1患者为例,他从父母中的一个人身上获得这个显性缺陷基因的几率是50%,另外50%的情况是患者自己身上的生殖细胞NF- 1基因发生了新的突变(通常是精子)(Thomson等,2002)。NF- 1(雷格林沃森病)被意识到是一种临床症状,最初是在19世纪末,被雷格林沃森发现,它的特点是出现一系列肿瘤和非肿瘤表现,严重程度和发生率各异(McClatchey,2007)。NF- 1的一个标志是神经纤维瘤的发生,神经纤维瘤是外周神经多种细胞混合组成的良性肿瘤。神经纤维瘤能够长成表皮下和真皮肿瘤,它是良性的,不会引起显著的临床症状,但可能影响美观。
大约有30%的NF- 1患者,其肿瘤的生长为丛状,这是典型的产生于更大的外周神经或神经根的肿瘤(McClatchey,2007)。丛状神经纤维瘤能够导致神经功能紊乱、疼痛,并且大约有10%患者的肿瘤倾向于转变为恶性外周神经鞘瘤(MPNST)(Mc-Clatchey,2007)。其他肿瘤类型,包括神经胶质瘤,主要以低等级视神经胶质瘤的形式存在于儿童中(Gutmann,2008),髓细胞样白血病和嗜铬细胞瘤也属于NF- 1的范围。NF- 1的非肿瘤症状包括皮肤色素异常,例如咖啡斑、认知障碍、虹膜错构瘤(虹膜色素缺陷瘤)、纤维组织发育异常、典型的蝶骨翼、椎骨和胫骨骨骼病变。NF- 1的严重性和开始的症状尽管和年龄有关,但却是无法预测的,即使是在一个患病的家庭内,不同的患者之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由于存在大量的共同和不同的临床症状,NIH为NF- 1的临床诊断设立了标准(Cawthon等,1990; Viskochil等,1990)(表2- 1),如果必要,还可以通过分子测试进行补充诊断。
表2-1 NF-1和NF-2的诊断标准(根据Stumpf等,1988)

1990年,NF- 1的基因通过定位克隆被确定,基因很大(大约350kb)位于17号染色体qll. 21,编码一个同样很大的蛋白,叫做神经纤维瘤蛋白(220-280kDa)(Viskochil等,1990; Cawthon等,1990; Wallace等,1990)。NF- 1基因的进化相当保守,在大部分真核细胞生物中都有同源基因,如果蝇和酵母。从基因上来讲,NF- 1基因可以被归为TSG,并可以通过遗传或者新的生殖细胞杂合突变使NF- 1失活,从而影响患者的生存。野生型等位基因的体细胞突变使得基因失去杂合性,从而导致肿瘤的产生。NF- 1突变也出现在散发的属于NF- 1范围的肿瘤中,例如MPNST、髓性白血病,这支持了NF- 1具有一些组织特异性的肿瘤抑制功能这一说法。
大量存在新突变的NF- 1散发病例可能是由于NF- 1基因本身很大,而NF- 1位点的突变率也尤其高。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由于小的缺失或是截位突变,也有可能是其他机制,例如基因转换,其他染色体上的NF- 1假基因,也可能是重复序列之间的NF- 1基因内部重排(Thomson等,2002; Dorschner等,1999)。NF- 1基因表现度的差异并未显示出强烈的基因型和表型的关系,尽管修饰基因可能会影响NF- 1患者中出现的表型多样性(Szudek等,2002,2003)。对于一个散发的NF- 1患者,他可以从一个存在生殖细胞NF- 1突变的镶嵌型正常双亲中遗传得到突变基因;也可以是双亲中的一位生殖细胞发生突变,且存在突变的生殖细胞最后参与形成受精卵,从而使该患者得到突变基因;或是双亲生殖细胞形成合子后在早期受精卵发育阶段发生突变,从而使得患者成为体细胞镶嵌型个体(Kehrer- Sawatzki&Cooper 2008)。后一种情况可以导致NF- 1患者表型的多样性。
对于NF- 1的肿瘤抑制和生理功能,在小鼠模型中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在NF- 1-/-纯和小鼠突变模型中,NF- 1基因失活导致胚胎在第13. 5天由于心脏缺陷而死亡,这反映了NF- 1基因在心脏发育时的内皮细胞中的重要性(Gitler等,2003; Jacks等,1994)。尽管NF- 1+/-杂合子小鼠有肿瘤易感性,正如在NF- 1患者中所见到的一样,例如髓性白血病和嗜铬细胞瘤,但它们不能概括所有NF- 1疾病的所有临床范围。进一步改进NF- 1小鼠,可以研究NF- 1在特定组织和特定肿瘤的进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神经元中NF- 1的组织特异性消除可能会导致大脑皮层的异常发育,这一表型和人类中具有认知障碍的患者是一致的(Zhu等,2001);部分细胞带有NF- 1-/-基因,发展为神经纤维瘤的嵌合体小鼠显示,失去野生型NF- 1等位基因杂合性,对于神经纤维瘤的发生是必要的(Cichowski等,1999)。将NF- 1+/-小鼠和具有其他肿瘤抑制基因缺陷的小鼠进行杂交,揭示了NF- 1在肿瘤发生中的基因协作。NF- 1+/-; p53+/-小鼠会发生MPNST和恶性胶质瘤。这些小鼠中的大部分肿瘤同时失去了p53和NF- 1的野生型等位基因(Reilly等,2000)。由于NF- 1和p53在人类中处于同一个染色体上(17号染色体),在小鼠中也处于同一染色体上(11号染色体),因此这种情况很可能由于失去野生型11号染色体发生(Cichowski等,1999; Reilly等,2000; Vogel等,1999)。有趣的是,这一表现的外显率和严重程度则取决于遗传背景和1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印记位点,这和人类疾病中各异的表现度和修饰基因的功能是一致的(Reilly等,2000; Richards等,1995)。此外,有证据显示和NF- 1相关的p53的失活对于恶性星形细胞瘤的形成至关重要(Zhu等,2005)。
NF- 1+/-; p53+/-的小鼠主要发展为恶性胶质瘤,在NF- 1患者中仅偶尔出现,并且不是视神经胶质瘤,这是NF- 1病的标志,在15%的NF- 1患者中出现。这和p53刺激GBM中的致病过程中具有的主要作用是一致的(McClatchey,2007)。仅在星形胶质细胞中存在NF- 1特异性失活的小鼠(NF- 1lox/ lox; GFAP- Cre小鼠)在周围细胞有NF- 1+/+背景的情况下,最终不会产生肿瘤(Bajenaru等,2002)。然而杂合子背景下的NF- 1-/-星形胶质细胞,其周围的中枢神经系统细胞,尤其是神经元是NF- 1+/-的情况下,发展为视神经胶质细胞瘤。同样的,最近研究显示神经纤维瘤的形成不仅需要NF- 1缺陷的施万细胞,也需要NF- 1杂合的骨髓细胞(Yang等,2008),显示了NF- 1发病机制中微环境的重要性。这些结果显示了微环境在NF- 1相关肿瘤的致病过程总的重要性。
激活的受体为细胞内信号衔接蛋白,如Grb2,它提供磷酸化酪氨酸残基,而它自己则和鸟嘌呤交换因子酶,如Sos连接,该酶可以将非活性Ras- GDP转化为活性Ras- GTP。激活的Ras- GTP能够激活各种后续信号分子或效应因子,例如Raf,从而传递信号,在细胞核水平调节转录。以上的信号流在多个层次上受到负调控,包括Ras- GAP,将活性Ras- GAP转化为无活性Ras- GAP。人类中更主要的一个Ras-GAP是神经纤维瘤蛋白,也就是NF- 1丢失的基因产物,通过活性GTP导致持续的生长促进信号。消除Ras- GAP功能的突变是人类癌症中最常见的致癌突变(图2- 7)。

图2-7 Ras/Raf/MAPK通路激活示意图
在细胞水平上,神经纤维瘤蛋白的功能是Ras信号通路的负调节因子。它有一个和Ras通路的GTP酶激活蛋白(Ras- GAPs)同源的区域,通过去磷酸化Ras- GTP抑制Ras的活性(Bernards&Settleman,2004)(图2- 7)。通过丢失NF- 1升高Ras的活性可能对于NF- 1肿瘤的致病是关键的(Basu等,1992),而已被深入研究的Ras依赖通路激活,如RafTMEK、PI3- K/AKT和Rac,在NF- 1-/-细胞和肿瘤中上升(Cichowski&Jacks,2001; Basu等,1992; Guha等,1996; Lau等,2000; Woods等,2002)。此外,NF- 1被显示能够调节果蝇中腺苷环化酶(AC)的活性和cAMP的水平,从而可以了解NF- 1缺陷果蝇(Guo等,1997; Guo等,2000)和星形胶质细胞和施万细胞这样的哺乳动物细胞(Dasgupta等,2003; Kim等,2001; Tong等,l 2002)的功能丧失情况。最近,mTOR被发现作为一个在NF- 1缺陷细胞中上调的关键因子(Dasgupta等,2005; Johannessen等,2004),并依赖于Ras介导的信号通路。mTOR对于肿瘤形成的影响似乎是通过CyclinDl介导的,而通过经典的mTOR靶点HIF1介导的情况则要少一些(Johannessen等,2008)。西罗莫司和其他相关的mTOR抑制因子由此被认为是充满前景的治疗NF- 1相关肿瘤的药物。
二、Ⅱ型多发性神经纤维瘤(NF- 2)
NF- 2的发生率大约是NF- 1的1/10,婴儿安全出生率为1/40 000。它也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50%的新病例是从自己双亲中的一位那里遗传得到,而另外50%则是来源于生殖细胞的新突变(Mc-Clatchey,2007; Evans等,1992; Rouleau等,1993; Trofatter等,1993)。像NF- 1一样,失去第二个正常NF-2等位基因的杂合性,是施万细胞瘤开始的首先步骤。虽然95%的外周神经和颅内施万细胞瘤存在于散发患者中,但是散发的体细胞中两个NF- 2基因失去表达的突变,几乎在所有的非NF- 2施万细胞瘤中被发现(Stemmer- Rachamimov等,1997)。和NF- 1的临床诊断类似的是,NIH临床标准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用于诊断(表2- 1),尽管由于NF- 2基因的克隆,如果必要,对患者正常细胞的分子诊断可以确诊。
NF- 2的TSG功能在动物模型中已被证明。在小鼠中,NF- 2基因的双等位基因突变会导致胚胎死亡,而杂合子小鼠则发展为各种恶性和转移性肿瘤。施万细胞中靶向NF- 2失活的转基因小鼠会发展为像人类肿瘤的施万细胞瘤(Giovannini等,2000)。在小鼠胚胎发育过程中,NF- 2启动子激活的研究已经发现,胚胎外胚层的显著表达以及之后在脑中表达。NF- 2启动子主要在神经管闭合期间在细胞移行的位点,以及听觉和三叉神经这样的接近肿瘤发生的解剖部位(Akhmametyeva等,2006)表现出活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了美林蛋白(Merlin)在胚胎形成时期组织融合和细胞迁移中的作用,以及美林蛋白在正常施万细胞和成人外周神经轴突之间重要相互影响中的作用,这都显示了美林蛋白在细胞-细胞和细胞-基质黏附中的作用(McLaughlin等,2007; Nakai等,2004)。这和美林蛋白的结构是一致的(膜突蛋白-埃兹蛋白-根蛋白样蛋白),它和ERM蛋白(埃兹蛋白、根蛋白、膜突蛋白)及其在膜细胞骨架界面的位点(Trofatter等,1993)强烈相关。美林蛋白同局部黏附复合蛋白,如庄蛋白和局部黏附激酶(Fernandez- Valle等,2002),以及同其他黏附分子,如β整合素和立林(lyillin)(Bono et al 2005)的相互作用支持了它在黏附中发挥作用。除此之外,美林蛋白通过调节肌动蛋白聚合参与了细胞骨架的组织(Muranen等,2007; Manchanda,2005),并且通过作为Rac和Cdc42下游的p21激活激酶(PAK)的磷酸化靶点,小GTP酶分子参与到细胞迁移、黏附和细胞骨架组织中(Hirokawa等,2004; Kaempchen等,2003; Kissil等,2003; Shaw等,2001)。因此美林蛋白的TSG功能-在通过去磷酸化丝氨酸518被激活后,能够介导细胞周期停滞和阻断细胞生长-最可能通过生长的联系抑制(Morrison等,2001)和与不同信号通路的相互作用间接实现。例如,去磷酸化的美林蛋白和一种透明质酸受体CD44结合,从而导致生长抑制。除了它的联系和黏附功能,美林蛋白还与几个参与细胞增殖的通路中间分子有直接的联系,包括Raf/Ras/MABK/MEK/Erk和PI3-激酶-Akt(Tikoo等,1994),这些是生长因子酪氨酸激酶受体(RPTK)的主要信号通路。另一个例子显示,美林蛋白参与到RPTK信号通路的过程,是美林蛋白与马基辛蛋白(Magicin)和Grb2形成三级复合体-一种协调RPTK和Ras信号通路的衔接蛋白(Wiederhold等,2004)(图7)。此外,美林蛋白能够抑制Ras和Rac的活性,而两者都是RPTK下游信号通路的主要组成部分(Nakai等,2006; Morrison等,2007)。其他研究还显示美林蛋白通过控制和协调它们在细胞膜上的可及性,从而调节RPTK活性的作用(Mc-Clatchey&Giovannini,2005)。最后,和它们与美林蛋白的直接相互作用无关,RPTK如PDGF- R,以及EGFR和TGFR- P家族成员,被发现在施万细胞瘤中水平上升(Cole等,2008; Curto等,2007; Doherty等,2008; Fraen- zer等,2003)。因此,即使目前已经发现的大量的美林蛋白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也还无法了解美林蛋白相关的信号通路的全景,已经认识到几个可能可以应用于临床的药物靶点。进入Ⅰ期临床试验的有: EGFR(赫赛汀)、Ras/Raf/Mek(索拉非尼),PI3- K- Akt (0SU3013,西罗莫司)、PDGFR(索拉非尼)。
三、结节性脑硬化
结节性脑硬化是一种多系统的家族性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或是TSC1和TSC2基因突变导致的散发性遗传疾病。这个疾病的临床范围包括错构瘤和多个器官的良性肿瘤,主要是脑、心脏、皮肤、眼睛、肾脏、肺和肝脏。结节性脑硬化的各种已发现的症状被归为主要和次要诊断标准(表2- 2)。满足两个主要标准,或满足一个主要标准和两个次要标准,即可诊断为结节性脑硬化(Curatolo等,2008)(表2- 2)。
表2-2 结节性脑硬化(TSC)的诊断标准

接近90%的患者均有脑部异常,包括皮层块茎(“块茎”这个术语指的是肥厚和硬化皮质脑回的土豆样外观);室管膜下结节,它可以被看作错构瘤也可以被看作室管膜下巨细胞星形细胞瘤(SEGA),良性,但其是真性瘤,由室管膜下结节转变而成。大部分脑结构异常在胎儿期便出现,在出生前即可通过胎儿超声或MRI诊断(Curatolo&Brinchi,1993)。临床上,结节性脑硬化的神经症状有癫痫发作、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行为问题和孤独症(Curatolo等,1991)。
在组织水平上,块茎的特点是发育异常的皮层位点,显示出和细胞异常相关的结构异常的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结构,例如巨大的神经元细胞和异形的星形胶质细胞。室管膜下结节主要是位于侧脑室室管膜壁的错构瘤。室管膜下结节可能进展为SEGA (Nabbout等,1999),通常为混合神经胶质系的良性的进展缓慢的肿瘤。大部分情况,SEGA的症状出现是由于门罗孔阻塞导致CSF流通受阻,以及由此导致的脑积水。
结节性脑硬化的遗传因素和TCS1和TCS2基因的突变有关,最初通过连锁分析被发现(Fryer等,1987; Kandt等,1992)。TCS1位于9号染色体q34 (van Slegtenhorst等,1997),而TCS2位于16号染色体p13. 3 (《欧洲人16号染色体结节性脑硬化联合》1993)。大部分散发和家族病例(70%~85%),突变的是TCS2,并和更严重的表型相关。突变包括大的缺失或是小的截断(无义突变、小缺失),TCS1或TCS2上没有明确的突变热点。有趣的是TSC2基因和Ⅰ型多囊性肾病基因PKD1邻近,并且TCS2部位大的缺失可能牵涉PKD1,从而导致不到3%的结节性脑硬化患者同时存在TSC和多囊性肾病。在TSC中,对TSC1或TSC2,一个等位基因的失活足以导致块茎的形成,以及产生显著比例的SEGA,然而肾血管肌脂肪瘤的产生更多和失去杂合性相关,也就是说需要出现第二次体细胞突变(Chan等,2004; Henske等,1997)。
TCS1的基因产物是一种叫作错构瘤蛋白的蛋白质(1164aa,130kDa),而TCS2的产物是一种叫作马铃薯球蛋白的蛋白质(1807aa and 180 kDa),在同一信号通路中通过形成细胞间复合体而发生相互作用(Tee等,2001)。尽管已经发现很多蛋白与错构瘤蛋白和马铃薯球蛋白存在相互作用,TSC中,错构瘤蛋白/马铃薯球蛋白复合体的主要功能被认为是mTOR(哺乳动物的西罗莫司靶点)介导的下游信号的接触面咬合(Tee等,2002; Gao等,2002; Inoki等,2002)。错构瘤蛋白/马铃薯球蛋白激活了一个GTP酶,将GTP从脑ras同源富集(RHEB)中去除,从而导致mTOR的抑制(Astrinidis&Henske,2005; Kwiatkowski&Manning,2005)。由于Akt是错构瘤蛋白/马铃薯球蛋白主要的上游抑制因子,Akt通过抑制错构瘤蛋白/马铃薯球蛋白复合体刺激mTOR,从而能够总结出该信号通路。mTOR是磷酸肌醇3激酶相关激酶家族的一个成员,是几个细胞过程中的主要作用物,例如生长调节、增殖控制和癌细胞的新陈代谢。异常的mTOR信号通路以主要的或次要的地位参与到其他遗传性综合征中,例如黑斑息肉综合征(突变位于LKB1),PTEN突变综合征,例如小脑发育不良性节细胞瘤和多发性错构瘤综合征,遗传性斑痣性错构瘤病或NF- 1。和TSC进展有关的通路中,mTOR通过磷酸化并使SE- BP失活,控制帽依赖的RNA翻译,从而抑制翻译初始因子eIF4E的活性(Jozwiak等,2005)。mTOR一种调节翻译的方法是通过磷酸化S6K1实现,S6K1是一种可以记过核糖体亚基蛋白S6的激酶,这种调节方法通过征募负责蛋白翻译的核糖体实现(Jozwiak等,2005)。除了mTOR调节,错构瘤蛋白/马铃薯球蛋白复合体在细胞黏附和迁移中发挥作用,其作用是通过和埃兹蛋白-根蛋白-膜突蛋白以及小GTP结合蛋白Rho的相互作用实现(Carbonara等,1996)。一些实验显示良性TSC相关损伤存在转移的可能,例如肾血管肌脂肪瘤(Karbowniczek等,2003; Marcotte&Crino 2006)。
四、遗传性斑痣性错构瘤病
遗传性斑痣性错构瘤病(VHL)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多系统遗传障碍疾病,特点是发生不同器官的血管肿瘤(血管瘤)(表2- 3)。这种疾病的原因是VHL基因的突变,VHL是一种TSG,编码一种参与泛素化和转录因子HIF(低氧诱导因子)降解的多蛋白复合体的一部分。临床上,遗传性斑痣性错构瘤病的特征是视网膜和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瘤的生长,以及神经透明细胞癌、嗜铬细胞瘤、胰岛细胞瘤、女性阔韧带囊腺瘤和男性附睾囊腺瘤的生长。在中枢神经系统中,VHL导致的血管网状细胞瘤的生长主要在小脑和脊髓中。血管网状细胞瘤是一种高度血管良性肿瘤,和间质细胞一样,被作为表达促红细胞生成素受体,并且失去VHL杂合性的原始血管网状细胞瘤(Chan等,2005; Chan等,1999; Vortmeyer等,2003; Vortmeyer等,1997)。
表2-3 遗传性斑痣性错构瘤病(VHL)的诊断标准

VHL基因首先通过连锁研究被定为在3号染色体p25,这一区域和散发肾癌有关(Seizinger等,1988; Seizinger等,1991),有6千碱基(kb)的转录物(Latif等,1993)。VHL基因包含3个外显子,可以合成4. 5kb的MRINA。VHL启动子包括PAX的结合位点,核呼吸因子1(Kuzmin等,1995)和TCF4(Giles等,2006),可以通过甲基化使之沉默(Herman等,1994)。VHL蛋白(Pvhl)有两个功能相似的异构体,均具有肿瘤抑制活性,它们是一个包含213个氨基酸的28- 30kDa的蛋白,和一个短一些的的蛋白,没有28- 30kDa蛋白前53个氨基酸编码N端氨基酸重复区域的18kDa。pVHL通过结合延伸因子C、延伸因子B、Cul2和Rbxl,形成一个多蛋白泛素连接酶复合体。这一复合体接下来可以将靶蛋白带到蛋白酶体进行降解。pVHL泛素连接酶复合物的主要亚基是HIF的3个α单位。在含氧量正常的情况下,pVHL复合体轻松地靶定HIF,并使之在蛋白酶体中降解。然而,当氧浓度下降,或者pVHL功能异常,HIF-α变得稳定,和HIF-β形成杂合二聚体(也被称作ARNT1-芳香烃受体核转位子1)。然后,该复合体转移到细胞核,激活参与细胞适应低氧的基因转录,这些基因的启动子中包含低氧反应元素(HRE)。这些基因包括血管生成介导因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小板衍生化生长因子(PDGF),还有参与无氧酵解和红细胞生成(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基因。对氧气浓度敏感的HIF-α 由EglN(产卵缺陷九)蛋白介导,于氧浓度正常情况下,在一个保守的脯氨酸残基上羟化HIF-α。这使得HIF和pVHL结合,最终启动泛素化过程。缺氧,以及其他因素,如线粒体在低氧条件下产生的活性氧(ROS),以及NO抑制EglN功能会阻止HIF-α的降解。总的来说,VHL中和血管网状细胞瘤相关的突变,导致HIF调节的改变和HIF依赖声场因子的过渡产生,如VEGF、PDGF、TGF-α和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些都会导致血管肿瘤细胞的增殖。
遗传性斑痣性错构瘤病是生殖系VHL位点杂合的常染色体显性疾病(Stolle等,1998),但是,和大部分遗传性癌症综合征一样,真正的VHL突变是隐性的,并且需要体细胞的VHL野生型等位基因失活(Pack等,1999)。大部分有VHL的人,具有VHL的家族史,尽管也存在VHL位点出现新突变的散发病例(Richards等,1995)。在大约20%的情况中,整个VHL位点缺失(Pack等,1999)。新的证据显示,VHL基因突变类型同临床表型和疾病的生化谱之间存在巨大关系(Chen等,1995; Crossey等,1994)。例如,Ⅰ型VHL病和缺失、无义突变、错义突变导致的VHL等位基因丧失有关,并且和嗜铬细胞瘤的低发生率以及HIF和EglN3的高表达有关。大部分有嗜铬细胞瘤的患者都为错义突变导致的Ⅱ型VHL。Ⅱ型VHL病可被进一步分为2A(患肾癌的风险低,轻微的HIF表达、低EglN3)、2B(患肾癌风险大、HIF表达相对低、低EglN3)、2C(只有嗜铬细胞瘤,没有中枢神经系统和视网膜的血管网状细胞瘤,HIF表达低,低EglN3)。
五、格尔林-戈尔茨痣综合征(基底细胞痣综合征)、成神经管细胞瘤和刺猬- Gli通路
这个综合征的是根据罗伯特·格尔林(Robert Gorlin)和罗伯特·戈尔茨(Robert Goltz)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在1960年描述了这一综合征(Gorlin&Goltz 1960)。该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疾病,患病率大约是50 000~150 000人中有1例患者(Gorlin,1999)。基底细胞痣综合征(BCNS),或戈尔茨痣综合征(GS)有很高的外显率,但表现度各异(Lo Muzio,2008)。对于这种综合征的第一次报告描述了基底细胞瘤、颌骨囊和分叉类之间的关系(Gorlin&Goltz,1960)。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临床症状被发现和GS有联系。目前,通过明确的主要和次要标准对GS进行诊断(Kimonis等,1997)。主要的临床特征和骨畸形影响与肋骨、四肢、脊柱和颅骨有关(Epstein,2008; High&Zedan,2005)。其他系统的异常,例如视觉异常、心血管异常、泌尿生殖系统异常、胃肠系统异常,也可能和格尔林综合征有关。格尔林综合征中发现的肿瘤有:基底细胞癌,这也是本疾病的标志;多纤维性髓母细胞瘤,这种肿瘤代表了一组不同的成神经管细胞瘤(Lo Muzio,2008; Amlashi等,2003; Herzberg&Wiskemann,1963);卵巢纤维瘤。脑膜瘤、颅咽管瘤、成胶质细胞瘤、横纹肌肉瘤在BCNS患者中也有过描述。BNCS患者的不同表型症状对患者有不同严重程度的影响,BCC的发生率在不同种族-患有BCNS的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也有显著差异(Goldstein等,1994)。
和该综合征相关的基因位于9号染色体q22上,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通过连锁分析被定位(Gailani等,1992)。几年后,通过定位克隆发现该基因和果蝇的“布丁”基因具有同源性(Hahn等,1996; Johnson等,1995)。PTCH1基因有23个外显子,包含34kb,编码一个含有1447个氨基酸的跨膜蛋白,该蛋白有12个跨膜区。在BCNS患者中,目前已经发现多余50个突变,其中包括缺失、无义突变或错义突变和插入(Boutet等,2003; Chidambaram &Dean 1996; Lench等,1997; Unden等,1996)。PTHC1突变主要集中在该蛋白两个大的细胞外环(Wicking等,1997),PTCH1的重排很常见,最终导致编码出截短蛋白(Epstein 2008)。尽管已经描述了PTCH1基因的很多不同突变,BCNS的表型和基因型之间的联系仍不清楚(Lindstrom等,2006)。
PTCH已经被广泛地作为果蝇中极性分割的调节因子,同时它在哺乳动物发育过程中的作用也很显著,包括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作用。PTCH是经典刺猬- Gli(HH- Gli)发育途径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生理环境中,HH途径参与多个胚胎和成人的细胞组织稳态的调节。在其他过程中,HH- Gli控制细胞生命、细胞数量和器官形成的调节。途径的激活因子HH是一种分泌的细胞外配体,主要是作为一种形态发生因子发挥作用,以梯度扩散的方式调节组织结构。在神经管的形成中,HH像分裂素一样发挥作用,促进细胞增生、祖细胞生存和具体成形的腹侧面脊髓(Jiang&Hui 2008; Ruiz i Altaba等,2003)。HH- Gli通路在再生和成人组织的完整性上有重要作用,包括上皮器官,如肺、前列腺、胰腺,还有中枢神经系统,其中HH- Gli调节祖细胞和肝细胞的维持(Beachy等,2004b; Fendrich等,2008; Karhadkar等,2004; Watkins等,2003)。因此激活的SHHGLI通路的生物效应是依赖于环境的,并能够在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类型的细胞中产生不同的生物反应。这种环境依赖性似乎是依靠特异的转录反应实现,而这种特异性的转录反应,又是通过和HH- Gli有特异关联的GLI转录因子的激活因子和抑制因子之间的平衡实现的(Ruiz i Altaba等,2007)。在机械水平,HH- Gli通路的传导流中存在重要的刺猬配体,两个跨膜膜蛋白,PTCH (HH受体和平滑子SMO),还有下游转录因子GLI。熔化抑制子(SUFU)是该通路的另一重要成员,在信号转导流中作为Gli的抑制子发挥作用。在人类中,刺猬因子家族的三个成员已经被描述了:刺猬因子-表达最广泛的基因、印度刺猬因子和沙漠刺猬因子。刺猬因子蛋白是分泌性细胞外蛋白配体,裂变为结合并激活胆固醇的和棕榈酸酯分子的底物。在缺乏分泌性细胞外配体HH的情况下,通路被关闭。在这种情况下,PTCH抑制SMO一种有七个跨膜区的蛋白,并阻止它激活下游的GLI转录因子。当HH存在的时候,活性HH和PTCH1第二大的细胞外环结合,由PTCH介导对SMO产生抑制。这开启了细胞内的信息流,最终导致锌指转录因子的GLI家族的激活。有三种不同的Gli蛋白: Gli1和Gli2是该通路的激活因子(GLIA),而Gli3则主要发挥抑制子的功能(GLIR)(Jiang&Hui,2008; Ruiz i Altaba等,2007)。该通路的激活是GLIA和GLIR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各种其他参与细胞增殖、存活、自我更新、分化、发育模式和血管生成基因的表达。因此,PTCH1失去功能最主要的后果是HH- Gli的过渡激活,导致发育异常和构成BCNS谱的肿瘤生长(Lindstrom等,2006)。PTCH的突变会导致通路的配体独立组成性激活,并如BNCS中看到的一样,促进肿瘤产生(Lindstrom等,2006)。
髓母细胞瘤是儿童中最常见的恶性脑肿瘤。它们被认为是由发育中的儿童小脑颗粒细胞前体产生,且预后很差,5年生存率40%~70%。只有一小部分髓母细胞瘤属于BNC,但这种联系提示,HH信号通路中一个基因缺陷足以引起脑部肿瘤的发生(Guessous等,2008)。在这方面,对基底细胞痣综合征和相关的HH信号通路的研究显著提高了我们对于髓母细胞瘤发病机制的认识。我们又一次观察到,基因突变与肿瘤形成之间的直接联系的证据是来自于转基因小鼠模型的。尽管纯合子PTCH缺失小鼠在胚胎发生过程中死亡,PTCH杂合子突变的小鼠(Ptch1+/-)会形成外显率刚超过10%的髓母细胞瘤,并呈现出若干可以在BCNS中见到的特征(Wetmore等,2001)。在PTCH杂合子的基础上,p53在无功能的(Ptch1+/-; Trp53-/-)小鼠中,髓母细胞瘤在几乎100%的小鼠中形成(Taylor等,2002),刻画了第二次打击如何可以大幅度地加快肿瘤发生。即使BNCS相关的髓母细胞瘤只占所有髓母细胞瘤病例中的一小部分,有证据显示HH- Gli信号通路也在散发髓母细胞瘤中发挥重要作用。HHGli信号通路中的若干组成部分如PTCH、SUFU、SMO所发生的突变在髓母细胞瘤的子集中有多次报道,但似乎在促纤维增生类型中占优势,其中这一类型占所有髓母细胞瘤的25%,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影响年龄大的患者且预后更加良好(Guessous等,2008)。同样,抑制融合基因(SUFU)的一个胚系突变在一组患有无BNC髓母细胞瘤的儿童中发现(Taylor等,2002)。近期研究提供了髓母细胞瘤的分子分类,具有一定程度的预后意义。能够影响预后,临床行为如肿瘤转移以及患者的人口学特征的签名基因和通路包含了HH- Gli,NOTCH,PDGF和WNT信号通路,这些基因一直参与小脑粒细胞前体的发育和维持。其他参与神经元分化,细胞周期,生物合成和感光器分化也在髓母细胞瘤的子分类也起到决定性作用(Kool等,2008; Thompson等,2006)。最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HH通路,甚至在缺乏某些特异的突变的情况下,能够在很多其他人类肿瘤的发病中起到关键作用,包括胃肠道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瘤、血液恶性肿瘤和胶质瘤(Karhadkar等,2004; Watkins等,2003; Stecca等,2007; Lindemann等,2008; Clement等,2007; Berman等,2003; Beachy等,2004a)由于这些肿瘤依赖于配体,它们适合于用一些化学剂如酚磺乙胺,一种SMO通路阻断激活的天然阻断剂,或相关的合成化学物(Ruiz I Altaba 2008)
六、李-佛美尼综合征
李-佛美尼综合征(LFS)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且易发癌症的综合征,具有一系列早发性癌症的特征。该综合征于1969年由Li和Fraumeni描述(最早包括了患有早发性横纹肌肉瘤的儿童的所属家族),特征是患有5种以下癌症:肉瘤、肾上腺皮质癌(ACC)、乳腺癌、白血病以及脑肿瘤,主要是神经胶质瘤和脉络丛癌(Garber等,1991; Li&Fraumeni 1969a,b)。LFS外显率高,临床特征具有异质性,女性发病率要高于男性(主要由于女性患者乳腺癌的发生),且与Tp53基因或者与p53具有功能联系的基因的胚系突变相关(Bell等,1999; Malkin等,1990)。如今已经发展出若干标准以确定Tp53胚系突变的家族风险。在Birch及同事们(1994),Eeles (1995)以及最近期的Chompret及同事们(2000,2001,2002)(表2-4)的贡献之下,LFS的纳入标准随着时间不断进化。诊断标准区分了经典型LFS,LF样或不完整LFS变种。重要的是,由Chompret定义的诊断标准增强了p53胚系突变检测的敏感性,包含了具有典型LFS肿瘤(早发性肉瘤、脑肿瘤、肾上腺皮质癌和乳腺癌)但无家族史的患者(Chompret等,2000,2001; Chompret 2002; Gonzalez等,2009)。各型LFS的根本分子生物学机制都与p53通路功能缺失相关。这可能是p53基因中的直接突变,占经典LFS家族中的80%,在LF-样综合征中占40%以及在不完整LFS中占6% (Birch等,1994; Eeles 1995; Chompret 2002)或者是p53通路中相关的基因突变,比如检验点激酶2(CHEK2,22q12. 2)(Bell等,1999; Bachinski等,2005),或者在1号染色体1q23上确定的基因座(Bell等,1999)。CHEK2与DNA损伤反应和复制检验点相关。CHEK2使p53磷酸化,导致有丝分裂停止并启动DNA修复。TP53的胚系突变大多数是在p53的DNA结合区的错义突变,与体细胞突变相似,但突变热点的分布频率不同(Varley等,1999)。剪接突变也在一些案例中被发现而且发生于生殖系的频率要高于散发病例(Olivier等,2003)。
表2-4 李-佛美尼综合征诊断标准

针对治疗患有李-佛美尼综合征的患者的临床指南包括了彻底的家族遗传咨询(包括针对受到LFS影响的夫妻的产前或者胚胎植入前诊断),肿瘤发生的早期筛查(即女性患者应当定期做双边乳房X线检查并且可以考虑预防性乳房切除术)以及针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远离电离辐射和损害DNA的产品的建议(Varley等,1997)。
七、Turcot综合征
1959年,Turcot及同事们描述了一个脑肿瘤与结肠癌之间的家族联系,并且随后也经常出现新病例的报道。Turcot综合征的分子基础在1995年阐明,通过展示在绝大多数家族中突变位于经典的结肠癌相关基因-腺瘤性结肠息肉病基因(APC,位于5号染色体5q21- 22)但少数家族在非息肉病相关的错配修复基因hMLH1(在3号染色体3p21. 3)以及hPMS2(在7号染色体7p22),以及形成人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综合征(HNPCC或Lynch综合征)的基因(Hamilton等,1995)。Turcot综合征患者中所报道的脑肿瘤主要为神经胶质瘤和髓母细胞瘤,但还报道过一些其他与该综合征相关的肿瘤的散发病例,包括室管膜细胞瘤、淋巴瘤、脑膜瘤、颅咽管瘤和垂体腺瘤(Paref等,1997)。
记录有APC基因突变的Turcot综合征患者还具有与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综合征(FAP)一致的发现,例如眼底病变和颚骨病变,但结肠息肉病不如后者明显。
Paraf和同事们(1997)提议将综合征分为两类:脑肿瘤息肉病1型(无FAP综合征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胶质母细胞瘤患病风险,而脑肿瘤息肉病2型(患FAP综合征的个体)具有更高的髓母细胞瘤患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