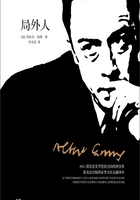
第一部
一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还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非常为我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靠到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人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的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的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是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堂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几把椅子和几个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白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你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拉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起。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 。”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带。
。”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上来了睡意。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你到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诧。现在他六十四岁了,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对我说,务必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很热,这个地区气温尤其高。那时他就告诉了我,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由于贫困,他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对我说:“要知道,您母亲的那些朋友,也要前来守灵。这是院里的常规。我还得去搬几把椅子来,煮些清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映在白墙上,容易让我困倦。他回答我说不可能。电灯就是这样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出进进,摆好几把椅子,还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壶,周围套放着一圈杯子。继而,他隔着妈妈,坐到了我的对面。女护士则坐在里端,背对着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的手臂动作来判断,估计她在打毛线。厅堂里很温馨,我喝了咖啡,觉得身子暖暖的,从敞开的房门,飘进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了一个盹儿。
我是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的。合上眼睛,我倒觉得房间白森森的,更加明亮了。面前没有一点阴影,每个物体、每个凸角、所有曲线,轮廓都那么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共有十一二个人,他们在这种晃眼的灯光中,静静地移动,落座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咯吱的声响。我看任何人也没有像看他们这样,他们的面孔,或者他们的衣着,无一细节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不怎么相信他们真实存在。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扎着腰带,鼓鼓的肚腹更显突出了。我还从未注意过,老妇人的肚腹能大到什么程度。老头子几乎个个精瘦,人人拄着拐杖。他们的脸上令我深感惊异的是,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在由皱纹构成的小巢里见到一点黯淡的光亮。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数人瞧了瞧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瘪进牙齿掉光的嘴里,让我闹不清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抽搐一下。我情愿相信那是他们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全坐到我对面,围了门房一圈儿,一个个摇晃着脑袋。一时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他们坐在那里是要审判我。
过了片刻,一个老妇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伴挡住,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号哭,很有节奏,让我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都很颓丧,神情黯然,默默无语。他们的目光注视棺木或者他们的拐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而且目不转睛。那老妇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不认识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了,可是又不敢跟她说。门房俯近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咕哝了两句话,又接着哭泣,还是原来的节奏。于是,门房过到我这边来,坐到我旁边。过了好半天,他才向我说明情况,但是并不正面看我:“她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密切。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待了许久。那女人唏嘘哭泣之声间歇拉长,但是还抽噎得厉害,终于住了声。我不再困倦了,只是很疲惫,腰酸背痛。现在,所有这些都沉默了,而这种静默让我难以忍受。只是偶尔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时间一长,我终于猜测出来,有几个老人在咂吧口腔,发出这种奇怪的啧啧声响。他们本人并没有怎么觉察,全都陷入沉思了。我甚至有这种感觉,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位死者,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现在想来,那是一种错觉。
我们都喝了门房倒的咖啡。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一时间我睁开眼睛,看见所有老人都缩成一团在睡觉,只有一个例外:他下巴颏儿托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单等我醒来似的。继而,我又睡着了。我醒来是因为腰越来越酸痛了。晨曦悄悄爬上玻璃顶棚。稍过一会儿,一位老人醒来,咳嗽了老半天。他往方格大手帕上吐痰,每吐一口,就好像硬往外掏似的。他把其他人都闹腾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都站起身。这样不舒服地守了一夜,他们都面如土灰。令我大大惊奇的是,他们走时,都挨个跟我握手——这一夜我们虽然没有交谈一句话,一起度过似乎促使我们亲近了。
我很疲倦。门房带我去他的住处,我得以稍微洗漱了一下,还喝了味道很好的牛奶咖啡。我从他那儿出来,天已大亮了。在马伦戈与大海之间的山丘上方,天空一片红霞。海风越过山丘,送来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很久没有到乡间走走了,如果没有妈妈的丧事,我能去散散步会感到多么惬意。
可是,我却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待。不过,我呼吸着泥土的清新气息便清除了困意。我想到办公室的同事们,此刻他们起了床,准备去上班:对我而言,这一刻总是最难受的。我还略微考虑了一下这些事儿,但是楼房里响起一阵钟声让我分了神。窗户里传出一阵忙乱的声响,随后又全肃静下来。太阳渐渐升高,开始晒热我的双脚了。门房穿过院子来对我说院长要见我。我走进院长办公室,他让我在好几份单据上签了字。我看到他穿着黑色礼服、长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抽空询问我:“殡仪馆的人到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请他们来合棺。合棺之前,您想不想再看您母亲最后一眼?”我说不必了。于是他压低声音,在电话里吩咐道:“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去做了。”
然后,他对我说要参加葬礼,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坐到办公桌后面,交叉起两条短腿。他事先向我打招呼,送葬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再加上出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都不准参加葬礼,他只是让他们守灵。“这是个人的问题。”他强调说。不过这一次,他准许妈妈的一位老友——“托马·佩雷兹”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微微一笑,对我说道:“您也理解,这种感情带点儿孩子气。他和您母亲还真的总相陪伴,不大离开。养老院里的人都开他们玩笑,对佩雷兹说:‘那是您的未婚妻。’他就呵呵笑起来。默尔索太太一去世,确实给他的打击很大。我认为不应该拒绝让他送一程。不过,按照保健医生的建议,昨晚我就不准他守灵了。”
我们待了许久没有说话。院长站起身,向办公室窗外张望。有一阵,他还观察到:“马伦戈的本堂神父已经到了。他提前来了。”他预先告诉我,教堂坐落在村子里,少说也要三刻钟才能走到。我们下楼去。本堂神父和唱诗班的两名儿童在楼前等待。一名儿童手上捧着香炉,而本堂神父俯下身,正给他调好银链的长度。我们一到,神父就直起身来,他管我叫“我的孩子”,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灵堂,我跟在身后。
我一眼就看到棺盖上的螺丝都拧下去了,厅堂里站着四个黑衣人。我听见院长对我说,灵车停在路上等候;同时又听到神父开始祈祷了。从这一时刻起,一切都进展得非常快。那四个人扯着柩单,朝棺木走去。神父及其随从,院长和我本人,都走出了厅堂。门外站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院长介绍:“默尔索先生”,但是那位女士的名字,我没有听见,只明白她是派来的护士。她那长脸瘦骨嶙峋,微微点一下头,没有一丝笑容。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抬着灵柩的人过去。我们跟在灵柩后面,走出了养老院。灵车停在大门外,呈长方形,漆得油亮,真像个文具盒。灵车旁边跟着两个人,一个是身形矮小、衣着滑稽可笑的殡葬司仪,另一个是举止做作的老者,我明白他便是佩雷兹先生了。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灵柩抬出门时,他摘下帽子),身穿一套西服,裤子呈螺旋形卷在皮靴上面,领口肥大的白衬衣上,扎着一个小小的黑领结。他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而鼻子上布满黑斑点;白发细软,露出两只晃荡荡的奇特耳朵,耳轮极不规整,呈现血红的,与苍白面孔的反差,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殡葬司仪给我们安排各自的位置。本堂神父走在前头,随后是灵车,由四名黑衣人围护,院长和我跟在灵车后面,收尾的是委派护士和佩雷兹先生。
太阳当空,已经普照全宇,铺天盖地压下来,温度迅速升高。我实在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等待了这么长时间才出发。我穿着深色外装,觉得很热了。那个重又戴上帽子的矮个儿老者,帽子又摘下来了。我略微扭头瞧他。这时,院长向我谈起他,说我母亲和佩雷兹先生由一名女护士陪同,傍晚经常去散步,一直走到村子。我望了望四周的田野,只见成行的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丘上,柏树之间透露出这片红绿相间的土地、这些稀稀落落如画的房舍,于是我理解妈妈了。在这个地方,傍晚时分,该是放松心情而感伤的时刻。然而今天,太阳暴烈,晒得景物直战栗,显得毫无人性,大煞风景。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觉,佩雷兹走路稍有点儿瘸。灵车行驶渐渐加速,老人就慢慢落单了,围护灵车的人也有一个落后,现在与我并行了。太阳在天空飞升得如此迅疾,令我甚感诧异。我这才发现,田野里虫鸣和青草的咯咯声早已响成一片。汗水在我脸颊流淌。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名职员忽然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他说话的同时,用右手微微推起鸭舌帽檐,左手拿手帕擦了擦额头。我对他说:“什么?”他指了指天,重复道:“真烤人啊。”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里面是您母亲吧?”我还是说:“对。”“她老了吗?”我回答:“差不多吧。”只因我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了。随后,他就住了声。我回头望去,只见佩雷兹老头落下有五十米远了;他急着往前赶,用力扇着毡帽。我也瞧了瞧院长。他走路十分庄重,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闪动着几滴汗珠,但他并不擦拭。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行进得稍微快了些。我周围总是同样的田野,通明透亮,灌足了阳光。强烈的天光让人受不了。有一阵子,我们经过一段新翻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鼓胀起来,一脚踩下去就陷进去,翻出亮晶晶的路浆。坐在灵车上面的车夫戴的那顶帽子,仿佛是用在这种泥浆里糅过的熟皮制作的。头上蓝天白云,下面色彩单调:翻出来的黏糊糊的柏油路浆呈黑色,衣服暗淡一抹黑,灵车漆成黑色,我置身这中间,不禁有点晕头转向。烈日、皮草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这一切再加上一夜未眠的疲倦,搞得我头昏眼花。我再次回过头去,觉得佩雷兹离得很远了,在熏蒸的热气中若隐若现,继而再也看不见了。我举目搜寻,看见他离开了大路,从田野斜插过来。我也看到,公路在前面拐弯了,从而明白佩雷兹熟悉当地,要抄近路赶上我们。他在拐弯处追上我们了。继而,我们又把他丢在后面,他又从田野抄近路追上来,如此反复数次。我感到太阳穴怦怦直跳。
接下来,事情确定而自然,进展得飞快,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情况:到了村口,那个特派的女护士跟我说话了。说话的声音很奇特,同她那张脸极不相称,一种颤巍巍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她对我说:“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浑身冒汗,进了教堂又会着凉,患热伤风了。”她说得对,真叫人无所适从。那天的情景,我还保留几点印象,例如:临近村口,佩雷兹最后一次追上我们时的那副面孔。他又焦灼又沉痛,大颗大颗泪珠流到面颊上,但因密布的皱纹阻碍而流不下去,便四下散布开,再聚集相连,他那张颓丧失态的脸上形成一片水光。还记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墓地坟头上天竺葵绽放的红花,佩雷兹晕倒了(活似散架的木偶),往妈妈的棺木上抛撒的血红色泥土,以及夹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那些人、那种嘈杂声音、那座村庄、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隆隆声,还有长途汽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时我那种喜悦,心想马上就能倒在床上,纳头睡他十二个钟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