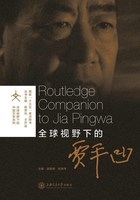
商州:贾平凹的小说世界
一、复杂心境
这块生长养育过他,被他选定要在这上面深深植以文学之根的陕南商洛山地,天荒地老,苍茫厚重,虽有巉岩峭崖向人提供猎物、柴薪和药材,有河道提供鱼群和航路,更有山地人异常的耐力、谨慎、节俭和坚韧、达观以及健忘,土地的贫瘠和生计的艰难迫使他们将使用于日常性事物的韧劲和节俭也同样使用于精神上,几乎怀着单纯的近于单调的观念生活着:劳动既是生存的手段,也是生存的目的。沉重的劳作吸收他们几乎全部充沛的精力和山地智慧,将他们的人生空间填塞得又充实又简单。他们的快乐和苦恼的内涵及其表达方式,意志、原则、怀疑和信仰,特别的方言和生活方式,务实的生活本性和某些准宗教的超脱感,这些在贾平凹以商州为母题的小说群体里复沓出现的一切,既然是从历史深处衍化而来的结果,那就自然会在新的时层中继续展开它的演变,而在对现代生活模态所做出的应答中,以往保持了不知多少世纪的沉闷、钝重、蹒跚和循环往复的脚步,渐渐开始变得迟疑起来。
《山城》大概可以算作贾平凹商州小说群体中比较粗糙、笨拙的一篇叙事作品,对它的败笔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是想说,要是我们暂且不去理会它在指涉现实生活时明显表露的不怎么可取的以意为之的主观倾向,越过它的具体语义,那么,这篇小说所写的那位小说家,对背倚着古朴文化传统的商州山镇女子和来自现代社会的省城时髦女诗人,在感情趋赴上回环逡巡,目光游移得相当厉害的情形,或许可以挪来作为贾平凹商州小说思维格局上的一种张力结构,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一个特定的角度,采取这个角度,也许能多少感受到贾平凹陈述商州世情的小说所具有的容易被人疑惑的现象,以及现象背后潜埋着的理由。
对商州所拥有的一切,贾平凹保持着两种感情。
一方面,是一种生命之根维系于此的挚念。他直接生活在他们里面,吸收他们,回忆他们,而不仅仅是冷眼旁观一番。他尊重这里的所有智慧和感情,因为凡此种种都培育和激发了他的自省自悟的心智的主要机能,玉成了他在文学天地中的充分舒展。这使他对世风和时尚的大幅度变迁,有时会身不由己地采取一种谨慎的眼光,担心衍化流贯在这块山地上的人的纯真、厚道、韧性的信念和沉实的生活态度,以及充满生命的原始本性的民俗风物,在趋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分解、消融,或者被外来的力量冲撞得支离破碎,不伦不类。
《九叶树》中那个罗子属于那样的老人,如果能把世界一分为二,那么他的头脑中堆积的绝大多数属于他的过去直到现在的一切,而对于它从今以后将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一切则茫然不知。对他来说,旧的世界因为熟悉所以是可亲近的,新的世界则因为陌生而有隔膜。他酒酣后对住店客人发表的那通对城里人生活近于滑稽的描述表明了这一点。女儿兰兰的迷误,在他看来正是对他生活信念的一种应验:人应该自足于已有的基点,放弃它,就会在生活中迷失自己的本性,这种内缩的、防备的心理虽然主要跟他几乎一辈子的生命是由传统生活秩序所铸成的这个情况有关,但也与新的生活方式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当它向山地蔓延时会遇到意想不及的力量的纠结有关。罗子的担心是有其合理的性质的。现成地承受着现代文化陶冶的人,摆脱了偏仄蒙昧的生产生活结构加诸人身的拘囿,但对个性的滥用又往往导致了褊狭、任性的私欲之心和纤弱脆孱的神经(《小城》中的省城女诗人),带来某种遗弃道德责任感的迹象(《九叶树》中的摄影师何文清),新的经济政策和新的职业构成也同时在为不义之徒提供机会(《远山野情》中的队长和《黑氏》中的信贷员),城镇个体经营上的松动所带来的效应也并不全都那么尽如人意,它不仅没能阻碍或改变某些琐屑情欲,反而对之有所助长(《商州》中的董三海)。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而暴露出来的人心弱点几乎与它的优越之处一样多,这自然引人感喟。
这时,对贾平凹来说,商州不仅仅是一块故土,而且也是一部无法断裂的历史,里边饱含着经历了阶级和时代的种种变异,却仍然保有某种形式的稳定性,不完全依附于经济、政治变革的相对独立和延续性的东西。在《冰炭》这篇小说里,贾平凹指给我们看那种绵绵衍生于商州山地的人道意识在劳改农场伙食管理员的妻子白香身上如元气般的凝聚。同样,从《远山野情》里那个手攥一块杂有金和铅的矿石然后离开深山野沟的香香身上,我们也能汲取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任何环境面前都不放弃自主自立的生活选择力和自尊自重的意志。要是商州在向现代社会的推进中,这些在艰难的劳动环境中产生,并且经受了千百年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一种世代相传的同类经验,一种遗传的文化心理,这种至深至厚的秉性素质受到了冷淡、遗忘甚至蔑视,那么,在贾平凹看来,这种进程就会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
另一方面,贾平凹则在他的商州小说群体中,汇聚起他心智和感情的绝大部分,向世人表明,传统生活秩序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被人们自觉地吸纳、整合到新的生活结构之中,才能不断地保有它的美质并继续发展它的功能,而这,只有当商州顺应山地之外的现代社会进程,物质上摆脱了贫穷落后和闭塞,心理、行为上祛除了小生产的印痕和宗法观念的束缚之后,才可望做到。事情也确实这样,既成的生活秩序如果能够满足商州人的身心需求,那就用不着去担心它会接受外面世界的影响而改变自身。此外,非道德因素也非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实际情况是,社会由于自己突进期的宏大激湍,以致还来不及完全协调自身的所有环节,臻达面面俱到的完善,环节间的发展不平衡留下的某些粗疏和空隙,便使得人类长久致力控制、改善的人性中不那么美好的因素,一时得到了放纵滋蘖的机会;但一旦社会完成了自己的突进期,有了重新调整平衡自身结构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一时抬头的非道德因素就可能在充满新鲜活力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比在此之前的社会结构中更加有效的规导与控制。从终极意义上说,有效地治疗人性的弱点,只能落实在经济文化不断向现代社会的推进中。社会的历史目标,自觉地为实现这些目标努力,这一切将使人的人性本质不断获得升华。这层道理,贾平凹心里是明白的。
黑氏从深山嫁到平川道后,从品行可憎的小男人那里得到的是感情的折磨,后来从老实巴交的木犊那里得到的也只是性的冷漠,直到来顺介入了她的生活,他们才突然从各自的对方意识到了自己生命活力的漫涨,然而这对男女注定还要经受许多的磨难(《黑氏》);甚至秃子、二水们的畸形反常的行为(《商州》《鸡窝洼人家》),都表明贾平凹仔细到不轻易放弃从一个极其特殊的方面,向世人说明文化的封闭与经济的落后,以及人们心理上与地域一样偏仄的道德规范,自然不可能帮助那些深藏在商州人心灵深处的正常欲求得到正当的实现和发展,而只能使它们受到压抑,以扭曲过的形式表现出来。既成的生活秩序由于无法再适应当代人激涨的需求,是注定要被改变和打破的。禾禾从他所择定的新的生产方式再三再四的挫败、困顿中,也从不理解他,面对他采取疏离、冷淡态度的乡邻们的成见中,乃至从个人最隐秘的内心的失意、沮丧、疲惫和感情的痛苦、烦恼中,坚定不移地出发,认准舍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向乡邻证明在他们的出生地上是完全可以开始一种比现有境况合理得多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而他最终也以很会谋划安排生活的智慧和韧劲以及希望别人同他一道过上好日子的真诚心肠,扭转了鸡窝洼人心的向背。看来商州山地发生的生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更易,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外面世界对商州的单向输入过程,若是没有禾禾们,没有绝大多数山地人身上拥有的趋赴现代生活的主动意向,没有具备承受住难以尽述的来自环境和自身的压力和痛苦的意志,外部现代社会的影响或刺激恐怕很难指望会在这里激发多少使人乐观的反应。
这里,贾平凹对养育了他的幼年到青年时代的、有着古朴风尚习俗的那块山地的挚念,演化为一种理性眼光。他以一种宽宏精神而又不无批评地指出了才才、回回们拥有的那种持续不变的心理,那种随遇而安,守己本分,接受并无限度地承担生活的窘迫的耐力,这些曾经支持了王和尚、罗子乃至王和尚、罗子们的祖先的人生的顽强生命力,在时代和社会有了合理变动,山地经济有了重大调整后,就并不完全再是美德了,它含有闷住自己的正常欲求,容忍那种缺乏活力、长久凝滞的自然经济规范继续绵延的厚重惰性。他真正动心地慨叹一个泱泱大族的衰退,为山地生活与外面日新月异的世界隔阂感到不安焦虑。他在这种心境中沉思,然后抬起头来,怀揣一种类似神圣的使命感,对立足故土地面上的门门、禾禾、石根、王才们,对这所有试图按照与现代生活主旨相称的价值标准,重新建构一种富有锐气和活力的生活秩序的努力,都那么急不可耐地发出自己由衷的欣悦和赞同。为他们所倾心、所关注、所偏爱、所表现。力求把握住明朗的趋势或隐蔽的微妙心理,从个人的意念中推测群体的心态,即使用暗示把前景稍稍打开一下,作为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呈展在人们面前也是好的(不过,一般说来,在叙事语调上,他对自己这个主题既不轻视也不夸张,对山地发生的变化的陈述,偏好专注于那种发生在心理深处的微澜)。正是这种全神贯注的大胆独立的研究和验证公认的时代真理(在别的当代小说家那里,这种验证是在生活给他们所可能提供的其他具体形式中进行的),结果使他以商州故土为母题的小说群体,拥有一股超越于某类乡土文学的厚实情致(那类小说实际上是对故土乡村作了偶像化的处理,沉湎于肤浅的感动中),也使他的小说提升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层面上。
问题并不在于看出贾平凹商州小说世界中并存着两种趋赴正好相反的感情倾向(尽管它们在量度和力度上悬殊之大,几乎无法对之等量齐观),而在于要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法协调的游移的二元性情感指向,其实是统一于这样一个耐人寻味、体现当代意识的文化接续课题。
贾平凹的《商州》曾经无意地写到了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对逆交流关系:就像照川坪的青年人迫不及待地从刚刚凿通的公路骑自行车去县城看新鲜世事的同时,省城的美术工作者却来到他们的出生地寻觅到了可以使现代艺术从中摄取智慧清泉的民间艺术。一方面,商州世界正在努力向外面的现代世界寻找自己的前景,另一方面,现代世界也从它业已超越的传统世界中重新发现了可资充实自己文化创造活力的东西,也就是说,两种文化都在试图突破自己,又都从各自所要突破的文化中寻找到了对自己有用的因素。的确,社会进步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的断裂或在此之前的文化的全然消失,它们之间除了具有对峙、超越、分离的性质,还具有连续、互补和整合的性质。并不是时序上较早的文化只属于昨天,只能无一例外地被淘汰、取代和废弃,就此永远沉没在历史的深渊中,时序较晚较迟的文化将是与之决然无缘的改弦更张。新的社会形态耸立于历史的地基上,这使它在高层面的发展中永远葆有一种绵延不断的母体血缘,而以往的文化由于被引导、整合到高层次的发展中,而由约变丰,由简变繁,被不断充实和深化。我觉得,贾平凹陈述商州世事时怀揣有两种指向不同的情感倾向的复杂心境,既在明朗地肯定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给商州带来的巨大而正当的利益的同时,又很有分寸地流露对传统生活秩序所蕴含的一切有价值的成分的珍重意向,以及对人们有时由于暂时的理由而看轻它们的感喟和忧虑,并不像有人担心的那样,存在着某种道德感情上的迷误和感伤现象,它实际是出于小说家对文化所具有的连续统一体性质,对历史的整体性原则的尊重和所拥有的良知。也就是说,贾平凹是试图站在广阔前景上,去观照两种文化,或准确地说,同一种文化的不同形态互相撞击时,变化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化的。
二、家庭结构
血缘上的亲和性与褊狭的地域上产生的重土观念的相互纠结,构成了传统生活秩序中家庭结构的强烈内聚力和稳定性。描述这种结构在更有生气的生活方式的搅动下的聚和散,解体乃至重新建构,常常是贾平凹观照商州世情人性播迁情况的一个有效角度。他的商州小说极其注重用家庭的组合与分化来作小说的结构中心,往往是情节从这里延伸出去,又归宿于此。不过,贾平凹深潜到一个又一个家庭结构的细节中去,并不是打算把自己限定于做一个日常性伦理现象的记录人,他是打算努力把这种自身整饬但格局很小的人伦结构放置在社会历史的宏大、系统的整体结构之中,观照社会历史进程在这一个个细小的家庭结构中接受或鼓励着什么,拔除、并使之一去不返的又是什么,观照它怎样使每一个家庭中的成员或正在筹建家庭的人,离开了自己原来的位置而进入新的生活轨道,世界因为变化而对他们变得陌生,从而迫使每个人重新调整自己的心理平衡,重新进行选择。
在《小月前本》中,那种超越个体意志的普遍的历史意志和实力,具现在小月对构成家庭结构一极的丈夫这个角度的明智而又伴随着痛苦的选择上:离开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生活秩序的才才,走向拥有开拓对山地人说来纯属未知世界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机智和能力的门门。《鸡窝洼的人家》所写的两户家庭的交叉聚集,虽然缠夹着生命繁衍一类琐细的原因,但直接的主导的起因,则无疑是他们对不愿继续屈从于既定的生活习惯而执着地寻求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禾禾所采取的迥异的批判:赞成同情还是怀疑失望。《天狗》中那个以夫养夫的奇异的家庭结构,看起来似乎纯属沿循古老民俗的结果,但井把氏女人对天狗充满古朴原始情味的倾心的内里,是与他身上拥有井把氏所没有的,豁达的脾性,敢去省城谋生,懂得鼓励五兴读书,会科学饲养蝎子聚财,这类更容易贴近现代社会的见多识广的素质不无关系。《九叶树》中那个在感情流露上既矜持而严肃,又慷慨而忘我的兰兰,最终冷静地归回到石根身边,显然是与石根在愤然而艰巨地甩脱自己栖身的那块山地上的蒙昧落后处境时郁勃而出的使命感、责任心、沉着的智慧和过人的意志膂力有关。这些素质,在放弃道德责任的城里小白脸那里是没有的。新的风尚不仅有力地投射在上述类型的家庭的组合过程上,它还具体地成为使建立在古老宗法制下、结构相当稳固的家庭变得不再稳固的缘由。《腊月·正月》中与韩玄子和专业户王才政治经济地位的交叉升降骈体而生的,是韩玄子对家庭内部成员从精神到行为的控制欲的隐忍内缩。除非对变动着的世界做出顺应性的自我调整,而变动着的世界并不会因为要迁就某个人的意愿、尊严之类就裹足不前。《远山野情》和《黑氏》所写的两个山地少妇充满缺憾和个体悲剧性的家庭际遇,似乎更属于偏离常态的异态,采取了与上述家庭类型相反的构思而与其互补,表明小说家估计到山地人在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过程中必须承受的艰难。历史常常以缺憾的形式,在普通人的命运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着自己的蜕变。而香香和黑氏拥有的超过常人忍耐限度的顽强生活力和对人近乎虔诚的善意,就是商州山地赖以生存、在历史发展中永不断裂的精神链条。
如果继续展开体验,而不只满足于单义性解释,那么,我觉得前述《九叶树》似乎还有一种阐释的可能。我觉得那个自私、怯懦、毫无心肝的城里人所以能一度致使兰兰着迷,乃是因为他身上毕竟拥有一种在山里人石根身上还暂时缺乏的文化气质,现代社会的浸润,使他现成地拥有一种在山地女子看来颇为不凡的风度和征服力。仅仅用好耽于幻想,容易受新式生活的虚影迷惑一类理由来诠释兰兰的行为,大概很难贴近她的真性,也有违小说家的本意。这样,《九叶树》写到的这个年轻家庭并不坦顺的组合过程,就还有这样一层提示含义:物质上开始充实起来的商州人,还面临一个难度更大的问题,即如何着手对自己在精神文化上从前辈那里沿袭下来的贫乏状况,做出富有实效的改变和弥补,使身心获得均衡健全地发展。
三、文体实验
贾平凹以商州为母题的小说群体在文体上的实验性极强。文体大致包括文字风格与结构体式。贾平凹商州小说既运挥流畅而浅清澄澈的文字,也驱遣古拙而重涩沉实的文字。规范的中篇叙事结构在他手里把玩得相当纯熟精娴之余,也驾轻就熟地采用靠拢他前些年间曾尽心尽力经营过的散文体式的笔记、杂传框架,并且还乘兴朝长篇体式作出一次跃进。这种文体——结构上的实验和新变,从他特有的创作路数,为中国当代小说多方开拓叙述语调、格局的可塑性尽了一份力。不过,迄今为止的迹象表明,贾平凹并不太擅长叙述能引起人持久注意力的故事,他不怎么善于把无限丰富的质料聚集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小说世界,把人物投进庞杂的情节,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纠结在一起,使之各居其位、各得其所,他似乎缺乏那种既包罗万象又井然有序的高度比例感,他的身上看来也没有那种法力:使沉重的心灵由此寻到安慰,激烈动荡的情绪得到规导,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的英雄欲由此听到唤醒它的神圣力量,可以肯定地说,雄视阔步高翥远翔,一般并不符合他那内向的心理素质,他突出的长处是使人从其看来简单的手法中获得不那么简单的印象,因此一般说来,规模适当、情节相当单纯的中篇体式对他是最得心应手的。
长篇《商州》在文体上显露出一种力不从心的忙乱迹象。那对年轻人的恋情并无出色之处,以至于如果纳入背景截然不同的别的小说框架中,也并不至于让人觉得太突兀。不过贾平凹在每个单元之首以其丰富的修辞知识和广博的掌故佚闻,详尽地写出的商州人的风俗人情、地理地貌,以作为故事的时空依托和文化注释,由于具有比故事的中心人物及其他离奇的行迹更厚实耐读的效果,使我们在阅读中感到的缺憾多少得到了补偿。这部分文字好比颤动的神经末梢那么敏感,吸收外面世界的一切感性印象,现象的推移和流动是不知不觉完成的,事实与传说、现状与历史不存在决然的界限,彼此打通的,恰如它所要陈述的商州生活本身。这里,小说家仿佛急不可耐地决定要告诉读者关于商州的一切,每一个最后的根因、线索、性质或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想在一次惊人集中的努力之中全都告诉我们。这种过于热忱的叙述句法由于感性直观的知觉的印象太庞杂、斑驳、拥塞,常常给急性子的读者增加了阅读上的疲劳,但要是他愿意合作,得到的酬劳也将是丰厚的。可惜,由于它所支持的小说的深层结构,即构成小说内容连续性的成分:情节及意蕴,缺乏厚实的内涵,使得它终究只能滞留在可爱的浅表功能上。
商州小说群体的开山作《商州初录》与晚近的《商州世事》,文体上可以与中国传统史著的“纪事本末体”,古典传记中的杂传、游记和肇始于魏晋大盛于明清的搜集坊间轶闻野语、杂录琐记、志怪传奇的笔记等体式接上渊源。它们是贾平凹作为一个具有当代其他作家罕有其匹的极其活泼的感受力和强健的形象、情绪记忆力,富有人道意识和良知的小说家,在商州山地里几经跋涉的收益。由于旅途的匆忙,也由于心理上的间隔(要知道,人跟人的沟通至少需要假以充分的时日,一个不顾场合随便就可以对旁人畅怀叙说心迹的人,往往只会在日常生活中引起旁人对他说话真诚性的怀疑了),这类小说里的人和事多半只是小说家依据当地对其家族渊源、个人身世的见仁见智的传谈,或者对其现有行状的直接揣摩,从外部的临摹而不是内部心理的描写,通过削繁就简和用神气上的充足来补偿行迹方面的简略的办法,复原而成的。几无陪衬拖带,大量的空白形成特有的韵律感,它们表明,商州的五光十色和千汇万状是没有什么不可能进入贾平凹的艺术视域的。它保留了对生活的生动活泼的新鲜印象,却又并不因行色匆匆而失去艺术上的从容。《初录》在它问世的当初,我就谈过阅读感受,至今并无更多想法好补续,这里仅就《世事》说点什么。我觉得,这类极其简省的结构,历史纵深感总是厚实的,叙事的时间幅度很大,推古及今或由今溯古。而那种将分散状态的山地生活现象按照分散状态的原样依次陈述出来的平朴纪实品格,常无意间指涉到了人生与人性的实质,流露出很高的悟性。
《说话周武寨》中两个家族的交替盛衰、暴虐和残杀,一度包含着情有可原的阶级复仇意味,使我们多少感到点恶性有报的快意。但它们的绵延不绝,成为一种以恶抗恶的恶性历史循环,则表明后来那场波及共和国最僻远的乡陬的“文化革命”所具有的反文化性质(因为它拥有纵容煽动人们心底里的盲目和暴虐的力量),个体心理中沉积着历史经验。人类心底是残留着一部分源于久远的种族记忆,那种野蛮时代的习俗,为了维护和扩张本部族的生存而相互残杀的习俗的。只是随着人类对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征服、改善,这种原始的暴力本能受到了文化的严格有效的规导控制,只在正义的范围内,才被允许启用。因之一切滥用它们的行为,不管以多么高尚的政治名义出面,都将被证明是对人类文化成果的摧毁。所幸的是这种看来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幸存下来的周、武二家的第二代和他们刚长成的第三代那里戛然而止了。关于亲善互助本性在两家人身上的复归,关于不计较历史恩怨、抚平内心创痛重新聚合起来的缘由,小说家没多说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他竭力不想多说的地方体察到他隐去的是什么。首先是一种顺应民意的清明政治所具有的文化规范力量;其次是命运的锁链是死的,人是活的,受缚于它还是摆脱于它,责任就在人自身。这就从一个极特殊的角度让我们窥见了人类对自身的信心:他有承受和控驭客观环境和自身命运的能力。
贫困和愚昧所造成的恶果不仅仅在于性的饥渴和紊乱,而且在于人性由于得不到滋蘖的合适土壤而可怕地萎缩,不得不长久滞留在混浊的生物水平线上。《刘家三兄弟本事》里的老大,在外人看来是忠于护山守林职守以及后来效命于捣毁民族文化的政治运动,其实对他来说却并不是想从集体和政治的事业中去体验那种人的意志、愿意外化后的乐趣,而不过是接受口腹本能的驱使。口腹的欲求就是他的全部生命活动内涵,他为此活着,也为此丧生。
《木碗世家》中那个敏慧的后生依据可靠的信息在经营上的左右逢源,表明摆脱了传统生活秩序和它的惰力之后,将会如何有力地释放出深蕴在商州人内心的创造性的心智、谋略和胆识,这与恪守古训的老人既惊讶又担忧,以及固执地不肯放弃业已无人问津的木碗制作业这条穷途末路,希望能凭此替儿子有朝一日背运时留下一条牢靠的退路,形成一种带着强烈幽默感的心理反差。对这个命里注定走到了尽头的角色下了个充满善意怜悯的历史判断。不过另一种阐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虽然老人对自己终身职业的依恋和矢志不移属于一种不入时调的守旧心理,但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文艺,任其散失又是可惜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它们与被古典哲学看作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道”所效法的“自然”态往往是贴合得那么切近时,感慨就越加深重了。它们的简单、质朴、凝重和接近生命的原色原性,对于过久地被繁缛技巧所累的近现代艺术,所拥有的启悟它们返回人类生命本性的契机作用,在前边我们已经看到了先例。
这类注意力相当繁杂的叙事作品,拥有小说家力求能对故土向现代社会的趋赴提供些有益意见的严肃意向,这种意向同样深浅不同地参合、弥漫在其他文体不同的商州小说中,并由此赋予它们一股健旺的活力、深沉的元气和厚实的艺术张力。
1986年1月30日
(原载《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