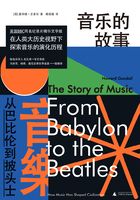
前言 奇迹诞生
也许你最喜欢聆听的是1600年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的音乐,或者是1700年的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800年的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900年的埃尔加(Edward William Elgar),也可能是2000年的酷玩乐队(Coldplay)。不论你喜欢的是哪一种,事实上,足以产生那种音乐的每个条件,例如和弦、旋律以及节奏等元素,大约在1450年就已经被发现了。
当然我指的并不全然是人们所使用的乐器,或是那些让每一首歌曲、协奏曲或歌剧听起来既独特又鲜明的无数新奇古怪创意,而是那些原始素材:音乐的积木。为了让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歌剧《唐·乔凡尼》(Don Giovanni)开场可以仅用三个戏剧性和弦就技惊四座,必须有人先想到同时演奏不只一个音的主意。为了让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能在他的乐曲《夏日时光》(Summertime)用高音独奏在旋律上空恣意翱翔,并制造出迷人的翘翘板伴奏效果,有人得先研究和声的魔法,以及那诱人的轻快节奏。为了使我能轻松写意地坐在家中钢琴前面,悠闲地弹奏这两首杰作——即刻且要如作曲家所想表达的一样——得先有人想出记谱的方法,并伴随着演奏表情指示。
事实上,21世纪的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音乐的选择上完全被宠坏了,只需用手指按个按键,就几乎能无所不听。但在距离我们不远的19世纪末期,即使是最痴迷的爱乐者,终其一生也顶多只能听三或四次他们最喜欢的曲子,除非你刚好有机会接触乐谱与乐器的专业演奏者;而且想在家中欣赏大规模曲式的作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在录音技术与无线电收音机科技问世之前,前人对于要听什么与何时可听这种事,实在没什么选择。由于录制音乐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自由购买喜欢的音乐,借由展示自己对某一首曲子或某种音乐风格的偏好来参与其中,并同时影响其他人。
然而无可避免的,音乐上的民主化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一直以来,音乐的流行品味都是由少数富有的赞助者与机构组织主宰,他们在景气繁荣时,偶尔会给作曲家一点实验空间,而作曲家们也不必害怕饿肚子。但后来这个被称为“流行音乐”的时代,却无预期地变成一道分水岭,在所谓古典音乐范畴的现代派音乐,以及较平易近人的当代音乐之间画出一条界限。对在世的作曲家而言,古典音乐的过去让他们承担沉重的压力,尤其当过去录制的大量音乐被发现又重新出版之后,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作曲家们不把愤恨转化成创意,并想办法结合其他领域的养分重新唤回听众,古典音乐几乎可说是走入绝境。现代的电影音乐,就是古典形态的音乐与现代流行艺术形式巧妙结合的其中一例。对音乐家而言,这种适应环境与随潮流改变的直觉,在过去100年来特别强烈——也特别需要,但它一直都是音乐生活的残酷现实。假使所有时代的作曲家都不愿意去学习、发明、借鉴甚至剽窃,那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听单音圣歌。很幸运的,他们共同努力的心血,转化成当代西方音乐的主干。
我们口中所谓的“西方”音乐——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音乐创作、记录与表演的媒介,在过去100多年来,吸收世界上“其他”的音乐文化加以混合——是起源于世界音乐地图的局部分支。欧洲地中海部落有他们独有的音乐形式,在非洲、亚洲、美洲及澳洲(他们至今仍保留其传统)的部落也是。造就“西方音乐”这通用的类别,是交织了其他音乐丝缕,由埃及、波斯、希腊、凯尔特、北欧及罗马人的音乐组成。然而,就像世界上所有音乐文化传统一样,音乐一开始都是即兴、分享、自发及短暂的。
世界上其他伟大的音乐文化,因其一直保留着即兴创作代代口述相传的传统,它们如今的面貌与几千年前几乎如出一辙,例如印尼与巴厘岛的某些传统音乐,已理直气壮地维持数百年不变。然而,从冰岛繁盛到里海的音乐分支,并没有原地不动,借由一连串的改革,它拥有了傲人的新能力。这么说并不代表我们所继承的西方音乐比印尼音乐来得更好,然而西方音乐发展形式,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完全不同,却也是无法忽视的历史事实。渐渐地,借由过人的决心与开创精神,西方音乐的语汇与脉络,现在看来已成为能够容纳世界上每一个音乐点子的共同语言。
然而要讲述音乐那精彩绝伦的发展的故事,对任何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都是一个谜。更糟的是,这个谜团似乎还是有意为之,笼罩在神秘的术语和扑朔迷离的分类之中,像是一个为专业人士俱乐部所设的特权圣地与保护区。
对于古典音乐的分类方法,人们延续了前人一连串错误且令人混淆的历史标签,几乎没有一个能精准描绘出当时音乐发生了什么事。以文艺复兴——“再生”(rebirth)——来说,那是大约介于1450—1600年之间,期间艺术、建筑、哲学与社会观的步伐,都往前迈进一大步。事实上,音乐也在此阶段经历许多转变,也就是它最伟大的那些变革——音乐记谱法的发明、韵律组织、和声与乐器制作的发展——其实这些过程早就随着许多生活的其他面向,在中世纪无数漫长、无知、黑暗的夜晚中悄悄进行。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有权势的人(顺道一提,没有一位是音乐家),受到古希腊罗马古典(classical)文明的灵感启发,但是在音乐上的“古典时期”,一直到18世纪晚期才真正萌芽,而古典这个词,却已经十分令人困扰地占领了所有西方音乐中非“流行”(popular)的地盘。而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还有巴洛克时期,巴洛克风格在艺术上以华丽多余的装饰著称,但在音乐上却以纯粹与简约的风格呈现。
接下来,音符本身出现一个混乱的错误标示。例如音乐中长度最长的音符称为“短音符”(a breve), “a breve”是“短”的意思,一个“breve”能被细分成四个“微量”(minim),意思是“最短的”——即使它最多还能再细分为八个。在英国公认的“八分音符”(quaver),到了法国却叫“croche”,英国化的“croche”叫作“crotchet”,但是它代表的却是原来“croche”两倍长的音符。德国人和美国人把两个“crotchet”称为“半音符”(half-note),然而法国人把半个“croche”叫作“double-croche”,把“crotchet”叫作“黑色”(noire),把“minim”叫作“白色”(blanche),但是这黑与白并不是指钢琴上的黑白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时代的错误与死胡同,摧毁了古典音乐自身的路标,我将逐章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解开前人遗留在身后那一团混乱的结。
最重要的是,我诉说的音乐故事主要聚焦在随着时代变迁而进化的声响,以及音乐本身的革新,而不在那些因为出名而出名的作曲家们。当然大多数的音乐改革是由知名的作曲家所发动,但有时改革的推动者是由许多不起眼的男男女女组成,他们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世界各大音乐厅的大厅石板上,他们代表的是庞大西方音乐拼图的一小块。世界上已经有许多书籍告诉你,贝多芬在他的钢琴下到底藏了什么,或是谁杀死了猫王,而我只在乎他们给音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你们到时就能知道他们两位如何改变音乐)。
这本书最主要的重点,是聚焦在西方音乐独特迅速的进步,必然会动用到其他音乐文化的观念与技巧,在“流行”“民谣”和“艺术”的音乐风格之间,毫无掩饰地摇摆。我的使命是用一般音乐爱好者能产生共鸣的方法,重新讲述一次关于音乐的故事。我想这样做的决心,因为相信音乐是一种统一的语言而更加坚定,而在一切的努力之后,我确信人们在不同阶段所做的区隔和分类,常常是过于刻意的。音乐家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演奏不同风格的音乐,并在各种领域之间转换技巧,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该是把这个事实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了。
音乐的故事——一波波探索、突破与发明的浪潮——是一种持续的过程,而下一波大浪也许会在中国北京的后巷发生,或在英国盖茨黑德(Gateshead)的某个地下室彩排区。不论你喜欢什么音乐——蒙特威尔第还是曼托瓦尼(Annunzio Paolo Mantovani),莫扎特还是摩城音乐(Motown),马肖(Guillaume de Machaut)还是混搭(Mash-up)——它所凭借的技巧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而是某人在某地率先想到的。要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必须先清理日常生活背景中无处不在的纷乱杂音,试着想象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创新发明,对曾经目睹它们诞生的人们而言,是多么充满革命性、多么令人振奋,甚至多么令人困惑。
不久之前,音乐还只是寂静荒野中珍稀微弱的耳语,现在它就像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到处都是。这奇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