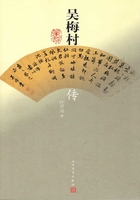
第2章 童年时代(十六岁以前)
一 家世
明朝万历三十年(1609)五月二十日(以下凡月日均采用阴历),一代著名诗人吴伟业诞生在江南太仓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中。
据说吴伟业的母亲朱氏临生产时,梦见身穿大红衣服的官府差役喜气洋洋地送来了一副牌匾,仔细看去,原来是明隆庆五年(1571)会试的第一名邓以赞高中的喜报,就在这时,她腹中一阵躁动,生下了伟业。这段传闻在吴伟业去世以后被弟子顾湄写进了《吴梅村先生行状》之中,不知是得之于吴伟业生前的自叙还是得之于其他什么人,真假莫辨,想来杜撰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一个几十年前的会试第一名,既难称当世名贤,也非乡里人望(邓以赞是江西新建人),朱氏知不知道,记不记得这一个人物都是疑问,更不用会梦见他了。不过,即使没有朱氏这一个预示吉祥富贵的好梦,吴伟业的诞生也同样让吴家上上下下欢天喜地。
添丁总是让人高兴的,何况在吴伟业诞生以前,居住在太仓的吴家的这一支脉人丁寥落,对于家族兴旺的期盼正非常强烈呢。
吴伟业父亲吴琨弟兄两人,他是弟弟。哥哥吴瑗一生没有儿子,而吴琨的原配陆氏也没有生下儿子。伟业的母亲朱氏是吴琨的继配,生下伟业时已经二十四岁,而吴琨已经二十六岁了。可以想见,伟业的诞生让“望子心切”“望孙心切”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如何的欣慰了。家中洋溢着一团喜气,从祖母汤氏到伯母张氏(吴瑗的继配)都跟着一起操劳忙碌,悉心照料着吴家的这个长孙、长子。
浓浓的喜气中融合着殷殷的希望。“伟业”这个名字不知是落魄一生的祖父所起还是年已二十六岁却连秀才也还没有考取的父亲所起。不管是谁所起吧,其中所寄托的那一份希冀、那一份期待则是显而易见的:盼望他长大以后能够成就一番了不起的功业,以光大门楣。振兴家业,使日益寒窘的吴氏家族重新追寻回往日的显赫与荣光。后来给他起字“骏公”也包含着同样的意思。
吴氏家族确实曾经有过一段让家族成员感到荣耀、乐于向人追述的历史。
吴伟业的祖上原本是河南人。他的七世祖字子才,名无考,大约只是个普通人。元朝末年,为了躲避兵乱,从河南迁居到苏州府昆山县积善乡。他的六世祖名埕,字公式,一字式周,由于早亡,也没有建立什么名声。可是到吴伟业的五世祖吴凯就开始发生变化。
吴凯,字相虞,号冰蘗,是吴埕的遗腹子。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吴凯自幼勤奋好学。考上秀才以后,由于擅长书法,被选拔参与了《永乐大典》的修纂。书成,获赐金币而归。后来贡入国子监,中顺天府乡试。明宣德年间,被授以刑部广东司主事,改行在云南司,再改礼部主客司主事。后母亲年老辞官归里,从此再未出仕。吴凯风度翩翩,持身恭谨严肃,而且精敏干练,故颇得乡里称誉。昆山名人、做过吏部左侍郎的叶盛就曾说过:“乡里做官,前辈当法吴丈,后辈当法蕴章。”[1]吴丈指的就是吴凯。
吴伟业的高祖名愈,字惟谦,号遁庵,是吴凯的第三子。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三十二岁时考中进士,被授以南京刑部广东司主事,进阶郎中。弘治五年(1492)升为四川叙州知府,在任十二年,颇有政绩。其后擢拔为河南右参政,第二年便致仕归。自此优游林下二十余年,八十四岁卒。吴愈性谦和,喜交游,所往来者多当时名士。著名画家文征明就是他的爱婿。在吴愈赴叙州知府任的那一年,文征明的父亲文林为他作文以送行。画家沈周为绘长卷并题短歌,书法家祝允明则在长卷上作序。此外,当时以词翰著名的文人如朱存理、刘嘉䋭等也纷纷在长卷上题写了赠行诗。由这一件事就可以想见吴愈当年的地位声望与文采风流了。一百多年以后,吴伟业晚年偶然从某当铺得到了沈周所绘长卷,激动不已,浮想联翩,写下了七言古诗《京江送远图歌并序》,他为有这样的“儒雅倾当代”的祖先感到无比自豪。
吴伟业的曾祖名南,字明方,号方塘,是吴愈次子。由于吴愈的弟弟吴惪没有子嗣,因而过继给吴惪。吴南被赐内阁中书,后官鸿胪寺序班。
从吴凯至吴南,吴氏三代仕宦,成为昆山望族,因此复社领袖张溥在给吴伟业祖母汤氏所献的祝寿文中说:“溥又闻吴氏为昆阳上族,先生(吴琨)祖裔多公卿钜人。”[2]这是一段让吴氏家族成员引以骄傲、无限追怀的家族史。
可惜吴氏家族的好景不长,到吴伟业祖父时,家道一下子就中落了。
吴伟业的祖父名议,字子礼,号竹台,是吴南的次子。他的哥哥名谏,弟弟名诰,兄弟三个都没有取得功名。不过,祖上三代做官,积聚的财富按说也足以让他们坐享其成,过上优裕的生活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保住家产。吴伟业幼年时曾经听祖父和祖母讲述家产败落的原因——吴伟业的祖父和叔祖吴诰因为是庶出,在家中没有地位,不能当家,家中财产全部掌握在伯祖吴谏手中。嘉靖、隆庆年间,倭寇入侵,经常骚扰昆山一带。吴谏用家财招募了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和倭寇转战于太湖、三泖之间。不幸战败,其左右皆死,吴谏也受伤,被一士兵背回,虽然免于一死,可是家产却已耗尽,显赫一时的昆山吴氏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了。吴伟业的祖父后来不得不入赘给居于太仓的琅玡王氏,叔祖也离开昆山,迁来太仓。伟业幼年时见过这位叔祖,既衰老又贫苦,十分可怜,靠给人占卜勉强度日。由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吴氏家道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了。
从吴伟业的祖父吴议入赘王氏开始,吴氏这一支就定居太仓,成为太仓人了。吴谏则迁往苏州。吴议对大哥吴谏的所作所为一定很不满意,因此从此两家就失去了联系。一直到吴伟业中进士后,荣归故里,路过苏州之时,听人说起,才知道自己还有个伯姑(吴谏的女儿)。他曾前往探望,那时,其伯姑已经七十三岁了。伟业回到家里,向家人说起这件事,他的父亲和伯父也才知道还有个伯姊在世。[3]
吴伟业的父亲吴琨,字禹玉、蕴玉,号约斋。他善于写文章,在应试的读书人中颇有些名气,张溥说他当时“文名震动江介”,[4]固然有夸张成分,但也不会完全是信口胡言。他还颇有几分豪爽之气,结交了不少当时的名士,例如上面提到的复社领袖张溥、崇祯朝官至首辅的周延儒、官至兵部右侍郎的李继贞、官至中允的李明睿就都与他交厚,在吴伟业成长与科举的道路上,这些人后来都曾给予过提携与帮助,这大概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只可惜他本人的命运不济,屡试不中,吴伟业出生之后四年,才考中秀才,那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了,此后便与举人、进士无缘。而伟业之后又添了伟节、伟光等孩子,负担愈来愈重,上有老,下有小,全靠他支撑,家中经济状况愈来愈拮据。他别无谋生手段,只得以授书为业。好在他小有名气,聘他做塾师的大户人家不少。他是谁家聘请就到谁家任教,没有固定场所,经常要变换地方。吴伟业小时候随父亲读书,就至少换过四个家塾,可见转换之频繁了。对于吴家来说,这是一段艰辛贫苦的日子,后来伟业的母亲向伟业提起这段生活,曾伤心得潸然泪下。[5]
重振家业,恢复往昔的显赫,成了吴伟业祖父和父亲纠结于心、挥之不去的梦。当这个梦在他们手里实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时,他们也就越来越殷切地把它寄托在儿孙身上了。
二 时世
吴伟业是在祖辈、父辈的小心呵护下长大的。他童年时体弱多病,祖母汤氏、父亲、母亲都对他关怀备至,大约是管束得既细致又严格,以至于他“十五六不知门外事”。[6]这一时期的生活对他来说相当平静和简单,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读书。童年的他绝对不可能理解甚至他的祖父和父亲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当时他们正处在怎样的一个时代。
吴伟业诞生的时候,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二百四十一年了。日益腐败的政治、不断积聚的社会矛盾就像可怕的癌细胞在这个帝国的机体内迅速扩散着,表面看来,这个帝国还很庞大有力,实际上已是虚弱不堪。而最后几位皇帝的倒行逆施,更加速了它的灭亡。
从出生到十六岁,吴伟业经历了明朝的三个皇帝:神宗、光宗和熹宗。
神宗是万历帝朱翊钧的庙号,吴伟业诞生时,他四十七岁。已经在位三十七年了。按常理说,他正当精力旺盛并且富于统治经验的年龄。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由于多年深居宫中,纵欲享乐,废弛政务,已经衰惫昏愚,老态龙钟了,正如当时有人形容的,他整个已成一个“痿痹顽钝世界”。[7]
神宗的慵懒是出了名的。从万历十七年起,他既不上朝,也不处理国家政务,竟然二十多年未曾一次接见大臣。许多大臣因各种原因辞官去职,他不闻不问,懒得补充,致使封建王朝的中枢机构——台省空虚。一段时间内,内阁中仅剩下叶向高一人,因不能正常办公而杜门三个月;六卿中也只有赵焕在,户部、礼部、工部各只有一名侍郎在支应;都察院自温纯罢官,三年无正职;给事中、御史缺员更为严重。[8]整部国家机器的零件大量缺损、锈蚀,已无法正常运转,接近于瘫痪了。大量奏疏无限期积压,名为“留中”,实则不予受理,政治一片混乱。
神宗的奢靡和挥霍也是出了名的。举几个例子吧。万历十九年,他一次就下令烧造瓷器十五万九千套;万历三年至三十九年,派织的潞绸、绫绸、丝纱、绒料竟多达六十八万九千多匹,其长度可绕故宫两千七百六十周;为册立皇太子,行冠婚礼,仅婚礼珠宝等项开支就花费九百三十四万两,加上采买袍服、锦缎和营建三殿、采集大木、扩大制造羊绒等项,那一年累计用银二三千万两,而当时的岁入只有四百万两。连年的不计后果的浩大支出将国家财政拖到了几近枯竭和崩溃的程度。
财政上的窟窿靠什么来填补?别无他途,只有靠加紧压榨百姓。别看神宗在朝政上慵懒,在压榨和剥夺百姓上他却比前辈干得更起劲。万历末年,他三次下令增加田赋,先后每亩加派共九厘,每年增赋凡五百二十万两,使本已穷困凋敝的天下百姓更加喘不过气来。这位“只知爱钱”的皇帝还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刮商民。这些宦官贪婪凶恶如同虎狼,所到之处,鱼肉百姓,横行不轨,敲骨吸髓,无恶不作,甚至公开掠夺,“折人之产,掘人之墓。”[9]弄得十室九空,天下嗷嗷,却无人敢于过问,因为他们是“奉旨搜金银”“奉旨抄没”。
有了这样的昏庸的皇帝,当时政治的败坏也就可想而知了。上行下效,大大小小的官员,并不谋其政,国计民生,全不在心上,一门心思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贪污成风,法纪废弛,土地兼并愈来愈猖獗,皇室、勋戚、官吏、绅衿、富豪都以剥夺民业为能事。潞王在湖广、河南等地占田多达四万顷,每年收取租银有四万两之巨;福王封藩洛阳,在河南、湖广和山东占田达二万顷,每年租银五万两。其他皇室、勋贵、富豪还有宦官占田万顷以上的不在少数。他们占田多,赋税却因为享有特权可以不缴,或者买通官府而脱免,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几乎全部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在贪官污吏的诛求之下,老百姓倾家荡产,日不聊生,很多人流离失所,转死于沟壑之中。有人形容当时“天下之势,如沸如煎,无一片安乐之地”。[10]
封建政治的腐朽和阶级矛盾的加剧,还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党争。
万历十四年发生的“国本”之争可以说是明末党争的发端。所谓“国本”之争,是指关于册立皇太子的争论。在封建君主社会,太子被视为国之根本,立太子即是确立皇位继承人,这件事关系国家前途命脉,非同小可。当时,神宗宠爱郑贵妃,一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因而故意拖延,迟迟不立恭妃王氏所生长子朱常洛。一部分朝臣阿附神宗意旨,但遭到另一部分官员的激烈反对,他们抱定无嫡立长的成规,不断上疏,坚决要求及早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即使被贬官削职也在所不顾。自此,环绕“国本”之争和与此相关之事,官僚中形成了对立的党派,纷争不已,势同水火。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终于被确立为太子,但是党争并没有止息,反而愈演愈烈。
到万历末年,基本形成了两大政治派别。一派是以在野的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东林党”。万历三十二年,在罢官家居的原吏部郎中顾宪成和他的弟弟顾允成的共同倡议下,将宋代杨时讲学之所东林书院修葺一新。他们延请学者,招纳学员,讲学其中。中坚分子除了顾氏兄弟外,还有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他们都是有正义感、有抱负却蹭蹬不得意的知识分子,虽然退居乡野,依然关心国事。顾宪成题东林书院的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很可以见出他们的胸襟。讲学之余,他们每每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天下之士多慕其风者,朝廷中一些正直、廉洁的官员也和他们遥相呼应,结合成一股不容小视的政治力量,忌之者遂称之为“东林党”。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
另一派是由达官势宦及他们的门生故吏形成的势力。这一势力内部派系林立,有齐党、楚党、浙党、昆党、宣党等等名目。他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可是,在对付东林党人上却相当一致。东林党人澄清吏治的要求、反对矿监税使掠夺的举动、开放言路的主张、实行政治改良的呼吁,均遭到他们的抵制、诋毁。他们从私利出发,不问是非曲直,“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11]每一件事都笔争舌战,互相攻讦。在与“国本”之争有关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上,更是聚讼纷纭,争执不休。结果,什么决议也形不成,什么事也干不成,使本来已是运转失灵的政府机构效率更为低下,本来已是十分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加恶劣。
吴伟业十二岁那一年,神宗去世,光宗朱常洛继位。他在位仅一个月,就因纵欲过度和误服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而死。然后由熹宗朱由校继位,建元天启。熹宗是一个年仅十六岁的不懂事的孩子,他把朝政完全交给了亲信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擅作威福,气焰熏天,野心不断膨胀。他有权随意易置大臣、转迁百官,朝中正直之士多被削籍斥逐。除东林党,其他派系多依附宦势,上至内阁大臣,下至地方官员,争相向魏忠贤献媚取宠,称魏忠贤为“九千九百九十岁”,为建生祠几遍天下。阿附魏忠贤、成为魏氏死党者,文臣有“五虎”之目,武将有“五彪”之目。此外,还有“十狗”、“十孩”、“四十孙”之号。政治腐败龌龊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人忧心如焚,奋起抗争。天启四年,也就是吴伟业十六岁那一年,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条条款款,义正辞严。魏忠贤恨之入骨,当年即将杨涟削籍为民,还将与杨涟互通声气的赵南星、高攀龙免官,将万燝廷杖致死。他仍觉不解恨,欲兴大狱。附之者乘机编造东林“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一个拿东林党人开刀,进而迫害所有正直敢谏之士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之中。一时黑云翻滚、恐怖气氛笼罩全国。(此后一二年内,魏忠贤果然下令拘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黄尊素等人。高攀龙投水自杀,其余诸人,皆下狱,遭酷刑折磨,惨死狱中。)
腐败黑暗的统治将农民逼向绝境,大量农民破产,无以为生。为求活路,饥民纷纷揭竿而起。万历末年,起义已是此伏彼起,连绵不绝。天启二年,更爆发了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大起义,队伍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虽然不久被镇压,但却猛烈地撼动了明朝的统治。
明王朝不仅“内忧”重重,而且面临着可怕的“外患”。在白山黑水之间,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落迅速崛起。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国;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公开对明宣战,当年就攻占抚顺;四十七年,明廷以兵部右侍郎杨镐为经略,统率四路大军征讨后金,双方大战于萨尔浒(山名,今在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结果明军惨败,险些全军覆没,经过这一场战役,明朝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后金日益壮大起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疆土被蚕食;天启元年,后金先后攻下沈阳、辽阳;二年和三年,原来向明称臣的蒙古各部落归附后金;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变全部发生在吴伟业十六岁之前。
这时的明王朝,表面看,架子还很大,实际已经中空,虚弱不堪了,就像一座大厦,风剥雨蚀,虫蛀蚁噬,梁柱都已经朽烂,只要再有一两场剧烈的震动,便会轰然崩塌。
三 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尽管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积聚、激化,吴伟业童年时期的明王朝已经露出败相,但是,这样一个庞然帝国的垮台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还在千方百计地支撑它,使它后来得以苟延残喘了二十余年。当时的多数人恐怕还不曾料想距离它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不算遥远了。
在那场天崩地裂般的大变动到来之前的岁月里,吴伟业的家乡——太仓,由于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其他各种因素,时代的暴风骤雨迟迟没有侵袭到它,它甚至显得颇为安宁。而吴伟业的家庭又是一个多多少少享受到一些封建特权的读书人之家,日子尽管过得拮据,但究竟还没有沦落到饥寒交迫的地步。这一切,为吴伟业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读书的环境。相对于吴伟业后来的生活来说,其童年时期是一段单调但却相当平静的日子。吴伟业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余生也晚,犹及见神宗皇帝之世,江南土安俗阜,风习最为近古。”[12]
吴伟业十六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太仓一步,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太仓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吧。
太仓位于长江南岸,接近长江入海口,与江中岛屿——崇明岛相望。再往东,就是浩渺无际的东海了。太仓与崇明岛相夹形成的狭长江道是内陆与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江上行旅、经商之船往来不绝。江道上太仓一侧有好几个入海港口,如新泾荡、茜浪港、七丫港等,刘家港尤为一个繁忙的大港,港内帆樯林立,不少异国来华经商的船只常停泊于此,因此当地人把刘家港叫做“六国码头”。从军事上看,由于太仓和崇明岛像钳子的两头一样控扼着狭长的江道,所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堪称是南京城——明朝初期的首都,迁都之后的留都——东边的第一道门户。明朝初年,这里便设立了太仓卫和镇海卫,驻扎着守军,后来在抵御倭寇入侵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从行政区划上说,太仓之地最早分属昆山、常熟和嘉定三县,并没有独立。明弘治十年(1497)出于治理的需要才始建太仓州,领崇明县,隶苏州府。
太仓处在长江冲积平原上,地势平衍,境内无崇山峻岭。有几座称作山的,如镇洋山、仰山、玉影山,其实都是垒土而成的大土堆。只有一座穿山,方显得有些气势。山下有一个贯通南北、可通往来的长洞,其称作穿山即缘于此。据说山原来是在海中,后来地壳变动,才显露于陆地之上。其高度实际也才不过五十几米,但因为是屹立在一坦平原之上,所以给人的感觉比较雄伟。前人在山上修建了寺庙,成为乡里人拜佛、游览的一个去处。吴伟业年轻的时候曾写下过一首《穿山》诗:
势削悬崖断,根移怒雨来。洞深山转伏,石尽海方开。废寺三盘磴,孤云五尺台。苍然飞动意,未肯卧蒿莱。
诗中化静态为动态,赋予穿山以勃勃生气,刻画出其峭拔耸立、凌空欲起的雄姿。
州境内有一条源于太湖,环州城而南、而东,至城东七十里的刘家港入长江的河流,名曰浏河,或浏家河,又名娄江。因之太仓古代又称“娄江”。这条河既能行船,又有灌溉、泄洪之利,但很容易被淤泥、河沙壅塞。一旦壅塞,则不仅舟楫不通,无法用以灌溉,更严重的是一旦大雨连绵,就会洪水泛滥,河两岸的良田便“废为斥卤”,弄得“土瘠民贫”。[13]疏浚河道自然就成了地方官的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所需人力、费用浩大,且须与上游的郡县协调合作,非轻易可办。只有在政治清明之时才能做到。
论起太仓的自然条件,实在算不得优越,它濒临大海,地势低洼,易生盐碱,易生洪涝,用吴伟业的话说,是“舄卤沉斥,沮洳污莱”,[14]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可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当地百姓的不懈治理——开沟挖渠,排涝压碱,精耕细作——硗瘠之地变成了膏腴之田,稻麦豆菽,棉麻桑竹,皆宜生长。尤适合种棉,全州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种了棉花,成了棉花生产专业区。每到收获时节,棉花堆积如山。购棉商人麇至,尤以闽商居多。吴伟业在七言歌行《木棉吟》中以一种充满感情的热烈笔调回忆了当年棉花生产与交易的兴盛:
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
棉花生产的兴旺带来了棉纺织业的发达。城里乡间,以棉纺织为生的人家连屋比闾,机声轧轧,子夜不休。据记载,当时太仓生产的棉布花色品种繁多,有飞花布、紫花布、夏布、纻经布等等名目,质量非常精致,例如飞花布,《太仓州志》称“最为轻细,妇女染裁作衣裙,极为朴雅”。[15]这些“软如鹅毳色如银”[16]的棉布行销到全国各地,受到人们的欢迎。
种棉业和纺织业的发达使得太仓变得富饶,出现了不少豪商富户,就连普通百姓,尽管在苛捐重赋的压榨和贪官污吏的诛求下,生活得十分艰难困苦,可比起北方和内地的百姓来说,日子还是好过多了。
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富裕程度往往决定了那里的教育文化水平。太仓的教育和文化是很发达的,其教育文化水平之高由科举之盛与人才之众就可见一斑。仅万历、天启两朝,这里中进士和中举人者就分别有三十八人和九十一人之多。很多人位至高官。如万历朝官至首辅的王锡爵、天启朝官至兵部尚书的王在晋、崇祯朝官至兵部右侍郎的李继贞等等,在当时都是颇有名望的人物。太仓所出的文化艺术领域名人尤多,在吴伟业童年前后数十年间,文学家就有明代“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和他的弟弟王世懋,学者就有陈瑚、陆世仪、江士韶、盛敬和顾梦麟,画家就有仇英、王时敏和王鉴,等等。文学家明末复社领袖张溥更是声名赫赫。此外,还有一些外地的著名人物当时长期寓居太仓,如书画家董其昌,文学家陈继儒,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等。他们论文谈艺,授徒讲学,在太仓营造出一片十分浓厚的文化艺术的氛围。
吴伟业就是在这样一个教育发达、人才济济、具有良好的文化艺术氛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受到了乡里前辈名贤的影响,和同时的许多名人都有交往,蒙受了他们的帮助、提携、指点或感染,他后来成为杰出的诗人、戏剧家、书画家,显而易见,和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四 才华初露
吴伟业家居住在太仓城中。城中大户人家很多,他的父亲就在这些人家的私塾里教书。
吴伟业大约从七岁起就开始随着父亲读书了,最初是在江用世家塾。很快,他就显示出卓异的天赋。他理解力很强,且过目成诵,无论学起什么都毫不吃力,因此有人说他“学如夙授”。[17]四五年以后,当他随父亲转到王在晋家塾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写出一手颇为漂亮的文章了。当时,江西人李明睿也在王氏家塾中教书,他教的是王在晋的几个小儿子,吴伟业父亲吴琨教的是王在晋的几个大儿子。他们朝夕相处,关系非常融洽。吴伟业只有十二岁,和王在晋的几个小儿子一起跟着李明睿学习。李明睿对吴伟业这样小的年纪就能写出如此出色的文章感到惊讶,极为赞赏他的才华,断言他将来必成大器。那一年岁末,主人家中设酒宴款待二位塾师,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取出了珍藏的玉酒杯劝酒。李明睿性豪嗜酒,不拘小节,饮到酣畅之处,忘乎所以,不小心把酒杯掉到地上,摔碎了。主人非常心疼,当面喋喋不休地埋怨、责备,激怒了李明睿。宴后对吴琨说:“我不能忍气吞声,继续留在这里了。”第二天一早就愤然地不辞而去。吴琨知道他囊中羞涩,恐怕他在路上困难,追上他,慷慨地把一部分教书的酬金相赠。李明睿很感动,临别,对吴琨说:“您的儿子是个奇才。目下,张溥正在大力提倡恢复古学,必将使东南学界振起,名声大作。您何不让伟业拜张溥为师,跟着他学习呢。”[18]后来吴琨照着李明睿的话做了,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李明睿真是慧眼识人,他不仅看出吴伟业是少见的天才,前程不可限量,而且看出了当时还只是一介生员的张溥所具备的超出常人的学识、宣传鼓动的本领以及非凡的感召力。他的建议也真是一字千金,它竟深刻地影响了吴伟业的人生道路。吴琨应该为自己的慷慨之举庆幸,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这一举动的回报是那样丰厚,他不仅受到点拨,为儿子找到了一位良师,而且后来伟业参加会试,其房师正巧就是李明睿,伟业得以考中会试第一名,多亏了李明睿的有力举荐。
李明睿向吴琨推荐的老师张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年龄只比吴伟业大七岁。其父张翼之,是明朝的太学生,伯父张辅之,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张溥兄弟十人,由于他是婢女所生,所以很受同宗人轻视,尤其是伯父的家人和仆人,对他特别无礼,曾经编造谎言在翼之面前诬陷他。他受此侮辱,气愤填膺,在墙上写下血书:“不报仇奴,非人子也!”谁知愈发遭到仆人的嘲笑,说:“一个‘塌蒲屦儿’(意思是庶出之子)又能怎么样!”张溥当时势单力薄,无可奈何,只能暗暗哭泣,同时暗下决心,一定发愤图强,刻苦读书,将来出人头地。他本来从小就酷爱读书,自此就更加勤奋,不分昼夜地攻读。[19]其所读书一定亲手抄录,抄完,朗诵一遍,即烧掉;之后,再抄,再读,像这样的六七遍,才罢手。他用这种方式来加强记忆。他的手指、手掌握笔处因此常常结成厚厚的茧子,过几天就得削去一层。到冬天,他的手总是皲裂,他就每天在热水里浸泡几次,暖暖手,然后继续抄写读书。后来他的书斋命名为“七录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20]他的学问与日俱增,到他考取诸生时,已是学贯经史,很有些名气了。他立志成为大儒,广交当世名贤,[21]尤与同乡张采交厚,时人号之为“娄东二张”。[22]
张溥不仅力学过人,学识也过人。当天下士人汲汲于功名,皆以揣摩钻研八股文为务的时候,他却敏锐地看出明朝近三百年以八股文取士的严重弊端:士人把毕生精力消磨于空疏无用的八股文,治学的目的只是为了科举,而要博一第,只需熟读宋代朱熹所注《四书》,善于揣摩题意,迎合当时的文风,就有希望考中举人、进士。但这样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往往不通经史,不懂经世济民,难以获得真正的学问。这样的人一旦做官,好的呆头呆脑,不能尽职尽责,坏的便只晓得奉迎上司,敲剥百姓,聚敛财富,成了害国害民的蠹虫,成了一心追求权势的无耻之徒。张溥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疗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复兴古学,引导士人认真研读儒家“六经”,以明道修身为目的,去寻绎和实践真正的儒家精神,同时也要提倡广泛学习历史和其他各种学问,追求真才实学,从而达到挽救世道人心和致君泽民的目的。[23]
张溥通过广交当世名贤,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当他考取诸生,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声望的时候,他的这些主张在太仓一带和附近地区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还远不足以改变读书人普遍沉迷于八股文的状况,但还是有不少有识之士接受了他的主张,努力促成和造就一种研读六经诸史的新风气。
大约正是受到这种风气的感染,吴伟业在拜张溥为师之前,就已经表现出对于俗学的厌弃和对于古学尤其是历史的浓厚兴趣了。他尤其爱读“三史”:《史记》、《汉书》和《后汉书》,[24]这些书让他着迷,他读得如醉如痴,烂熟于心。后来他写诗,喜欢大量用典,典故的出处大部分来源于“三史”,正是得益于这段“幼功”。他的文思也越来越敏捷,文笔越来越酣畅了,能够做到“下笔顷刻数千言”。[25]他练习的虽然仍旧是八股文,但每每不按规定去写。按照规定,八股文的题目主要是摘自《四书》,所论内容必须依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所谓“代圣贤立言”,不允许自由发挥。而他却常常不顾这些框框,随意选择古书中合意的段落,将其内容改写成八股文的形式,为的是驰骋文思与文辞。他后来回忆那时的情景,说自己“于经术无所师授,特厌苦俗儒之所为,而辄取古人之书,捃摭其近似者隐括为时文,年壮志得,不规规于进取,乃益骋其无涯之词以极其意之所至”。[26]
吴伟业的这种治学的态度和文章的写法不合时尚,却正好符合了张溥的主张,使得他得以顺利地成为了张溥的弟子。吴伟业拜张溥为师是在十四岁那一年,当时,张溥的师门是很不容易进的,四方闻其名,欲拜他为师者甚众,因此他择徒十分严格,不问穷富,必先献上文章,不中意的,一概拒之门外。太仓邻县嘉定有一个富人的子弟,一心想拜张溥为师,自知文章浅陋,拿不出手,就偷出吴伟业在书塾中的习作数十篇,投给张溥。张溥读后,大惊,后来得知是吴伟业所撰,不由自主地赞叹说:“文章正印,其在子矣。”于是主动将吴伟业请至家中,收为弟子。[27]吴琨当然非常乐意,了却了一桩很大的心愿。
拜张溥为师可以说是吴伟业童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他人生道路初始阶段的关键一步。自此,他就直接受到张溥的教诲与影响了。古话说“名师出高徒”,从张溥那里,吴伟业实在是获益良多。在张溥身边,他得以亲眼见到老师手抄《周易注疏大全合纂》、《尚书注疏大全合纂》、《诗经注疏大全合纂》、《四书注疏大全合纂》等书,感受到其治学的勤苦。[28]在张溥的指导与熏习下,他更加自觉地抛离了把八股文当成学问和敲门砖的狭隘治学门径,更加注重和努力追求“通经博古之学”,[29]广涉经史子集,从而打下了广泛而坚实的学问基础。另外,由于张溥的关系,他的交游范围扩大,名字逐渐为人们所知。不过,后来吴伟业在科举考试中的一些意想不到的遭际和做官后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党派斗争的旋涡,也都和张溥有着密切的关系,但那已是后话了。
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择师而从固然重要,择友而处也不能忽视。吴伟业童年生活中的几位少年同窗这里也值得一提。
一位叫穆云桂,字苑先,是伟业父亲的“执经弟子”。他自少能文章,然终身不得志,平生笃于师友之情,师友死生患难之际,每每倾身为之周旋。伟业十一岁时就认识他了,他们“居同巷,学同师,出必偕,宴必共”,[30]成为最要好的朋友。在以后的五十年中,他们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吴伟业称“余虽交满天下,其相知莫如君”。[31]
另一位叫吴继善,字志衍。其家境丰饶,伟业的父亲曾到他家教读,伟业跟随着去读书,地点是位于太仓城西隅的五桂楼(又名南楼)。[32]当时伟业十四岁,志衍长他三岁,二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志衍性情豪爽,才华过人,他通经史,善诗歌,工绘画,“下至樗蒲、六博、弹琴、蹴踘,无不毕解”。[33]伟业对他十分倾慕,而他对伟业的才华也非常称赏,他们彼此钦服,乐于接近,所谓“惺惺惜惺惺”,这成为他们友情的一个基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相同的志趣,二人俱好古书,而“特厌苦俗儒之所为”,[34]思想上都接受了张溥的影响,又都满怀理想与憧憬,希望一展抱负,所以非常谈得来。伟业后来作诗,常常追忆起他们当年的交往:“予年始十四,与君早同学。君独许我文,谓侔古人作。长揖谢时辈,自比管与乐……词场忝两吴,相与为犄角,”[35]“我昔读书君南楼,夜寒拥被谈九州。动足下床有万里,驽马伏枥非吾俦,”[36]由这些诗句可以想见他们心心相印的友情以及他们风华正茂、壮志凌云、豪情满怀的精神面貌。
少年时代的吴伟业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只等着将来一展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