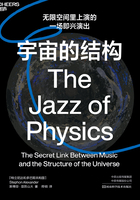
音符的魔法
在一个炎炎夏日里,已为人祖母的露比·法拉(Ruby Farley)正襟危坐在自己的摇椅上,头戴一个华丽的加勒比风格的发带。孩子们在她位于布朗克斯的褐色砂石屋外玩着威浮球。祖母用她那悦耳的特立尼达口音喊着:“哎呀,我才不管你会练习几个小时的钢琴呢,反正你必须练到掌握这首歌为止!”她8岁的孙子——也就是我,很难把手指放在正确的琴键之上。我泫然欲泣,因为我唯一能听到的“乐声”就是小伙伴在外面玩耍时发出的欢笑声。突然,祖母严肃的表情柔和了下来。她笑了笑,自言自语般唱道:“啊,仿佛现在就可以看到,我孙儿的名字在百老汇的星光大道上闪耀。”祖母在布朗克斯区做了30年的护士,积攒下了一些钱,希望能把我送上成名之路,但我并没有成为一位钢琴演奏家。
法拉是我的祖母,于20世纪40年代在特立尼达长大(那时特立尼达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并在60年代迁居到纽约。当时,加勒比海地区和纽约之间的音乐交流非常活跃,因而她带去的不仅是她的特立尼达口音,更多的是当地的音乐。当她从特立尼达返回纽约时,她会带回来卡利普索大师的唱片,如《小麻雀》(Mighty Sparrow)和《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正是通过这些唱片,我才得以把灵魂乐(soul music)与特立尼达本土的卡利普索音乐(calypso)结合在一起。这种被称为“卡利普索之魂”的索卡音乐(soca music)融合了东印度文化与非洲文化,于6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并在70年代特立尼达的艺术家在纽约录制唱片时成形,灵魂乐、迪斯科音乐和放克音乐(funk music)都曾对它产生影响。
对祖母和她那一代的许多非裔加勒比人来说,音乐家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经济地位与社交地位的职业之一。早在我8岁时,在我的父母及其兄弟姐妹离开特立尼达,来纽约与祖母同住之前,祖母就为我制订了学习古典音乐并成为钢琴演奏家的宏伟计划。这是她试图给我一张通向经济自由的船票的方式,而无论是她还是我的父母都从未拥有过这种自由。我的钢琴老师迪·达里奥(Di Dario)夫人是一位年逾古稀的意大利女士,也是一位严格的监督者。对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跟随她弹奏练习曲、记忆音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正是这种必须成功的潜在压力迫使我坚持下去。虽然我不喜欢在祖母期盼的眼神中进行枯燥的练习,但那些创作了我练习曲目的古典作曲家还是勾起了年少时的我的好奇心。他们竟然可以把音阶组合在一起构成音乐!我深深地为“仅仅12个音调就可以构成大量歌曲”这个想法着迷。每当练习钢琴时,我就会被一些杂乱的想法分散注意力,而这些想法会逐渐变成意义深远的问题。人类是如何发明这种被称作“音乐”的事物的?当我演奏大音阶时,我为什么会感到愉悦?C大调中的关键音符C、E和G都是令人愉悦的音符。“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歌曲《情不自禁爱上你》(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的第一行“Wise(C)men(G)say(E)”正是这3个音符。然而,当我的手指从白E键滑到黑E平键上时,令人愉悦的音符就变得令人悲伤了。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