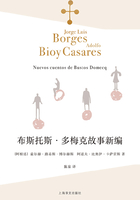
第1章 生死友谊
一位年轻朋友的来访总是非常圆满。在这乌云密布的时刻,如果你不能跟年轻人在一起,那最好还是留在墓地。于是,我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贝尼托·拉雷亚先生,并且还建议他到街角的一家乳品商店会合,免得麻烦我太太。我太太清扫房间的时候,脾气越来越不好,我们只好换个地方。
你们中有人可能会记得这位拉雷亚先生。他父亲去世以后,继承了一些小钱,还继承了家族的一座大庄园,那是他父亲从土耳其人手中买下的。那些小钱都花在了吃喝玩乐上,但是他并没有卖掉那座在他身边逐步衰败的白玉兰庄园。他甚至没有离开他的房间,整天沉迷于沏马黛茶和做木工这两项爱好。他宁愿穷得体体面面也不愿意在任何时刻做不体面的事情,或者跟黑社会有什么瓜葛。贝尼托现在已经三十八岁了。我们都越来越老了,谁也无法逃脱。而且,我还看到他总是情绪沮丧,连送牛奶的人上门送奶时,他也从不抬起头来。隐隐约约地发现他生活过得不如意,于是我告诉他,好朋友随时都愿意帮他一把。
“布斯托斯先生!”他痛苦地说,一边还趁我不注意偷了一个羊角面包,“我已经快被淹到耳朵了,如果你再不帮我一把,什么荒唐的事情我可都能做得出来。”
我想他肯定会扯我的袖子向我借钱,我时刻提防着。这个年轻朋友摊上的事还要严重得多。
“这个一九二七年对我来讲是糟糕的一年,”他解释说,“一方面,饲养患白化病的兔子,这是隆戈巴迪报纸上那种豆腐干小广告所号召的,把我的庄园搞得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洞穴和绒毛。另一方面,我在体育彩票和跑马比赛中都没有中过一个比索的奖。老实跟你讲,我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瘦牛的影子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在我们那个街区,商店已经不愿意再给我赊账,老朋友们远远地看到我都会绕道避开。我求助无门,处处碰壁,于是我只好决定求助黑手党。
“在卡罗·莫尔甘蒂自然死亡周年的时候,我穿着丧服参加了塞萨尔·卡皮塔诺在奥罗尼奥大街的小洋楼举行的纪念会。我没有用金钱方面的问题惹‘教父’心烦,因为他最不喜欢这样的坏品味。我让他明白我的到场没有一点儿私心,纯粹是为了表达我对他卓越领导的事业的追随之情。我本来非常担心纪念会开始阶段那冗长的仪式,人们对此谈论得够多了。但是现在,你看到了,他们向我敞开了黑手党的大门,好像罗马教皇的特使在支持我。堂·塞萨尔先生在与我单独交谈时,告诉了我一个让我感到非常光荣的秘密。他跟我说,由于他的地位太稳固而招来了很多的敌人。还说他最好到一座几乎被遗忘的、枪子儿也打不着的庄园去住上一段时间。而我正好是一个不愿意错失机会的人,我立马就回答了他:
“‘我正好拥有您在寻找的东西:我有一座白玉兰庄园。位置也是很合适的:对认识路的人来说其实并不远,但是众多的兔窟鼠洞会让陌生人望而却步。我以朋友的名义提供给您,甚至供您免费使用。’
“这最后一句话可谓一锤定音,是当时那情形所必须的。为了彰显大人物所拥有的那种大方,堂·塞萨尔先生问道:
“‘吃住全包?’
“为了不输任何人,我回答他:
“‘您还可以拥有一位厨师和一个小工,就像拥有我一样,这样能满足您哪怕最任性的各种需要。’
“我感到自己被上下打量。堂·塞萨尔先生皱了皱眉头,他对我说:
“‘还说什么厨师小工的呀。我相信你,一个陌生的外人也许已经是在瞎胡闹了,我发疯也不会同意别的人再插足咱们俩之间的秘密的。他们会把我像卖废铜烂铁一样卖给康伯萨奇家族的。’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厨师,也没有什么小工。不过我答应他当天晚上就会把那两个人辞退。
“大老板皱了皱眉头,告诉我:
“‘我接受了。明天晚上九点钟声敲过,我就会提着行李,在北罗萨里奥等你。让大家以为我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你什么也不要讲了,马上离开这里;人们总是会打坏主意。’
“这是我的计划中最耀眼、最成功的部分。我高高兴兴地跨出大门,离开了。
“第二天,我从屠夫科塞尔借给我的钱中取出相当部分,向邻居借了一辆四轮大马车。我自己当起了车夫。从晚上八点开始,我就在车站的酒吧里等他,每隔三四分钟就要探头看一下是不是有人偷我的车。卡皮塔诺先生还是来晚了,要是乘火车的话,他肯定误车了。他不仅仅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这在非常看重行动的罗萨里奥地区来说是既受欢迎又令人生畏的——而且还是一个滔滔不绝的金嘴巴,根本就没有你插嘴的机会。直到鸡叫时我们才精疲力尽地赶到。喝了一杯香喷喷的牛奶咖啡以后,客人又精神抖擞起来,马上重新捡起话题。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足以显示出他对纷繁的歌剧世界非常了解,特别是对于恩里科·卡鲁索[1]的歌剧生涯的了解。他赞美前者在米兰、巴塞罗那、巴黎的成功,在纽约歌剧院以及在埃及和联邦首都的成功。因为家里没有唱机,他便模仿偶像在《弄臣》和《费朵拉》的音色高歌起来。由于我显得那么深信不疑,因为我对音乐了解甚少,仅限于拉扎诺[2],于是他就引经据典,让我心服口服。他自己说曾经为卡鲁索在伦敦的一场演出就付了三百英镑,还提到在美国,黑手社组织曾经以杀死他相威胁,要勒索他很多很多的钱,在黑手党的干预下才阻止了那些恶棍违背道德实现他们阴谋的行为。
“恢复体力的午觉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钟,解决了吃午饭的问题。没过多久,卡皮塔诺站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刀叉,餐巾系在后颈,唱起了《乡村骑士》,虽然不够完美,但是声音洪亮。双份肉糜,再配上一瓶奇安蒂红葡萄酒,共同支撑了他口若悬河的讲话;我被他的口才征服,虽然几乎没有尝上一口饭,不过我还是了解到不少卡鲁索私下和公开的轶事,几乎可以应付一场考试了。虽然令人讨厌的睡意越来越强烈,我却没有落下他讲的任何一句话,也没有忽视一个主要的事实:客人不太关注口中吞咽的食物,而只关注他的演讲。凌晨一点钟他回到我的卧室,而我则在唯一一间淋不到雨的柴草房安顿下来。
“到了第二天,当我麻木的身体醒来,准备戴上厨师帽的时候,发现储藏室里的粮食没剩多少了。这不是什么怪事:尽管我的朋友科塞尔特别喜欢放高利贷,但是他还是提前告诉我,他不会再借给我一个铜板;从我的日常供货商那里,我只搞到猫牌马黛茶、一点点糖和一些可用作果酱的橘子皮碎片。我十分慎重地告诉了所有人,我的庄园里住着一位能够施展得开的大人物,很快我就会不缺钱花了。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甚至我想,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关于收容的事。面包店老板马内格利亚更是过分,他当面顶撞我说,他已经厌恶我骗人的假话,并要我别指望他的慷慨大方,哪怕是喂鹦鹉的一点点面包屑。非常幸运的是我遇见了杂货店老板阿鲁蒂,我纠缠他直到搜刮出一公斤半的面粉,使我能够勉强撑过一顿午饭。对想跟虚荣的人交往的基督徒来说,世界并不是鲜花满地。
“当我买好东西回来,卡皮塔诺正睡得像死猪一样,鼾声四起。当我第二次按响喇叭——这是法院拍卖那辆斯蒂庞克汽车时我拯救下来的老古董——他骂骂咧咧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很快就喝完了两碗马黛茶外加奶酪碎屑。直到这时,我才发现门旁边放着一把令人胆战心惊的双管猎枪。你一定不会相信,但是我尤其不喜欢住在由魔鬼掌管的武器库里。
“就在我拿出三分之一的面粉,准备给他做意大利丸子当午餐的时候,塞萨尔先生没有浪费他黄金般宝贵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大搜查。他一个一个地打开所有的抽屉,结果发现了一瓶我遗忘在木工间的白葡萄酒。他就着丸子,居然喝光了那瓶酒。更让我瞠目结舌的是他竟然还演唱了卡鲁索的《罗恩格林》。大吃大喝、夸夸其谈之后睡意袭来,下午三点二十分他就上床睡觉了。我在里边洗着盘子、杯子,哀叹着又一个痛苦的问题:今天晚上给他做点什么?一声令人恐惧的呼叫把我从思考中惊醒,只要我活着,我必须永远牢记在心:现实比我们所有的预想更加恐怖。我的老猫‘叉杆儿’按照它的老习惯,不小心来到我的卧室,结果被卡皮塔诺先生用指甲剪割断了喉咙。很自然,我为之感到十分惋惜,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不免庆幸它十分有价值的贡献,因为它为我们的晚餐菜谱提供了食材。
“真是令人震撼、急转直下。吞下了猫以后,卡皮塔诺先生竟把音乐方面的话题抛到一边,开始展示他对我的信任,向我透露他最最秘密的计划,都是些我觉得根本就行不通的计划。你一定不会相信,这让我毛骨悚然。那计划是拿破仑式的,它不仅包括用氢氰酸毒杀康伯萨奇本人及其家族,而且还包括对形形色色同伙的灭口:封希,小便池炸弹魔术师;萨皮神父,肉票儿的忏悔牧师;毛罗·莫尔普戈,别名‘髑髅地’;以及阿尔多·阿尔多布兰迪,死神小丑。所有这些人或多或少的都会轮到。塞萨尔先生一拳砸烂了玻璃杯,对我说:‘对于敌人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讲了如此激烈的话以后,他抓起软木塞,以为是饼干,差点儿噎死。他终于吼了起来:
“‘来一升葡萄酒!’
“这是照亮黑暗的一道光。我在一大杯水中滴了几滴色素,随即被他一饮而尽,并使他摆脱了困境。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让我直到清晨鸟儿叽叽喳喳叫起来的时候,也没能睡着。我从来没有哪个晚上会这样思来想去一整夜!
“我有棉花和樟脑丸。用这些配料,我为星期二的大胃王做了一大盘较前次略寒酸的丸子。一天又一天,我巧妙地不断增加剂量而未受惩罚,因为塞萨尔先生正热衷于卡鲁索或者沉迷于他的仇杀计划。但是,我们这位沉迷音乐的人,还知道重新回到大地上来。请相信我,他曾不止一次指责我是老好人:
“‘我看你太瘦了。你得多吃点,尽量多吃点,亲爱的拉雷亚。我最最希望的是你精力充沛、精神抖擞。我的复仇需要你。’
“同从前一样,骄傲又一次毁了我。在听到早晨送奶工人的第一声喊叫时,我的计划整体上已经成熟了。命运之神让我在一本过期的《信使年历》中发现一些压得平平整整的钞票。我煎熬着不用这些钱去喝两杯牛奶咖啡,而是马不停蹄地去购买木屑、杉木板和颜料。在地下室,我不知疲倦地用这些材料制造了带有铰链的木头蛋糕,超过三公斤重,而且我还艺术化地把它涂成了栗子色。一把长期不用、走音失调的吉他,给我提供了一套销钉和插销,我把它们精心铆接成装饰花边。
“我漫不经心地把这个杰作献给了我的保护人,他特别喜欢,张嘴就咬,可他的牙齿远不如美食坚固。他大骂了一句,站起身,右手拿起猎枪,命令我最后一次祈祷万福马利亚。你能看到我哭得有多伤心。我都不知道是出于鄙视还是出于怜悯,老板同意让我的生命再延长几个小时,他命令我:
“‘今天晚上八点,当着我的面,您把这个蛋糕吃掉,不得留下任何碎屑。如果做不到,我就杀了您。现在您自由了。我知道您不敢告发我也不敢试图逃跑。’”
“这就是我的故事,布斯托斯先生,我请求你救救我。”
情况确实非常微妙。卷进黑手党的事,跟我的作家身份毫不相称;然而,要我抛弃一位青年,让他听天由命,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但是最基本的理智劝阻了我。他得为自己收容人民公敌住在他的白玉兰庄园忏悔!
拉雷亚尽力站起来,向死亡出发。要么被木屑噎死,要么被子弹打死。我毫无怜悯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