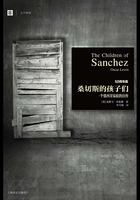
第6章 曼努埃尔(1)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八岁。我跟弟弟罗伯托一起正睡在地上的一张席子上。我的两个妹妹,康素爱萝和玛塔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在床上。我好像正在做梦,突然之间听到爸爸在大喊大叫。他发现我的母亲从他身旁滑到一边去,觉得她就要死了,于是赶紧叫我们。我一般睡得比较沉,所以父亲只得提高嗓门。这下子他完全是在高声咆哮:“起来,王八蛋!起来,蠢猪们!一群废物!你们的妈妈就要见阎王了,你们却在睡大觉。起来,你这龟孙子。”紧接着,我战战兢兢地爬了起来。
我还记得妈妈的眼睛,和她看我的眼神。她口吐白沫,说不出话来。他们已经派了人手去叫医生,医生就住在一个街区之外,可我的母亲还是没能挺过来。她的脸色越来越暗,当天晚上就死了。母亲死的时候还怀着一个弟弟,可能就要生了,因为我记得妈妈的肚子已经很大很大。别的女人照看着我的妹妹,所以玛塔一直长不大。
究竟是因为怀孕,还是因为他们跟我说的“心脏和肝脏感染”,我不知道。但当我的母亲瘫软下去时,她肚子里的东西,也就是我的弟弟,还在起伏乱动。他还在乱动,我父亲却神色绝望。他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让人剖开她的肚子把他取出来,还是就让他那样子算了。我父亲哭得很厉害,他哭着去跟他的亲戚朋友们报告了消息。
她的过世让所有人都很震惊。她只有二十八岁,噢,对了,很健康,很健康。人们当天还看见她在清扫院子,侍弄家务。唉,那天下午她都还在替我父亲捉虱子。当时我母亲坐在门廊里,父亲就躺在她的脚边。
那段时间,我们住在特诺奇蒂特兰街上的一个居民区。傍晚,妈妈会对我说:“出去买点玉米饼和玉米粥回来。”我于是走到街角,在一个妇女摆的摊子上把那些东西买了回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星期一,因为头一天是星期天,我们跟着爸爸和妈妈去巴西利卡郊游了一趟。
那个星期天,我们全都吃了鳄梨、猪肠和荔枝,发火前后吃这些东西对胆很不好。对了,星期一早上,我母亲因为弟弟罗伯托的事儿发了很大的火,她还跟隔壁一个女的狠狠吵了一架。
那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父亲下班回家后,他们俩的心情都很好。我们几个孩子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们还在吃饭。那天晚上,我母亲病情发作的时候,父亲甚至来不及找个牧师,赶在她死之前为他们做个婚礼。
参加葬礼的人很多,有租户,也有市场里的人。我不知道尸体在家里能放多久,可父亲就是不让大家把她的尸体抬出去。人们甚至有些微词了,因为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变质。到了墓地,人们把我母亲的棺材放到坑里的时候,我爸爸还想跟着她一起跳进去。他仿佛心碎了一般号啕大哭。一想起她,我父亲就没日没夜地哭。
安葬了母亲,爸爸对我们说,他只有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做好孩子,因为他既要当爹又要当妈。他说到做到。他很爱我的母亲,过了六年才再娶了艾莱娜。
我相信,我的父亲很爱我的母亲,尽管他们经常吵架。我父亲很犟,是一个用行动说话的人。他经常跟我母亲吵架,是因为他是个很爱整洁的人。如果他发现什么东西位置不对,或者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就会跟她吵。看到他们大吵大闹,我总是怕得要命。有一次,他们吵得非常厉害,父亲很激动,想用刀子捅我的母亲。我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吓唬她,反正我是站到了他们中间。我的身高还不到他们的腰部。我一站进去,父亲马上就平静了下来。我哭了起来,他于是说道:“好,儿子,别哭了,我们不打了。别害怕。”
我爸爸十分反感喝酒——甚至连闻一闻都讨厌。一次,我妈妈去参加瓜达卢佩姨妈的圣徒纪念日,他们灌她喝了很多酒。于是,他们大吵了一架,我依稀记得他们还分开了一段时间。我应该只有三四岁。我们那时候住在贝克大街十四号的居民区,只有一个房间,一间厨房。我母亲去了住在同一条大街上的瓜达卢佩姨妈家。人们问我是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我想,我那个时候更喜欢妈妈,因为我说要跟她。他们分开了两个星期的样子。
我母亲的性格跟父亲截然相反。她性情开朗,喜欢跟大家交谈。我还记得,每天早晨,她一边唱歌一边生炭火给我们做早餐。她会一直唱个不停。她喜欢各种动物,那也是我们唯一一次养过狗。“悠悠”曾经悉心看管过我和罗伯托。我妈妈想在家里养上许多植物和会唱歌的鸟,但那个时候我爸爸坚决反对花钱做这样的事儿。
妈妈喜欢聚会,做事很讲排场。不管是替我父亲的圣徒节办舞会,还是给我们的生日小小庆祝一下,她都会准备几大盘菜,把所有的亲戚朋友请到一起。她甚至喜欢喝上一两杯,不过只有聚会的时候才这样子。她是可以把自己的饭菜分给有需要的人的那一种人,而且经常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夫妻睡在我家厨房的地板上。
她活着的时候,我们家真是快乐无比。她死后,我们的房子里再也没有举办过聚会,也没有人来看望过我们。我从来不知道父亲是否有朋友,他可能有朋友,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说到串门,我父亲进过的房门只有他自己的家。
母亲大多数时候都要做工来帮衬我的父亲。房租是他付,他也会给她买菜的钱,但姨妈告诉我,他从来没给过钱让我母亲去买衣服穿,或者做其他事情。整整五年的时间,她就在周围一带卖面包屑。她从艾尔格兰雷诺面包店买来卖剩下的面包屑,然后以五分至一毛钱一小堆的价格卖出去。后来,她又认识了几个做二手服装买卖的人。她在市场上摆了个摊子,常常会带我一起去罗马区购进服装,拿到摊子上出售。
可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很悲伤的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中还有一个男人。我并不知道,但我相信母亲是出于爱才嫁给我父亲的。他们是在一起做工的拉—格罗里亚餐馆相识的。可还有一个名叫卢裴塔的女人,也在那家餐馆做工,我母亲对她嫉恨不已。她有一次对我说,那个女人就是我父亲的情人。也许就因为这个,我妈妈才偷偷去见那个做二手服装买卖的人。她经常带着我一起去,也许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不想跟他走得太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单独见过面。
我很生气,但那个人像所有的男人对付小孩一样,会给我一点零花钱,带我们去看电影,或者给我买点小东西。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放开过母亲。我会拉着她的手,不让她和他说话。有一次,我威胁说要跟父亲讲。她说:“去吧,去跟他说吧。他如果杀了我,看你没有了我怎么办。”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那个胆了。我的父亲为此嫉恨得要命。
我不记得跟那个男人的事情持续了多长时间,但我们总共只看过三场电影,然后我母亲就死了。他一定很爱她,因为他甚至来为她守了夜。看见他走进我家,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真是恨死他了。我父亲也在场,他怎么有胆量还敢来?后来,那个人开始酗酒,潦倒不堪,不到一年也死了。现在,我可以原谅他,因为他诚心实意地爱过我的母亲。我那个时候不太懂事。
我妈妈非常喜欢朝圣。有一次,她带着我和罗伯托去查尔玛神殿参拜。查尔玛是穷人最爱去的神殿,穷人们满怀虔诚和热爱,要在崇山峻岭间行走六十多公里。背着毯子、食物和衣物,那真是一段艰难的路程,也是一种牺牲。我们去的时候,一路上有很多人。我们走了四天才到达那个地方,一路上就睡在山林里,或者小镇上,就在屋外,睡自己带去的草席。我和罗伯托一到晚上就很害怕,因为我们听那些女人说过,女巫会吸小孩子的血。一个女人对我母亲说:“看好小孩子啊,因为女巫在这个时候特别活跃。知道吗,昨天他们发现了三个小孩子,身上的血被吸得一滴不剩。”
罗伯托问:“哥哥,你听见了吗?”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害怕得要命。我说:“你懂什么?我们晚上用毯子盖住脑袋,他们就不知道我们是小孩了。”
一路上,到处都是十字架,那是曾经死过人的标志,于是所有的妇女都认为,死人的灵魂在等着吃掉路过的小孩子。带着孩子的妇女每经过一个十字架,都要大声喊出自己孩子的名字,这样一来,孩子的灵魂就不会被留在那里了。
到了山间,人们会看见一团团火球从这个山顶飞到那个山顶,于是齐声喊道:“女巫!女巫来了!”接着,人们会跪下祈祷,母亲们则会把孩子给藏起来。妈妈先用毯子把我们盖起来,然后紧紧地抱住我们,这样女巫就找不着我们了。人们说,抓女巫最好的办法是跪在一把打开呈十字的剪刀跟前,并向上帝祷告。每念一句“我的主啊”,你就用围巾盖着打一个结。打完最后一个结,女巫就会掉到你的脚边,然后你就可以用生木头点一把火把她给烧掉。
穿过一个个山口的路上,妈妈会给我们讲查尔玛的传说。她会指给我们看“牵兽人”,那是一块长得像人的岩石,穿着印第安人的服饰,牵着一头驴和一条狗。有人说,那个牵兽人在上山的途中杀死同伙,自己也被变成了岩石。接着,我们又经过了“干亲石”,也就是位于河流中央的几块大石头。那原本是几个互为对方孩子教父母的干亲家,但因为走到此处的河中央发生私通行为而犯了原罪,结果也被变成了大石头。还有一块我很好奇的大石头,活像一个牧师,戴着帽子,披着斗篷,一只手撑着腮帮子似在沉思。谁知道他犯了什么原罪呢,反正他也被上天惩罚了。老人们相信,这些岩石每一年都会往神殿的方向滚动一下,等他们哪天滚到了神殿,也就醒了,又会恢复各自本来的面目。
我们也遇到了悔罪者,这些人立誓以跪姿沿岩石小路爬到神殿去,有些人还把自己的脚踝严严实实地捆了起来。他们走得很慢,大家相互搀扶着,走到神殿的时候往往血流不止,不光磨破了皮,有些甚至露出了森森白骨。那样的场景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妈妈和她的家人定期要去查尔玛。他们对于拉各斯的圣胡安圣女也很虔诚,去那里朝觐需要的时间更长;妈妈每年都会带我们去一趟。爸爸只陪她去过一次,但没有陪她去过查尔玛。他不喜欢朝觐,那也是他们争吵的另一个原因。我爸爸总是这样评价我妈妈的家人:“那么虔诚,可去神殿的路上还是照样喝酒。”
那倒是真的,因为我母亲的几个兄弟,何塞、阿尔弗雷多和卢西奥都很会喝酒。实际上,他们几个都是喝死的。瓜达卢佩姨妈每天也喜欢喝点雪利酒。但我想不起我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外祖母喝酒的事情了。她是个活泼的老太太,走起路来腰板挺直,总是穿得非常干净。不干净的东西她从来不穿,鞋子总是擦得铮亮,她的着装很严谨,黑丝袍,黑长裙。
我外祖母原来跟瓜达卢佩姨妈住在漆匠大街。每天早晨,爸爸上班之后,外祖母会在早饭时间来我们家里。她来帮我妈妈,把我们的脸、脖子和小手擦洗一遍。她用捣碎的茅草团给我使劲擦洗,我忍不住要大叫一通。她总会说:“你们这些淘气鬼,怎么会弄得那么脏?”
外祖母对宗教十分着迷,比我母亲更着迷。她也像我们的教母,教我们画十字、做祈祷。她虔信天使长圣米盖尔,教会了我们怎样对他祈祷。她还笃信上帝,说那是医治百病的良药。每逢重大节日她都要祈祷上一个小时,如复活节、圣灵降临节、亡灵节……。亡灵节那天,她会点起蜡烛,拿出玻璃杯,摆上供品面包,鲜花和水果。她和我母亲死后,家里就再没有人做过那些事儿。外祖母是唯一懂得传统,并尽量想传给我们的人。
我父亲的家人生活在韦拉克鲁斯的一个小镇上,我们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我和罗伯托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的爸爸派人来找过我们。爷爷很孤单,因为奶奶死了,几个叔伯也死了,当然我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爷爷在瓦清朗格开了一间很大的杂货铺,村里很多人都欠他钱。他说那间铺子归我们,我父亲后来把它给卖了。但我的一个叔叔,以及跟我爷爷算得上半个兄弟的一个人为了夺走我父亲的钱,把他告进了监狱。我猜他们是想把他杀掉,还是想别的怎么样,可我母亲趁着黑夜溜了出来,还跑到监狱。那只是个乡间监狱,她用棍子打昏了守卫。我不清楚她到底做了什么,反正就是把爸爸救出了监狱,于是我们连夜赶回了墨西哥城。后来呢,我父亲从爷爷的店铺中一分钱也没有拿到。
康素爱萝出生的时候,我六岁。我和罗伯托看着接生婆来到家里,在那里不断地忙活着,但我们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儿。我们被赶出了房间,接着就听到婴儿的啼哭声。我一直喜欢听婴儿的啼哭声,而且觉得有个妹妹是一件好事。可当她在床上挨着父母睡觉,当我母亲走到哪儿都抱着她,抚慰她,还叫她“我可爱的小女儿”的时候,我产生了龌龊的想法。母亲发现我很嫉妒,于是告诉我:“别这样,儿子,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都不要相信。”的确,当她外出卖东西的时候,经常都会带上我。我们把罗伯托留给外祖母看管,我就跟着妈妈走了。因为知道她很爱我,所以我看见什么东西都要她买给我,她不买我就大发脾气。她总是说:“唉,儿子,我很爱你,可你也太难伺候了。真不知道你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
一天,我跟妈妈去格兰雷诺面包房买面包屑。她正在跟她的姐妹,也就是康素爱萝的教母说话,我发现有血顺着她的腿流了下来。我问她是不是哪里伤着了,她低头看了看,然后对我说:“我想应该是伤着了。”她回到家就躺在床上,然后叫人去找我的父亲。
稍后,替康素爱萝接生的那个女人又来了,我又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我和弟弟一定像两只受惊的兔子,因为我爸爸走出来安慰我们,叫我们不要害怕,说那位女士用箱子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妹妹。我第一眼看到玛塔的时候,觉得她真是难看死了。我说:“嗨,妈妈,你应该让那位女士送一个更白更漂亮的才对。”
生了这两个女儿,我父亲真是高兴极了。他巴不得生的全是女孩。他对我的两个妹妹感情更深些,但那个时候我还看不太出来,因为母亲在的时候,爸爸还是很爱我们的。至于罗伯托呢,我就记不太清楚了。我爸爸一直不喜欢黑皮肤的人,可能就因为罗伯托肤色较黑,所以他一直不喜欢罗伯托。不过,我们小的时候,他对我们并不严厉。他跟我们讲话的声调有点不一样。我猜想,我和弟弟最大的不幸是长成了大人,因为我长到八岁之前都还觉得无忧无虑。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渐明白了性交是怎么回事儿。当时我妈妈正在生炭火,于是叫我到隔壁去借把扇子来。我跑到邻居的房子跟前,没敲门就走了进去。床上躺着佩佩塔和她的丈夫,佩佩塔跷着双腿,她的丈夫脱掉了裤子,一丝不挂。我觉得很难为情,但又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对劲。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我惊扰了他们两个正在干的一件什么坏事儿。佩佩塔脸色不悦,停止了动作,但两个人谁也没有改变姿势。她说道:“啊,拿去吧,就在那边的火盆上。”然后我就回了家,给我母亲讲了这件事儿。唉!她竟然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
那以后,我就想亲自体验一把,于是想方设法找来居民区的女孩跟我一起做“爸爸妈妈”的游戏。我母亲请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帮忙,只要我们单独在一起,我就会跟她做那样的游戏。有一天,她上房顶去晾衣服,我跟了上去。“来吧,”我说。“就在这里做。”我强行掀起她的衣服,以便褪下她的裤子。就在她快要让步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拍打窗户。那个时候,我们的房子对面是一家织袜厂。我转头去看是谁在拍打窗户,才发现工厂里所有的工人,无论男男女女全都跑到了窗子跟前,指着我们俩哈哈大笑。有人大声说道:“他妈的,看看这个小杂种。”我迅速跑下了房顶。
母亲送我上学的第一天,我害怕得哇哇大哭。趁老师不注意,我转身跑回了家。我的第一位老师卢佩小姐非常严厉,谁只要不听话,她就会拿黑板擦扔谁。有一次,她朝我扔过来一把直尺,尺打在我的手腕上断成好几截。
那一年,我认识了桑提亚哥这个朋友。在学校,他是我的守护天使,总会保护我。有大孩子想打我的时候,我马上会对他讲,他就会去追讨他们。可他从不帮我欺负比我还小的孩子。他会说:“好意思哭,羞不羞?既然他比你小,你直接揍他不就行了吗!”桑提亚哥教我怎样保护自己,教我学说脏话,还把有关女人的事儿全都告诉了我。
我在那所学校读到了四年级。就是在那所学校,有人给我取了奇诺[1]这个绰号,因为我的眼睛有些斜视。我上到三年级的时候,罗伯托开始上一年级,从那以后,我为他打了好多次架。他小子真是可怜!从小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他总是惹麻烦。一下课,我就看见他被人拖着哭哭啼啼地往校长办公室走,去为他做错的事而受罚。我很气愤,总是会掺和进去。
我弟弟有一次流着鼻血,哭着跑进我的教室。他说:“弗朗西斯科简直是头猪,他竟敢揍我,莫名其妙。”我什么也没说,径直来到那头猪的教室对他说:“弗朗西斯科,为什么打我弟弟?”
“因为我想打他,怎么啦?”
“好,来打我,”我这么说着,他还真打了我。我抓住他好好揍了一顿。他拿出刀子向我扑过来,要不是我立刻弯腰闪开的话,他肯定刺到我的脸上了。
有人跑去告诉了我的父亲。不巧,那天星期三,是他的休息日,他刚好在家。那天下午,我害怕得不敢进屋,站在那儿从门上的缝隙往里看,看父亲的心情如何。不过,那次他没有教训我,只是跟我说要尽量少打架。
有一次正逢母亲节,我哼唱着在学校排练过的一首歌回到了家里。“原谅我,亲爱的妈妈,因为我能给你的只有爱。”我父亲正好在家,他好像很自豪很幸福的样子。
“不,儿子,我们还可以给点别的东西,你看我买了什么。”我看见衣柜上摆着一部小收音机。
“爸爸,真漂亮。”我问道。“是给妈妈的吗?”
“是的,儿子,是给妈妈的,也是给你的。”
当时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卖彩票赚了钱,就用来买了收音机。后来,我开始慢慢地讨厌那部收音机,因为它惹得家里人不时发生争吵。我母亲老听收音机,惹得父亲非常生气。他说事情完全乱了套,“为家里这这那那付钱的人是我!”他觉得只有他在家里的时候才能听收音机。
母亲死后,外祖母照顾了我们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她,母亲死后,只有她真正疼爱我。我只向她一个人讨教过主意,我不吃饭的时候,只有她才会掉眼泪。她曾经说过:“曼努埃尔,你太固执,我担心得很啊。有一天我死了,你看还有谁哭着要你吃饭。”
外祖母从没打过我,哪怕有时候我不愿意跟她跑腿,她也只会扯我的头发,揪我的耳朵。妈妈经常打我们,尤其是罗伯托,因为他太淘气。哦,有一次,我弟弟躲在床底下不肯出来,妈妈抓起一根铁棍朝他捅了过去。刚好捅到他的头上,立马起了一个大包。跟母亲相比,外祖母简直就是温柔的代名词。
父亲跟我外祖母很合得来,也就是说,他们不存在任何分歧。她教我们要懂得尊重他,因为是他给我们挣来了饭钱,什么都是他给的。她常说,我们有那样的父亲,应该感到珍惜才对,因为世上像他那样的父亲并不多见。不管什么事,她都会给我们提建议,她还教我们要记得自己的母亲。
瓜达卢佩姨妈有时候也会照看我们。一天傍晚,爸爸让我们出去买糖。我猜想他巴不得我们去的时间长一点,可我偏偏提前回来了,刚好看见父亲想凭力气把姨妈搂进怀里,知道吗?我觉得他想跟她求欢,而我惊扰了他们。我可不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不过,唉,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不是吗?我不想对他妄加评判。
后来,父亲又雇了个女的来照看我们。第一个仆人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她抽烟很厉害,牙齿全给熏黄了。有一次,她正在洗衣服,我走过去把手伸进她的衣服里。“嘿,规矩点,放手,把手拿开,要不我让你好看,小杂种。”那老娘们不让我碰她,不过我还是掀开她的衣服,看到了她的下身。嗨,她的毛真多,真难看!
我们从漆匠大街搬到了古巴街。我们家的房子又小又黑,十分破败,住在里面可真糟糕。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遇到了艾莱娜。
我不记得我们两家人的房号了,不过假设我家住一号,艾莱娜和她丈夫住的是二号吧。我爸爸干的事情就是把她从二号搬到一号,让她变成了他的老婆。在此之前,我差不多当她是我的玩伴。她长得年轻漂亮,经常要我读笑话给她听,因为她自己不识字。她是我们的朋友,对吧?所以,当她爱上我父亲的时候,我们都有种上当的感觉。为了掩饰那些事儿,她来到我家当仆人,结果却成了我家的主人。
一天晚上,她丈夫带话说要见见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个子很小,可他还是去了。他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抓了一把刀子藏在皮带下面。他们两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真是担心死了。我对罗伯托说:“我们去楼顶吧,那家伙要是动手的话,我们两个一起给他扑过去。”我们不过是两个小孩子,可还是爬上了楼顶。但是,我们没法看见他们,因为他们把里间的门也给关上了。我真是害怕极了。我担心那个人可能会杀了我的父亲。终于,爸爸走了出来。从那以后,艾莱娜就留在我们家了。
租户们对这件事情说三道四——说艾莱娜从这家走到了那家。我父亲是何等的了得啊!然而人言可畏,爸爸只得搬家,于是我们住进了奥兰多大街。
我们搬家那天,父亲早早就下了班,下午一点整吧。因为他一贯喜欢速战速决,于是他喊道:“好吧,把床拆了,把席子卷起来。”
于是我们卷起席子,他用一块床罩给包了起来,以遮掩上面的斑斑污点。紧接着,爸爸要我们搬家具,收拾好所有的锅瓢碗盏。艾莱娜把锅瓢碗盏从挂钩上取下来,放进浴盆里,以便搬运。我们用来储水的浴盆有好几个,因为我们那种居民区经常缺水。我们没有雇车,全都自己搬运。爸爸请了个搬运工搬运大衣柜,因为我们的新家在一个半街区之外。
那个居民区更大更漂亮,我们第一次住进了两居室的房子,这让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了有钱人,我为此高兴不已。我们的房子位于三楼,朝向天井的楼梯平台只有一个小小的扶手,于是我父亲做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护栏,以防我们不小心跌落下去。
可父亲对奥兰多大街的房子并不称心,于是我们又搬回了古巴大街。这里有他认识的两个女人,都在餐馆做工。其中一家有个女儿名叫茱莉亚,我非常喜欢。我想让她做我的未婚妻,可她家比我家要好,我有点自愧不如。我发现她家的房子装修得十分漂亮,也就决定不要她做我的女朋友了。
起初,艾莱娜也想对我们好。她自己没生过孩子,对我们几个充满了慈爱。不知为什么,当我们搬回古巴大街之后,她对我们就没有那么好了。那时我父亲对我们的态度也开始变了。她会为一点点小矛盾跟罗伯托大打出手,然后父亲会一反常态地把可怜的弟弟揍上一顿。我记得父亲唯一关心罗伯托的那次,是他的手臂被居民区的一条狗咬了一口。我父亲很生气,气得脸都白了。他的脑子一片混乱,完全不知所措——还是一个邻居帮了大忙。
注释:
[1]原文Chino,意为斜纹棉布。——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