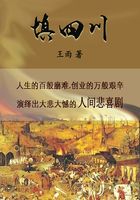
第10章
整整九十七天无雨。
那个好大的太阳把云朵雾气全烤干了,天空呈现一派炽烈的黄红色。“常家土楼”四周的山林片片黄褐,是耐旱的却枯死了的大片竹林。初秋时节已是一片肃杀的晚秋景象。附近那尊卧佛的肚脐眼常年都有股清泉流淌,现今也只见点滴了。农田龟裂,庄稼枯萎,正逢生姜收获的时节却颗粒无收。狗儿有气无力地“汪汪”两声便耷拉下脑袋喘息。
宁徙立在院坝里哀叹:“今年真是颗粒无收了。”
她倍感孤独无援,尤思夫君。本来,有焦知府的相助,她以为与夫君可得重逢,却不想,十里长亭与夫君一别就是六年,至今没有夫君音讯。焦知府、宣知县都派人四方寻找,常维翰与那两个兵差均下落不明。
那两坛金子呢,给她家带来了财气也带来了祸害。县、里、甲、村各级都来“惠顾”,都理由多多来索取钱财,美其名曰:大户常氏为民行善。更可气的是,土匪安德全一伙不仅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加嚣张,把她家的金子全都抢走。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土匪突然来袭,将睡梦中的全家上下捆绑到了院坝里。土匪们举着火把,安德全扬言要烧毁“常家土楼”,问她要土楼还是要金子。这融合有闽西老家风情的土楼可是来之不易,是她与老憨和重庆府的名工匠精心谋划、设计修建的。刚建成,就遇一场山火,差点儿被焚毁。她只好让老憨交出了一包金子。安德全仍不罢休,用双刀架住常光莲、常光圣两个孩子的脖颈,问她要娃儿还是要余下的金子。她生怕伤了孩子们,只好忍痛让老憨交出了余下的金子。土楼、孩子和家人们总算保住,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为防土匪再来抢劫,她雇了家丁护院,开销更多。
她又去“跷脚土地菩萨”小庙烧香时,细看细想了石碑上那“金其里,银其里,金银在这里,谁能识得破,要得千担米”的隐句,才悟出,这隐句里说得明白,谁能识得破,要得千担米。是啊,金子不是靠意外得来的,是要靠千辛万苦劳作收获“千担米”换来的。“呼童早起勤耕稼,教子迟眠苦读书。”她写下这话激励自己,倍加努力地勤奋耕耘,勤俭持家,决心把这个家维持下去,决心靠勤劳致富。
她万万没想到,会遇了今年这百年未遇的大旱,往后的日子咋过啊。
“夫人,我找到天旱的原因了。”汗湿衣衫的管家老憨喘吁吁走来,说。
老憨刚从县城买布匹回来。冬天快到了,宁徙让他去买些布匹回来,做一家人的冬衣。他走过万灵寨里的那“赵家大院”时,看了看“赵家大院”前山上新修的那座白塔,白塔在日光下熠熠生辉。心想,赵家是在求福。过大荣桥时,见河里的水流好小,摇头哀叹。过桥后,看见口中念念有词的算命先生,没有理会,各自走,听见那算命先生念道:“桥是弯弓塔是箭,射倒常家土楼院……”开先并未细想,走一阵心里发怵,赶紧回身。那算命先生已收摊走了。
“打雷立秋,干断河沟。天旱是龙王爷发怒,还有啥子原因。”宁徙长叹,她的四川话很地道了,“我们给龙王爷烧过高香磕过头了的,巴望会来甘露。”
老憨放下布匹,说:“夫人,你跟我到屋顶上去。”
宁徙不解,跟老憨上到屋顶。屋顶热风股股,身上的汗水更多。
老憨用手刮脸上的汗,朝濑溪河下游指:“夫人,你看见啥子没得?”
宁徙脸热。她时常独自上这屋顶来,可以遥望见河下游的“赵家大院”,心里总有股莫名的惆怅。她知道,老憨晓得赵书林喜欢她,可我们两家至今已没有了来往。埋怨道:“老憨,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开玩笑。”
老憨认真说:“夫人,你看,赵家前山新修的那座白塔!”
宁徙看见过那白塔:“这有啥子,就不许人家建塔求福?”
老憨道:“真要是这样倒好,事情不是这样的。”就说了遇见算命先生的事情,“那算命先生念叨‘桥是弯弓塔是箭,射倒常家土楼院’,我在回来的路上,听见娃儿们也这么说唱,这不分明是针对我们常家来的么。”
宁徙的心发紧,胸脯起落:“唉,赵书林,你这又是为何啊?”
老憨说:“最坏的是他那姑妈赵秀祺,她恨死了你。”
宁徙点头。可不,赵书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连夜来告知维翰要被问斩的消息的。后来,她听说,赵秀祺为赵书林给她通风报信的事,用黄荆棍痛打了他,还让他到祖宗的牌位前罚跪、悔过。是老憨听吴德贵说的。吴德贵还对老憨说,赵秀祺说了,赵书林若再与她往来,就要让族人长老问罪,用家法族规惩处。
“夫人,你得谋思对策,不然,常家会败落的。”老憨发急。
“这咋办,总不能去拆了那白塔。”宁徙六神无主,“只好祈求菩萨保佑了。”
当晚,老憨去万灵寺请来和尚念经驱邪。堂屋里,烛火点点,香烟缭绕。和尚们敲打木鱼念念有词:“下游邪恶来作怪,箭箭穿心射过来,左方菩萨右方神,保佑此地祥瑞来……”
八岁的常光莲、常光圣看着,好奇不已。老憨、桃子就招呼下人们摆放供品。宁徙坐在一旁叹息。她求菩萨保佑是为诉说心愿,却不信鬼神,母亲对她说过,她父亲就不信鬼神,算命先生曾对她父亲说,他日后会娶得个公主,结果娶的是宫女,还是冒杀头罪娶得的;她父亲敢一个人夜走坟山,目视鬼火嗤之以鼻,说,他在宫廷里与洋人传教士贝鲁格熟悉,贝鲁格说那是磷火。想到父亲和算命先生,她立即去厨房找老憨。老憨正张罗厨师们为和尚做夜膳。
“老憨,我问你,你说你遇见算命先生了,他啥模样?”宁徙问。
老憨想了想,说:“穿身麻布长衫,不胖不瘦不聋不瞎,一个人在那里叨念。”对瘦厨师瞠目呵斥,“呃,你傻儿呀,咋个恁么整!”
宁徙回身走,一定是那个算命先生了。就想起算命先生当年那“世事无常,人生苦短,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不阴不阳半吞半吐话来。爸爸,你在哪里啊?你还在人世么?
和尚念经到深夜方毕。
宁徙请和尚们用夜膳,给他们银钱,送他们出门,好忙乎一阵。老和尚出门后又折回身来,双手合十,说:“矛得盾挡,阿弥陀佛。”拂袖而去。
宁徙不解其意,老憨、桃子都纳闷。
常光圣说:“妈,我知道是啥子意思。”
宁徙看常光圣:“你说。”
常光圣道:“明天说。”
常光莲拍打常光圣:“弟娃,你跟妈妈还装怪,快些说。”
常光圣拍胸脯:“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说明天说就明天说。”
看着两个孩子,宁徙倍感欣慰。她为孩子们请了私塾老师教“四书五经”,自己为他们讲做人之道:“做人要做好人,做事得做好事。”教他们唱客家“劝孝”、“戒懒”的山歌:“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番大水(雨)一番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晡(昨天)看花花正好,今晡(今天)看花只有草。细子(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父母)爱(要)趁早。”“冬瓜花,番(南)瓜花,花谢结成瓜。瓜大把钱卖,人大爱(要)勤快。有钱唔(不)勤爱(会)落魄,毛(无)钱唔(不)勤毛(无)食(吃)着(穿)。”还教他们武艺,给他们讲族谱,盼望他们早日成才。她发现两个孩子都聪明,光圣尤其精灵,还有些歪点子。有次,她在花坛里捉虫。光圣走来问:“妈,你靠花坛那么近做啥子?”她说:“妈在捉虫,虫子太小了,妈得靠近些才看得见。”光圣道:“妈,你好笨,你等虫子长大了再捉,不就看得见了。”她听后大笑:“我的个傻儿子啊!”想着,她扑哧笑,且看光圣明天说出啥歪点子来。老憨来喊他们去吃夜宵。宁徙也饿了,就叫了两个孩子一起去堂屋里吃夜宵,桃子张罗着上菜。
管家、丫环、家丁、长工们在厨房里吃,老憨一伙男人端了土碗喝酒。
吃罢夜宵的宁徙走过厨房门口时,朝里面看了看。她治家勤俭,却不亏待下人,这个家要支撑下去少不得他们。也忧心,老天爷如此地不赏脸,颗粒无收的这个家会被吃空的。
宁徙安顿两个孩子睡觉,自己也困了,回到卧室。上床后却睡不着,倍思维翰,也晃动着赵书林的音容。一晃,已近而立之年,却独守空房。焦知府申斥过宣贵昌,不许他骚扰她。宣贵昌倒是有所收敛。可眼下的情况变了,变得不可思议,宣贵昌高升到重庆府任从六品理问,勘核刑名诉讼;焦达却降职为荣昌县的知县。这世道咋了,好人咋无好报?咋恶人当道?有人说,焦达是因为庇护土匪头子常维翰被降职的。这不是天大的冤枉么?可无德无才、贪赃枉法的宣贵昌又凭啥高升?老憨说,定是宣贵昌那龟儿子陷害了焦知府。还说,宣贵昌一定是拿贪赃的钱财去疏通的官路。儿子常光圣怒道,我长大后要当大官,宰了宣贵昌。她为儿子这豪气而感动。左想右想,恍恍然入睡。
秋月似圆非圆,似笑非笑。
老憨的酒喝高了,双脚老重,走到桃子屋门口时,伸手敲门。桃子拉开道门缝,睡眼惺忪:“老憨,有事?”老憨推门进去:“㞗,㞗个事。”桃子只穿了腰裤和肚兜,露出的肌肤在月辉下放亮:“个死老憨,夜半三更敢到老娘屋里来,我喊夫人了!”老憨抱住她:“你,你喊,尽管喊,喊了这一屋……屋子的人都来看。”桃子没敢喊,让人看见丑死人了,挣扎着:“老憨,我晓得,你龟儿子喝高了。你先放开我,我穿好衣服,我给你泡杯浓茶解酒。”老憨松开她:“穿,穿啥衣服嘛,你我都,都不小了……”桃子赶紧穿衣裙。老憨道:“你怕,怕我看?”桃子道:“个大男人,不许你看。”老憨盯她邪笑:“桃……桃子,我……我晓得你长得好看。可你总没……没有西施好看吧。即,即便是西施,做的也是一样个事情。”将桃子扑倒到床上。
桃子惊恐又有股莫名的冲动。
老憨是个健壮的男人,是有权势的管家,是夫人的心腹。自己是个丫环,当然,是管丫环的丫环,跟了老憨也是可以的。可夫人知道咋办?老憨要是只把自己耍一耍又咋办?就竭力反抗。
桃子的反抗没用,老憨的力气好大,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次日早饭时,老憨不看桃子,桃子倒死盯他。老憨大口扒完饭,抹嘴朝院坝里走,桃子扔下碗筷跟他走。老憨觉得背后有两道芒刺,抬首望天,扯开喉咙吼:“重阳不打伞,胡豆光秆秆。抬头顶上光,龙王不开腔。云朝东,一场空……”吼声带了哭腔。宁徙领了两个孩子走来,都挑着水桶:“老憨,叫大家都下河挑水,挑水浇地。”老憨的两眼有泪:“夫人,人是斗不过天的。俗话说,有雨天边亮,无雨顶上光。今日这天顶无云,还是没得雨!”桃子的两眼也湿了,想起什么,对常光圣说:“少爷,你不是讲今天说么?”宁徙才想起光圣昨晚说的话:“对,儿子,你说。”常光圣捣头,说:“那老和尚说,矛得盾挡。赵家那白塔是矛,我们得用盾挡。”老憨击掌:“对,老和尚是在指点迷津!”宁徙半信半疑:“总不能我们也修座白塔吧?”常光圣就拿出个破镜片,将阳光朝赵家方向反照。常光莲领悟,说:“妈,镜子,你每天梳头都要照镜子。”宁徙说:“梳头当然要照镜子。”桃子惊叫:“对,镜子!”老憨吼叫:“对,用镜子将那邪恶的白塔反照回去!”宁徙摇首:“这不是以恶对恶么?”老憨道:“夫人,常言道,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没收在于水。他赵家出此恶招,是要让我们颗粒无收。事情是他们挑起的,我们不过是自卫。”宁徙说:“就算这天旱是他们造成的,可对他们也不利呀。”老憨道:“他们是在濑溪河下游,房院田土都挨河,取水比我们方便。不管怎么说,赵秀祺的心是太歹毒了。”桃子说:“我恨死她了。”宁徙被激怒了:“赵秀祺,你出此阴招也太狠了!”老憨和桃子走后,常光圣说:“妈,莫跟赵伯伯家闹翻脸,我和姐姐跟他们家的庚弟哥哥、赵燕和赵莺妹妹都是好朋友。”常光莲附和:“就是。”宁徙听了,倒内疚起来,是啊,娃儿们自小在一起玩耍,大人们倒做起这种恶事来。
老憨办事雷厉风行,当即请人在后山那“跷脚土地菩萨”小庙附近修了道正对赵家白塔的照壁,在照壁上挂了面镜子,放出话说:“墙如盾牌镜似箭,反射下游赵家院。”
日头落山,酷热不减。
宁徙回到屋里,仰躺到床上呻唤,挑水浇地一天的她累得腰酸腿痛。老憨说得对,我们常家在高处,去山下的濑溪河取水实在劳累,一个来回就得走上半天。女儿光莲好不容易挑了半担水上来,快到地边时,腿脚一软,摔了一跤,半担水全洒了,哇哇哭。看着这半担没流进地里的珍贵的水,她那心好疼,呵骂女儿吃长饭却不中用,给了她一耳光。女儿伤心地哭。
宁徙这么想时,常光莲进屋来,为她打扇。常光圣跟进来,端来碗面条。痛定思痛,宁徙边吃面条边想,种地是靠天吃饭,老天爷一发怒,就会减产以至于无收。现今家里还有些积蓄,得办点其他事才行,就对两个孩子说:
“光莲、光圣,妈一直在想,我们常家要发,得向老家那些做手工发家的大户学。焦知府还在重庆府的时候,妈去拜见过他,对他说过这想法。他很高兴,领我去看了重庆府的纺织、猪鬃、玻璃业,看了瓷器、面粉、造纸、印刷业,还看了皂烛、制革、丝绸和水泥业。嗨,你们都想想,我们又能做点啥子?”
两个孩子都皱眉头想,都说了想法。
宁徙听着,笑而不语。
常光莲说:“对了,妈,我们地里的桑树长得好。”
常光圣受到启发,吟道:“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常光莲道:“这是《诗经》里写女子种桑的诗,弟娃记得好清楚。”
常光圣得意:“老师说我过目不忘。”
宁徙笑:“光圣,看你得意的。”觉得孩子们都长大起来,懂事起来,“你们这一说,倒使我有了想法。也是呃,这里适合种桑养蚕,可以用来做丝绸。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是客家人,我们的先祖是中原人,历经了五次大迁徙才到了闽西老家定居。你们外婆给我说过,种桑养蚕是在中原地区盛行的,很早,我国的丝绸之路就很发达。她还说,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抽丝,嫘祖是生葬于古西陵国的,就是现今四川的盐亭县。嫘祖首创的桑养蚕法和抽丝编绢术,改变了人们蛮荒的历史呢。”
常光圣说:“我外婆真行,晓得恁么多。”
宁徙看两个孩子:“你们外婆给我说,她是听你们外公说的。”
常光莲道:“我外公得行!”
宁徙叹曰:“这说明啥子,说明四川早先的丝绸业就很发达。”
常光圣道:“妈,我想起来了,《说文》里道,‘蜀’乃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
宁徙抚光圣的头:“儿子,你记性确实好。你们外婆给我说,嫘祖的儿子叫子昌,娶了蜀山氏的女人,嫘祖给蜀山氏传授了种桑养蚕的技术。”
常光莲问:“妈,蜀山氏是谁?”
宁徙道:“女儿,蜀山氏指的是种桑养蚕的一个族群,说明巴蜀的养蚕业发源很早。唉,现在不行了。我想呢,我们在巴蜀的小荣村种桑养蚕,应该是会有收益的。”
说到种桑养蚕,宁徙忽然想起从老家带来有苎麻种子的。对呀,还可以自己种麻、织布呀,母亲柳春教过自己种麻、织布的。咳,只可惜那装有麻种的担子失落了。决心下定的事情她就要办,这之后,她四处打听从老家来的移民,还真找到了,还真从老乡移民那里买到了从家乡带来的苎麻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