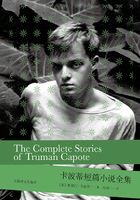
第5章 物形(1944)
一位体型纤弱,梳着高卷式发型的白人女子沿着餐车的过道摇摇晃晃地过来,一点点地挪进靠窗的一个餐位。她用铅笔勾画完要点的食物后,半眯着一双近视眼瞥了一眼桌子对过坐着的一个面颊红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一个心形脸的姑娘。一瞥之间她已经注意到姑娘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金婚戒,用一条红带子扎着头发,认定了这姑娘不上档次;暗自已经把她归类为那种战时新娘了。她模糊地微微带笑,摆出乐于搭讪的样子。
那姑娘回了她嫣然一笑,“你这么早过来就餐还算是走运,车上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刚才就没能吃上午饭,因为一大帮俄国士兵在吃……还是怎么的。天啊,你真该看看他们那副德行,看着就活像是鲍里斯·卡洛夫[8],真的哎!”
那声音活像是嘁嘁喳喳鸣响的茶壶,引得那位女子清了清嗓子。“是呀,我敢说肯定是这么回事,”她说。“开始这趟旅行前,我真真做梦都没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多,我是说这么多士兵。你得亲自登上一列火车才能意识到。我就不断地问我自己,他们都是打哪儿来的呀?”
“征兵局呗,”那姑娘说,然后傻乎乎地咯咯一笑。
她丈夫歉然地脸一红。“您是远道而来的,夫人?”
“算是吧,不过这班火车真是慢得呀,简直就像是……”
“蜗牛爬!”那姑娘大叫一声,然后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唧唧呱呱开了,“哎呀呀,我真是太兴奋了,你都没法想象。我从早到晚都看不够这窗外的景色。我来的那个阿肯色州全都是一马平川,所以我一看到这些大山,简直激动得都要跳起来了。”然后又转向她丈夫,“亲亲,你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卡罗来纳了吗?”
他朝窗外看了看,车窗玻璃上笼罩的暮色渐浓。凄凉的暮光迅速地辏集,一个个小山包连绵不绝,相互应和。转回到餐车明亮的光照之后他不禁眯起了眼睛。“一定是到弗吉尼亚了,”他猜测道,耸了耸肩膀。
一个士兵突然从硬座车厢的方向趔趄着朝他们走过来,然后就像个布娃娃一样生硬地跌坐在他们这张餐桌的空座上。他很矮小,军装整整大了一号,皱巴巴地窝在他身上。他的脸很消瘦,轮廓分明,跟那位海军陆战队员相比显得很苍白,黑色的小平头在灯光下闪烁,就像戴了顶海豹皮的帽子。一双倦怠的眼睛迷迷瞪瞪地端详着他们仨,仿佛在他们之间突然挡上了一块幕布,紧张不安地拉扯着缝在袖口上的两个袖章。
那女子局促地挪了挪,靠车窗更近了。她琢磨着他肯定是喝醉了,看到那姑娘也皱起了鼻子,知道她也是这么想的。
看到系着白围裙的黑人侍应在他面前放下餐盘,那个下士说:“我想要的是咖啡,要一大壶咖啡和双份的奶油。”
那姑娘用叉子搅了搅面前的奶油鸡。“你不觉得这些家伙的要价实在是可怕吗,亲爱的?”
然后就开始了。那个下士的脑袋开始无法控制地一抽一抽地上下摆动起来。松垮垮地暂停了一会儿后,他的脑袋古怪地向前耷拉下来;然后肌肉的一阵抽搐又使他的脖子猛地扭向一边。他的嘴巴恶心地扭曲起来,脖子上的血管绷得老高。
“哦我的上帝,”那姑娘大叫一声,那女子则把黄油刀一扔,不由自主地举起一只敏感的小手捂住了眼睛。海军陆战队员茫然地盯视了他一会儿,然后很快镇定下来,从兜里摸出一包烟。
“来,兄弟,”他说,“你最好来一根。”
“请,谢啦……真慷慨,”那士兵嘟囔着,然后伸出一个指关节都攥得发白的拳头,捶打着餐桌。银餐具颤动起来,水溅出了杯子。空气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凝固了片刻,远处爆发的一阵笑声刀子般平滑地切过车厢。
那姑娘在意识到大家都在注意他们后,抬手把耳朵后头的一绺头发抚抚平。那女子眼睛朝上看,咬着嘴唇,她发现那下士正努力把香烟点燃。
“来,让我来吧,”她主动提出要帮忙。
她的手抖得太厉害,把第一根划着的火柴都给弄灭了。第二根火柴划着、终于把烟点上以后,她勉强一笑。过了一会儿他安静了下来。“我真是太惭愧了……请原谅我。”
“哦,我们能理解,”那女子道。“完全能够理解。”
“疼吗?”那姑娘问。
“不,不,并不疼。”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以为你肯定很疼。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我猜是不是有点像打嗝?”她突然惊跳了一下,仿佛有人踢了她一脚。
下士的手指沿着桌边一路抚过去,随即道:“我一直到乘上这趟火车都好好的。他们说我会好起来的。说,‘你没什么,大兵。’那是因为过于兴奋的缘故,知道你已经回到美国了,已经自由了,那该死的苦挨已经结束了。”他抹了一下眼睛。
“对不起,”他说。
侍应把咖啡放下,那女子想帮他。他有点生气地一把把她的手给推开了。“现在请别费心了,我知道怎么弄!”她又尴尬又有点困惑,于是朝窗户转过身去,望到了窗玻璃上映出的她自己的脸。那张脸看起来很平静,这让她有点吃惊,因为她觉得有点晕眩般的非现实感,就仿佛在两个梦之间来回摆荡。她故意把思绪引开,关注起海军陆战队员的叉子从盘子到嘴巴的那个庄严的旅程。那姑娘也狼吞虎咽地大吃了起来,可是她自己的食物却在变凉。
然后又开始了,这次不像刚才那么剧烈。在对面开过来的火车炫目的探照灯照射下,窗玻璃上那个扭曲的映像模糊了,那女子叹了口气。
他轻声地咒骂着,听起来倒更像是在祈祷。然后他的两只手就像老虎钳一样狂暴地紧紧攫住脑袋的两侧。
“听我说,兄弟,你最好还是找个大夫看看,”海军陆战队员建议道。
那女子伸出手来,放在他举起的胳膊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她道。
“他们过去帮我止住的办法是直视着我的眼睛……只要我看到了别人的眼睛,它就会停了。”
她把脸靠过来紧挨着他的脸。“好了,”他道,马上就开始安静下来,“好了,现在。你真是个甜心。”
“到底是哪儿?”她问。
他皱起眉头说,“有很多地方……是我的神经。全都被撕碎了。”
“你要去哪儿呢?”
“弗吉尼亚。”
“是回家,对吗?”
“是呀,家在那儿。”
那女子觉得手指上一阵疼痛,就陡然松开了紧握着他胳膊的手。“家就在那儿,你必须记住别的一切都是不重要的。”
“听我说,”他轻声道。“我爱你。我爱你,因为你很傻很天真,因为除了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点东西以外,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爱你,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弗吉尼亚,我就要到家了。”那女子陡然把目光掉开来。一种遭到冒犯的紧张感更加深了那阵沉默。
“你认为就这么回事了?”他道。他靠在桌子上,困乏地摸弄着自己的脸。“是这么回事,可是还有尊严的问题。当有人出了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以为我想跟他们或者你们这样的人在同一张餐桌旁就座,让他们觉得厌恶?你以为我想吓唬旁边坐着的这个小姑娘,让她以为她自己的男人也会这副德性!我已经等了有好几个月了,他们都跟我说我已经好了,可是我一踏上……”他说不下去了,眉头紧锁。
那女子把两张钞票悄悄放在账单上,把椅子往后推了推。“请让我过一下好吗?”她道。
下士费力地站起来,望着那女子没有动过的盘子。“还是继续吃你的吧,该死的,”他道。“你必须得吃!”然后他头也不回地消失在硬卧车厢里。
女子付了咖啡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