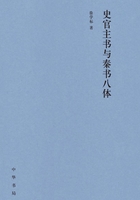
第二章 史官“主书”与“主文”
一、史官与文字的关系
文字乃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1),它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汉书·艺文志》:“《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说文解字·序》:“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说明了文字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应用功能。在古代,与文字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莫过于史官,几乎所有与文字有关的工作都是由史官来负责完成的。
按文献所载,文字最早产生于史官之手。《说文解字·序》: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吕氏春秋·君守》《韩非子·五蠹》《世本·作篇》《淮南子·本经》中,都有“仓颉作书”的记载,另《风俗通》及卫恒《四体书势》,皆谓黄帝之时与仓颉同制文字者,尚有沮诵,亦为史官。这种把文字的产生归功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创造的说法,自然不符合文字产生及发展规律。《荀子》卷十五《解蔽篇》言:“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最大的可能是黄帝时期的仓颉、沮诵二人,在文字产生与早期发展过程中曾经进行过专门的规范整理工作,贡献突出,影响最大,此就如同李斯、赵高、胡母敬之于小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黄帝之时仓颉、沮诵的史官之名是汉之后人们追加的(《说文解字》之前,只言仓颉、沮诵创文字),但这只能说明远古时期史官名实发展的不同步性,而丝毫改变不了仓颉、沮诵所从事的是后来人心目中的史官工作。戴君仁说:“因史是识字专家,写字专家,读字专家,极可能亦即造字专家。”(2)《说文解字·序》把文字的产生与史官联系起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期的历史事实。
文字的功能主要在于其社会应用性,史官与文字的密切关系,主要就是从文字的社会应用角度而言的,史官是文字的主要应用者。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吾考古代史官,职司记事,位非甚崇,试以周制征之。周礼,春官之属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掌赞书;而六官所属诸职司,莫不有史。史与胥徒并列,故又释之曰:“史掌官书以赞治。”郑注云:“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征之汉制亦然。《汉书·艺文志》云:“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则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如谓仓颉、沮诵为黄帝之史官,则其所掌当不外是。凡掌官文书者及起文书草者,日与文字为缘,整齐其现行之字,以供起草之用,亦史官之所有事。周之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命,御史掌赞书,是史职起文书草之证也。太史掌邦之六典,内史掌八枋之法,外史掌四方之志,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是史掌官文书之证也。凡周之六典、八枋之法、四方之志、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或为当代之法典,或为治事之案据,今日称为寻常之官文书,异日则视为极可贵重之史料,古今一揆,理无二致。周代有然,黄帝以来迄于夏商,亦莫不如是。是则史之初职,本以记事为务,史官之多,亦以此也。(3)
金氏将“记事”与官书的“起文书草”混而言之,是不妥当的(下文将论),但“记事”与“文书起草”主要为史官所执掌,是官方主要的文字应用领域,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因史官撰写文书、载笔记事之职,使之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遂使文字的应用成为史官专职。故此,夏曾佑谓“学术、艺文、朝章、国故,凡寄于语言文字之物,无不掌之于史”(4)。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刘师培的“古学出于史官论”,以及今所见汉以前的大量甲骨、青铜、刻石、简牍等文字资料几乎全部出自史官之手,这些都无不说明了史官是文字的主要应用者。
史官又是古代文字的整理、传承与监督者。《左传·襄公十三年》载晋国史赵通过拆解“亥”字字形的方式来标记绛县老人的年龄,可见这一群体对文字的熟悉程度。史官由应用文字、熟悉文字,进而成为文字的整理、监督与传承者。戴君仁说:
史字形状,象人手执简册,表示他的生活和书本不离。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广泛起来,他的职务范围,便一天天扩张,不但书籍归他们掌管(《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索隐》云:乃周藏书室之史。)极可能连作教科书用的识字本,也是史所编制的(《说文序》谓黄帝之史仓颉造字。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博学篇》)。仓颉其人之有无不可知,太史籀据王国维氏说亦非人名。这些只是传说,而认为他们都是史官,却暗示着史和作字有关系。秦时作仓颉三篇,恐怕只有胡母敬是真正的作者,而李斯以丞相居名,赵高以权臣居名,如后世官修书之领衔者。(5)
《仓颉篇》之后,汉代影响最大的字书《急就篇》,也是出自史官之手。这些字书既是学童的识字、练字教材,又是官方整理、规范、统一文字的标准范本。两汉时期往往“以史篇为字书之通名”(6),更说明了在一般人心目中史官与字书的密切关系。
《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周礼·大行人》“九岁,属瞽史,谕书名”,王聘珍注:“九岁省而召其瞽史,皆聚于天子之宫,教习之也。”《汉书·艺文志》自注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这些都是史官负责文字教育与传承的记载。
又《说文解字·序》:“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僮……课最者以为尚书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太史试学僮”,说明了太史负责文字的考课;“课最者”尚书史的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之”,则说明了史官负有监督文字应用之责。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7)“史是古代教育极不普及状况下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流传,有莫大贡献。凡是文字的功绩,都可以说是史的功绩。”(8)这些都是对史官与文字关系的高度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