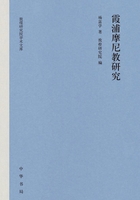
上编 霞浦摩尼教史论
第一章 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述评
第一节 关于摩尼教之入闽与霞浦摩尼教抄本的发现
摩尼教,亦称明教,为波斯人摩尼创于3世纪,它积极吸收了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等各大宗教之教义,将其创教之人吸纳入自身的“光明使者”抑或先知的体系中,并让摩尼本人成为“众使徒之封印”,此即后世摩尼教“五佛”之来由。摩尼教在摩尼生前即积极向东西方发展,其徒末冒已将光明教义传至中亚,至7世纪后期,约在唐高宗抑或武则天为帝之时,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华。
和任何一种夷教一样,摩尼教在中华大地传教经历亦极坎坷,虽安史乱后于各州立大云光明寺,然会昌灭法,几乎没顶,之后“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今福建福清市),授侣三山(福州市),游方泉郡(泉州市),卒葬郡北山(泉州北郊清源山)下。”(1)这位呼禄法师,无疑即闽系摩尼教之鼻祖。然而,关于法师名字之语源及含义,素来众说纷纭,主要有呼嚧唤、大(法师)和吉祥三种说法。其中呼嚧唤一说提出最早,支持者最多。刘南强考证认为,其应音译自中古波斯文xrwhxw'n/xrohxwan,汉译呼嚧唤,当属中亚摩尼教团(2)。笔者以为,据《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呼嚧唤称“教道首”,即传教士。属摩尼教五等级中第四级,乃专知寺院奖劝,又称阿罗缓,译言一切纯善人,为级别较低之选民,高昌回鹘时期更形同佛教之使唤僧,与能够“授侣三山”的高级法师呼禄法师身份似不称,而且“呼嚧唤”属官号,似亦可意译为法师,如此“呼禄法师”岂不成了“法师法师”?叠床架屋,斯当取乎(3)?然林悟殊《唐季摩尼僧“呼禄法师”其名其事补说》(4)一文则指出,“叠床架屋”、音译意译合璧之译名并不鲜见,如东南亚之“湄南河”(Menam),泰语本即“大河”之义,而复缀以河(River)字,《摩尼教残经》第15行之“未劳俱孚山”,芮传明以为,俱孚为中古波斯语kof(山脉)之音译,“未劳”则是(苏)迷卢之音译(5),则其山名亦属“叠床架屋”,是独呼嚧唤不得称法师乎?林先生之驳议,看起来有些道理,实则完全两码事,作为地名,这种情况太多见了,如库鲁塔格山,“塔格”即为“山”意,卡拉库姆沙漠,“库娒”即“沙漠”意。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但笔者讨论的为人称,惜林先生独无一例反证列举。林先生并且认为,吐鲁番文书中作为使唤僧的呼嚧唤,其性质已不同于唐代《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的呼嚧唤,而接近于月直的身份了,以10世纪高昌摩尼教团的任命情况状唐代,显然扞格(6)。“呼禄法师”为“大法师”之说为森安孝夫所提出,以为呼禄即回鹘语“Uluɣ”,意为大,指[宗教]法师(7)。然而“Uluɣ”与“大”对译准确,不难理解,似不必用此音译,回鹘常见之所谓“大汗”(Uluɣ Qaɣan)、“大将军”似从未有翻译成“呼禄汗”“呼禄将军”者,何以“大法师”定要译为“呼禄法师”呢?不过,森安氏对“呼禄”一词源出回鹘语的判定亦给后学者一定启发。在前辈学者诸说基础之上,笔者在《〈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之第四节《回鹘摩尼僧之开教福建》中提出呼禄实当为“Qutluɣ”即骨咄禄之对音,意为“吉祥”。骨咄禄,又译“骨禄”“骨都”“胡禄”,而“Qutluɣ”在回鹘又常被人格化为“保护神”,其用以对译“呼禄”无疑再合适不过。故而呼禄法师诚当来自漠北回鹘,会昌法难之际南下,开教八闽。当然拙意亦仍属假说之一种,究其实如何,还需更多发现以证实。但总而言之,这位呼禄法师应该是逃会昌法难,自中原而来传教八闽,过去很多学者疑其自海路来,显然是无据的(8)。
如今,摩尼教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早已为陈迹,唯在中国闽北部分山区中尚有孑遗,外媒曾以“中国发现摩尼教村”报导过,此即本文要谈之霞浦摩尼教:宋以来摩尼教每外托道教而存身,其性质与唐代已然大不相同,庶几已完全华化。明朝时其教遭严摈,留在福建日渐与道坛法事结合,由此产生以民间道坛仪式为框架,摩尼教教义、神名为内容的清幽仪式,正其事也。霞浦摩尼教发现于2008年,当归功于霞浦本地人林鋆,其于2008年回乡时,宗人示以秘传旧物,林以为其当与某神秘宗教相关,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霞浦盖竹乡上万村等地调研,6月乃由霞浦县全国文物普查组出具《霞浦县摩尼教(明教)史迹调查报告》,召开鉴定会,终确定遗物之宗教性质。摩尼教实迹有盐田乡飞路塔,所供泗洲大圣,造于洪武初年,外书“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按:此八字代表摩尼教在教义理论方面实行了本质的中国化,将基本教义归结为斯八言以便念诵,虽仍存有摩尼教原典的内核,却是大大简化了,堪称方便说法,一如佛教之净土宗教人念阿弥陀佛,禅宗之宣传明心见性即可成佛一般,信仰程序的简化才能吸引更广大的信众也);有孙绵大师所创乐山堂之遗址,有明教传人、被视为闽浙摩尼教主之林瞪墓等,文物则有原塔后村三佛塔残构件、雕像,雕像疑为“三清”摩尼、夷数、电光王,另有林瞪所用印玺、甪端,所获摩尼教文书则多为当地法师所用之科仪本。陈进国、吴春明《论摩尼教的脱夷化与地方化》及陈进国、林鋆之《明教的新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9)为早期考察、调研霞浦摩尼教之第一手资料,亦为霞浦摩尼教研究开山之作,其中有大量霞浦摩尼教遗迹、遗物及科仪文献的照片,弥足珍贵。两文对所发现的大批文书皆作了部分或全部录文及初步研究,虽不免存在些许谬误,然其功仍不可没。至于“脱夷”之说,林悟殊以为会昌灭法,斩断了域外与中土摩尼教会的关系,反而促使其在华夏自我生存。宋摩尼经可入藏,说明其已似佛藏完全华化,其教徒若非华人,即入华数代之胡裔,本已非“夷”,何脱之有?其教名由音译的“摩尼”改为“明”就很说明问题(10)。以摩尼经入藏和信徒为华人而否认摩尼经之脱夷化特点,似乎过于绝对。就以佛教而言,自汉代入华,佛经译汉,信徒亦为华人,但不能说隋唐八宗形成前佛教已完全华化。摩尼经之脱夷化问题与之同理也。
同年,马小鹤发表“Remains of the Religion of Light in Xiapu(霞浦)County, Fujian Province”(11),简要介绍宁德、霞浦之摩尼教遗迹,指出德国学者以为福鼎太姥山摩尼宫为中唐摩尼教遗迹,然而林悟殊以为还当找寻更多证据,盖“摩尼”本出佛典,摩尼宝珠是也,今宫中石佛非具佛身道貌,岂可以为摩尼佛?考虑福鼎临近霞浦,摩尼宫记录者林嵩同为长溪林氏,而霞浦已获大量摩尼教文献,此或可为其宗教属性提供证据。笔者总结福建摩尼教百年发现与研究存在之问题时亦以为摩尼宫或为佛教“摩尼宫殿”之意,与摩尼教无关。另,侯官神光寺亦不应因曾名“金光明院”“大云寺”而误为摩尼寺,盖此皆佛语也(12)。继草庵之后福建第二所摩尼教寺院的比定目下乃需文献与考古的双重认证。马氏此文最早对摩尼教《四寂赞》做了对音释读,并对比霞浦与敦煌本诸佛名号,对比霞浦文献中道教神名与传统道教神名,列其同异,考证“三天教主张大真人”为明代正一派张天师,因霞浦摩尼教与龙虎山道教关系至为密切。值得指出的是笔者指其为张角(13),盖摩尼教于宋时常被认为与三张左道有密切关系也。按:《青溪寇轨》以为:“后汉张角、张燕辈……其流至今,吃菜事魔,夜聚晓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观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时不饮酒食肉,甘枯槁,趋静默,若有志于为善者,然男女无别,不事耕织,衣食无所得,则务攘敚以挻乱。”(14)是故官方又将摩尼左道称为“张角术”(15)。
马氏因白玉蟾精雷法且谙明教,翻检其文集,新获一条明教信息:“明教专门事灭魔,七时功德便如何?不知清净光明意,面色萎黄空自劳。”可知历史上那些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为号召的暴乱确与明教相关(16)。
2008年10月以来,福建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周围发现了大量摩尼教文献、文物与古遗迹,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金泽副所长、黄夏年研究员、陈进国博士和郑筱筠研究员等专家的系统调查研究,确认为摩尼教遗物。承蒙发现人、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1003—1059)第29代裔孙林鋆先生及张凤女士之美意,将差不多全部现有资料转交于我,嘱托研究,计有:
《摩尼光佛》,83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封面磨损严重,现有书题“陈培生存修摩尼光佛”,当为后来补写,非原书遗墨。内有“赞天王”“四寂赞”等小标题,应为林瞪所传承者。
《兴福祖庆诞科》(清抄本,甲本),34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兴福祖庆诞科》(新抄本,乙本),30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乐山堂神记》,10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明门初传请本师》,17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祷雨疏》,71页,谢道琏法师传用,内含《牒皮圣眼》《牒皮式》《奏申额式》《取龙佛安座牒式》《安座请雨疏式》《牒雷公电母》《牒本坛》《申东岳》《请龙佛祈雨谢恩词意式》《祈雨谢恩牒式》《谢雨完满疏》《谢雨申唤应》《谢雨献状》《奏三清》等多篇文字,反映的是一套完整的祈雨仪式。
《求雨秘诀》,12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奏申牒疏科册》,清抄本,65页,用两种字体抄写,当出自不同的书手,为谢道琏法师传用。
《点灯七层科册》,又名《功德奏名奏牒》,26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谢道琏法师传用。
《冥福请佛文》,14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付锡杖偈》,1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富春孙氏族谱》,手抄本,霞浦柏洋乡禅洋村藏。
《高广文》,4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吉祥道场门书》,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吉祥道场申函牒》,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济南郡林氏宗谱·盖竹上万林氏宗谱世次目图》,清同治十一年抄本,霞浦县盖竹乡上万村藏。
《借锡杖文》,4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借珠文》,3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门迎科苑》,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摩尼施食秘法》,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四寂赞》,2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送佛赞》,3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送佛文》,8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送三界神文》,4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无名科文》多件,手抄本,其中最长者达165页,陈培生、谢道琏法师各有所传。
《凶看贞明经毕用此文》,4页,手抄本,霞浦柏洋乡上万村陈培生法师传用。
此外,还有上万村部分林氏宗谱、上万村“阙下林”资料、孙氏宗谱有关记载及有关文物照片等(17)。
2016年3月,福建屏南县降龙村又发现了三件摩尼教文献,即《贞明开正文科》《贞明开正奏》和摩尼教文献《第二时科》残本一件,皆手抄本,由屏南县寿山乡降龙村韩氏传用。尤其是《贞明开正文科》,与霞浦本《摩尼光佛》存在着密切关系,其中的许多内容,又见于霞浦本《兴福祖庆诞科》和《点灯七层科册》,尤其是祝颂语,是直接继承《下部赞》而来的,说明这些福建摩尼教文献与敦煌所出唐代摩尼教写本当出自同源(18)。
2017年,在福清市高山镇又发现了35本摩尼教经典科仪文本,其中有描述摩尼光佛诞生和赞美摩尼教的《谢经莲台》:“托荫石榴国,现祥瑞,皇后启瑞果,摘此吃,精神异,胸前化诞,卓世超群无比,四岁出家,十二成道,说法转金轮,现灵奇,两元三际。”
《血盆宝忏》:“西方跋缔苏邻国,九种现灵常吞末。”
《稽经道场》:“摩尼大法王,最后光明使,出现于苏邻,救我有缘性。”
宣扬教义教理的《送日光科》:“光明圣化日光王,展自金轮照三界。”
《水路灯科文》:“摩尼佛大明天,显三际二宗……遮夷但,伽度师,光明众,志心齐。”
《普度法奏》:“大圣——照、统、降,临三界——日月光、电光王、宝光王。”
《扬幡科文》:“摩尼光佛救度,九赞日月光。”
在《香空宝忏法卷(中)》里,则教导信众如何尊奉三宝、认识四生六道和严守十诫等。
还有《明教焰口》文本,将摩尼教中国化后的称呼直接标明出来,以别于其他宗教的道场焰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稽经道场》里,直接点出摩尼教组织的名称:“一念皈依清净会,三轮旋转惠明宫。”这说明当时福州地区的摩尼教组织被称为“清净会”,组织形式已经完备。
而《扬幡科文》第8页和第9页,则高度集中地把摩尼教教义教理的主要特征全都展现出来,“五妙相身,释迦牟尼,夷数伊恒,清净法身,大力法身,智惠(慧)法身,四寂法身”“从觉明使正法以来,知闻二宗三际奥义于四法身。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就是著名的摩尼教教义浓缩的标记口号(19)。
这些文献尽管发现地不同,传承人有别,但都属于霞浦摩尼教系统,故而可统称作霞浦摩尼教文献。
屏南、福清所见文献皆无霞浦之丰富,且福建各地摩尼教皆宗奉长溪(今霞浦)上万之林瞪,故悉可纳入霞浦摩尼教之体系中。甚至拥有摩尼草庵、塑像与呼禄法师墓之泉州,亦奉林瞪为境主(都天灵相)(20),故泉州摩尼教亦当属霞浦摩尼教之体系。乃至日本大和文华馆等所藏宋代闽浙所制摩尼教之绢画等,亦有与林瞪关系较密者,如《冥王圣帧》等,其中提到菜院等,可证宋代所谓“吃菜事魔”无疑即摩尼教。
霞浦摩尼教文献甫一发现就轰动了世界摩尼教学界,众专家学者悉给予极高评价,笔者认为:“在正统摩尼教消亡千余年之后,福建摩尼教仍能够在东南沿海之偏僻一隅得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穿越千年时空而不绝如缕,成为中国伊朗丝路文化交流的活化石。”(21)林悟殊虽然对霞浦文献的宗教性质颇有质疑,然仍从宗教多元性角度对其予以肯定,认为相关抄本的学术研究价值甚至远不止于明教领域,而是包含了摩尼教及其他夷教的诸多遗迹,故此次发现之意义重大难以估量(22)。这一大宗文献,对于敦煌吐鲁番发现之摩尼教文献残卷(片)自是大有补益之力,对古代史书相关明教(吃菜事魔等)之语焉不详记载多有证成之功,即于西方发现之摩尼教写卷亦不乏互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的发现为摩尼教研究开辟了华化(世俗化)研究这一新领域,使得学人得以重新审视摩尼教入华之传播史及宋元以来其在中国民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