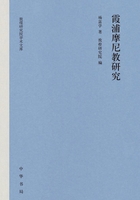
第三节 敦煌摩尼教与霞浦摩尼教文书夷偈校译研究
摩尼教夷偈或称梵字,或云弗里真言,此皆掩人耳目,以摩作佛者,据研究,其多数为帕提亚语和中古波斯语的音译。在《下部赞》中有三篇夷偈亦即音译诗,而在霞浦、屏南文献《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点灯七层科册》《请神科仪合抄本》《贞明开正文科》等中则不下十余篇,后者中不乏在一部文献中重复出现或反复出现在多部文献中及改换、混淆偈(咒)名者,部分夷词夷句与《下部赞》有继承关系而整体不同。针对夷偈之翻译研究,林悟殊著作甚丰,兹罗列如下:
《摩尼教〈下部赞〉三首音译诗偈辨说》,《文史》2014年第3期,第5—57页;
《霞浦钞本明教“四天王”考辨》,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6—204页;
《霞浦钞本夷偈〈四寂赞〉释补》,《文史》2016年第1期,第169—200页;
《霞浦钞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9—139页;
《霞浦钞本“土地赞”夷偈二首辨释》,《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70—82页;
《霞浦钞本夷偈〈明使赞〉〈送佛赞〉考释——兼说霞浦钞本与敦煌吐鲁番研究之关系》,《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6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37—157页;
《霞浦抄本无题夷偈一首考释》,《欧亚学刊》新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73—190页;
《霞浦钞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释》,《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第339—367页;
《霞浦钞本赝造夷偈一首考辨》,曾宪通主编:《华学》第12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2—105页。
马小鹤亦多有研究:
《摩尼教下部赞第二首音译诗译释——净活风、净法风辨释》,《天禄论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89页(收入《霞浦文书研究》,更名为《摩尼教三常四寂新考》);
《摩尼教〈下部赞〉第二首音译诗补考——霞浦文书〈兴福祖庆诞科〉研究》,《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0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9—164页;
《摩尼教〈下部赞〉二首音译诗偈补说》,《文史》2016年第1期,第201—234页;
《霞浦文书〈摩尼光佛〉胡语音译词语综考》,《西域文史》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1—49页;
《唐宋摩尼教胡语音译异文初探》,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8—59页。
另有吉田丰撰,马小鹤译《霞浦摩尼教文书〈四寂赞〉及其安息语原本》,《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9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3—121页。
林悟殊《摩尼教〈下部赞〉三首音译诗偈辨说》乃就《下部赞》之三首音译诗偈,在西方语言学研究基础上参合汉文音译习惯,揆诸传世文献、佛典及霞浦文书,申论《下部赞》辑入诗偈之因,以为乃宗教仪式脚本之用,其对第一首残破诗偈进行一定复原,认为第一句可译为“救拔失心同乡众”,此偈当名为《阿弗利偈》(《赞愿偈》)。第二首偈乃反复赞美明尊、明子、师僧(按:“于而勒”一词帕提亚语当作wjydg,意为活的、被选中的神灵,即所谓净法风,林译师僧恐误)、神、光明、大力、智慧等,林氏怀疑其为上偈《普启赞文》之梵呗,疑为道明自谱,非西土摩尼教之元偈。第三偈乃摩尼教教义、美德之赞,全偈分二十二赞,皆以“无上”领起,如“无上明使”“无上至真”“无上明性”等。此偈或存在部分错简,径更正之,亦为华夏信徒特撰之偈也。
林悟殊《霞浦钞本明教“四天王”考辨》乃就宋明教流传之《四天王帧》与霞浦文献中大量涉及的音译四天王之名(以《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之《土地赞·四天王偈》及《摩尼光佛·天王赞》为中心,两本文字略异)展开讨论并译释之,《四天王偈》为夷汉合璧,其中夷语部分可译:“祈请显灵、祈请救拔!乐明第二使、慈悲支姑尊!福德众明使,笃信众听者!”林氏指出,四天王皆以“逸”结尾,或为模仿道教,整偈难言为西域传承,当是拼凑音译夷名附以汉文而成。《天王赞》则可译为:“上启明使,无上四逸,圣灵守牧,福德三明使:吾等……师僧、听者……愚痴羔儿,得臻欢喜宽泰,究竟如所愿!”四大天王据马小鹤言乃出自基督教四大天使,可勘同粟特文M7800文书四“啰”神征战二百魔鬼,此乃出自《大力士经》。然林氏以为四“啰”未必堪比四“逸”,至于宋代流行的天王信仰,似亦非如霞浦所谓四天王领四大部洲也,故其以为四“逸”天王与《四天王帧》之天王实貌合神离,难言传承。按:林氏以有限的传世文献记载为圭臬强束霞浦,未免武断,笔者以为,仍当从马氏,以西域四大天使——宋代《四天王帧》——霞浦四逸天王为一完整传承也。
吉田丰撰,马小鹤译《霞浦摩尼教文书〈四寂赞〉及其安息语原本》乃以吉氏学术报告《霞浦汉文写本的中古伊朗语术语——帕提亚文的父的四面尊严》为本,复将存于《请神科仪合抄本》中的全偈释读英译,由马小鹤译为汉文(59)。《四寂赞》在德藏吐鲁番文献中有可以对应的伊朗语和粟特(回鹘)语文本,参照其内容,暂译如下:“向神祇、光明、大力(和)智慧,我们谦卑地祈祷。我们赞美耶稣、仙童女(M1397称为电光女神)(和)惠明、主摩尼(和)众使徒。给予我(我的)虔诚的希望。保护我(我的)身体(和)拯救(我的)灵魂。戒月结神圣的是末摩尼,光明使者!圣哉!圣哉!愿我的灵魂欢乐,永远神圣!”吉田丰于胡语音译词辨析上甚力,其文对《四寂赞》等音译诗切分转写,并试探讨霞浦民间《去煞符》中“ ”一字,以为或是受祆教影响而造此字以象征最高神(60)。按《下部赞·普启赞文》末数行“清净光明力智惠,慈父明子净法风。微妙相心念思意,夷数电明广大心。又启真实平等王,能战勇健新夷数。雄猛自在忙你尊,并诸清净光明众”,可能与《四寂赞》同源。
”一字,以为或是受祆教影响而造此字以象征最高神(60)。按《下部赞·普启赞文》末数行“清净光明力智惠,慈父明子净法风。微妙相心念思意,夷数电明广大心。又启真实平等王,能战勇健新夷数。雄猛自在忙你尊,并诸清净光明众”,可能与《四寂赞》同源。
林氏《霞浦钞本夷偈〈四寂赞〉释补》乃为吉田丰文之补正,其选取《摩尼光佛》《请神科仪合抄本》两个版本,重作释文,据《摩尼光佛》译云:“上启尊神辈,应现诸船主,光明大力,智慧骁勇;月光佛、夷数佛、仙童女、大智甲、摩尼尊,月光圣众乃至善业法门,志礼!哀请救拔!无上光明祖师摩尼尊青莲下,善善阿驮诸先知,圣哉永世!”《请神科仪合抄本》与之基本相同,唯无摩尼弟子阿驮之名。与马小鹤不同的是,林氏采取了归化译法,严格遵循《下部赞》等之措辞予以汉译,唯月光与夷数本为一佛(如屏南文书中即有“月光夷数佛”之谓),林氏强分为二,剥离夷数的月神身份,似是不妥。值得一提的是“戒月结”当是指五月斋戒结束举行法会送佛,此俗与佛教有关,与明教无涉。至于四寂,似已非仅指父之四面尊严,而泛指诸神之德与力,乃至僧人勤修亦可达此境界。四寂亦即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在福建各地明教中都被奉若圣言,而宋后更被剥离大明尊,转赋予摩尼佛,成为其佛身所具之四品性,使之升为教主、无上至尊,完全代替了明尊崇拜。
林悟殊《霞浦钞本夷偈〈天女咒〉〈天地咒〉考察》研究释读了《摩尼光佛·天女咒》和《兴福祖庆诞科·天地咒》两个相近文本。按《天女咒》当因偈赞光明少女(仙童女)而得名,《兴福祖庆诞科》第33行云“首举 天女咒 咒水 净坛”,而后则是一则与天女毫无关系的偈文,其41行的《天地咒》方是《天女咒》,另第33、34行亦有一段已不完整的《天女咒》。三者大体内容相同,唯所用音译字略异,林氏推断当为对同一口传夷偈之不同笔受,失真之处亦难免。大体可对译如下:“天龙天龙乎,真实造相,光明大力,心默灵魂,公允平正。第三明使,救苦夷数,仙童女,大智甲:恳切哀请,救拔群羔,善力佑助!善善弥勒,公正大力,救苦救难。弥勒大佛,清净救世,夷数仙童女,聪明大智甲,圣哉,圣哉!”按:这里弥勒即指摩尼而言,对于摩尼教徒来说,摩尼就是弥勒佛,因为耶稣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26节中承诺过他作为圣灵,将会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重新出现于尘世。在一首庇麻节赞美诗中,摩尼像被置于祭坛上,信众用庄严的诗句致辞:“弥勒佛降生了,末摩尼,那个使徒,他从上帝耶稣那儿带来了胜利(救赎)。”(61)
作为西方宗教,摩尼教素来无土地崇拜的观念,然宋代明教徒所崇拜者即有灵相、土地,无论草庵诗签抑或霞浦文献皆有“土地诸灵相”之颂词,盖因民间特重土地信仰,故从俗以吸引信众也。是以霞浦出现《土地赞》之类夷偈。《霞浦钞本“土地赞”夷偈二首辨释》解读《摩尼光佛·土地赞》,赞文分五段,为夷汉合璧,《兴福祖庆诞科》亦有此偈。其第一段大体可复原如下:“宽泰救苦者,守护圣洁灵魂、福德教法,愿诸明使善神降临,祈求摩尼尊大力救拔,性命警卫者,净风明使施光明,受苦之人臻安康,宽泰救苦,圣哉。”第三段:“志礼众明使,佑护虔诚善良、圣洁福德珍珠,恳请救拔!”珍珠是诺斯替教永恒的譬喻,喻指清净灵魂。夷偈虽云《土地赞》却无一字赞颂土地抑或天地,乃至摩尼教中“地藏明使”亦无踪影,严重名实不副。推其原因,或因制作《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之法师非笔受夷偈者,乃乡间法师,得夷偈如获至宝,而又不懂梵字,径安土地天地之名耳。
林悟殊《霞浦钞本夷偈〈明使赞〉〈送佛赞〉考释——兼说霞浦钞本与敦煌吐鲁番研究之关系》考释了《摩尼光佛》本《明使赞》与《请神科仪合抄本》之《送佛赞》这两个相似文本,大意如下:“愿吾神摩尼尊赐明使之仆以欢喜荣誉,愿神夷数赐业已忏悔显得仁慈的王子以安泰。愿审判之神光临。愿清净之神净化沙普尔的宝殿。奴婢也,真实父,慈悲救世永不息。摩尼圣尊,欢乐明界,生机盎然。救世夷数,福德神灵,摩尼大法,赦免灵魂轮回。”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分夷偈混用了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这应该是西域摩尼僧口授元偈如此。按敦煌本《下部赞》亦出现混用现象,如其第二首音译诗,第1—4、11、12、15个短语属阿拉美语,余者为伊朗语。故知其非霞浦本特有现象。林先生一贯认为,此文中仍旧认定,霞浦抄本上限多不逾明清,且非真正明教人士所用,仅仅采纳部分夷偈夷神而已,既不能与敦煌吐鲁番出洞之真媲美,亦难说其与之一脉相承,当然,其亦并不否认其夷言词组之宗教活化石作用。
在《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和《点灯七层科册》中存在的大量夷偈,不少被冠以“弗里真言”之号,《霞浦钞本夷偈“弗里真言”辨释》一文乃举三篇文献开篇弗里二偈,对校释读之,分别译为:“启福德诸明使,永恒初化显现尊,十二宝殿十二船,捞渡灵魂众船师,救拔吾辈净童男!庄严唤应警觉声,圣灵性命警察者,慈悲怜悯诸圣尊,真实先知,无上摩尼尊,佑助智慧清净(童)女。究竟如所愿。”这里特别提到佑助清净童女,突显女性信徒地位。后篇:“无上摩尼尊,清净光明使,无上清净神,具智光明使。”《摩尼光佛》中复有类似短偈“无上摩尼尊,清净光明智慧使”,或为十六字《摩尼公咒》之原型,唯少“大力”耳。
在《摩尼光佛》第65页有数行夷文夹于荐亡词列,就中出现那罗延等五佛之名,林悟殊《霞浦钞本赝造夷偈一首考辨》命之为《五佛偈》,以为乃完全赝造之作,无西域文本根据。可译为“佛陀慈悲,乞赐善男信女以宽泰!那罗延、苏路支、释迦文、末尸诃、末摩尼诸佛!圣哉!永远!”
马小鹤《摩尼教〈下部赞〉第二首音译诗补考——霞浦文书〈兴福祖庆诞科〉研究》对校《下部赞》第二首音译诗与《兴福祖庆诞科》第8页音译诗,指出霞浦本音译诗个别较之敦煌本更近胡语原音,可校敦煌本之误。吉田丰以为霞浦文书音译词以浊辅音对应伊朗语的浊音,亦不像敦煌本省略伊朗语中辅音,可见其音译系统略早于敦煌本的音译系统,虽然闽地从晚唐方得法,然呼禄法师之传承应当更早于《下部赞》的传承者,从《兴福祖庆诞科》之准确拟音,或可判断林瞪弟子制作科文时,当仍能领会夷偈含义。
同样针对此首音译诗,林悟殊得出的结论与马氏略为不同,林氏以为其原为呼禄等经回忆创制的再生文本,并非《下部赞》原物,盖赞文明言“于圣经典不敢增减一句一字”,而此偈虽音译较《下部赞》为准,然用字无章,当非为摩尼僧所记。此偈无题,《下部赞》亦仅称《次偈》,盖摩尼教偈颂多本即无名,华人特为安名以便诵也。此偈堪为《摩尼公咒》十六字之原型,故当用于多场合,不便题名。林氏发现次偈隐去多处关键词“伽度师”(圣哉),乃有秘藏此偈为宝意,《兴福祖庆诞科》本新添之颂段“老者如山常不□”亦具此特点,藏头露尾之功利心断非明教徒之当有也。
马小鹤《摩尼教〈下部赞〉二首音译诗偈补说》参校其二三首夷偈,其中第三首《初声赞文》有帕提亚文、粟特文、回鹘文、科普特文和汉文等多语种相同或相似文献参照:科普特文《集会》(Synaxeis)序言即包括“初声赞文”,说明其渊源于摩尼以古叙利亚文撰写的大经《生命福音》(《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后翻成科普特文,西传到埃及;又翻成帕提亚文,音译成汉文,也翻成粟特文和回鹘文,传播到西亚、中亚、东亚。《初声赞文》无疑是摩尼教传播最广的诗偈之一。故译释较为成功,在前人基础之上,马氏译如下:“初声、初语,初使者,初开扬,初智能,初真实,初怜悯,初诚信,初具足,初和同,初忍辱,初柔濡,初齐心,初纯善,初广惠,初施,初寻求,初赞呗,初赞礼,初选得,初妙衣,初光明,具足圆满。”为切合“初声”主旨,其将重复了二十二次的前缀词“喝思能”皆从其原始义译为“初”,不同林悟殊之归化的“无上”译法。“初声”二十二赞多与敦煌本《摩尼教残经》惠明五施十二相契合,余者如妙衣等亦与西域经典相合,在敦煌摩尼教写本中亦能找到对应。
马氏《霞浦文书〈摩尼光佛〉胡语音译词语综考》将《摩尼光佛》完整文本中可释读的音译词语做一综合考释总结,包括源于梵语之佛教词汇与源于伊朗语之与摩尼、夷数、苏路支有关的摩尼教词汇,摩尼教护法音译名,用以对应“四寂”的伊朗语词汇等。该文梳理总结了《兴福祖庆诞科》中的胡语音译或半音译词汇,指出《兴福祖庆诞科》中三大圣及四大天王的名字皆源于《摩尼光佛》,后者并有讹谬。《摩尼光佛》与《兴福祖庆诞科》内容相当的音译文字所用字常常出入甚大,似乎很难完全用传抄讹误来解释。故以为二者所根据原始文献可能不同,因此其所用的汉字亦不同。
《唐宋摩尼教胡语音译异文初探》则比较敦煌、霞浦诸本内容相同夷偈之用字参差,认为呼禄法师入闽,携弟子共撰《摩尼光佛》,乃仿佛教礼忏文,抄撮音译诗,口授夷偈赞诗而成文。林瞪卒后,弟子编《兴福祖庆诞科》以庆冥诞,亦广采音译诗。马小鹤认为,至明清时,霞浦摩尼教法师则似已对夷词夷语不甚了了,如《明门初传请本师》等写本中仅列“四梵天王”之名而不书“弥诃逸”等四名,其他写本去掉“耶俱孚”(雅各布)之耶字,而称“俱孚元帅”“俱孚圣尊”,又如“吉思”大圣本为基督教圣徒乔治,在景教《尊经》称“宜和吉思法王”,在霞浦,其先是被简化为“吉思”,《吉思咒》见《摩尼光佛》;吉思又一变为“吉师”(屏南《贞明开正文科》称“移活吉师大圣”),并近一步加封闽地特色明显的“爷”号,《吉祥道场门书》称“吉师真爷”。由是,或可推测霞浦法师或已不知法王的真正来历,亦不知《吉思咒》实为《圣乔治殉难记》的汉译。故其怀疑明清以迄当代法师所撰科仪写本乃是依据原始文书如《兴福祖庆诞科》等肆意切割夷词,随意加封西方神祇以中式头衔之产物。
已出之《摩尼光佛》《兴福祖庆诞科》《请神科仪书合抄》《点灯七层科册》及年内当出之《贞明开正文科》《祷雨疏》《奏申牒疏科册》等之录校,基本已将霞浦等地所获之摩尼教科仪文献一网打尽,其录文详尽而准确,为摩尼教研究提供极大便利,而林、马二氏从诸文献中勾稽胡音夷偈,对廓清呼禄所传之摩尼教原本面貌亦有巨大意义,此概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