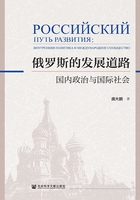
第二节 政治稳定的制度保障
为了确保政治稳定和国家杜马选举获胜的绝对把握,普京政权在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联邦制度和选举制度上采取了相互关联、完整一体的举措。这里笔者从对国家杜马选举有直接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简称《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修订入手,详细解读普京的政治控制实质。
《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修订的背景之一,是俄罗斯议会制度自身的改革需要。俄罗斯议会制度改革是从选举俄罗斯人民代表开始的,以1993年十月事件为标志结束。此时,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93年12月新宪法通过前,俄罗斯议会选举依据的法律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选举法》。1993年10月1日和11日,叶利钦以总统令的形式分别签署并颁布了《1993年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和《1993年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选举条例》。在杜马代表选举条例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混合式代表选举体制”的主张。1993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采用了混合选举制。从此时开始到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前,一直采用混合选举制。2005年5月19日,普京签署《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取消“混合选举制”,改为“比例代表制”。自2007年开始,比例代表制实行了两届。这一改革是为了培育全国性大党——“统一俄罗斯”党。2011年12月,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全面实行政治体系改革的建议,其内容主要包括直选各地区行政长官、简化政党注册手续以及降低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门槛、改变国家杜马组成原则等。2012年普京国情咨文提出恢复混合选举制。选举原则与方式的根本变化必然要求重新制定完备的有关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法律。
《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修订的背景之二,是“后克里米亚共识”导致主要议会党派在政治生活中出现默契一致的现象。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与公正俄罗斯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党纲领上的差别本来就已模糊,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外交局面的错综复杂、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持续高位,各主要议会政党原本的区别更是几乎消失。“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与其他议会反对派政党在意识形态甚至是选举问题上,都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这在地方选举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2014年在很多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如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等地,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均宣布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提名的候选人。滨海边疆区和奥伦堡州的州长均来自“统一俄罗斯”党,他们随后向联邦委员会举荐了来自公正俄罗斯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议员进入议会上院。到了2014年9月14日的地方选举日,各党均对总统提名的州长候选人表示支持。在奥伦堡州,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卡塔索诺夫虽然得到当地俄共及公正俄罗斯党分部的支持,但还是被本党将名字撤下;在巴什基尔共和国,“公民力量”党让自己的候选人萨尔巴耶夫弃选;在奥廖尔州,“俄罗斯爱国者联盟”劝退了本党代表莫夏金,祖国党也撤回了对伊萨科夫的提名。[16]
按照修改后的政党法,政党不能组成联盟参选。上述类似政治同盟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各政党之间的高度默契。议会各政党之间为了政治利益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并不鲜见,但在地方选举中如此大规模的合作与意见一致充分说明“后克里米亚共识”的深远影响。地方选举中出现的这种各政党之间的默契联合,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选前据俄罗斯媒体披露,“统一俄罗斯”党等议会四党之间在单一选区席位的分配上达成了秘密共识,以至于在俄罗斯政坛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各党派大团结的局面。
即使出现这样的局面,普京依然在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上采取了周密的控制举措。2013年3月1日,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新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草案[17]。国家杜马经过广泛讨论,直到2014年2月14日才三审通过该法。2014年2月22日,普京正式颁布总统令公布该法。[18]从该法公布之日到2016年选举前,该法又经过了8处修改。[19]具体分析2014年通过的新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法律条文就可以清晰看到在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上普京有的放矢地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20]
该法第4款第8条规定,犯有严重罪行的公民十年内无权参加国家杜马选举,这等于剥夺了类似霍多尔科夫斯基和纳瓦利内这样的现政权反对派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该法第6款第4条规定,政党可以提名非本党成员参选,第39款第5条具体细化为在全联邦区名单中可以提出的非本党候选人不得超过全联邦区名单的50%。第40款的第8条规定,在单一选区可以提出非本党成员的候选人,而且并没有规定非党成员的比例。这项规定首先是为“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参加单一选区选举打开了大门;其次也为类似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这样的全国性大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吸引社会独立人士加入该党竞选阵营留下广阔的运作空间。
该法在规定可以有非党成员进入选举名单的同时,在关于全联邦区和单一选区候选人名单组成规则的条款中又都明确规定,不允许提名其他党派的成员为本党候选人。也就是说,虽然可以提名非本党成员参选,但是非本党成员只能是其他政党以外的公民。这其实等于规定在选举过程中不能建立政党联盟。这又是有利于“统一俄罗斯”党这样的全国性大党整合力量。其他类似左翼派别的政治力量,由于建党原则和条件的宽松,出现了大量左翼小党反而实际上削弱了类似俄罗斯共产党这样全国性大党的力量,因为不能成立竞选联盟而造成力量分散。
该法第44款第1条和第3条规定,进入最近一次国家杜马的政党以及进入联邦主体立法机构的政党可以参加在全联邦区的选举;未能进入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的政党,如果要参加全联邦区选举,需要征集不少于20万选民的支持签名,而且在每一个联邦主体的支持签名不能超过7000个。根据上述规定,2014年10月28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了当年地方选举后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及国家杜马已有的政党,公布了可以不用征集签名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14个政党,分别是:“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亚博卢”、右翼事业党、俄罗斯爱国者党、公民平台党、共产党人党、俄罗斯退休者党、祖国党、共和党—人民自由党、绿党、公民力量党。[21]到了2016年选举前夕,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最终公布的参选名单依然是上述14个政党。可见,每个联邦区不超过7000人、总数不少于20万人的签名对于小党来说难以企及。对于有一些全国性影响但整体力量薄弱的政党来说,选举法现有的参选规定也是非常严苛,它们基本没有参选的机会。这也再次说明,普京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表面上增强了政治的竞争性,实际上却加强了政治的控制性。
该法第44款第2条的规定,进入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的政党可以提出自己在单一选区的候选人。除去符合条件的政党可以提名外,单一选区也接受自我提名的候选人。该法第44款第5条规定了单一选区自我提名的原则。自我提名的参选人应征集不少于参选的单一选区选民总数3%的支持签名,若是少于10万人的选区,则需要征集不少于3000人支持签名。上述规定也是对“统一俄罗斯”党有利。该党作为政权党,行政资源得天独厚,并得到普京的大力支持,在单一选区拥有强大的政权支持力度,自我提名的候选人要想在单一选区获胜,只有获得“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才有可能。事实上,最终唯一当选的自我提名候选人列兹尼克是从“统一俄罗斯”党退党参选的社会人士,与该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变化,俄罗斯在政党制度建设上也出现新特点。一是体制内实际不存在反对派。正如圣彼得堡政策基金会所指出的,亲政权的政党联盟正在实际形成当中,议会党派选择不与政权对抗,事实上表明自己是亲政权的政党联盟中的一员。[22]二是右翼政党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在2014年地方选举分析报告中指出,右翼自由派政党的活动积极性显著下降,即便它们结成同盟,在杜马选举中取胜的机会仍不容乐观,甚至会被选举拒之门外。[23]2016年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佐证了上述观点。
总之,“控制局势”的议题是普京在俄罗斯政治领域的核心任务。[24]而普京也通过在俄罗斯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机制上进行的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改革,实现了对政治体系的内部控制。
问题在于政治机制缺乏竞争性导致出现政治退化现象。俄罗斯政治生态出现各主要政治派别高度默契一致的局面,这种局面反映的是政治竞争的弱化。还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前,2010年11月,梅德韦杰夫曾经指出包括政党机制在内的政治制度改革的成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处于停滞的状态,而停滞会导致不稳定,停滞对执政党和反对党来说都是非常有害的。如果反对党在议会竞争中没有一点获胜的机会,那么它就会退化,并逐渐被边缘化。而如果执政党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失败的可能,那么它也会铜锈化,最终也会退化。摆脱困境的途径就是要提高俄罗斯政治竞争力,政治体制能够得到重大调整,变得更加公开和灵活,最终变得更加公正。只有政治竞争力和存在有分量的反对党才能保证国家真正的民主。[25]俄政治局势的发展印证了梅德韦杰夫关于政治退化现象的担心。
政治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集中管理模式与强力领导人紧密结合,政治人格化现象严重。这种结合的问题在于政治体系难以得到持续改良。到下一个十年,普京时期出于自然规律也将走向终点。在这种情况下,公认领袖的离去可能会引发一连串冲突并演变为政治失序。[26]叶利钦时期政治转型的问题在于俄罗斯各主要派别缺乏政治妥协观念,出现政治分歧时往往以政治对抗的途径解决问题。现在俄罗斯政治生态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政治竞争严重弱化,以民主的手段实现了集中,反而对俄罗斯民主化的推进产生了阻碍。
二是政治体系的权威性很难树立。政党机制趋同性的同时,弊端也暴露出来——社会不再信任政党体制的权威。根据2014年地方选举以后的调查数据显示,70%的受访者知道政党及其领导人、纲领及活动,但仅有4%的人信任这些政党。俄罗斯舆论基金会的民调也表明,近两年来,不明白多个政党存在有何必要的公民比例从28%增至39%。如果民众不认同这些政党存在的合理性,那么选举机制带来的合法性就会降低,政治退化最终会对政权党以及体制内反对派产生负面影响。[27]在叶利钦时期出现的政治现象是由于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缺少政治妥协精神,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对抗,社会对议会、政党、法院等执行权力机构的信任度逐年下降。[28]现在从俄罗斯的政治实践看,如果没有建立在良性竞争机制条件下的政治对抗,社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度也会下降。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政治妥协精神是俄罗斯政治转型中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所谓政治妥协,不仅仅是避免政治对抗,也包含良性的政治竞争。而且,政治妥协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仅仅指在政治生态上达成政治一致或竞争。政治妥协问题的根本解决,将与俄罗斯的地域范围、地缘政治、种族、文化、地区差异以及其他很多因素有关。[29]
政治性抗议运动有逐渐向社会性抗议运动转变的趋势。高度政治共识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种政治压力,没有政治派别公开质疑政府行为,即使体制外反对派的抗议运动也远没有了2011年的声势。库德林领导的公民倡议委员会以“俄罗斯人政治情绪监测”为主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认为,人们对体制内政党的不信任、对经济形势恶化不满、对外交成就的怀疑正与日俱增。即便如此,虽然也出现了零星的抗议示威,但是当前俄罗斯抗议运动的特点是人们不赞成政治性抗议,而只支持社会性抗议。这既受俄罗斯高度一致的政治局面有关,也与随着外部局势的恶化,民众担心重蹈乌克兰覆辙有关。[30]从各政党2011年以来的政党建设方向也可以佐证这一变化。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统一俄罗斯”党在两个方向加强了党的建设。其一就是加大力度关注社会问题。2013年10月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梅德韦杰夫谈到了“统一俄罗斯”党所肩负的重要社会责任:“宪法规定俄罗斯是一个社会福利型国家。我们有提高预算供养人员工资的重大责任在身。尤其是医生、教师、军人。”[31]梅德韦杰夫要求“统一俄罗斯”党讨论社会重大民生问题。其二,“统一俄罗斯”党开始了一场清理党员队伍的运动。中央机构向所有联邦和地区级领导人下达认真处理所有投诉的指示。[32]体制内反对派社会性抗议活动的目标也很明确,在教育、卫生、反腐和发展中小企业这样一些极其重要的领域纷纷提出自己的纲领。[33]
“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简称人民阵线)的壮大除了着眼于单一选区选举以外,也是普京推动政治发展的尝试。人民阵线是围绕普京战略建立的,遵循普京提出的国家发展思路和价值观。有评论指出:2013年普京决定改组和加强人民阵线是因为他对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速度、对纲领性竞选文章和“五月总统令”的实施机制失望。几乎所有方面的工作,包括住房公用事业改革、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改革都在空转,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普京赋予人民阵线的权力是公民可以直接提出任务,并提出为完成该任务需要出台法律和国家决议的建议,以推动解决那些陷入官僚主义泥潭的问题。[34]
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概念叫“中期”,即四年总统任期的时间中点。俄罗斯政治的“中期”则是一个新现象,因为原先的四年总统任期中基本上不存在任何中期。一切都十分紧凑:总统大选,一年间歇期,规划新的竞选热点,新一届杜马选举,新一届总统选举。现在,杜马选举和总统任期分别延长为五年和六年后,俄罗斯政治的“中期”概念也出现了。在“统一俄罗斯”党赢得史无前例的超高席位后,社会和民众会把“中期”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政权党的身上,普京要直面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经济增长疲软,精英团结出现裂痕且需要更新换代,民众有可能出现厌倦和不满情绪,在叙利亚等问题上遭遇地缘政治困境。这样一个“中期”无法回避。[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