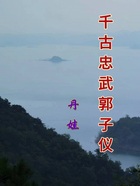
第18章 卫州寄愁思
公元758年8、9、10月
八月二十六日,唐廷送宁国公主至回鹘和亲已有月余,皇帝催请援军之书不绝于路。千呼万唤,该国允诺“天可汗”的三千重骑终于抵达长安。李亨大喜,命太子李俶携百官于丹凤门前相迎,并亲手将宫制锦袍金甲赠与领兵回鹘将军骨啜和副将帝德。回将奏请仍归朔方大将仆固怀恩麾下,并言明乃二王子移地健之坚请,因是他的岳父,最可信任。帝立时准奏,回军即进驻东禁苑朔方大营。
李俶因未见结拜兄弟叶护太子随军同来,心中郁郁不乐。回到府中,与姬妾子女饮酒解闷,不由得提及此事。一旁伺候的内宦程元振闻听,插嘴道:“老奴可是听说,那回鹘太子已被其弟移地健软禁了。”
李俶大惊,忙问:“可知所为何来?”
元振道:“老奴听说,他领兵回国时,那二王子清点所携回的金帛子女,皆不如其所愿,怒而禀告父汗,说是太子私通唐廷,欲行谋篡汗位,求斩之。那汗王因我国已允妻之以嫡公主,便不问叶护死罪,只凭移地健将其软禁。”
俶闻之黯然,幽幽道:“英武可汗怎会坐视次子囚禁太子?”
元振叹口气道:“老奴听说那移地健与太子并非一母所生。他生母一族乃西域大姓贵族,坐拥土地牛羊无数,还蓄有几万世代死忠的部落骑牧。他本人生性狂妄自大,几年前从外族家承继了万余精兵骏马,还有金宝珠玉。又仗着那些坐拥实力的疏唐酋长撑腰,不但不把那位家族早已没落,性情懦弱的亲唐太子放在眼里,更欲取而代之。老可汗已近六旬,精力不济,兵权旁落,身边又多是二王子的疏唐拥捧者,也是无可奈何。”
一旁静听的独孤氏见丈夫眉头愈加紧锁,料想是被触动了自己生母乃罪臣之女的心病,便责备那内宦道:“程老官哪里听来这许多故事,怕是以讹传讹罢。”
元振立刻会意,忙道:“独孤孺人说得是。老奴只听宫中人传言,未必是真。”
李俶料他定是从李辅国口中听得,该是八九不离十。一时想起那日随父皇送小妹宁国公主至咸阳,她在诀别一刻留下句“为家国复兴,死而无憾”,竟引得父亲在回长安路上泪流不止。他与小妹在百孙院住得最近,也最疼爱她,当时看着送亲礼队越走越远,心痛不已。后来护送公主的册礼使李瑀回朝述职,言及葛勒可汗见大唐使者时,先是十分傲慢无礼,欲坐榻上接受册封。后经李瑀一番正言厉词,斥他未经开化,不识中国天朝礼节,那可汗方认同以子婿名分下榻跪受册礼。他听后更为嫁到那荒蛮不化之地的小妹忧心不已。此时想起来,倍觉心酸,缓缓道:“宁国孤苦矣。”
元振听闻,实悔多嘴,忙慰道:“圣上赐公主陪嫁媵侍三人,皆女中翘楚,果敢担当。听说内有一位闺名仆固琳琅,容貌娇媚,却性烈如火,随身佩鸳鸯双剑,可一剑封喉,几个壮男也难近身。太子不必过虑也。”
独孤十分好奇,问道:“仆固琳琅是何许人?”
升平闷坐已久,抢答道:“就是海花亲妹子。在灵武时,有次见小姑母被几个无知子无赖弟纠缠,拔剑相助,吓退众人解了围。二人遂成闺中密友,时常相伴。”
独孤赞叹道:“又是仆固将军之女,倒真是一门忠勇!”
升平却又道:“记得曾读过古书《穆天子传》,说是西域有‘子可纳庶母’之民风。想那可汗已是老迈昏庸,一旦死了,宁国姑母若被逼嫁叶护或移地健,不是乱伦吗?”
一旁李适早听得不耐烦。今天恰是他十七岁生辰,听闻父王召他饮宴,以为是给他庆生,便兴冲冲而来,却不想席中竟是不相干之议,他这太子长子生辰大倒无人提及。又想到返京已近一年,却不见父王尽心寻找失落的沈姬,他的生母,不觉且悲且愤,对升平大声斥道:“你不知小姑母和亲之前已连丧二夫?此时来提可汗年迈,莫不是咒她婚姻再不得善终!”
升平素知大哥言语刻薄,正要反唇相讥,却被父亲用目光止住。
李俶和颜对李适道:“今日居家小饮,本为王儿十七岁舞象之年庆生。为父将你皇太爷当年所赐龟龙戏珠宝剑一柄,为儿作寿礼。”
说着命人捧上剑来。李适慌忙跪接,捧在手中定睛观看。只见:黑檀为柄,黑铜为鞘,黑玉雕磨一龟一龙盘弄一粒硕大黑珍珠,嵌在剑鞘上,流光潋滟,夺人心魄。他惊喜交集,忙向父王叩谢。
一时家宴散去,无人注意华阳悄然神伤。她心中只想:我若是如小姑母被远嫁异域,与心爱之人再不能见,与死何异。
眼看九月已至,皇帝李亨敕命五路兵马集结东禁苑。除先到朔方郭子仪部,又有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襄邓节度使鲁炅、荆南节度使季广琛及河南节度使崔光远等四路大军。又令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从太原,关内节度使王思礼从潞州(山西长治),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从亳州(安徽),平卢兵马使(节度使之下,专掌兵马实权,安、史皆曾领之)董秦从青州(山东)等另四路大军于十月中旬分别向邺城进发。
九月二十五日,郭子仪正待与李嗣业等四方节度使赴皇帝御赐出征宴,忽接宫中密敕,即刻发兵,夺取卫州(河南卫辉)。
原来那日宰相李岘辞别子仪后,几番考量,终在御前进言道,可先遣一劲旅剿除安阳郡南部卫州城里盘踞的强寇安太清。一来削减贼军主力,而来为总攻邺城造声势。帝觉甚妥,准奏。其实李岘本意若此战子仪获胜。便可进言皇帝放弃设置观军容使,而用子仪为帅。因恐走漏消息,遭内官作梗,特请下密敕,立即送往郭营。
子仪接旨不敢稍延,即率军经洛阳东杏园北度黄河。途径县城获嘉,军探来报,贼将安太清正在此招兵买马,于是趁其不备杀进城来。一场速战,杀贼数千,得民伕数百。那安太清眼看难敌唐军威猛,仓皇率兵逃返卫州城,同时遣快马至邺城,急报求援。
身在邺城的伪皇后高氏得知独子危急,立逼安庆绪派重兵相助。于是太清一进城,就迎来叔父伪郑王安庆和及大将崔乾佑、田承嗣等率上万精骑,一时士气大振。
郭子仪领军追至卫州城外,远远望见城头各色旌旗招摇,正中一幅阔大“安”字帅旗,两旁几面将旗分别是“安”、“崔”、“田”,便知贼叛援军已到,强攻无益,忙命距城十里处扎下营寨,又急召各部将商讨克敌之策。
唐军连夜悄然侦察布兵,直至天光微明。郭子仪铠甲鲜明,亲率几千轻骑冲到城下。安太清在城头看得明白,那“郭”字大旗下正是威名赫赫唐帅本尊,急忙命城上弓弩同时放箭,霎时唐军阵前飞矢如雨。
子仪见状,命前军后退,从阵中推出十数架抛石机,令旗一挥,只见上百石弹砸向城墙。这卫州城原是年久失修,土砖墙早已剥蚀薄弱,哪经石炮轮番猛轰,眼看几处开始坍塌,露出破绽,引来贼兵一片惊叫。
安太清哪里按捺得住,立率本部兵马冲出城来。伪郑王安庆和一时没拦住,只恐侄儿坏了性命,无法向皇兄皇嫂交代,只得也率部跟着冲出城。崔乾佑与田承嗣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
子仪见贼将杀来,虚应一阵,便率军撤退。太清眼看大唐名将就在咫尺,心中振奋,哪里肯舍,仗着年轻气盛,挥舞一杆长马槊,呼啸而来。他紧盯前方那金甲背影,目中无他,只顾策马直追。眼看追至一处废弃兵营门前,猛听得几声震天鼓噪,营墙上忽地立起无数弓弩手,齐声呼喊:“休走了贼子安太清!”随之箭如飞蝗,扑面而来。太清如梦方醒,心知上当,急忙勒住马头。正待传令后撤,已见身边士卒纷纷坠马,心中惊慌,拨马便逃,也顾不得继而冲来的叔父安庆和。
此时子仪指麾朔方军调转马头回击安军。又有仆固怀恩一马当先,正遇着不知前方有变的安庆和挺枪来战。怀恩迎上去,抡起圆月弯刀,一刀劈下,将伪郑王手中长枪削去大截。紧随其后的回鹘将军骨啜趁势将庆和挑于马下,即刻就被唐兵绑了,送到大帅马前。子仪立遣部将杜黄裳押送这安庆绪胞弟回京报捷。
后面贼兵见主将一逃窜,一被擒,皆震骇而逃。正在城上观望的崔、田二人见自家人马丢盔散甲往回逃,后面更有凶悍回鹘骑兵紧迫追击,一路砍杀,如雷霹雳,势不可挡,早慌了手脚,急忙奔下城楼,拉起本部兵马,弃城直朝邺城方向逃去。
子仪派人清点战绩,得贼尸两万余。战前探得安庆绪已聚贼七八万,此一战便歼其三分有一。再点朔方折损仅百余。众将士闻听,无不鼓舞,于是入城安民,休整补给。
子仪却不得稍息,立召众将商议:卫州既然已得,或是在此等待皇命,或是乘胜追击穷寇。皆曰,此城向北不足二百里便是邺城,我应一鼓作气,剿尽残贼。怀恩更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不必坐等。
子仪权衡再三,认定终结安氏伪朝之最佳战机就在眼前,转瞬即逝,便下令大军明晨进发。
众将领命,正待返回本部,有军士押着一个村姑模样青年女子进帐来。
只听军士上前禀报:“我等巡街见这一女子藏头露尾,形迹可疑,捉了问她,自称从范阳来寻找夫婿。小的恐是叛营派来的奸细,押来见大帅。”
子仪闻报,命众将少留,共听听女子如何解说。
那女子早见一众横眉立目之武将壁立中,有位威仪凛然,姿容绝世的白袍金甲大将端坐帅案之前,又听军士尊他为大帅,心知定是那位早已耳熟能详,玉丹口中的义父郭子仪。她不等人开口审问,先就细步上前,屈膝福拜道:“奴本范阳辛氏,小字柳。只因战乱失却未婚夫婿音讯,来此寻找,实非奸细。”
子仪略为思忖,问道:“你夫婿姓甚名谁,怎知就在此处?”
女子犹豫再三,但闻他和言缓语,便轻声道:“奴千里寻夫,一路打听,方得知他就在此城戍防,故而赶来。不料正遇城破,再无处得觅。”
子仪闻听,忽然记起那石国王子武昭拓曾言及在范阳史府结拜一辛姓女子,甚知书理,不肯从叛而逃离,便问:“小娘子可是史思明之侄女,辛柳?你夫婿便是叛将安太清?”
辛柳不想子仪竟知她底细,大吃一惊,眼中含泪,默默点头。
众将立时哗然。子仪见她温文静雅,不似无知愚妇,坦言道:“那安太清已被我击溃,不知所向,你当如之奈何?”
辛柳腼颜道:“奴知太清必不肯善罢甘休,待获援军,必来恶战。然他与奴情深有约,元帅遇着他时,还望先将我二人儿时密语呼唤于他,使知奴千里来寻,或念旧情肯来归降,也未可知。若彼已将青梅竹马之约抛却,定要与王师为敌,元帅尽管杀之,奴亦随后赴死,了断孽缘。”说罢,眼中泛起泪光。
众将面面相觑,单听令公如何处置。
子仪沉吟良久,方问:“汝可能书否?”
辛柳道:“先父在世经营书馆,奴自幼琴棋书画皆通。”
子仪又问:“汝适才言道儿时密语,可否说来一听?”
辛柳扫了众人一眼,赧颜道:“奴与他私下互称‘雄峻郎君’,‘花柔娘子’。”
子仪缓缓点头,道:“某愿助你一了此情。可将心中之意写成一信,某命人携带之。果若再遇那安太清,必设法传送与他。只是他肯否改恶从善,与你再叙前情,不在某,而在你信中言辞。你须仔细想来再写。”
辛柳连连点头。子仪命军士将她送到城中一户多有女眷的富家暂歇并看守,不得为难于她。
女子被送走后,仆固怀恩不解,问子仪:“郭公又来婆婆妈妈,打仗就是动刀剑,怎的还替人‘鸿雁传书’?”
子仪大笑道:“怀恩文思大有长进,竟知《汉书》词句。”转又正色道:“某要这女子写信与那贼小将,一来看他年纪尚幼,有勇无谋,只听命于上,并不真知为何而战。若能动之以情,毅然弃战,即可减我军阵前伤亡。二来战乱经年,已不知拆散几多少年情侣。若这女子有幸劝得情人逃脱不义之战,哪怕作对贫寒夫妻,也强似为刀下鸳鸯。”
怀恩摇头道:“只怕小贼有负郭公美意。”
一旁浑释之手拍腰间佩剑道:“某之铁勒(北方突厥)长剑专候那无情无义之贼!”
翌日,朔方大军出发前,看管辛柳的军士将一封未缄之信交与元帅。子仪并不拆看,只瞟了一眼封面上几个娟秀小楷:“吾兄雄峻郎君启”,即将信交给箭术最佳的仆固玚,命他绑在箭上备用。军士仍回去看管辛氏,战后再作道理。于是大军向北进发。
行进不到百里,有军探来报:安庆绪得讯卫州已失,知邺城难保,便点起所有近五万兵马前来阻截。现已等在十几里外必经之路,愁思冈。
子仪与众将略作商议,继续前行。不到半个时辰,就见前方一处逶迤平冈。子仪才命摆开阵势,就听得一声火炮巨响,金鼓齐鸣,冈上涌出黑压压一片人马。只见中央一面“燕”字大旗下立马横枪的就是伪皇安庆绪,左手崔乾佑,右手安太清。二人见唐军近前,于马上高喊:“还我卫州!”挺枪纵马一路冲下冈来。身后紧随一排排铁甲骑兵。
子仪见贼军来势凶猛,忙挥令旗,命前阵怀恩部略退,将陌刀营尽出。只待叛军近前,百柄长刀一齐横扫,瞬间数十匹前锋快马喷血倒下。怀恩瞅准时机,一马当先冲入敌群,回鹘铁骑呼啸追随,霎时间刀枪剑戟杀成一团。
怀恩之子仆固玚于马上张望,待看清那贼小将,便持弓箭迂回接近,猛然朝他大喝一声:“雄峻郎君听了,花柔娘子有信与汝!”见他闻听骤然一愣,玚乘机将箭书射过去,正中其左肩。
太清于乱军中忍痛将箭拔出,见上面果然绑有一信,急扯下来塞进胸甲之内。再寻射箭之人,已无可能。
此时后阵浑释之及陈回光诸将也率军杀来,正遇着贼将田承嗣、孙孝哲领兵冲下愁思冈,两下相撞,奋死厮杀。战不到一炷香,安太清左肩箭伤难忍,更惦记怀中书信,已是心神散乱,不肯恋战,瞅个空子兀自冲出重围,奔上冈去。众贼将见了心生狐疑,皆不敢久战,纷纷鸣金收兵。
子仪见敌方弃尸遍地,自家亦有众多伤亡,于是号令收兵,退后十里扎营。
入夜,忽接混入贼营的斥候密报,那里不知何时走失了骁将安太清,正悄悄拔营而去。子仪猜想必是与那辛氏女子的书信有关,即刻下令追击。叛军却凭着道路熟悉,天明之时已抢渡过安阳河。待子仪大军赶到,只见残众贼已渡河而去,渡船正在河对岸燃烧,火光浓烟之后,隐隐可见远处邺城角楼。
子仪心中估算,安军经愁思冈一战再损近半,逃回城中不过两三万。朔方与回鹘合军近五万,追渡过河,不怕困兽插翅。但见河边再无渡船,于是命扎营河边,沿河搜船。然经两日搜寻,仅得渔船数十。子仪与众将商议,将五万人马渡过河,至少来回数百趟。而那贼酋断不肯坐等我全军渡过,方来应战,必是来一杀一,故分批多次过河,无异于逐次投肉于虎口也。
众人正搓手顿足,无计可施,有附近渔民献策,离河不远有座林虑山,上多松树,可砍来扎成大木筏,以渡大军。子仪闻听大喜,赏了渔民,命兵士白天上山伐木,夜里就篝火扎筏。
两日后,几百大筏沿河排满。子仪正与众将观看新筏,忽见留在卫州监护辛柳的军士骑马奔来。到得跟前,滚鞍下马,气喘吁吁急报:“那辛氏女子再找不见……四路节度使齐聚卫州……”
众人闻听皆摸头不着。子仪命人端茶水来,容他慢慢讲来。
原来朔方军离了卫州第二日,辛柳便在人家待不住,借口看街景买花买朵在城中游逛。开始军士还紧跟在后,但见她尽往女人群聚的店铺去,渐渐脸上挂不住。次日就不再跟着,只嘱她早些归来。那日她倒听话,不到一个时辰便回。只是第三日她再出门就没回来。他急得满街寻找打听,不得准信。却遇见四路节度使大军浩荡入城,被叫住问话,再找不到辛氏,只得快马来报。
子仪听了暗自思忖,辛柳失踪之日恰是安太清离贼脱身之时。想来必是他依情人信中所示,寻着她,相携远走高飞而去。不由得心中赞叹:好一个睿智女郎,竟说得嗜血贼人丢下屠刀,立地成佛。
只听仆固怀恩等将忙问四路节度使进卫州城之事。军士道,他被北庭行营大将李嗣业召见询问,郭令公可接到圣上敕令,与四节度于卫州集结待命,他回答未曾听闻,又说以他所知,郭老爹若接着圣旨,断不会违旨擅自率军追击逆贼。
子仪命军士归队,复与诸将商议,决定先不过河,继续造筏,以待圣命。
三日后,皇帝敕令送达安阳河南岸朔方军大帐,子仪与众将跪听中使宣读。
“中书令郭子仪文德武胆,术应通方,统率锐师,连克获嘉、卫州两要镇。朕得此天赐帅才,佳慰良深,意气更发。知令公已逐贼至邺城之南安阳河,朕欣待捷音。前已令李嗣业等四节度自卫州向北与公合军。今又令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三节度与平卢兵马使董秦共四路从各自辖镇赴邺,九军围聚会战。”听宣至此,群情昂奋,摩拳擦掌。子仪正要伸手接旨,却听那中使又读:“禁军三军大将军鱼朝恩,侍朕经年,深称朕意,兼知兵法,宜令权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集统令九军,并取决断。着子仪辅之,务使邺城之战毕其功于一役。望卿知朕意焉。乾元元年十月二十日。”
宣旨已毕,众将面面相觑,不敢置信,皆忘了起身。子仪先跪接圣旨,站起身再谢皇恩,问中使道:“使臣可知圣上欲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否?”
中使微微摇头,道:“不曾听闻。在下倒听得宫中有人问鱼将军,观军容使为何职,答曰,凌驾诸路将帅之上者也。”
子仪遂不再问,只请中使于后帐稍歇,又命备酒肴为之洗尘。
怀恩早已不胜其怒,只待那宦官中使离了大帐,便切齿道:“我等昂藏伟丈夫,此番却要受那无卵阴人挟制也!”
诸将附和,议论纷纷,皆愤懑不已。子仪无言相劝,又恐少时酒席上难免有人口无遮拦,冲撞中使,便命各回本营,监造渡筏。
一时酒席摆上,子仪恭请中使,亲自相陪。席间中使告知令公,皇太子册封大礼已于日前在大明宫宣政殿行毕。帝改太子李俶名为李豫,同日随帝、后同谒太庙,会群臣,受朝贺。子仪虽未能亲历盛典,却欣慰自此李豫储君之位已成正统。又听中使言及宰相李岘加任吏部尚书,颇得圣上倚重,也在心中暗贺。
席罢,子仪亲送宦官歇息,以备明日返京。见诸事妥当,方信步走到河边,立于一土坡之上。放眼望去,金乌已坠,沿河堆堆篝火通明。各营将士由随军匠人指点,将日间拖下山的木料削砍截齐,铆接连排,一派壮观。抬眼眺望安阳河北岸,远处邺城半隐于苍茫暮色之中,极似一庞然坟茔,那该是安氏伪朝葬身之地。子仪观之,又觉心中沉重。刚才众将所发怨声不无道理:战火两年,兴亡满目;万千将士血垢凝于爪发,虱虮结于兜鍪;四方士民青壮死于兵役,老弱馁于蓬蒿;堆尸如山,血臭千里。经大小几十仗,方得收复二京。眼见得贼酋最后窝聚之处将被王师踏平,却又来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军将口碑恶差,威与信皆无的鱼朝恩来制统二十万兵马,犹如着冠沐猴领引虎豹之师,谁能心服首肯,胜算又有几何?思想至此,不由得口中叹道:“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可叹子仪睿智过人,也猜不透那鱼朝恩竟是如何于中宫邀宠弄权。
原来近日那张皇后察觉,一直视为心腹之大宦官李辅国渐不似以往耳提面命,凡事禀报。每每见他敷衍塞责,遇事躲闪,又不肯在皇上面前助她废李豫,立李佋,直令她对这年老丑奴日增厌恶。而一向熟视无睹的鱼朝恩渐入关注。虽为宦官,他却生得丰神伟仪,气势不凡。一双三角眼不甚讨喜,倒也无伤大雅。几次召他谈经论道,皆口若悬河,七横八纵,头头是道。言语间又是那般柔声顺气,极尽谦恭,更令她受用,大有识人恨晚之叹。又见他颇有野心,便作往后倚重之想,有意笼络。听得皇夫欲设观军容使以制衡平叛之众节度,立即举荐鱼朝恩。
那日张后为嫡子李佋病情反复甚为烦恼,便去御花园散心。忽然树间闪出鱼朝恩,抱拳恭立,口称求见皇后。只见他身着绣金战袍,甲胄鲜亮,一副气宇轩昂,张后心里先就喜欢。虽然从无本宫以外的内官敢求见皇后,但见他神情焦急,必有非常之事禀告,且听他讲来。于是召他近前讲话。
鱼朝恩俯身再拜,又以目暗示,有宫人在旁不便言讲。张后会意,命她们远处候着。朝恩这才毕恭毕敬道:“臣闻前方战况,颇为忧虑,还望皇后指点,拨云见日。”
张后矜持微笑,道:“何不说与皇上听?”
朝恩神色黯然道:“圣人近日深信朝中宰相李岘等人,微臣恐多说无益。”
张后笑容依然,道:“你怎知说与本后便有所益?”
朝恩拱手道:“自那日皇后召微臣讲演《周易》,臣便知本朝国母具则天圣皇之胆略胸怀,因此方敢犯颜求见。”
张后闻之大喜得意,却收起笑容,正色问道:“你且说来听听。”
朝恩近前几步,低声言道:“圣人数日前已拟下敕令,任微臣观军容使,主统九节度邺城剿贼之战。不期宰相李岘横生枝节,说动圣人命那郭子仪先取河内(黄河凹处北岸以东)数城。今闻报朔方军连获大捷,追残贼至安阳河边,另外九节度也正在前往合兵的路上……”
张后有些不耐,打断他道:“既是王师连胜,你何故忧虑?”
朝恩忙道:“微臣闻听圣上因此已示中书省,暂留观军容使敕令不发,有意再设兵马大元帅,由郭子仪出任。臣以为又是李岘主张。”
张后颇不以为意,道:“只要郭令公可剿灭逆胡,受封大元帅又何妨。观军容使不设也罢,今后还怕没你施展之机?”
朝恩三角眼一转,斟字酌句道:“微臣失却功勋之机倒也罢了。然据臣所知,那郭子仪竟不接圣旨,擅自追贼至安阳河,显见得欲独占大功。臣只恐因此藩镇军阀再次做大,朝廷不能制衡,又生动乱,帝国复危矣。”
此番话顿时惊醒张后。她也听说各地时有乘乱犯造反,打杀主官者。那安史二贼便是犯上作乱的先锋,怎知再无后来者。郭子仪固然是不贰忠臣,但越是对帝国忠心越难为我所用。看他自平叛以来与李豫同袍一年有余,生死与共,又甘冒死罪,独担清渠兵败之重责,以维护当时广平王威望和地位。有朝一日我若策动废太子李豫,另立新储,老将军岂肯坐视?再看那李岘也是可恶,前番竟说服皇上只处死十几名大恶之叛臣,余皆从轻发落,令皇权森严何在?这鱼朝恩是本后举荐于皇上,他又来插手干预。他便是凤子龙孙,我也是太上皇外戚……
想着,她气狠狠道:“偏不信那李岘有本事一再欺君罔上。此番本后定要你作成这观军容使,看谁敢来螳臂挡车!”
朝恩见张后面色铁青,已知触动其心思,事必可成。于是再行大礼跪拜,顿首谢恩而退。
果然,不到两个时辰,大唐立朝以来首次颁发“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之敕令便宣达与这宦竖。
鱼朝恩接旨欣喜若狂,飘飘然仿佛置身云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等不及要看到那等将他视作无物的“雄男子”们,从此如何对他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不敢一事违抗。他怀揣圣旨和满心得意,欢天喜地跨上骏马,一刻不停奔出长安,直朝北方安阳河而去。
*********
再说安庆绪大败退回邺城,伪皇后高氏不见爱子太清同归,顿时惊惶万状。待问明他已于愁思冈战场失踪,死活不得而知,竟一时急火攻心,犯了疯癫,乘随侍不备,独自奔出城去寻找,从此失了下落。庆绪知唐廷大军已集结于城外十几里安阳河对岸,即将兵临城下,便无暇顾她,只召残部共商对策。
见众人皆灰头土脸,萎靡不振,庆绪发狠道:“尔等休作狼狈小儿之态。如今大燕尚有两条前路可走。一是举城降唐,生死由他。但只看那唐皇如何处置自家降臣,尔等尚存刀下留命之望乎?二是负隅顽抗,与他血战乾坤,倒还有几分活命希冀。是战是降,各自速决。”
众人交头私语,片刻后只听悍将崔乾佑率先道:“某也曾大败唐廷名将封常清于洛阳,至其被昏君所杀;又设计‘灵宝-潼关之战’,杀唐军二十余万,获其老帅哥舒翰,使我安军得以长驱直入进长安;还曾与他兵马副帅郭子仪恶战数回,早是唐廷目中之刺,必除而后快。既然降也是死,不如拼死一战,岂不快哉!”
骁将田承嗣因洛阳兵败一度降唐,前几日再领残部来投邺城,此时瞠目大声道:“大丈夫能胜能败!今虽退守孤城,幸而粮草存储尚多。若一面坚守,一面求援于范阳,不愁无胜算也。”
伪中书侍郎高尚却摇头道:“唐军已从四面来围,而城中只有万余人马,如何掩护求援之兵出城?”
田承嗣拍胸道:“某愿单人匹马冲一条血路,直奔范阳。”
庆绪闻听,含泪抚其肩道:“邺城或存,或亡,皆系将军一身也!”
承嗣道:“事不宜迟,某即备马出城。”
可怪的是,自田承嗣去后,安阳河边不见大动静。城内日夜提心吊胆,生怕唐军突然攻袭,却连一声马嘶也不曾听得。诸将众说纷纭,或言就此固守待援,或言乘唐军尚未围城,弃城走范阳,投奔史思明,如此种种,莫衷一是。安庆绪心烦意乱,终日饮酒,惟盼援军速来。
*********
再说安玉丹见范阳军惨败而归,便知自己传送情报准确有用,大为振奋,越发将南下寻亲之心收起,逐日支起耳朵,在节度府内四下扫听。只因她已俨然史府内眷,有意无意无处不至;且又人缘极好,衙内军士仆役等对她全无戒心,遇事有问必答,如家人闲话一般。
那日她正从府内后花园路过,只听粉墙里有嘤嘤啜泣之声,忙闪在墙边,闪睛从壁上花窗朝里张望,只见有人正隐在墙角树间私语。定睛一看,一高壮,一纤细,竟是史思明的亲兵总领曹平将军和那宠伶锦衣,不禁吃惊好奇,这两人怎生到得一处,也未免忒胆大了。于是耳贴花窗,眼观其人。见曹平捧着锦衣的手柔声道:“因何又不当心,惹大帅火气?”那宠伶泣道:“奴只给他讲了一个新听来的笑话,道是一偏将战后回家与妻行周公之礼,妻曰:‘愿郎君此时莫再言昨日战败之事,有负好时光。’偏将道:‘贤妻说得是。请猜今夜元帅能与爱妾再战否?’不料大将军听到此处飞起一脚,将奴踹到地下。幸亏将军你进来禀报邺城有使者在议事厅候见,奴方逃得性命。”只听曹平长叹一声道:“此次偷袭太原不成,反损兵折将,大将军气得对朝义小将军都发了狠话,你倒讲这等笑话,白惹他恼怒。”
玉丹此时无心再留,耳朵里只有“邺城使者求见”。她早知“堂兄”安庆绪自洛阳败北邺城,今日遣使来此,是为何故?想着便蹑手蹑脚离了后花园,直奔议事厅。
疾步来到厅门前,她见有两名校尉守在那里,便对其中一个相熟者道:“吴兄,听说邺城来人,小弟欲知堂兄近况如何,烦请通报大将军,可许我进去旁听否。”
校尉点头进去。一时出来道:“大将军命你就在里面门口凳上坐了,不得插嘴。”
玉丹忙进得厅内,捡个靠门的方凳坐了,静观那边众人。除了史家父子及数位心腹将领,她一眼认出客座上那穿着安军甲胄者乃叔父安禄山宠信大将之一,田承嗣。她曾在洛阳伪皇宫中见过他,也听李猪儿说过就是此人率叛军作前锋,一举夺得洛阳,迎贼酋入紫薇城称帝,故得特准带剑上殿进见伪皇。不想却在这里见着。
只听史思明道:“汝来请兵救驾,按说庆绪是我侄儿,本当救之。但人人皆说他弑父篡权,深恨之,救他何益?”
田承嗣道:“弑父一说纯是讹传。今去救驾,即是救史将军自身也。”
思明斜眼问道:“此话怎讲?”
“将军睿智,心知肚明,何须在下饶舌。”
思明冷冷一笑。他固然知道眼下战局看来不容自保。昨日已得报,唐廷九大节度使二十余万兵马正朝邺城围聚,而安庆绪近一年来召集的七、八万残兵败将又被郭子仪歼灭过半,眼看那小朝廷被催枯拉朽已成定局,再派兵去救,如同掷盐于水有去无回。但若不救,唐军取了邺城,调转枪头便直指范阳。他纵拥兵十三万,也难抵挡二十万重兵,何况其中还有几千回鹘悍骑。但此刻他无意说出心底话,只教众人议论。
座中史朝清早已按捺不住,指田承嗣道:“你休想搬动俺家一兵一卒!但念你也是一员骁将,劝你不如就此留在俺父帅麾下,还怕没有好大前程。”
其兄史朝义听着心中好笑。他也知道父亲断不肯与人火中取栗,但各军营尚有不少将士追念先帝,只恐果真一兵不发,遭人诟病无情无义,失了军心。本欲开口,又记起日前太原兵败后,父亲叱骂“再出狗头昏招,定斩不饶!”只得三缄其口。
却听大将周挚道:“邺城范阳形同唇齿,彼失守,则我暴露,不可不救。”
另一大将令狐彰也道:“与其坐等唐军乘胜来攻,不如我先行南下,伺机而动。”
先从安营来投的大将李归仁也附议:“死守范阳如同自缚手脚。善用兵者知游刃有余,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也。”
史思明耳听众将之议,心下飞快盘算:庆绪小儿已是行尸走肉,俺也早不甘于孺子阶下称臣,弃而自立之心已非一日,只是碍着“燕皇”之名分尚在,军中诸将对禄山仍怀尊崇,眼下不宜躁动而乱军心。听令狐之言甚合俺心,何不借着救援之名,引兵南下,坐观虎斗,以惑唐军,遮俺本意,伺机突袭……
思想至此,他嗽了嗽喉咙,正色道:“古圣贤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先皇与某情同手足,其子虽不肖,某仍念先皇恩义。如今邺城危在旦夕,焉有袖手之理。”说着走到议事厅中悬挂的地理图前,以手中马鞭指图,又道:“本帅已决,先遣李归仁将军率一万步骑随田将军南下,至邺城之北滏阳(河北磁县),屯兵以观,休急于与唐军接战。这里獾奴整顿大军,随父后行。豺奴仍留守范阳,广募奚族、同罗壮丁以充守备,谨防唐军趁虚来攻。”
诸将随思明指点圈画,聚睛于地理图之前,却无人在意安玉丹已不见身影。
一个时辰后,她现身城西张兴客栈,传与店主人口信:“史营将有大动,欲再作乱反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