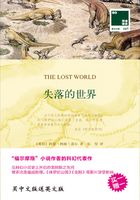
第3章 不可理喻的人
我朋友的担心或者说希望注定不能成为现实。当我周三前去拜访的时候,那封盖着肯辛顿西区邮戳的信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信封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字迹潦草得像铁丝网篱笆一样。信的内容如下:
恩摩尔公园,西区
先生,来信已如期收到。您在信中提到赞同我的观点,但我不知道这些观点是否需要您或其他什么人的赞同。关于我对达尔文主义这个话题的论述,您冒险使用了‘猜想’这个词,我必须要请您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这样的词语可以算得上某种冒犯。但从信的其他部分可以看出,您犯下这样的错误只是由于无知和笨拙,而非恶意,因此我愿意不予追究。您在信中引用了我演讲中的一句话,并且看样子理解起来有点困难。我本以为以正常人的智商不可能理解不了的,不过如果您真的需要进一步阐释的话,我会尽量克制自己对各种来访以及来访者的厌恶,同意于您提到的时间与您会面。至于您关于我修改自己观点的建议,我想提醒您我的观点一经提出,肯定已经是深思熟虑了,我没有再改的习惯。来访时请您将此信封出示给我的助手奥斯丁,因为他要负责为我挡住那些自称‘记者’的烦人的无赖。
此致
乔治·爱德华·查林杰
塔尔普·亨利早早过来听我冒险的结果如何,我将这封信读给他听。他只说了一句:“有点儿变化,外表光鲜了点儿,比山金车花还好看了呢。”有些人就是有这种超凡的幽默感。
我收到信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十点半了,我乘坐了一辆出租车,才得以及时赴约。车在一座豪华的房子前面停了下来,这座房子带有门廊,窗口被厚重的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这些迹象都表明这位令人敬畏的教授拥有着不小的财富。开门的人看上去外表古怪、肤色黝黑、老态龙钟,身穿黑色的飞行员夹克和棕色的长筒皮靴,从外表没法判断他的年龄。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司机,因为连续有几个管家辞职他才临时代理的。他那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有预约吗?”他问。
“有。”
“预约信带了吗?”
我拿出了信封。
“对!”看样子他认识不了几个字。我跟在他身后沿着通道走去。突然,一个小个子的女人从餐厅走出来,将我们拦了下来。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人,有着一双深色的眼睛,看样子不像英国人,倒更像个法国人。
“等一下,”她说,“奥斯丁,你在这儿等着吧。先生,您进来。我能不能问一下,您以前见过我丈夫吗?”
“没有,夫人,还未有幸。”
“那么,我要先向您道个歉。我必须要告诉您他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绝对不可理喻。我现在把这一情况提前告诉您,请您做好心理准备,希望您能谅解。”
“您真是太体贴了,夫人。”
“如果他有暴力倾向,您就赶紧出来。千万别跟他争执,已经有几个人因此受伤了。事后公众又会传得沸沸扬扬,这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希望您不是为了南美洲那件事来的吧?”
我没法向一位女士撒谎。
“天啊!那可是最危险的话题了。他说的话你一个字也不会相信的——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但是千万别跟他这么说,因为这样会让他非常狂暴的。您就假装相信,可能就没事了。您一定要记住,他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您最好不要提出异议,太诚实是不行的。再等的话他就要起疑了。如果您发现他有危险倾向——真正的危险——您就按铃,在我到达之前不要跟他冲突。就算在他最狂暴的时候我一般也能够制止他。”说完了这些鼓励的话,这位女士将我交给了那位沉默寡言的奥斯丁。
刚才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一直静静地等着,像一尊青铜的思想者雕像。现在,他带领我走到通道的尽头,在门上敲了一下。随着屋里传来一声牛吼一样的声音,我进了房间,见到了这位教授。
他坐在一张旋转椅上,面前是一张宽大的桌子,上面堆满了书籍、地图、图表之类的东西。我一进门,他就将椅子转过来面对着我。看到他的样子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虽然已经预见到这个人非同寻常,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还是被他表现出来的强悍个性震撼了。光是他的个头就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他身材粗壮,气势逼人。他拥有一颗巨大的头,几乎是我见过的人类最大的头了。如果把他头上那顶帽子摘下来扣到我的头上,那么肯定会将我整个头都扣住,帽檐直接落在我的肩膀上了。他面色红润,胡须颜色极黑,黑中似乎还带有点蓝色,像一把铲子一样垂在胸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亚述的公牛。他的发型怪异,一缕长长的卷发从他那巨大的额头上垂下来。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在乌黑的睫毛遮掩下发出了清澈、审慎而又专横的目光。他那两只长着又黑又长的汗毛的双手,宽大的肩膀和木桶一样的胸膛在桌面以上露出来。嗓音低沉而响亮。这就是我对查林杰教授的第一印象。
“怎么?”他极其傲慢地盯着我说,“什么事?”
我还不能马上公开我来访的真实目的,否则恐怕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能够有此机会与您见面真是不胜荣幸,先生。”我拿出信封,谦恭地说。
他把我的信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自己面前。
“哦,你就是那个连简单句子都看不懂的年轻人,对吧?你对我提出的结论持赞赏的态度,我理解的没错吧?”
“没错,先生,完全没错!”我特意加强了语气。
“老天啊!你的赞赏真是大大巩固了我的地位,不是吗?你的年龄,你的外貌,都使得你的支持有了成倍的价值。嗯,至少你比维也纳的那群猪要强多了,然而就算他们那嘈杂的哼哼声也比那些离群索居的英国猪显得彬彬有礼多了。”他一边作着比喻一边瞪眼看着我。
“看样子他们的行为比较可恶啊。”我说。
“负责任地说,我一个人就可以打赢这场战役,绝不需要你的怜悯。你就不要搅和进来了,先生,就让我一个人身处绝境吧。那样,乔治·爱德华·查林杰就最高兴了。好吧,先生,虽然你可能不会同意,但是我的厌烦已经超出了语言表达的范围,还是让我们尽量缩短这次会面的时间吧。你似乎想让我了解,关于我在论文中提出的观点,你有话要说。”
他的表达方式简直直接到了粗野的地步,这让我很难再继续回避下去。但是我必须再掩饰一会儿,尽量等待一个好点儿的机会,之前想的可能过于简单了。噢,我那爱尔兰人随机应变的能力啊,在我如此迫切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帮不了自己了吗?他那两道犀利的目光像钢针一样,似乎要将我刺穿。“说吧,说吧!”他用低沉的嗓音说着。
“当然了,我来这儿只是来求教的,”我笑着说,故意表现出愚蠢的样子,“除了诚心请教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了。同时,据我了解,在这件事情上您对维斯曼的态度有点苛刻。不是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地位日渐稳固吗?”
“什么证据?”他的语气很冷静,却又显得咄咄逼人。
“嗯,当然了,我知道这些算不上你所谓的确切证据。我想我可以这么说吧,我所指的只是一些现代思想潮流,以及较为普遍的科学观点。”
他身子朝前靠了靠,一副很认真在听的样子。
“我想你应该知道,”他一边端详着自己的手指一边说,“颅骨索引是一个不变因素吧?”
“那是自然,”我说。
“而先父遗传还尚未定论?”
“毫无疑问。”
“种质与单性卵不是一回事,知道吧?”
“当然了!”我大喊着,为自己的大胆感到有点得意。
“但是在这又能证明什么?”他转而用温和的语气问。
“啊,就是呢,”我小声嘟囔着,“这能证明什么呢?”
“那让我来告诉你好吗?”他亲切地说。
“荣幸之至。”
“这证明,”他突然一声怒吼,“你就是伦敦最可恨的骗子——一个卑鄙、龌龊的记者,写作方面不怎么样,科学知识就更别提了!”
他站起身来,眼睛里的怒火像是要喷出来了一样。即便是在那样紧张的时刻,我还是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惊讶不已的现象,这位教授个子很矮,他的头甚至都没有我的肩膀高——像一个没长开的大力神,那非凡的活力都用在大脑的发育、思想的深度和知识面的广度发展上了。
“胡扯!”他身子前倾,双手放在桌面上,头向前伸着,大喊一声,“小子,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那些科学知识,全都是胡扯!你是不是觉得凭你那榆木脑袋也配跟我耍滑?你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你这可恨的蹩脚文人,不是吗?你以为你的赞扬就能成就一个人,你的指责就能让他一败涂地吗?我们都得向你鞠躬,竭尽全力获得你的赞赏,是吗?这个受到你的抬举,那个受到你的训斥!鬼鬼祟祟的害虫,我认识你!你干得出格了。你耳朵失了聪,也丧失了主次观念。你这个自我膨胀、夸夸其谈的人!我要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没错,小子,你没有通过乔治·爱德华·查林杰的考验。现在还有一个人能管得住你,他警告你知难而退。但如果你还是要来,天知道你这么做是在冒多大的险。放弃吧,马龙先生,我劝你放弃吧!你是在玩一个相当危险的游戏,现在你已经输了。”
“看这儿,先生,”我一边说一边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但是也要有个底线,你不能侵犯我的人身安全。”
“我不能?”他咄咄逼人地慢慢向前走了几步,但是继而又停了下来,将手插进了他穿着的那件很孩子气的上衣侧兜里。“我已经把好几个像你这样的人赶出房子去了。你不是第四个就是第五个,平均每个值三英镑十五便士,很贵但又是必需的。现在,先生,你为什么不效仿你那些兄弟们呢?我觉得你必须那样。”他又继续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一边走一边指着自己的脚趾,姿势像个舞蹈教师,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我本想朝大门跑去,但又觉得那样未免也太丢脸了。况且,一丝正义的愤怒此刻像火焰一样在我的胸中燃起。我之前的行为确实有错,但是这个人的威胁反而将其纠正了。
“麻烦您别动手,先生。我受不了的。”
“天啊!”他冷笑了一下,那乌黑的胡须向上抬起了一点儿,一颗尖牙在嘴角闪出了一丝白光,“你受不了,是吗?”
“别做傻事,教授。”我大喊,“你希望怎么样?我体重十五英石(合二百一十磅),身体坚硬不亚于铁钉,每周六的比赛中都代表伦敦的爱尔兰人打中后卫。我不是那种人——”
就在这时,他朝我冲了过来。幸亏我提前打开了房门,不然我们两个人估计就直接把门撞破了。我们俩像转轮烟花一样一路从过道滚过去。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抓起了一把椅子,一起扑上了大街。我的嘴里满是他的胡须,两个人的身体紧紧互相缠绕着,胳膊也紧扣在一起,那几根可恶的椅子腿也跟我们的身体缠绕在一起。警觉的奥斯丁已经把大门打开了。我们两个人一个后空翻从门前的台阶滚了下去。我曾经在马戏团里见过两个人尝试过做这个动作,但是想要在不受伤的情况下做到似乎不太容易。椅子在我们身下碎成了碎片,而我们俩也滚到了排水沟里。他站起身来,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喘得像个哮喘病人。
“怕了吧?”他气喘吁吁地说。
“你这个该死的流氓!”我一边打起精神一边大叫。
他又冒出了嚣张的气焰,我们眼看又要打起来了,但我还算幸运,终于,救星出现了。刚好我们身边有一位警察,手里拿着记录本。
“怎么回事?你们应该感到羞愧。”警察说。这是我在恩摩尔公园听到的最理智的一句话了。“嗯?”他转向我,继续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攻击我。”我说。
“你攻击他了吗?”警察问。
教授大口喘着粗气,什么都没说。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警察摇了摇头,严肃地说,“上个月你也出了这样的事情。你打伤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你要指控他吗,先生?”
我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不,”我说,“不要。”
“为什么?”警察说。
“这事儿怪我自己,是我先冒犯他的,他警告过我了。”
警察“啪嗒”一声合上了记录本。
“别再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事了。”他又朝聚集过来看热闹的一名肉店伙计、一个女佣,还有一两个闲汉说,“好了,走了,走了!”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朝前走去,将这一小群人驱赶开来。教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目光里似乎暗含着某种诙谐幽默。
“进来!”他说,“我跟你还没完呢。”
他的语气里好像还是有些危险,但我还是跟在他身后进了屋子。他的男仆奥斯丁像个木偶一样,在我们身后将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