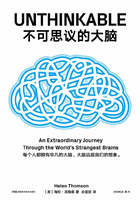
引言 大脑的神奇之旅
有些瞬间令人永生难忘,比如当我第一次看到人脑标本。它就摆在桌上,用来固定标本的福尔马林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久久挥之不去。
这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头颅,房间里总共有六个不同解剖断面的人脑标本。我面前的这个是从下颔骨下方切开,然后再沿鼻腔一分为二。看得出它生前属于一位年迈的绅士:额头上深深的皱纹仿佛在诉说主人漫长的一生。我绕着桌子细细端详,看到了大鼻子里探出的几根灰白鼻毛,一条不羁的眉毛和颧骨上方的一小块紫色瘀伤。而大脑就在这坚实的颅骨之中。
它灰中泛黄的色调和纹理不禁让人联想起一个闪闪发亮的焦糖布丁,尤其最外层就像是撒了一圈核桃碎。它凸凹有致,这里的一块像是碎肉,而背面的一块又像一颗干瘪的花椰菜。要不是严禁触摸,我真想用手指感受一下它光滑的轮廓。我尽可能地靠近它,想象这个大脑曾拥有过怎样的一生。我亲切地称它为克莱夫。
我一直热衷于了解人们的生活,也许这就是我大学期间痴迷于脑科学的原因。归根结底,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感受到的每件事,我们所经历或讲述的每个故事,都要归功于颅骨之中的这重达1.5千克的组织。
当然这个今天看来顺理成章的观点并非一直那么显而易见。在一部名为《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Edwin Smith Papyrus)的手稿中,古埃及人第一次提到“大脑”这个名词。他们写道,识别大脑的方法是“把手伸到内部的伤口,用手指轻弹感受它的颤动”[1]。很显然这是个不被重视的器官:如果头部受了伤,他们就在上面涂些膏油,然后测量病人的脉搏,“来检测他的心脏……以获取有用的信息”。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思维是存在于心脏而非大脑里,所以人死后,心脏会被妥善地处理并保存在体内,让亡灵得以顺利地转生,而大脑则通过鼻腔被一点点掏出来扔掉。
大约公元前400年,柏拉图认识到大脑才是不朽的灵魂的居所,之后这个理念逐渐在医学界受到重视。尽管柏拉图的理论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学者,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被说服。即使是柏拉图最器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坚信灵魂存在于心脏之中。当时的医生不倾向打开人的遗体,因为担心影响灵魂转生。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主要基于各种动物解剖:许多动物的大脑微乎其微,又怎么可能胜任如此重要的角色呢?
亚里士多德宣称,心脏扮演着理性灵魂的角色,为身体的其他部分提供生命。大脑只是一个冷却系统,调节心脏的“温度和沸腾程度”。[2]
(稍后我们会谈到,可能这两个人都是对的:如果没有心灵和大脑的彼此沟通,你就无法进行思考或感受。)
到了公元前322年,人们终于有机会进行人脑解剖。古希腊的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不再专注于灵魂的问题,而是展开了一系列基础生理研究。他们发现了从大脑到脊柱再延伸至身体各处的纤维网络——现在被我们称为神经系统。
然而,大脑真正成为故事的主角是在古罗马角斗士的竞技场中。因为古罗马律法禁止解剖人脑,身兼哲学家、医师和作家的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只能前往尘土飞扬的竞技场,通过治疗头破血流的角斗士来窥见大脑的解剖结构。
事实上,盖伦最有名的实验是猪的活体解剖。当着一群观众的面,他割开了连接着大脑和猪声带的咽神经,尖叫嘶吼的猪当场安静下来,令围观群众瞠目结舌。就这样,盖伦首次在公开场合向人们揭示出,操控我们行为的是大脑而非心脏。
盖伦还在人脑中发现了四个腔,后来被称为脑室。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脑室是脑内部充满脑脊液的一组腔隙结构,以保护大脑免受物理撞击和疾病侵扰。但在当时,盖伦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却被认为在这些脑室中悬浮着我们不朽的灵魂,它们被传递到“生物精气”中,再被输送到身体各处。当时的基督教会高度推崇这个理论,因为他们对人脑是灵魂的物质基础这一说法充满焦虑:如果灵魂存在于如此脆弱的肉体中,它如何能做到不朽?而灵魂存在于这些“虚无”的空间中听起来要合理多了。
盖伦的大脑学说统治了长达1500年,而宗教也一直鼓励人们继承发扬他的理论。举例来说,笛卡儿著名的理论主张:心与身体是分离的(现在称为“二元论”),心是非物质的且不服从物理定律,它通过松果体——大脑深处的一个小叶状区域,来发号施令。松果体会移动,并释放出某种特定的生物精气,来满足灵魂的需要。笛卡儿之所以要区分这两者,是为了驳斥当时那些“无信仰人士”,他们坚称灵魂不朽的说法需要有科学依据。
而到了17世纪,在英国牛津激烈的争论愈演愈烈。在这座大学城的小巷深处,一位名叫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的年轻医生正在准备一场手术。
当着众多解剖学家、哲学家和感兴趣的公众,他将一具尸体的躯干和大脑切开,为观众展示其复杂的解剖结构。由于得到了查理一世国王的特许,他可以解剖任何被处死的罪犯尸首。因此,他绘制了细致入微的人类大脑图谱,而且相传他已经“对开颅成瘾”了。[3]
正是从威利斯的手术开始,大脑是人类的标志这一概念才渐渐深入人心。他通过观察病人生活中的行为变化,将其与尸检过程中看到的病变联系起来。举例来说,他注意到一些后枕部痛的人,也就是靠近小脑的大脑区域,经常有心绞痛。为了证明这两者的关联,威利斯活体解剖了一条狗,钳住连接两个区域的神经,狗的心跳当即停止并瞬间死亡。威利斯后来还研究了大脑中的化学递质是如何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包括做梦、想象和记忆,这是一个他称之为“神经化学”的项目。
在19世纪,德国解剖学家弗朗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提出的脑功能定位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大脑的理解。他认为大脑由一个个隔室组成,每个隔室各司其职,比如有的负责诗词歌赋的天赋,有的则掌管着杀戮的本能。他还认为头骨的形状可以决定个性。加尔有位朋友眼球突出,而且他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语言天赋,他就认定负责这些功能的脑区位于眼睛后方,而正是由于这些区域太大导致眼球鼓出来。尽管后来颅相学被证明是伪科学,但加尔关于大脑机能定位的理念是具有前瞻性的,他甚至对有些区域的功能进行了正确的解读。例如,他认为“欢愉的器官”在前额眼睛的正上方。后来有神经科医生刺激这个区域,果然可以令病人开怀大笑。
加尔的观测法标志着几百年来的形而上研究的结束,终于迎来了脑科学的新时代。不久之后,人们渐渐接受了原子和电子的概念,脑科学也告别了过去的“生物精气”学说。神经不再是一根根满足灵魂需要的空心管道,而是一群可以产生电信号的细胞。
到了19世纪,科学家们开始流行用电极刺激来定位各个脑区的功能(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些区域显然是一个主要因素),而20世纪中叶的科学家开始更多关注各个脑区之间是如何交流沟通的。他们发现在解释复杂行为时,不同脑区之间的交流方式比任何一个单独区域的活动有着更重要的作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脑电图和CAT三维断层扫描使我们能够看到大脑的精细结构,甚至可以研究大脑在高速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活动。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现在已知,在头颅中颤动着的重达三斤的组织有180个不同的区域。而我在布里斯托大学的解剖学室中,想要详细深入地了解每个区域。
面对眼前的克莱夫,我可以直接看到人脑中最明显的区域——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是大脑的最外层结构,它被分成两个几乎相同的半球。我们一般将每个半球划分为四大区域(脑叶),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大脑功能。当你摸额头时,手指触碰的那个脑区被称为额叶,它的作用是帮我们做出决策,控制情绪,并帮助我们理解他人。它赋予了我们各种性格特质:我们的雄心壮志,我们的远见卓识,还有我们的道德准则。用手指继续沿着头侧摸到耳朵,你会找到颞叶,它能让我们理解词汇和言语的含义以及识别人脸。手指从这里向上一直到头顶,你就到达了顶叶,这个区域负责我们的很多感受功能和某些语言功能。最后沿着后脑勺下去就是枕叶,它的主要职责是视觉处理。
在这个大脑的后面还有一团小小的花椰菜状的“小脑袋”。这就是小脑,它对我们的协调、运动和姿势至关重要。最后,如果轻轻撬开两个半球(有点像掰开桃子露出桃核儿),你就会看到脑干,这个区域是我们用来控制呼吸和心跳的;以及丘脑,它作为一个宏大的中转站负责传递各个脑区之间的信息。
大脑中充满了被称为神经元的细胞,不过它们太小而无法直接用肉眼看到。这些神经元就像老式电话的电线一样,以电脉冲的形式将信息从大脑的一侧传递到另一侧。神经元像树上的枝条一样形成许多分杈,每一个都与相邻的神经元形成连接。这些连接的数目如此庞大,如果你每秒钟数一个,那么需要300万年才能数完。
现在人们认识到,我们每时每刻的思维都是由这些神经元的某一种实体状态决定的。正是在这混沌之中,产生了我们的情绪,塑造了我们的个性,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这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已知的最神奇和复杂的现象之一。
所以它会出各种问题也不足为奇。
杰克(Jack)和贝弗利·维格斯(Beverly Wilgus)是老照片的爱好者,他们记不清自己是如何找到这张19世纪的老照片的。照片上是个英俊但有残疾的男人,他们猜想他握着的棍子是鱼叉的一部分,称他为“捕鲸者”。男人的左眼瞎了,所以他们编了一个故事,他在和一头愤怒的鲸鱼搏斗中失去了那只眼睛,而眼睑被缝了起来。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不是鱼叉,而是一根铁棍,而这张照片是目前人们已知的唯一一张关于费尼斯·盖奇(Phineas Gage)的肖像照。
1848年,25岁的盖奇正在铁路床上工作,当时身后的东西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就在他回头去看的过程中,他用来灌装炸药粉末的铁棍撞到了一块石头上,产生的火花引爆了炸药。铁棍从他的左下脸颊刺入,穿越左眼后方,再由额头上方另一侧的头顶穿出脑壳。虽然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自此性格大变,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盖奇了。曾经乐观善良的那个小伙子变得咄咄逼人、粗鲁无礼,常常不分场合地谩骂。
阿朗索·克莱蒙斯(Alonzo Clemons)小时候摔倒在浴室地板上,头部因而遭受了重创。由于严重的后遗症,他学习困难,智商低下,还有读写障碍。但自此以后,他表现出了惊人的雕塑天赋。只需要看上两眼,他就能用手边的任何材料——橡皮泥、肥皂、焦油,就地取材塑造出一个完美的动物模型。他的病情被诊断为获得性学者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而复杂的疾病,患者一般是在头部受到创伤之后出现了超凡的音乐、记忆或艺术才能。
而被学术界代称为SM的患者,即使在枪口下和两次被刀威胁的时候也毫不畏惧,事实上她根本没有能力体验“恐惧”这种情绪。因为一种叫作类脂蛋白沉积症(Ubach-Weithe)的罕见病,她的杏仁核逐渐钙化了。这个杏仁状的区域位于大脑深处,负责人类的恐惧反应。由于没有恐惧感,好奇的天性让她会不假思索地去触摸毒蜘蛛;她与抢劫犯对话时也对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顾忌;即使在花园里发现致命的毒蛇时,她也直接把它们捡起来丢掉。
当我大学毕业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正是由于这些不幸的事故、非常规的手术、各种疾病和遗传突变,才让我们认识到大脑的不同区域是如何分工的。盖奇的案例告诉我们性格和前额叶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像克莱蒙斯这样的学者综合症患者推动了我们对创造力的理解。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仍然在尝试让SM感到害怕,以此研究如何帮助那些患有恐惧症的人们。正是这些不同寻常的特殊大脑让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大脑,这真是太令人着迷了。
在不久之前,一个人的大脑只要有些异常就会直接被关进疯人院。仅仅在过去的200年,人们才开始使用心理疾病这个术语;在那以前,任何不寻常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中邪,而原因可能是被诅咒,或“被恶魔附身”,或“体液失调”了。[4]如果“中邪”的你住在英国,很可能就被送到著名的疯人院伯利恒(Bethlem),比如麦克·杰伊(Mike Jay)的书《如此疯狂》(This Way Madness Lies)中就描写了其中的情况。在18世纪伯利恒还是一家老式的疯人院,到了19世纪转型为精神病人收容救治所,现在成为21世纪精神病医院的范本。[5]
这所医院在不同时期的定位,反映了社会在治疗大脑疾病上的根本性转变。伯利恒刚成立时,主要职能是防止这些“失心疯”的病人在外面乱跑。病人们大都患有暴力倾向和妄想症,失忆失语,失去理智,和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流浪汉、乞丐和盗贼。
患者接受统一治疗,包括放血、冷水淋浴、吃用来清肠的催吐药,因为人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体质。这种看法直到国王乔治三世的疯癫才有所改变。当时乔治因为肠胃里有寄生虫而得病,很快就开始口吐白沫,神智不清。有治愈这种疾病美誉的牧师弗朗西·斯威利斯(Francis Willis)很快被传唤过来。他的方法简单直接:他让乔治下地干活,吃饱穿暖,锻炼身体,并鼓励他保持积极的情绪。过了3个月,乔治的精神健康与身体症状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从此,医学界也开始认识到发疯是可以被治愈的。到了19世纪,越来越多的救治收容所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人们对大脑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当然,在进步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紧身束衣依然屡见不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许多疗法都非常野蛮。但医生们开始考虑患者的家庭如何参与治疗,病人如何与外界建立互动,以及哪些药物可能有助于缓解疼痛和焦虑。到了20世纪初期,“精神错乱”被重新命名为“精神疾病”,医生们开始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理基础。正如托马斯·威利斯当年预言的那样,人们开始研究到底是大脑内部的何种变化引起了那些不正常的行为和观感。
现在我们认识到,所谓精神疾病或者说是精神非正常,可能是由于脑部的电信号异常、激素失衡、病变、肿瘤或遗传突变引起的,有的我们可以治疗,有的我们还不能治疗,还有的我们已经不再认为是疾病了。
当然我们距离解读大脑还很远,事实上,我们对所谓“高级”功能——记忆、决策、创造力和意识——的理解都还远远不够。比如,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乒乓球让任何人出现幻视(稍后我会告诉你如何做到),但我们还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见的幻觉。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特殊大脑为我们理解所谓“正常”大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些事迹揭示出我们大脑还有惊人的潜力以待开发,说明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甚至令我们质疑自己的大脑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正常。
在获得神经生物学的学位后,我决定成为一名科学记者。我认为这是理解新奇而神秘的大脑运作方式的最佳渠道,同时还让我有机会了解人们的生活和讲好一个故事。我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读了科学传播学的硕士,后来成为《新科学家》杂志的新闻编辑。
现在,作为一名自由记者,我为包括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和卫报在内的一些媒体撰稿。但不论做什么样的健康专栏,我始终放不下这些不可思议大脑的事迹。我参加过许多关于神经病学的研究会议,如饥似渴地阅读科学论文,甚至收集了很多医学怪谈杂志,只因为其中一两篇讲述了非同一般的大脑的故事。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更让我痴迷了。
不过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件易事。18世纪和19世纪的医生们会用生动形象的笔墨来描述他们病人的生活,但这种传记体的案例研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的病例是客观的、冰冷的和去个性化的。病人只能用名字的字母缩写来代称,他们的个性标签已经被抹去,他们的生平丝毫不被提及。这些特殊大脑的主人们,作为神经病学的研究对象,在科学问题面前变得无足轻重。
一天晚上在办公室加班时,我偶然看到一篇与众不同的文章。它描述了一种奇怪的症状,首次发现于1878年美国缅因州的深山老林里。美国神经学家乔治·米勒·比尔德(George Miller Beard)受邀去调查当地的一小群伐木工人,他们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折磨着。比尔德的发现非常惊人:在这群人中,有几个后来被他称为“缅因的跳跳法国人”。只需要一个简短的口令,跳跳人就会无条件地服从并不断地重复下去。让他扔飞刀他就扔飞刀,让他跳舞他就跳舞。
第二页的照片和病历描述一样神奇,上面是一个得病的女人。照片是在她家里拍的,她正跳起来,腿还悬在半空中。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发表在科学论文杂志上的案例实拍照片。
在伐木的淡季,工人们会去旅馆工作,于是比尔德在森林里住了几周,又跟着去了旅馆。他与这些人的朋友和家人交谈,在文章里会提及他们的爱好,他们的感情纠葛。他尝试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以此来更好地认识他们的大脑。最终他成功地讲述了这样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我看着文中的照片,不禁想象要是我也尝试这样做会怎样呢。我能够像比尔德一样去面对面采访这些不寻常的大脑和他们周围的人,从而揭示出人脑的独特之处吗?
我想起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要想真正理解一个人,理解他的内心,你需要抛开成见,在一旁静静地观察他们是如何生活、思考和追求自己的理想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重大发现。
我再次浏览堆在我面前的厚厚一摞文件——这是我十年来收集的各种不同寻常大脑的学术报道,大多数案例都是以名字的首字母缩写、年龄和性别来代称的。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桌上拿起来放在地板上一一摆开,坐在那儿一口气读了几个小时。这些奇怪的事件就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普通人身上,他们之后又将度过怎么样的人生呢?我不禁浮想联翩。还有,这些人会同意我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吗?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走遍世界各地,寻访那些有着不寻常大脑的人们。虽然他们都见过很多医生和研究人员,参与过各种测试、脑成像扫描和精神分析,但他们几乎没有公开谈论过自己的个人生活。当然,萨克斯(Sacks)写了一系列这种类型的书,其中最有名的是他1985年出版的《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在这本书中,他将他的案例调查报告称为“探索未知领域的神奇之旅”。[6]他写道,没有这些人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世界在他们眼中竟是这样的存在。
我想现在是时候再次开展这样的调查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30年来神经科学的革命性进展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出现了哪些新领域。我还想做一些萨克斯没做过的事,我想将这些故事跟病理和神经学研究完全隔绝开来,我想把他们视为朋友,尝试着深入了解他们的世界;问那些科学家们避而不谈的问题,听听他们童年的故事,他们如何找到人生的真爱,他们又是怎么带着与众不同的思维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和探索的。我想知道他们的生活到底和我的有多大区别,想知道我们人类的大脑到底能够有多么不可思议。
这段奇妙之旅始于美国,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过目不忘的电视制片人和一个在家里也会迷路的女人。在英国,我拜访了一位老师,她觉得自己的记忆不属于自己;我也采访了一个有前科的男人一家,他在一夜之间性格大变。我飞越亚欧大陆,去见了一个变成老虎的男人,一个永远生活在幻觉中的女人和一个能看到不存在色彩的年轻记者;还有,格雷姆,一个认为自己在三年前已经死去的男人。
他们之中,有些受访者会和自己奇特的大脑坦然相处,有些则一直把它们当作秘密隐藏起来。这一路上,我还遇到不少边缘学科研究者,他们试图揭开现实的本质,神迹和启示的存在,人类记忆的极限,等等。接近旅途的尾声时我遇到了一位医生,他的大脑是如此非凡,以至于改变了我对人类的定义。
在旅程开始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最终能否理解他们每个人在世上的独特经历;然而当我最后把他们的人生故事一一呈现出来时,我认识到我们能够以此绘制一个大脑的流程图,而且是对我们每个人都适用的。通过这些故事,我认识到大脑是如何施展它的魔力,以一种出乎意料,甚至可以说是精妙绝伦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人生的。与此同时,这些故事也告诉我们如何伪造一段永久记忆,如何避免迷路,以及死亡是怎样一种体验。他们还教会我如何能瞬间让自己快乐起来,如何能引起幻觉,如何做出更好的决定。我还学会了如何长出幻肢,如何看到更真实的现实世界,甚至如何确认自己还活着。
而这一切变化是何时发生的,我并不确定。也许是从我开始看到那些不存在的人开始,或者是在我知道怎样听到自己眼球转动的声音时。我可以确定的是,从暴风雪的波士顿到尘土飞扬的阿布扎比骆驼竞技场,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在了解世上那些不寻常的大脑,更是在了解自己大脑深处的秘密。
这些故事有的发生在最近,有的则发生在几个世纪以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旅程吧,不过不是在21世纪,而是回到古希腊的一场宴会上,在可怕的灾难即将发生的前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