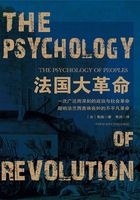
第四章 革命大众的心理
一、大众的一般特征
无论革命的起因是什么,除非它已经渗透到群众的灵魂当中,否则它就不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代表了大众心理的一个结果。
虽然我在另外一本著作中已经详尽研究过了集体心理,但在这里我还是有必要再重述一下它的主要法则。
个人在作为大众的一员而存在时,具有某些与他在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时迥然相异的特征,他有意识的个性将会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淹没。
个体身上产生的大众心理并不一定需要实质性的接触,由某些特定事件激发的共同的激情和情绪,通常就足以实现。
集体心理在瞬间就可以形成,它表现为一种非常特殊的集合,其主要特征在于它完全受一些无意识的因素控制,并服从于一种独特的集体逻辑。
在群众具有的另一些特征中,我们应当注意这一点,那就是他们很容易轻信,对事物过于敏感,常常缺乏远见,对理性的影响不能做出反应。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几乎就是说服他们的唯一手段,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群众可能相信任何事情,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群众极其敏感,所以他们的情绪——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总是夸张。这种夸张在革命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哪怕是一点小小的刺激都可能导致他们采取最狂暴的行动。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轻信就已经十分严重,更何况在革命时期,那只能够变本加厉;痴人说梦般的呓语都会让他们信以为真。阿瑟·扬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在克莱蒙附近的水泉处游历。走到半路,他的向导被一群人挡住了去路。原来他们也不知是听信了谁的谣言,竟认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来这里准备引爆小镇的。当时,到处流传那些关于王室的可怕谣言,最后王室简直被说成是盗尸者和吸血鬼的巢穴。
诸如此类的特征表明,群体中的个人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已经堕落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层次。他变成了一个野蛮人,带有野蛮人的一切性情和缺陷,有着突如其来的狂暴、热情和英雄主义。就智力而言,群众是无法与单个人相比的;但是,就道德和感情而言,群众则可能要略胜一筹。群众很容易犯下罪行,就像他们很容易自我克制一样。
个人的特性在群体中很快就会消失,群体对个人施加的影响相当大:吝啬鬼变得慷慨大方;怀疑论者成了信徒;最诚实的人成了罪犯;懦夫也可以变成勇士,诸如此类的转变在大革命期间比比皆是,屡见不鲜。
作为陪审团或是国会中的一员,“集体人”做出的判决或颁布的法律,都是他在个体状态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在集体的影响下,作为集体组成部分的个人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后果之一就在于他们的感情和意志的同质化。
这种心理上的同质化赋予了群众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
一个精神上的统一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群体中的态度和行为极富感染力,仇恨、狂怒或热爱之类的情感在叫嚣声中很快就会得到支持,并反复强化。
这些共同的情感与意志源自哪里呢?它们通过感染而传播,但在这种感染发生作用之前肯定要有一个出发点。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将会寸步难行。
要想解释我们大革命中的诸多因素,要想理解革命议会的种种行为及其单个成员的转变,我们就必须具备大众心理的知识,了解它的规律。由于受到集体无意识力量的推动,群众常常说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因此往往投票赞成了他们原本不赞同的那些动议。
虽然集体心理的定律有时会被一些高明的政治家凭借直觉识破,但政府部门中的大部分人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些定律。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这些定律,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赶下了台。我们看到,有些政府居然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颠覆——路易·菲利普的君主政体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这的确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实际上这都是忽视集体心理的结果,其危险是显而易见的。1848年,法国的军队足以保护国王,但当时的法军统帅显然没有理解允许群众与他的军队混在一起意味着什么。结果,军队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竟然不知所措,最后弃之不顾。他不知道,因为群众对威信极为敏感,所以实力的展示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起到威慑作用,当时这样的展示可以立即镇压反对派的示威。同时,他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集会都应该立即驱散。所有这些教训都已经被历史经验验证,但在1848年,它们都被忽视了。在大革命时期,能够理解大众心理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二、民族精神的稳定性如何限制大众心理的摇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一个民族比作一个群体,这一群体具有某种特性,但这些特性的变动要受到民族精神或民族心理的限制。民族精神具有一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群众的短暂心理不具备的。
当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它的传统精神之后,群众的精神就会由此得到控制。
一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于群众,还在于民族是由一些利害好恶各不相同的群体聚集而成的;而严格意义上的群众——比如说,一次群众性集会——则包含了各种各样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个人。
一个民族有时似乎像群众一样易变,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它的易变性、热情、狂暴和毁灭性背后,民族精神还保持着极为顽强和保守的本能。大革命及其后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保守精神是如何最终战胜破坏精神的,人们打破了一个又一个政府体系,然后又一个接一个地将它们恢复。
民族心理,也就是种族心理,并不像大众心理那样容易发生变化。对民族心理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比较缓慢——比如杂志、会议、演讲、书籍等,而说服的原则也不外乎标题中已经给出的那些,诸如断言、重复、声望和感染等等。
精神的传染可能会迅速蔓延到整个民族,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一个群体传递给另一个群体。宗教改革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法国传播的。
一个民族远不像群众那样容易激动,但有一些事件——比如国家的耻辱、面临侵略的威胁等,可能会立即唤醒整个民族。这种现象在大革命时期屡屡发生,尤其是当布伦瑞克公爵公布他那篇傲慢无礼的宣言时,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当公爵以武力相威胁时,他对法兰西民族的心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布伦瑞克公爵的这一举动不仅是极大损害了路易十六的事业,而且也是引火烧身,他的干涉激起了全法国人民的愤怒,他们迅速组成一支义勇军开赴战场。
这种整个民族同仇敌忾情绪的突然爆发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可以见到。当拿破仑决定大举入侵西班牙和俄罗斯时,他就低估了这种热情可能迸发的力量。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瓦解乌合之众的肤浅心理,但在历史悠久的民族精神面前却常常变得束手无策。俄国的农民显然是一群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天生粗野狭隘,而一旦他们得知拿破仑入侵的消息,就像立即变了个人似的。只要我们读一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写的一封信,我们就会信服这一事实。
王后还向她的母亲讲述了这样两个故事,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对俄罗斯人顽强的抵抗精神有所了解。
对于大众心理的诸种特征,我们必须指出,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免不了迷信神秘主义。人们总是对那些非同寻常的存在——如神祇、政府或伟大人物——确信不移,并相信他们拥有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事物的神奇力量。这种神秘主义心理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崇拜的强烈需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教义,人们必须有一个崇拜的对象。这就是人们受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时会企盼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的原因。
同群众一样,整个民族也容易对于一个对象发生由崇拜到憎恨的转变,不过这一过程比较缓慢。一个人在某一段时期里可能被视为民族英雄,但最后又被人们诅咒,任何一个时代的大众对政治人物的态度都可能发生逆转,克伦威尔生前死后的荣辱变幻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例子。[5]
三、革命运动中领袖的作用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任何一种类型的群众——无论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无论是议会、民族,还是俱乐部等等,只要还没有出现一位领袖来领导他们,他们就无法实现团结,采取共同的行动。
在其他地方,我已经通过某些生理学上的实验来证明,群众的无意识集体心理与领袖的心理密切相关。领袖赋予群众一个单一的意志,并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
领袖尤其喜欢通过暗示来影响群众,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激发这种暗示的方式。有许多实验可以证明一个集体对暗示可能服从到何种程度。[6]
在领袖们暗示的作用下,群众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镇静或狂怒,罪恶或英勇,这些暗示有时候也可能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但也仅仅是表面上合乎理性。事实上,群众很难服从理性;唯一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就是以想象的形式激发的情感。
群众在不同领袖的刺激下,很容易做出截然对立的冲动之举,这样的事情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上不胜枚举。我们看到,群众对于吉伦特派、埃贝尔派、丹东派以及恐怖主义者的相继胜利和倒台,无一不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同时也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群众对于这些走马灯似的事变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一无所知。
从远处看,我们只能够对这些领袖扮演的角色有朦朦胧胧的认识,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在幕后操纵。如果想深入领会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必须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研究,这时我们就会看到,领袖们煽动一场极为激烈的群众运动是何等容易。在这里,我们不考虑邮电工人罢工或铁路工人罢工之类的小事件,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可能起作用的仅仅是其雇员的不满,而群众对它们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少数几个社会主义领袖是如何在巴黎平民当中挑起一场群众骚乱的。那是费雷尔在西班牙被处以死刑后的第二天,虽然法国民众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费雷尔这个人,在西班牙,他的死刑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但在巴黎,少数几个领袖就足以煽动一支民兵冲向西班牙大使馆,并打算焚毁它;政府因此不得不派出一部分卫戍部队来保护大使馆。虽然这些攻击者被有效击退了,但他们还是洗劫了一些商店,并设置了一些路障,然后扬长而去。
无独有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有力证明了领袖们的巨大影响。最后,这些领袖意识到焚烧外国使馆可能非常危险。于是,第二天他们又改变策略,代之以和平的示威运动。就像起初他们接受指令发动暴乱一样,现在群众又忠实地服从新的命令。没有什么事例比这更能够显示领袖的极端重要性以及群众的温顺驯服了。
那些历史学家们,从米什莱到奥拉尔,都认为革命大众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照样能够行动自如;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理解革命大众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