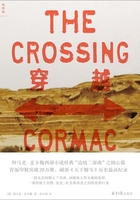
父子俩又骑上了马。他们越过了眼前的这片低地,又骑进了那头的一片林子,跟随着牛畜的足迹沿着沟谷边骑着。比利又转头看了看那两只乌鸦,片刻间它们已经跳下树,又悄悄地飞回牛尸上去。
父亲在这个山口下方埋设下第一个捕兽夹。他们知道这狼是从这儿经过的。比利坐在马上看着父亲把一片小牛皮毛面朝下扔在地上,下马踏脚在上面,把背篓也放在上面。
父亲从背篓里拿出鹿皮手套戴上,取出一把铲子在地上挖了一个坑,他把两爪钩放进去,随着把连在一起的铁链子也放进去盖住爪钩,然后用土埋好。其后他又在旁边照着捕兽器的形状挖了一个浅坑。他把捕兽器放进去试了试大小,又挖大了一些。他把挖出来的土放一些在木制筛盒里,把铲子放在一边,从篓子里取出一副C形夹钳,用它拧紧兽夹的长长的弹簧板,打开颌形夹具。他拿起兽夹,注视着饵盘上的凹口,然后又退回一扣螺丝,调整了一下板柄(启动杆)。朝阳透过树枝把花花的影子投在他的背上。他蹲在那里,把兽夹举在眼前,对着早晨的晴空仔细察看着,就像是在校正一些古老而又精致的仪器,如观察天象的星盘或六分仪等。又像是一个人弯着腰,以某种方式在世界上为自己定位一样,此人正专心埋首,通过弧和弦的关系来测定周围世界和本身存在之间的距离,如果真有这个距离,如果它是可知的。他把一只手放在张开的颌形夹具下方,用大拇指把饵盘稍稍翘起一点。
“我们不想让这夹子离松鼠出没的地方太近,”他说,“但是已经很近了。”
一切检查好了,他松开C形夹钳,把兽夹放入坑中。他用一张蘸过熔蜡的方形纸盖住夹子的颌形夹具和饵盘,用筛盒小心地把泥土筛回到这张纸上,又用铲子把一些腐殖土和木屑轻轻地撒在上面。然后他蹲在旁边仔细察看,直到一切都伪装完好。最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埃科尔斯的一瓶专门用来做饵料的波欣酒,打开软木塞,伸进一节小树枝蘸了一下,把这小枝插入距兽夹一尺的地方。然后,用木塞堵好瓶子,放进衣袋里。
父亲站起身把背篓递给儿子,自己弯下腰把那张小牛皮带土叠起来,然后把脚插进马镫里,骑上去,再弯下腰把那张小牛皮拉到鞍谷上,让马退了两步,再欣赏一遍布设的陷夹。
“你觉得你能自己埋夹子了吧?”父亲问儿子。
“是的,爸爸。我觉得能行。”
父亲点着头。“过去埃科尔斯会把马蹄上钉的U形铁拔下来,然后他会把他自己做的牛皮套鞋包到马蹄上去。这样可以不留马蹄印,免得狼起疑心。奥利佛告诉我,他能不下马就埋设兽夹,就坐在马上弄。”
“那他是怎么弄的呢?”
“我也不知道。”
比利坐在马上,双手托着背篓,背篓架在膝盖上。
“把它背上,”父亲说,“如果你想自己去埋夹子的话,你得学会背着。”
“是的,爸爸。”
到中午时分他们已经又埋了三副兽夹。人饥马乏,他们便选了在克洛弗代尔上游的一丛黑皮橡树下吃午饭。他们双腿盘坐,胳膊肘斜倚在大腿上,吃着三明治。他们的眼光越过山谷,看到瓜达卢普山,向东南方又看到了山脉的横岭。那里,云海的阴影正缓缓移动着盖住宽阔的阿尼马斯山谷。再往前,在蔚蓝色的远方,就是墨西哥的群山。
“您觉得我们能抓到它吗?”儿子问。
“要是抓不到它,我就不会来了。”父亲答道。
“要是它以前被抓住过,或者它以前见过这些夹子怎么办?”
“那样,抓它就难了。”
“我觉得我们这里没有狼,狼都是从墨西哥跑过来的,对吗?”
“也许是吧。”
吃完饭,父亲将包装三明治的纸袋折叠起来并塞进口袋。
“你吃好了吧?”他问儿子。
“好了,爸爸。”
当他们父子二人骑回自家那块地,骑进马厩时,他们离家已经十三个小时,都已经疲惫不堪,骑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最后的两个小时是在黑地里骑行,到家时,整个房子除了厨房外都黑了。
“快去吃晚饭吧。”父亲心疼儿子。
“我没事儿,爸爸。”
“快去吧,我来拴马。”
这只母狼在西经约108度30分处穿越了墨西哥与美国的国境线,然后又横穿了国境线以北一英里处印第安部落领地的一条旧路,沿着怀特沃特溪向西进入了圣路易斯山脉,再向北跑到阿尼马斯山脉,穿过阿尼马斯山谷,一直跑进佩伦西洛山。它的臀部有一个很大的疤痕,那是它的同伴两星期以前在索诺拉山的某一个地方给它留下的。那只公狼咬了它是因为它不肯离开。公狼的一只前脚被捕兽器夹住,血迹斑斑,挣脱不得。母狼距拴兽夹的铁链只有几步远,但无计可施。公狼自知厄运来临,末日已到,便向母狼嗥叫着,赶它离开,以保一命。但母狼放倒双耳悲鸣着,就是不肯离开。就这样,两只狼各自带着伤,淌着血,僵持了一夜。到了早晨,猎人们骑马远远地来了。母狼只好一跛一拐地跑开,在一百多码之外的一个山坡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去迎接黎明的死亡。
它在马德拉谢拉山岭的东山坡上游荡了一个星期。它的祖先们曾经在这片地面上追杀过大如骆驼、中如原始小型马一类的动物,但如今它在这里几乎无物可食。几乎所有的猎物都被赶尽杀绝;几乎所有的林木都被砍伐,填进了矿山捣矿机的庞大锅炉。千百年来,狼在这个山野里大肆追杀、捕食牛畜,但这类畜生的愚昧无能始终令它们迷惑不解。这些牛畜喋血惨叫,蹒跚而行,拖着它们宽大的四蹄和无尽的困窘,满山遍野地凄哞。它们悲吼着,在泥泞或深雪中挣扎,在绝望中冲过了栅栏,身后拖带着缠连的栏杆和铁篱。牧人们说,这些凶狠蹂躏牛畜的做法是他们从未对任何野兽做过的。好像这些懦牛在它们心里激起了莫名的愤怒,好像这些懦牛因违反了某种古老的规律、古老的典仪、古老的礼节而冒犯了它们一样。
它蹚过巴维斯匹河继续北上。此时它已经怀有身孕,肚子里拖着第一胎的幼仔们。但它还不知道它所处的困境。它现在离开这个地带北移,不是因为这里已经没了猎物,而是为了找到狼的同类,它太需要和它们在一起了。当它在新墨西哥州佩伦西洛山的福斯特谷口扑倒那头小牛的时候,它已经有两个星期除了动物的腐肉之外没有吃过别的什么了。它现在一副困惑忧愁的样子,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见到同类的踪影。它吃了睡,睡了再吃。它一直吃到肚子大得拖地。但它现在决不走回头路,它也不再回头打扫吃剩的猎物[7],它不愿在白日里越过公路或铁道,它更不会在同一个地方两次从一个铁篱下面钻过去。这些都成为新规矩,是过去从来未有过的限制,但现在都存在了。
它向西漫游,进入了亚利桑那州的科奇斯县。它越过了骷髅溪的南分岔水再向西跑到饥饿谷的谷头,又向南跑到猪谷泉,然后它又折回东边,跑到克兰顿沟和福斯特沟之间的高地。夜间,它喜欢跑下阿尼马斯平原去驱赶野羚羊,欣赏它们在自己激起的尘灰中如洪水般奔流、幽灵般旋转的景象,这些尘灰从远处看上去就像是盆地里冒出的一串串狼烟;它喜欢欣赏它们四肢关节的精巧结合及它们轻盈头颅的惊慌摇动;它还喜欢欣赏它们或聚或散的奔跑队形。它也在搜索着它们之中任何可以沦为它的猎物的弱者。
这个季节,正是母鹿怀仔的时节。但通常它们会在分娩期远远未到的时候流产,流下这还未睁过眼便永远长眠的不幸胎儿。已经有两次,它发现这种苍白、娇嫩的流产鹿胎儿。胎体还是温热的,被丢弃在地上,歪着脑袋,张着小口仿佛在呆视着什么东西。这未成熟的鹿胎儿在黎明的料峭中冻得浑身乳青,几乎通体透明,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里误投过来的一个生命。这些令人怜惜的胎儿无知无觉地死在雪地里,被饥兽当作鲜美的早餐吞噬着。它连这些鹿胎儿的嫩骨都吃得干干净净。在日出之前,它离开了平原,走到山里去,它十分孤独、苦闷,心中有无数的烦恼和忧伤要排遣、发泄。于是它站上一块大岩石,抬起头,俯瞰着暗沉沉的山谷,在这可怕的寂寥和寂寞中一通通地嗥叫……要不是突然嗅到了布莱克峰西侧山口的下面有狼的味道,它几乎要离开这个地区了。它立即停住了脚步,好似撞到了一堵墙上。
它朝着发出气味的地方跑去,跑到了埋兽夹的地点。它围着这个点转圈子,足足有半个小时,它分辨着这里各种各样的气味,小心地把它们各自所代表的主体和动作归理、联系起来,竭力去重塑不久前在这里发生过的事件。它被上次同伴的蒙难弄得心有余悸,十分谨慎,想到应当多看几个地方。于是它找到了三十六个小时前埋夹人骑马留下的足迹,穿出这个山口,向南跟行。
到晚间时分,它已经发现了全部八个埋设的捕兽器。它还是选择回到了发现头一个兽夹的山坳。它先绕着埋兽夹的地方转了几圈并发出哀叫,仿佛是在为遇难的同伴追悼一般。然后,它便开始刨地。它用两爪在紧靠夹子的地方刨洞,洞壁的泥土崩落后便发现了捕夹上的颌形夹钳。它盯着看了一会儿,又继续在夹子周围刨坑,当它离开时,整个夹子完全暴露出来了,只有中心部分遮盖着饵盘的蜡纸上还残留着一撮泥土——它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这个部分——上次的悲惨事件还记忆犹新。第二天早上,比利和父亲骑马经过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裸出地面的夹具。父亲从马上下来,仍然落脚到那张小牛皮上。他仔细观察这套夹具。比利坐在马背上看着。父亲又重新埋设了这套兽夹。他站起身来,满含疑惑地摇了摇头。他们又检查了全线其他的埋夹。次日早上他们再次来看时,那套兽夹又被刨出,另外有四套也被掀开了。他们用其中的三套在这条路线上又埋设了更为隐蔽的夹子。
“有什么办法能不叫牛踩到夹子上去呢?”儿子问。
“没有什么办法。”父亲答道。
三天以后,他们发现又一头小牛被吃。五天以后,他们埋设的一个隐蔽夹被挖出,而且弹簧被扳起,这个夹子翻倒在一边。
晚间,他们父子又去了SK Bar牧场去找桑德斯先生。大家围坐在厨房里向老人讲述了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老人边听边点头。
“埃科尔斯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抓狼就像抓孩子一样难,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比我们更聪明,而是因为它们一心就想着怎么去逃脱。我跟着他去过一两次。他总是把兽夹埋放在不像是野兽要跑过的地方,我问他为什么要埋在那个地方,多半时候他也回答不出。”
父子们又一起去了那小木屋,又取了六套捕夹带回家去煮洗。第二天早上,母亲到厨房准备早饭时,博伊德正坐在地上往兽夹里打蜡呢。
“你是不是想,这样做爸爸就不会把你给晾在家里了?”母亲问。
“我没想。”博伊德耷拉着脑袋答道。
“那你那张脸要板多久?”母亲有点忧心。
“我又没板脸。”儿子不承认。
“他也是像你一样倔强。”母亲指着父亲。
“那我们都麻烦呗!”儿子气呼呼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