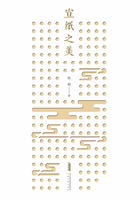
2. 纸的历程
在探究宣纸的奥秘和沿脉的过程中,诸多历史的空白让人常常叹喟:自古以来文人墨客总是习惯于将视线对外,喜欢对世事人生摹写咏叹,对于手中的书写工具与载体却懒得理会,以致纸笔本身的沿脉一片空蒙。这实在是辜负了纸张自身的价值,辜负了过去的时光,也辜负了诗意的起源。
中国文字,一开始的书写载体,是具有神灵意味的牛胛骨,以及具有神灵意味的龟甲。在早期的中国人看来,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有资格安放文字。因为,文字是神圣的,也是有灵魂的。随后,文字依托雄伟典雅的青铜器,依托纪念碑似的建筑,既镌刻在各种礼器之上,也镌刻在瓦当、玺印、石鼓、石碑,以及山水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甲骨文也好,铭文、崖刻也好,都是字字千钧。即使是竹简和木简,在世人看来,也有着不可随便修改的性质。文字落于其上,便有斧劈刀砍的坚硬。中国自商朝完备的史官制度,就如实记录天子的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臣子奏事,国君回复,每一句话都必须记录在简牍上。这其实是以文字的不朽来约束权力。史官的记录,帝王是不能御览的,更不能随便改动。史官很有骨气,不畏死,也不屈服。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仲和叔继续如实记载,也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的第三个弟弟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齐庄公之死写成暴病而死吧!”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将他释放。季走出来,正遇到史官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季会被杀,也准备慷慨赴死。中国古代知识人如此壮怀激烈地对待史乘,这是对文字的尊重,更是对神灵的敬畏。
纸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使得文字摆脱了沉重,摆脱了权力的控制,变得实用、随意,不再带有斧劈刀砍的坚硬。与龟甲、青铜和竹简相比,纸轻盈而柔软,易腐又易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似乎神灵盘桓的成分也要少很多。不过由于传统和习惯,人们依旧对纸上的文字怀有某种敬畏。在纸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敢用带字的纸做不敬的事,更不敢用其如厕。凡废弃的带字的纸,也要求放于火炉中烧毁。不过从整体上看,人对于纸,不再像面对甲骨那样谦卑,也不再像面对简牍那样敬畏,相互之间的关系趋于平和、平等而松弛。这种状况更具现代意义,可以视为一种觉醒,也可视为一种进步。在纸上,汉字不再带有斧凿刀刻的沉重和笨拙,而是与水融合,与墨融合,与人的性与命融合。
纸张就这样慢慢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工艺水平,让纸更平整、更润滑、更柔顺、更轻薄、更细腻,一直是造纸工匠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在长期的实践中,造纸的技艺和手段,从总体上来说,慢慢固定为几个不可或缺的步骤:一、锉,把造纸的原料切短碾碎;二、煮,把锉过的原料蒸煮,分解纤维间的粘结物质;三、捣,把原料放入石臼中舂捣,使纤维帚化;四、搅,将捣碎的原料放入水池,加入水及悬浮剂后不断搅动;五、抄,用苫,即现在的帘,将水中的纸浆抄起。这个过程,也可以归纳为浸湿—切碎—洗涤—舂捣—打浆—抄纸—晒纸—揭纸。这当中,工艺最复杂,也最难掌握的,是抄的技术。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发明了一种相对快捷的新模具———帘,即捞纸浆的竹筛,要求在舀起时前后摇晃过滤。纸浆均匀覆盖模具后,将之沥水后倾覆———一张薄薄的纸就产生了。后来,人们又尝试着在纸上涂上一层蜡,降低纸的吸水性,使之更适合书写。
造纸术发明之后,造纸业进步飞速,各地的纸层出不穷,一场漫长的角逐随即开始。一段时间里,简牍、绢帛与麻纸三分天下,都可以作为文字的载体。纸张很快呈现出优势,其中的原因,除了轻盈、便捷、快速之外,还有纸张对书写状况的改变———毛笔在纸上书写的愉悦感,使得书写由一场艰辛的劳作,变成了相对愉快的创造。随着工艺的不断进步、原料的不断开发,纸张很快占据半壁江山,又很快遥遥领先。
晋之时,书写材料发生很大变化,由于生产的纸张越来越好用,人们慢慢抛弃和远离昂贵的绢帛、笨重的简牍,选择在纸上写字。可是那时候的纸与绢帛相比仍有致命的弱点,最主要的是易潮和虫蛀。易潮的问题还好解决,只要远离潮湿之地,保持干燥,避免让水侵蚀即可。虫蛀这件事就比较棘手——— 一般只要放一段时间,纸张就容易从内部生长虫豸,这一问题严重阻碍纸张的发展。人们一直尝试采取各种办法,比如在纸浆中掺入能够杀死虫豸,或者让虫豸讨厌的植物。从总体上说,在纸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绢帛的地位要高于纸,因为绢帛防水也防虫,更有利于贮存。
魏晋时出现了染纸术,纸有了不同的颜色。道家葛洪曾用黄檗染色,发明了最早的染色加工纸———黄麻纸。葛洪如此做,其实是阴差阳错,本意是想利用黄檗的杀虫性能,制造一种能防虫的纸,没有想到的是,黄檗汁的加入使纸变得漂亮光滑。相比于麻纸,这种加入黄檗汁的黄麻纸更受书写者欢迎。随后,染纸技术逐渐成熟,或先潢后写,或先写后潢。王羲之、王献之都爱用黄纸写字,他们的很多书法作品,都是用黄纸写就的。像王羲之的《姨母帖》就是写在硬黄纸上的。
魏晋南北朝时,各地纸坊层出不穷,有官办的,有民办的。官办纸坊由朝廷和官府纳入建制,生产纸张。民办纸坊往往跟官府合作,民间生产,官府收购。各地依据自然植被特点,就地取材造纸。北方以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及山西、山东、河北为中心,主要生产麻纸、楮皮纸、桑皮纸。东晋南渡后,会稽、安徽南部、建业(今江苏南京)、扬州、广州等地,依靠各地的材料,陆续成为造纸中心。东南的一些地方开始生产竹纸。葛洪《抱朴子》云:“逍遥竹素,寄情玄毫。”这“竹素”就是竹纸。用竹造纸,让南方大片竹林有了用武之地。以竹子为原料生产出的纸,优点是既轻又薄,光滑洁白;缺点是纸张太脆,容易破损。就这样,各地纸张的产量、质量或加工都有很大提升,原料不断扩大,工艺不断进步,生产的纸越来越平整、洁白、光滑、方正、细腻。南北朝人萧察《咏纸诗》云:“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宣情且记事,宁同鱼网时。”由此可见一斑。
那时候南方各地的纸张加工还出现了施胶技术。早期施胶剂是植物淀粉,或刷在纸面上,或掺入纸浆中。如此处理,可以改善纸浆的悬浮性,降低纸的透水性。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写本《律藏初分》所用的纸,就用了施胶技术处理。砑光技术也随之出现,就是用胶黏剂将白色矿物细粉均匀涂刷在纸面上,再用卵形、元宝形或弧形的石块碾压或摩擦,这样可以增加纸表的洁白度和平滑度,减少透光度,使纸表紧密,吸墨性好。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文书纸及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所用的纸,都用了这项技术,比欧洲早一千四百多年。
东晋末年,权臣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诏书虽寥寥二十几个字,却有石破天惊的历史意义,意味着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简牍、绢帛和纸并存的局面不再,在三者的拉锯战中,相对年轻的纸大获全胜,纸的时代正式到来。
隋唐时期是中国纸张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纸质材料和用品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大规模抄经和佛传绘画活动对纸的需求量很大,促进了南北各地造纸业的发展。各地官办和民办的造纸作坊,在纸浆性能、造纸设备等方面不断取得进步,纸的尺幅越来越大,纸面也越来越平整。从总体上来说,麻纸仍是当时的主流,官府的诏令、表等,皆用白麻纸;民间抄写,也用白麻纸;至于寺庙写经,则喜用黄麻纸。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保存的大量纸本经卷和画作,大部分是用麻纸抄写的。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虞世南摹王羲之《兰亭集序》天历本,以及杜牧大和三年(829)的书法作品《张好好诗》,使用的都是麻纸。
纸张质量提高明显,防虫技术却一直裹足不前。唐朝时,朝廷下令造纸商在制作政务文件所用纸张时,要加入从喜林芋花蕊中提取的毒素,以防止纸张被虫鼠咬食。唐代一些名贵纸张,比如黄蜡笺,也就是硬黄纸,就是加入了天然黄檗汁防虫蛀,又均匀涂蜡,经过砑光形成的熟纸,人们经常用这种纸写经和摹写古帖。因为虫蛀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凡是贵重的书画、典册,都尽量避免使用纸,虽然绢帛的价格更高。
中唐之后,由于纸张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麻类植物经常不能保证需求,以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皮纸大量出现。最为普遍的,是用楮皮、桑皮造纸。以楮皮为主要原料生产的皮纸,不仅产量大,且相对于麻纸,更细腻坚韧,适合书写,慢慢成为主流。
那个时候,各地都有意识地探索造纸原料,有一些地方利用瑞香皮、木芙蓉皮、竹子造纸,也有一些地方,比如浙江嵊州,利用当地特产藤皮造纸。藤皮产于剡溪沿岸,用其造纸,更白净、轻薄、柔韧、细腻、润滑,不滞笔,为当时的书画者所喜欢。可是藤纸的产量较小,原料有限,很难大批量生产。唐人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一文,描述了由于藤皮需求量过大,古藤被不分季节地砍伐,“绝尽生意”的现象。公元6世纪,官方的诏书一般用藤纸,书画家更喜欢用桑皮纸或者竹纸,因为其吸墨性更强,有柔边和模糊效果,能够凸显中国山水画的朦胧美。


有观点以为,舒元舆《悲剡溪古藤文》写到的藤条造纸,其实就是青檀,只是冠以藤的名称而已。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那么,宣纸的历史又有了新的佐证。消失的古藤条纸,也可以从宣纸中找到一丝安慰。
纸的天空也好,宣纸的天空也好,就这样飘逸着不确定的云彩,它们像一个个无法追究的梦,也如星星点点的历史碎片。中唐之后,熟纸制作蔚然成风。所谓熟纸,其实是生纸的再加工。生纸是直接从纸槽抄出,经烘干而成的未加工处理过的原纸;熟纸则通过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施胶等,让纸张变得平滑和精致,更易于书写,更适合绘画。唐代绘画讲究布局,重视细致的笔法,具有工笔写实的特点,在熟纸上呈现效果更好。中唐之后,社会普遍崇尚个性化的纸张,从朝廷到个人,都喜欢尝试以各种方法加工生纸,也探索了一些新办法,比如相对成熟的施蜡法和施胶法:用淀粉剂、动物明胶以及植物胶,也就是松香胶等做施胶剂,加入明矾作为沉淀剂,涂于纸上,阻塞纸面纤维间的毛细孔,以保证在创作白描、工笔设色花鸟以及人物时,不至于走墨而晕染,颜料也不会扩散和渗透。
唐末之时,具有个性的高级信笺很受欢迎。当时稍有名气的文人都愿意定制个性化的信笺,甚至有人自己动手,生产加工有特色的信笺,成就了一段段诗情画意的佳话。唐元和四年(809),隐居在成都郊外百花潭的女诗人薛涛,见到了慕名来访的年轻才子、来蜀公干的监察御史元稹,两人一见钟情。时人王建有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薛涛是年41岁,美人迟暮,风韵犹存;元稹是名扬天下的才子,如日中天,倜傥风流。薛涛爱慕元稹的年轻与才华,元稹则喜欢对方空谷幽兰般的清丽与体贴,两个人整日流连于锦江畔,相伴于蜀山麓,度过了最美好的三月时光。薛涛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池上双鸟》等诗,“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诗句柔情似水,人物风情万种。之后,元稹调离川地,任职洛阳。朝朝暮暮的日子,一下子变成劳燕分飞。为了飞雁传书的浓情,薛涛取宅旁浣花溪水,以芙蓉、鸡冠花等为原料,对书信所用纸张进行了再加工:摘下各种鲜花的花瓣,淘洗晾干,将花瓣捣成泥,加上清水和胶质,涂抹在纸上,再用手绘和洒金,成功地制作成芳香美丽的深红小笺,称为“浣花笺”,也称为“薛涛笺”。纸笺上的每一个字,都如一瓣落英,携有暗香,泛着温情,像春天的纸鸢般飞过去。这种美好的感觉,颇似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枕草子》一书中一次又一次地描述的与写信有关的情愫,以纸为寄,以纸为媒,以纸为信。可一切还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薛涛的朝思暮想、幽怨渴盼戛然而止,成为流传千古的名诗《春望词》: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
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
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
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
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
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
五代之后,以楮皮为主要原料的皮纸渐渐显出优势,麻纸全面衰落,只有北方和西南的一些地方仍在生产。楮皮纸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楮树面积广,生长快,在楮皮产量上有保证。以楮皮制造的纸张,质地平滑坚韧、洁净柔软,既用来书写绘画,也以之实用。纸张的制作工艺仍在改进,人们多在纸浆中加入明矾等沉淀剂,使纸张质地更加饱满和明亮,且不洇墨。随着熟皮纸质量的提高,纸张渐渐应用到绘画上,取代绢帛,成为绘画的主要材料。
宋朝是纸本绘画较为兴盛的时期,有大量绘画开始在纸上呈现。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赵昌的《写生蛱蝶图》、毛益的《牧牛图》、法常的《水墨写生图》均为楮皮纸本,其中《维摩演教图》纸质匀细平滑,为当时上乘楮皮纸。至于苏轼的《三马图赞》,用的是上等桑皮纸。北宋的很多法帖,诸如米芾的《苕溪诗帖》《韩马帖》、苏轼的《人来得书帖》,还有李建中的《贵宅帖》、赵佶的《夏日诗帖》等,也是用的楮皮纸。这些皮纸洁白干净,表面光滑受墨,纤维交织均匀,少有束结,细帘条纹异常清晰。
宋朝造纸工艺进步,还体现为纸张尺幅增大,可以造出巨幅的匹纸。匹纸长三丈有余,中无接缝,为当时书画师创作巨幅绘画提供了理想材料。宋徽宗赵佶,就曾在长1172厘米、宽31.5厘米的巨幅描金云龙笺上,用狂草写就《千字文》,一气呵成,奔放流畅,颇为壮观。
在宋时的南方,皮纸和麻纸是主流,有作坊继续尝试用竹子和稻麦秸秆造纸。宋时的竹纸,产地主要是东南的浙江、福建和广东,工艺相比东晋隋唐时的竹纸有了很大进步,含纤维较多,经过砑光加工,表面平滑,颜色淡黄,看起来很精致。有人开始尝试用质地不错的竹纸写字画画。有记载,王安石喜欢将竹纸制成小幅,用以写诗和写信。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记载:“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从记载中可以看出,竹纸易破损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米芾晚年曾在竹纸上创作了一幅著名的《珊瑚帖》,从北宋至今仍保存完好,时间跨度九百多年,由此可以看出竹纸的质量。米芾在《评纸帖》里认为,越州竹纸的质量,超过了著名的杭州由拳纸(剡藤纸)。南宋之时,竹纸质量更好,越来越多的书画家开始在竹纸上写字画画。南宋人陈槱在《负暄野录》卷下提到竹纸的特性:“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宋之时,还有人用竹纸临摹了王羲之的《雨后帖》以及王献之的《中秋帖》。
竹纸的大量生产,对于造纸术来说是一次飞跃。之前造纸,原料大多为枝梢的韧皮。竹纸制作,原料不仅仅是竹子的枝梢,茎秆也被一并拉入,这就扩大了纸张的产量,降低了纸张的成本。之后以稻麦秸秆为原料,应是受到竹纸的启发。稻麦秸秆的加入,为明清以青檀皮加稻草为原料的宣纸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打下了基础。


北宋 · 李公麟 维摩演教图


北宋 · 赵昌 写生蛱蝶图

北宋 · 米蒂 珊瑚帖
每一个写在纸上的字,都可以被视为以萤火虫般的光亮,照亮黑漆漆的道路。纸,就这样载着星光,一路走来,走得辛苦,走得艰难,走得缓慢。在白天和夜晚,每时每刻都有无数蘸着墨汁的笔尖在纸上疾走,它们叠加记忆,释放情怀,也放飞梦想。纸,是布满星辰日月的天空,是和煦温润的春风,更是孕育生机的大地。纸,像源源不断的河流,奔腾而下,孕育和催生无限生机。在河流两岸,有陶渊明的“桃花源”,有谢灵运的山水诗,有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有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李清照的梧桐雨,有辛弃疾的“灯火阑珊处”,更有绵延万里的长卷《富春山居图》……打个比方,纸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飞毯一样,载着中国文化飞行;也像道路,让世界文明开启了漫漫征程。历史和文化的浩瀚记忆,就这样纷然落下,如飞流的瀑布,如浩渺的云雾,如呼啸而去的舟船。很难想象的是,如果没有纸,文化的记忆何在?个体的心灵历程如何触摸和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