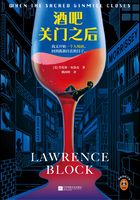
第2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
那是1975年夏天,就更广阔的背景而言,记忆中那年夏天似乎没发生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尼克松辞职是一年前,一年后是两党集会、各种运动、奥运会和两百年国庆。
彼时主宰白宫的是福特,他的政绩不能说特别耀眼,但至少还算令人心安。格雷西大厦的主人名叫亚伯·比姆,尽管我从没觉得他真心相信自己是纽约市长,正如杰里·福特从没相信过自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
。
在这段时间里,福特拒绝帮纽约度过财政危机,《每日新闻》的标题是:“福特对市政府说:去死吧!”
我记得这个标题,但不记得它出现在那年夏天之前、之中还是之后。我读过这篇文章。我很少会错过《每日新闻》,不是在半夜回旅馆的路上买一份晨间版,就是在吃早饭时扫一眼午间版。我时不时也读《纽约时报》,要是有我关心的事件,我往往还会在下午买一份《邮报》。我几乎不关注国际新闻和政治消息,或者说除了体育新闻和当地犯罪版,其他我都不怎么看,不过我对世界大事也算略知一二,说来好笑,我对这些事的记忆消失得还真是彻底。
我到底记得什么呢?哦,莫里西酒吧被抢后三个月,辛辛那提队要和红袜队打七场系列赛了。这个我记得,菲斯克在第六场打出本垒打,彼得·罗斯从头到尾表现得好像全人类的命运都取决于他投出的每一个球。纽约的两支球队都没能打进季后赛,但除此之外我也没法告诉你具体战况了,我只知道我去看了五六场比赛。我带我的孩子们去了两次谢亚球场,另外几次是和朋友们去的。那年纽约体育场在翻修,因此,大都会队和扬基队都在谢亚打比赛。我记得我和比利·基根去看扬基队打某个球队时,比赛中途暂停,因为有几个白痴朝场内扔垃圾。
雷吉·杰克逊那年为扬基队打球吗?1973年他还在奥克兰为查理·芬利效力,我记得那年的系列赛,大都会队输得一塌糊涂。但斯泰因布里纳是哪年把他买到扬基队的来着?
还有什么?拳击?
那年夏天阿里打比赛了吗?我在闭路电视上看过他和诺顿打的第二场,阿里离场时下腭骨折,不战而胜,但那至少是一年前的事了,对吧?后来我近距离见过阿里,在麦迪逊花园的拳台边。厄尼·谢弗斯对吉米·埃利斯,谢弗斯第一回合刚开始就打得对手不省人事。老天在上,打昏埃利斯的那一拳我记得太清楚了,他老婆和我隔着两排座位,我记得她脸上的表情,但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不是1975年,这个我敢确定。那年夏天我肯定去看了拳击,但到底看了谁的比赛呢?
重要吗?我觉得并不重要。假如重要,我可以去图书馆查《时报索引》,或者直接找一本那年的《世界年鉴》。不过那些一定要记住的事情,我反正都记得挺清楚。
斯基普·德沃和汤米·蒂拉里。想到1975年夏天,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他们的脸。我和他俩厮混了那一整个季节。
他们是我的朋友吗?
是,但程度有限。他们是我的酒友。我很少会见到他们,除了去陌生人扎堆喝烈酒的那种地方——不过那段日子我本来也不怎么见人。当然了,那会儿我还在喝酒,而且酒精对我的坏处(至少看起来)还没超过对我的帮助。
几年前,我的世界像是有了自己的意志,一天天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下了哥伦布圆环以南和以西的几个街区。我抛弃了十二年的婚姻和两个孩子,从长岛的赛奥西特搬进我现在住的旅馆,它在西57街上,位于第八和第九大道之间。差不多同一时期,我离开了纽约市警察局,我在那儿尽心尽力的年份和混吃等死的日子几乎一样多。我能养活自己,不定期地寄支票去赛奥西特,靠的是替人办事。我不是私家侦探——私家侦探要有执照、提交报告和按时报税。我只是给朋友帮忙,他们用钱报答我,我总能交上房租,也总有钱买醉,隔三岔五还可以寄张支票给安妮塔和儿子们。
如我所说,我的世界从地理上变得狭小,那个区域也主要局限于我睡觉的房间和我醒着时度过大部分时光的酒吧。这些酒吧也包括莫里西那儿,但我去的并不频繁。我通常一两点上床睡觉,有时候混到酒吧关门才回家,去深夜酒吧熬通宵的次数屈指可数。
这些酒吧之中还有凯蒂小姐,也就是斯基普·德沃那儿;还有波莉笼子,它和我住的旅馆在同一个街区,贴着红色植绒墙布,常客以下班后的人群为主,到晚上十点或十点半就开始散场了;还有麦戈文酒吧,狭窄的店堂毫无生气,顶灯不装灯罩,客人连一个字都不说——我上午心情不好时,偶尔会进去飞快地喝一杯,酒保斟酒的手常常抖个不停。
同一个街区还有两家靠在一起的法国餐厅。一家叫圣米歇尔山,座位永远空着四分之三。几年来我请不同的女人去那儿吃过几次饭,偶尔也会进吧台喝杯酒。他们隔壁的餐厅名声很好,生意也更兴隆,但我从来没进去过。
第十大道有个叫斯雷特餐厅的地方,那儿有很多中城北区和约翰·杰伊大学分局的警察,我有时候情绪上来,想和这种人打打交道,就去那儿吃饭。他们的牛排非常好,环境也很舒适。百老汇大街60街路口有一家马丁酒吧,酒卖得便宜,保温熟食台上的腌牛肉和汉堡也很好;他们的吧台顶上有一台大彩电,是个看球赛的好去处。
林肯中心对面有一家奥尼尔吧龙——那时候有一条古老的法律还没作废,法律规定禁止给营业场所起名叫“沙龙”,奥尼尔家定做霓虹灯时不知道这个规定,于是他们改掉了一个字,说去他的就叫这个了。下午我偶尔会去晃一圈,但他们到夜里就太时髦也太欢腾了。还有安塔列斯与斯派罗酒吧,这个希腊人待的地方开在第九大道57街路口。它算不上我喜欢去的那种地方,许多胡须茂密的男人都在痛饮茴香酒,不过我每天夜里回家时都会经过那儿,有时候也会进去飞快地喝一杯。
第八大道57街路口有个不打烊的报刊亭。我通常在那儿买报纸,400熟食店门口的人行道上有个流浪女人叫卖报纸,我有时候也会买她的。她以每份两毛五的价钱从报刊亭买报(那年所有报纸似乎都卖两毛五,除了《新闻报》卖两毛),然后以相同的价钱出售,真是一条艰难的谋生之路。有时候我会给她一块钱,说不用找了。她叫玛丽·爱丽丝·雷德菲尔德,但直到几年后她被人捅死时,我才知道这个名字。
有一家咖啡馆叫红色火焰,当然还有400熟食店。有两家过得去的比萨小店,还有一家店卖芝士牛排,从来没有回头客。
有一家意大利面馆叫拉尔夫餐厅,还有两家中餐馆。有一家泰国馆子让斯基普·德沃痴迷不已。58街上有一家乔伊·法雷尔餐厅,他们去年冬天刚开业。哦,还有,那附近有的是能喝酒的去处。
大多数时候我在阿姆斯特朗酒吧。
我的天,我就住在那儿。我回旅馆睡觉,也会去其他的酒吧和餐馆,但那几年,吉米·阿姆斯特朗酒吧就是我的家。要找我的人都知道该去那儿找我,有时候他们会先打电话到阿姆斯特朗,然后再打到旅馆。那地方上午十一点左右开门,白天是个叫丹尼斯的菲律宾小子守吧台。晚上七点,比利·基根来接班,两点、三点甚至四点打烊,具体几点取决于客人的数量和他的心情。(这是工作日的排班。周末白天和晚上是另外几个酒保,他们的营业额要高得多。)
女招待来来去去。她们找到演出的工作,和男朋友分手,找到新男友,搬家去洛杉矶或者回苏福尔斯城的家,和厨房的多尼米加小子干架,因为偷窃被开除或者自己辞职,或者怀孕。那年夏天吉米本人很少出现。我记得那一年他正在北卡罗来纳州物色地产。
我该怎么形容这个地方呢?你从大门进来,右手边是个长吧台,左手边摆着桌子,桌上铺着蓝色格子桌布。深色的护墙板上挂着照片,还有镶了框的旧杂志里的广告。最里面的墙上挂着一个与环境格格不入的鹿头,我最喜欢的桌子就在那东西底下,因为坐在那里我就看不见它了。
客人五花八门。有街对面罗斯福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有福特汉姆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有电视台人员——CBS在一个街区外,ABC也没几步路,还有附近居民和左邻右舍的店主。有几位古典音乐人,一名作家,还有一对黎巴嫩兄弟,他们刚开了一家鞋店。
年轻人不多。我刚搬到这附近时,阿姆斯特朗店里有一台点唱机,爵士乐和乡村布鲁斯的曲目相当可心,但吉米很快就撤掉了点唱机,换成立体声音响,放起了古典乐磁带。这样能赶走比较年轻的顾客群体,女招待也很高兴,她们讨厌年轻人,因为他们待得晚、点单少而且几乎不给小费。这样还能降低噪声,让店里更适合长时间慢慢喝酒。
我去那儿就是为了这个。我想保持微醺的感觉,但不想喝醉,只是偶尔酩酊一场。大多数时候我用咖啡兑波本威士忌,晚上行将结束时换成纯烈酒。我在那儿能读报,能点汉堡包,也能点全套大餐,要是有兴趣聊天,无论是长篇大论还是搭两句话也都有人聊。我不是每天都从早待到晚,但很少会有一天连一次门都不进,有时候丹尼斯开门才几分钟我就来了,到比利准备打烊时我还没走。每个人都得有个去处嘛。
酒友。
我在阿姆斯特朗那儿认识了汤米·蒂拉里。他是常客,一般七天里会出现三四天。我不记得我第一次是怎么注意到他的了,但和他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你很难不注意到他的存在。他块头很大,嗓门也不太能压得住。他不算很吵,但几杯酒下肚,他的声音就会充满店堂。
他很能吃牛肉,很能喝芝华士威士忌,两者都体现在他那张脸上。他应该快四十五岁了,下巴堆了一层又一层,面颊上坏死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
我一直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叫他“硬汉汤米”。也许斯基普说得对,也许这个绰号就是为了讽刺他。大家叫他“汤米电话”是因为他的工作。他做电话销售,在华尔街附近的一家野鸡交易所通过电话推销投资机会。我知道混那一行的人换工作就像换衣服。能够通过电话哄骗陌生人拿出真金白银投资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天赋,其拥有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工作,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雇主。
那年夏天,汤米在一家名叫坦纳希尔公司的机构工作,销售房地产联合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股份。按照我的理解,买这东西在税务上有好处,而且有望得到资本收益。我是根据推理得出这个结论的,因为汤米从不向我和酒吧里的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有一次罗斯福医院的一名产科住院医生向他询问他销售的东西,汤米东拉西扯打发了他。
“不,我是认真的,”医生坚持道,“我总算挣了点钱,应该考虑这种事情了。”
汤米耸耸肩。“有名片吗?”医生说没有,“那就找张纸写下你的号码,还有什么时候打给你比较好。你想被灌迷魂汤,我就打给你,仔仔细细说给你听。不过我先警告你一声,我在电话里那叫一个所向披靡。”
两周后,他们又遇上了,住院医生埋怨汤米怎么不打电话给他。
“天哪,我一直想打来着,”汤米说,“让我记一下,回头就打。”
他是个过得去的伙伴。他喜欢说方言笑话,而且说得相当好,该笑的时候我会捧场。里面有些笑话很下作,但一般来说没有恶意。当我情绪上来了,想缅怀一下我的警察生涯时,他也是个不错的倾听者,要是我讲个有趣的故事,他会笑得分外响亮。
他嘛,总的来说,有点太吵,也有点太欢乐。他的话有点太多,而且会惹得你坐立不安。如我所说,他每周会有三四个晚上出现在阿姆斯特朗店里,差不多一半时间里,她会陪着他。卡罗琳·齐特汉姆,加罗林岛的那个卡罗琳,说话带着柔和的南方口音,就像某些烹饪用的香草,但泡在酒精里就会变得劲头十足。有时候她挽着他走进店里;有时候他先到,她后来。她住在附近,和汤米是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我猜——要是我愿意费神去想的话——是办公室恋情把汤米带进了阿姆斯特朗酒吧的门。
他关注运动项目。他会向一名赌注登记人下注——以球类比赛为主,有时也赌马——要是赢钱了,他保证会让你知道。他有点太友好,有点太自来熟,但他眼睛里偶尔会闪过寒光,这会抵消声音里的友好。他有一双冰冷的小眼睛,嘴唇四周有一团软肉,那是个弱点,但这些都不会影响他的声音。
你明白他为什么擅长打电话了吧。
斯基普·德沃的本名是亚瑟,但我只听见过博比·罗斯兰德这么称呼他。博比可以叫他亚瑟。他们从四年级起就是朋友了,他们在杰克逊高地的同一个街区长大。斯基普的教名是小亚瑟,他很早就有了“斯基普”这个绰号。“因为他那时候总是逃学 。”博比说,但斯基普的说法不一样。
。”博比说,但斯基普的说法不一样。
“我有个舅舅当过海军,一直放不下这个身份,”斯基普有一次对我说,“他是我母亲的兄弟,给我买水手服、玩具船。我有一整个舰队,他叫我船长 ,很快其他人也跟着叫了。这还不算倒霉呢。我们班上有个小子,人人都叫他虫仔。别问我为什么。估计现在别人还这么叫他。”
,很快其他人也跟着叫了。这还不算倒霉呢。我们班上有个小子,人人都叫他虫仔。别问我为什么。估计现在别人还这么叫他。”
他三十四五岁,和我差不多高,但比我瘦,也比我壮。他前臂和手背上青筋明显,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肉,皮肤随着骨头高低起伏,让他的面颊深邃得像是雕刻出来的。他有个鹰钩鼻,蓝眼睛目光灼灼,在合适的光线下,蓝中稍微带点绿。所有这些,再加上自信和满不在乎的举止,都让他很受女性的欢迎,只要他想要女人,他费不了什么事就能找个姑娘带回家。但他一个人住,不和任何人保持稳定的关系,而且似乎更愿意和男人混在一起。他曾经和某个女人同居过,甚至有可能结了婚,但他几年前结束了那段关系,从此就不愿再和其他人牵涉太深了。
汤米·蒂拉里的绰号叫“硬汉汤米”,他的举止里确实带点硬汉气质。斯基普·德沃则确实是条硬汉,但你必须看透表面才能觉察到。他的硬不是摆给你看的。
他参过军,不是你以为的海军,尽管他舅舅应该会这样培养他,他参加的是陆军特种部队,就是戴绿色贝雷帽的那个。他高中毕业就应征入伍,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被派往东南亚。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某一天退伍,去念大学,但中途退学,然后去了上东区的一家单身汉酒吧守吧台。几年后,他和约翰·卡萨比安把积蓄加起来,盘下一家歇业的五金店,签了个长期租约,用剩下的钱重新装修,开了他们的凯蒂小姐。
我偶尔会在他自己的地方见到他,但更多时候是在阿姆斯特朗酒吧,他只要不当班就经常来这儿坐坐。他是个令人愉快的好伙伴,很好相处,也没多少事情能让他皱眉头。
但他有点特别之处,我认为可能是某种冷静而无所不能的气质。你会觉得他有能力处理他遇到的任何问题,而且连一滴汗都不会出。你会觉得他是个能办事的人,而且能在行动中快速做出决定。也许是因为他戴着绿色贝雷帽去过越南,因此得到了这种气质,也可能是我知道他有过这段经历,因此赋予了他这个光环。
这种气质往往出现在我见过的罪犯身上。我知道几个重量级劫匪有这种气质,他们专门抢银行和武装押运车。还有个给运输公司开长途车的司机也是这个德行。他提前从西海岸回到家里,发现老婆和情人正在床上,于是徒手杀掉了这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