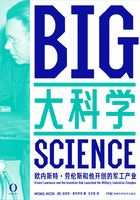
引言:创造与毁灭
2012年7月4日,两个国际科学团队共同宣布,借助于地球上最复杂的研究机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他们发现了被称为“希格斯玻色子”的基本粒子。近半个世纪以来,或者说自从它的存在于1964年被提出以来,希格斯玻色子一直是物理学家重点寻找的目标。当时人们是将它作为赋予宇宙中物质质量的一种场的载体提出的,现在人们终于在对撞机上找到了它。
作为LHC的建设者和所有者,位于瑞士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总部为此举行了计划中的新闻发布会。这一消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物理学界高层的目光。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彼时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这位曾预言存在这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粒子的英国物理学家,像其他贵宾一样,应邀出现在CERN演讲大厅的屏幕前。屏幕上播放着显示实验数据的幻灯片,这些数据出自LHC实验中高能质子束之间几乎难以想象的猛烈碰撞。LHC实验希望通过这种对心碰撞能让希格斯玻色子在瞬间爆发的能量聚集中显露原形。数据让在座的嘉宾明白,在一个令人信服的概率范围内,实验者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当演讲结束时,全场起立,为研究团队鼓掌,并向将他们带向胜利的不可思议的装置表达崇敬之情。
LHC的一切都是大的。它的建造,从概念到第一束质子的产生,就花去了25年时间和100亿美元。这台机器位于风光绚丽的法国和瑞士边境的90米深的地下。装置的混凝土隧道的周长达27千米。隧道内装有9600个磁体部件,每个部件都被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下,以便能引导质子以接近99.99%的光速做对心碰撞。
对撞机以及2012年夏天宣布的这一发现,成为对大科学的最好诠释。大科学研究是一种由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科学项目驱动的工业规模的研究模式——原子弹、登月竞赛、派遣机器人作太阳系外的深空研究、微观尺度上的亚原子粒子的性质研究,等等,无不如此。当今时代,大科学主导着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的研究方向。它解决大问题,因此需要巨大的资源,包括由成百上千的职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来操控的设备。其项目资金往往是一所大学,甚至一个国家难以承担的。CERN的对撞机不仅得到了来自21个成员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还得到了其他60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支持。从这些数据可看出当今大科学的规模。正如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R.Wilson)所阐述的那样,这种规模的研究不是哪个独立机构能够单独实现的:“独自从事核科学研究就如同独自登月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大科学创立本身曾是一种孤独的努力。这种探索自然奥秘的新方法可以追溯到90年前的加州伯克利。当时一位极富魅力和机智的年轻科学家不仅物理秉赋出众,而且在推动一项新发明方面独具天才。他甚至宣称:“我就要出名了!”
他的名字叫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他的发明在核物理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然而这还仅仅是其影响的开始。这项发明改变了科学运行的基本模式,许多方面直到今天依然十分重要。它重塑了我们对大自然的基本构造的理解。它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帮助。这就是劳伦斯所称的回旋加速器。
大型强子对撞机是劳伦斯的发明的直接产物,虽然今天很少有人能认清这个家族的相似性。劳伦斯亲手建造的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成本不到100美元,而大型强子对撞机则包括了几种先进的回旋加速器和同步回旋辐射加速器,以及用来驱动亚原子粒子到极高速度的其他先进加速器。所有这些后代均源自最初的设计原理。劳伦斯在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在鼎盛时期雇用了60位科学家和十几名技术人员。与其学术前辈比起来,这种团队规模似乎更像一支军队。例如剑桥大学传奇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欧内斯特·卢瑟福爵士,当年带着两个助手,采用手工工具(其中一些便于他在工作台上操作),就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发现。但在公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两个研究团队看来,即便是劳伦斯当年的团队也显得微不足道。今天的团队每个都有三千名成员。
劳伦斯作为大科学工程的缔造者的地位得到了他的同龄人的广泛承认,但如今这种地位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有几个原因值得再探讨。一是驱使他做此研究的本性和雄心,以及他极具个性的管理风格,使大科学染上了持久的个体特征,但还远不止这些。他的事迹是一段令人叹服的科学探索传奇。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发现,而且也被置身于科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的风口浪尖。
从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国家层面的科学政策几乎不存在问题,而在欧内斯特·劳伦斯看来,这种政策却不是他要追求的。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的发明者和最大的国家级实验室的领导者,他的影响力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迅速扩张。为了支持盟军建造原子弹,他押上了个人承诺,从而将这一项目在几乎肯定要被取缔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回来。战争结束后,正是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推动了发展氢弹计划的实施。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正不安地处在热核武器这柄达摩克利斯剑的威胁之下。不管是从好坏哪方面看,这些肯定都是欧内斯特·劳伦斯留给现代文明的遗产。
1929年的一天,劳伦斯通过头脑风暴法意识到,他想出了一种极为有效的加速亚原子粒子的新方法。他的目标是用它们作探针去发现原子核的结构,就像人们拿着螺丝刀去捣鼓一台无线电电子设备。原子核是一种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带电内核,它占有原子的大部分质量。他的回旋加速器从概念上说很简单,它能解决如何使亚原子粒子——特别是质子(即氢原子的核)——获得能量的难题,使它们可以穿透原子核的电场。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设法攻克这个难题。劳伦斯解决了它。
当时的物理学正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型期。小科学时代的天才,像卢瑟福、伊莲娜和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夫妇(玛丽·居里的女儿和女婿),都曾将自然赋予他们的简陋工具运用到极限。凭借着手工器具,卢瑟福发现了原子核,并且凭直觉预言了中子的存在。后来,他的副手詹姆斯·查德威克,在另一项小规模的实验中发现了这种粒子。约里奥-居里夫妇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继续玛丽·居里的事业——探索放射性的奥秘,学习如何通过放射性照射使一种元素转变成另一种元素。这两个实验室依托的都是天然放射性物质(如镭和钋)所产生的看不见的亚原子粒子作为探针。
他们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他们无法逃避这样一个现实:要对核结构作进一步研究,就需要有比放射性物质随意发出的射线脉冲速度更快、能量更高、准直性更好的子弹。换句话说,物理学家需要的是人造射线弹。聚焦高能粒子束并让它们打到靶上,不仅需要实验室的台面设备,而且需要大到几乎无法安装在室内的大机器。卢瑟福和约里奥-居里夫妇知道,他们是手工操作科学时代最后的杰出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不得不让位给新的一代。
老传统下的这些物理学家怀着敬畏的心情注视着带给他们的科学领域的新变化。正如毛瑞斯·戈尔德哈伯(Maurice Goldhaber)——其辉煌的职业生涯跨越小科学的鼎盛期和大科学的成长期——在回忆这段过渡期时说的那样:“第一个瓦解原子核的是欧内斯特·卢瑟福,有一张照片反映的就是他抱着放在他膝头上的装置。这时我总想起另一张照片:建在伯克利的一台著名的回旋加速器,所有人都围坐在它周围。坦率地讲,这种对比会给你一个一切都变了的印象。”
戈尔德哈伯并没有夸张。他提到的回旋加速器是一台建于1938年、有自己的专设大楼的庞然大物。这台机器的巨型电磁铁就重达220吨,高达3.4米。戈尔德哈伯提到的照片记录确实是劳伦斯实验室的全体工作人员——27个成年人——站在或坐在马蹄形磁铁的周围(图1)。

图1 辐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和同事坐在152厘米加速器的磁铁轭的底边上,此时克罗克实验室尚处于建设阶段。实验室的人员结构如下:前排(左起):约翰·劳伦斯、罗伯特·塞尔博、弗兰兹·库利、雷蒙德·伯奇、欧内斯特·劳伦斯、唐·库克西、亚瑟·斯内尔、路易斯·阿尔瓦雷斯、菲利普·埃贝尔森。第二排:约翰·巴克斯、威尔弗雷德·曼恩、佩尔·埃伯索尔德、埃德温·麦克米兰、欧内斯特·莱曼、马丁·卡门、大卫·卡布菲尔、温菲尔德·索尔兹伯里。后排:亚历克斯·朗斯道夫、萨姆·西蒙斯、约瑟夫·汉密尔顿、大卫·斯隆、罗伯特·奥本海默、威廉·布罗贝克、罗伯特·科尔诺格、罗伯特·威尔森、尤金·维兹、杰克·利文古德。
欧内斯特·劳伦斯的性格与他带来的新时代之间有着十分完美的匹配。他的科学风格属于那种在沉静的学术研究世界里很少见的类型。他善于同百万富翁、慈善基金会和政府机构打交道。他那种和蔼可亲的中西部人的个性如同其科学天分一样重要,都是他成功的关键。科学天分加上他对工程的直觉,使他对物理学有一种本能的把握。他宅心仁厚,很少发脾气,从不出言不逊。(“哦,sugar!”是他最严厉的咒骂了。)他筹集大笔资金往往依靠的是积极宣传,记者们也总是乐于帮忙传递信息。记者笔下的人物不仅具有吸引人的个性特征,而且富有科学探索精神,而欧内斯特正好兼备这两方面要求。在他30多岁时,他已经是美国本土出生的最著名的科学家,这一点可由他的照片荣登1937年11月的《时代》杂志封面来佐证。“他创造但也破坏。”不久之后,1939年,他便获得了活着的科学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
劳伦斯颠覆了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家的刻板印象,好像他们总是在一所远离尘嚣的实验室(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里,以狂热、神秘的激情埋头于孤独的工作,他们的创作设计常常让其制造商几乎抓狂。在流行文化中,科学家的典型特征是超凡脱俗,《时代》杂志曾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描绘成一个成天将自己关在大铁门后的阁楼里独自从事着稀奇古怪的天才构思的人:“憔悴、紧张、烦躁……数学家爱因斯坦甚至不会记账。”
相反,劳伦斯不仅非常睿智,而且体力充沛。他终于成功地建成了这样一座实验室,它不是那种幽暗的哥特式城堡,而是一座矗立于山坡之上的现代化科学殿堂。它既远离喧闹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又可俯瞰旧金山海湾迷人的景色。他一点都不孤独,他主持着一个由朝气蓬勃的年轻科学家和研究生——物理学家、化学家、医生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所有人都在跨学科的协作中艰苦跋涉和认真思考;他管理着数以百万美元的经费,以确保这种协作能够顺利实施。他以其雄心、气魄、智慧和财富体现了新世界强劲有力的作风。布鲁斯·布利文(Bruce Bliven),一位经常行走于愤世嫉俗的政客和厌世专家之间的进步记者,很快为著名的劳伦斯教授——科学奇迹的奠基人所倾倒,发现他“很容易说上话,完全是那种你能想象的美国人”。
• • •
“大科学”一词是由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在1961年——欧内斯特·劳伦斯去世三年后提出的。温伯格从他作为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该实验室是按照劳伦斯的规格要求建立的,用于生产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浓缩铀)主任的角度,调研了前几十年的科学研究模式,并对这一时期作了这样的定义:其科学成就的标志——高耸的火箭、高能加速器、核反应堆——都是用铁、钢和电线电缆搭建的,就像早期文明用蟠纹石教堂和大金字塔向天上的神和世俗的国王表示他们的虔诚一样。
只有官僚作风的管理模式才会保留下这些科学运作的古迹。在劳伦斯的辐射实验室里,核心装置——回旋加速器——在技术上是如此复杂,操作上又是如此容易失灵,以至于需要专职工程技术人员时刻保持警惕。“保持一切按部就班的逻辑——无论是指科学机械还是指精心设计的像机器般运转的组织架构——已成为这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温伯格回忆道。在照管机器的那些人眼里,这种因科学问题的令人生畏的复杂性所强制的宏大承诺已变成一种信仰。“如果不付出巨大努力,不采用庞大的工具,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获取有关物质最微小的结构和宇宙最大尺度上的信息。”劳伦斯实验室的前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Wolfgang K.H.Panofsky)如是说。
追求更大更好的推动力有其自身的逻辑。回旋加速器的每一项发现都为物理学家所做的探索开辟了新的前景;要揭开每一个新的谜底,就要求机器做得更大,能量更高。每一项新发现都给该机构带来新的威望,为它招募到更多的科学家,获取更多的荣誉,以及为筹集更多的资金创造出更多的动力和机会。
使大科学作为科学探索的典范而得到最终验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技术成果:雷达和原子弹。如果没有跨学科的合作和几乎无限的资源支撑(这已成为新范式的标志),要开发出这两样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肯定不可能及时发明出来而影响战争结果。建立第一座观察核的链式反应的原子反应堆被公认为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功劳。这种链式反应对于开发钚弹,就是后来扔在长崎的炸弹,至关重要。费米不仅构思了这一概念,而且监督了它的建造。但要实现费米的这一设想,则需要建立一支由“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仪器专家、冶金学家、生物学家,以及可以把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物的各类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温伯格观察到,“链式反应堆可要比核物理学家的一项实验大得多”。
劳伦斯在科学工作中的研究风格的这些变化不仅让人敬畏还给人带来不安,直到今天它们依然如此。
甚至在劳伦斯职业生涯的早年,当大科学仍处于形成阶段时,科学家、大学校长和其他专家便已开始担心它对知识追求和传播的影响。1941年,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也是一位精通回旋加速器的物理学家——就曾对侵入学术界的那种对金钱和名望的争夺的“反常的竞争要素”感到忧虑。他不安地对朋友诉说道:“要维持一项积极的计划和运转良好的员工队伍,需要的是更积极的宣传而不是科学界的津津乐道。”一些科学家看到的是过度竞争,完全不协调的工厂式研究模式,那些仍采用旧世界管理方式和研究程序的大学对于像伯克利这样的大科学机构唯恐避之不及。而另一些人,譬如帕诺夫斯基,则认为大科学对于解决物理学的大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在伯克利的新系统内训练自己,然后将大科学的福音传播开来。(帕诺夫斯基将它带到了斯坦福大学。)
有关大科学如何永久地改变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这一点,早在战争年代就已有著述。当时科学和技术共同体主要是集中精力赢得胜利。然而,随着和平的到来,科学家们开始重新琢磨大科学带来的变化。有些人担心,“个人灵感”这一在过去取得突破的法宝是否还会有用武之地。匈牙利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就曾这样问道:“一个跨学科的团队能够发现相对论或薛定谔方程吗?”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担心的是日益增长的管理上的需求将使最有才华的科学家离开实验室。在小科学时代纯粹致力于自身课题研究,并口耳相传地教授学生的研究人员,现在不得不应付许多其他职责:他必须管理好筹集到的大笔资金,写课题申请报告,为各种委员会提供咨询服务,在华盛顿的国会和各执行机构的走廊上徜徉以打探消息。研究机构的领导人不仅得是科学家,而且还得是老板、拉拉队队长和推销员。
资金很充足,但到款都是有条件的。随着资助规模的增长,这些条件变得越发苛刻。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资助自然主要是针对军事研究和发展。但即使在1945年德国和日本投降后,政府仍然是美国科研机构最大的单一资助者,其军事用途仍继续主导着学术界科学家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物理学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着是朝鲜战争,然后是被称为冷战的漫长、紧张的生存时期。而且军事服务现在已演变出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军工产业。在战后时期,大科学和“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逐渐融合曾让艾森豪威尔总统深感不安。工业对学术实验室的日渐深入的介入给科学家带来了压力,他们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工作的商业可行性。物理学家不是在从事基础研究,而是开始“把时间花费在追求经济上可获得专利的方面,而不是探索科学的基础原理方面”,科学史学家彼得·格里森(Peter Galison)这样观察道。作为大科学的先驱,欧内斯特·劳伦斯比大多数同龄人更早面临这些压力,但专利争夺战——不仅仅是什么能申请专利,还有在大科学团队中谁该拿大头——很快就在学术界成为普遍现象。政府和工业界也很快就加入到这一狂欢中:为了保密,为了一体化,抑或为了大投资带来更大的收益。
正是劳伦斯帮忙播下了产业界参与研究的种子。他让他的投资人看到回旋加速器是如何服务于他们所青睐的目标的,从而培育了产业界的雄心。对于生物研究机构,他利用加速器生产了大量的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用以了解光合作用的复杂性和杀死癌细胞的效果。他让企业家看到了原子核作为发电机的美好前景,一旦实现核能发电,电能将变得难以想象的便宜,而且几乎是用之不竭的。至于那些仍然致力于基础研究的慈善基金会,他向它们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揭开自然世界奥秘的项目,从而提高了这些基金会的声望。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总裁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B.Fosdick)最简洁地一语道出了大科学在这方面的本质作用:“新的回旋加速器已不只是一台研究设备。”他在1940年这样说道,它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它代表着人类对知识的渴望,是人类精神最高尚的表达方式,是人类对真理无畏探索的象征”。那一年,这个非营利基金会的董事会投票决定资助劳伦斯100多万美元,用以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回旋加速器。
没有人对劳伦斯照顾到他的资金支持者的利益诉求说三道四。如果他无法用创纪录的成就来支撑他的承诺,那么他在筹集资金上的艰苦努力就会前功尽弃。伯克利的辐射实验室开创了新的核医学科学来与疾病作斗争。它的回旋加速器经常加班加点用以生产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所需的放射性同位素。劳伦斯的期盼——原子能总有一天能用于取暖,用于几百万个家庭和工厂的照明,用作船用动力让海轮远航全球——极富远见,而且完全发自内心。当然,这一切现在都已实现。
大科学的成功给科学家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他们因帮助赢得战争而倍受人们尊敬和钦佩,他们被看作人类渴望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活的宝库。但这种高看热捧不可能持久,因为科学知识是不完善的,公众总有一天会感到幻灭。随着大科学项目变得越来越大,科学家们开始变得举步维艰,因为用于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所需的公共资源有很大一部分被大科学占用了。
到20世纪末,社会对大科学的信任开始消退。回想起来,它的许多成就似乎模棱两可:是的,原子弹赢得了战争,但代价是核的阴云永远在人类的头顶徘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带来了电力,但其价格远远高于其倡导者当初的预想,而且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三哩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灾难,带来了人类是否真能可靠地驯服核技术的问题。人类漫步月球,但在那壮观的瞬间过后,公众对太空探索的兴趣迅速消退。所有这些花费——图什么?
在1961年提出“大科学”一词的同一篇文章里,阿尔文·温伯格概述了当时人们关于大科学对研究、对大学和社会的影响的疑虑。他十分公允地说道,如果建立大科学所需的大规模支出吸干了稀缺的资源,并将科学家从探索与人类生存条件更密切相关的领域引开的话,那么,“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宁愿选择一个优先考虑如何治愈癌症的项目,”他写道,“而不是把第一个宇航员送上火星。”
在美国,这种疑虑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引起关于是否应该上马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的激烈争论。这台加速器原定设在得克萨斯州的沃克西哈奇附近,其能量将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3倍。该项目最终因地区和预算政策而搁浅,但它的致命伤是公众已经怀疑其目的性。1993年,超导超级对撞机的项目被国会否决了。
大型强子对撞机是如此巨大、复杂和昂贵,以至于一些科学家认为它可能标志着国际级大科学的终结。它做出的发现所提出的关于自然世界的问题,只能通过更大、能量更高的对撞机来回答,正如劳伦斯的每一台回旋加速器造就了未来对更大的加速器的需求一样。像大型强子对撞机一样,下一代机器,如果要建造的话,将需要多国联合来进行。让多个国家就一项在外人看来十分抽象的探索组织在一起进行合作是很不容易的。
欧内斯特·劳伦斯从未表现出这样的疑虑。他的目标是如何解决“研究自然的问题”,正如罗伯特·奥本海默所说的那样,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这一目的。我们现在来评估大科学的影响并不贬损他的成就。但大科学确实迫使我们去审视它是怎么来的。故事要从小科学世界里的大人物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