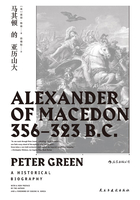
1991年重印序言
自我收拾好初步的笔记和基本的文本——阿里安、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福斯、查斯丁等的,然后退居到当时不为人知的希腊岛屿阿斯堤帕莱亚岛上去创作《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初稿,现在已经二十二年过去了。我沉浸在亚历山大的学术史中,包括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和现代希腊的(作为爱国象征的亚历山大——不止是在上校军政府的统治下——值得另写一部专著),直到我觉得快要淹死了。我需要脱身一下,清理一下我的脑袋,找回透视感,清楚地看一看亚历山大,跳出那让人分心的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大合唱。当然,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宣传(有些是自发产生的)贯穿国王的一生,而且他一死就被人神话化了——其实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种神话化就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
尽管如此,我最初进行叙述时的境遇还是在本书中留下了印记,正如类似的限制对琼斯(A. H. M. Jones)的出色且独树一帜的斯巴达研究(1967年)所造成的情况一样。特别是,我不得不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仔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存的史料,依靠他们现存的状态来做判断(即便最早的狄奥多罗斯也是生活在他所写事情的约三个世纪之后了),而不是去进行复杂的史源探究训练,这种史源探究是专门推断并评价现存史料所利用的更早的作家作品的学问。
作为初步的研究方法,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也就是说,做出判断经常是基于常识而非学术论证或共识;但那时候我不认为,现在回顾的时候也不认为这必然是件坏事。我所沉浸于其中的学术史——尤其是当时恩斯特·巴迪安提出非常有说服力的极简主义论点——不可避免地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就像后来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而且住在希腊的时候,我比多数人都更清楚马其顿研究正在发生怎样激动人心的转变。但是,很大程度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依然只是一部基于文本的史学尝试,另外还受惠于对希腊的地貌、气候和只有长年定居才会产生的对风俗习惯的熟悉。1971至1973年间我在本版出版前做了大量的修订,但其中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修订是在大学院系里进行的,那里可以充分接触到学术文献。做此修订是为了提供一个平台,以补充初稿中经常忽略的学术背景和争论。
结果便形成了一部有趣的混杂之作。由于一些与文学或史学都无关的原因(版权纠纷、出版商之间的分歧),本书只作为一本厚厚的平装书在英国问世,此后——因为此版很快就脱销了——像一个学术幽灵一样存在了几年,之所以没有被人不公正地遗忘,只是因为有少数学者发现了我的研究的价值,引用并向他们的学生推荐了本书。不幸的是,要找到本书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在过去的十六年里,重印的念头一再出现,但直到现在这个念头才最终有了结果,只是有人觉得实际上已经太迟了。
由于已过去了很长时间,亚历山大研究自1974年以来也在不断发展,在过去一两年里,我的想法逐渐倾向于在第二版中做一次相对彻底的修订;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我准备编写的这一文本。任务十分繁重,很可能——我还有其他事务——要花三四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许多领域已经完成大量研究,我需要加以了解。最明显的例子是马其顿史,由于博尔扎、考克威尔(Cawkwell)、埃林顿(Errington)、格里菲斯(Griffith)、哈蒙德(Hammond)和沃尔班克(Walbank)等学者的工作,以及安德罗尼科斯(Andronikos)在维吉纳大墓(Great Tumulus of Vergina,现在已确认是古代的埃盖,正如哈蒙德早就预测过的)中所取得的著名考古发现,这个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海伦·桑启西-威尔登堡(Heleen Sancisi-Weerdenburg)、苏珊·舍温-怀特(Susan Sherwin-White)和阿梅莉·库特等学者对波斯和其他东方档案的最新研究,阐明了亚历山大的东方联系和帝国管理制度。铭文得到重新解读,钱币得到研究,地形图得到修订;军事后勤这一大块问题也因我从前的学生唐·恩格斯(Don Engels)的研究而有了全新的基础。任何修订都需要参考这些丰富的学术成果,而我就是这么打算的。
在准备修订和更新文本的过程中,我想我还找到了一个重新发行1974年版——实际上该版从未在美国发行过——以满足(迟做总比不做好)学院和大学持续增长的需求的有力理由。确实,我目前的著作还缺少额外的一个方面,即最近二十年的学术发展所能够且应当提供的东西(包括关于阿里安的第一种批判性注疏,虽然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通常很小但令人不快的各种印刷错误以及文学或事实方面的笔误仍然存在(例如,第53页“学园”[Academy]误作“吕刻昂”[Lyceum],第405页“源头”[headwaters]误作“总部”[headquarters]),足够挑剔的评论者作靶子用。
但是,最近重读全文——再加上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生组成的研讨班提出的那种不仅尖锐而且有时还很激烈的意见——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我重获信心。的确,有好多地方我都需要再考虑考虑(例如在菲罗塔斯事件中,阴谋是实有的还是被人捏造来反对他的?)。有些难题(例如哈尔帕罗斯的第一次出逃)依旧令人困惑。而更为突出的例子便是本书关于格拉尼科斯河战役的附录,最新的研究使我确信我绝对错了。但是,总的来说我找不到理由说我1968年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天赋或动机的分析是错误的,却可以找到大量的论据来支持我通过仔细研究古代史料而不得不得出的结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并非乐事,他们或者相信马其顿统治者是国际法的支持者,相信法治原则;或者相信马其顿统治者是热衷冒险的浪漫理想主义者,依旧热切地固守着塔恩的博爱幻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从事这项寂寞的任务时所在的希腊岛屿,恰好是上校军政府用来放逐保皇派军官和那些拥有独立想法的思想家的地方。当“不做我兄弟,便做刀下鬼”这句革命笑话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出现时,我正看着亚历山大把它运用到忒拜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提尔或奢羯罗的防御者身上。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的事件促进了我的判断的形成,正如塞姆对奥古斯都的论断——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驻罗马古典研究院中构思出来的——不可能不受墨索里尼派法西斯主义活动的影响。
在学术界中有一种贬低这种偶然的个人经历的倾向,认为这种经历会影响我们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历史书写。我不同意。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奥斯都非常清楚,要书写历史就得参与到历史当中去,无论其角色多么边缘。吉本(Gibbon)明白,担任汉普郡近卫步兵第一团上尉对他成为罗马帝国史专家不无裨益。正好,上校军政府把亚历山大宣传成伟大的希腊英雄——特别是对军队新兵: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把亚历山大看作半马其顿半伊庇鲁斯血统的野蛮征服者,他们定会和我一样觉得这种变换太过讽刺。
此外,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希腊化时代,特别是亚历山大继承者们(Diadochoi)——这些瓜分了战利品的坚忍不屈的元帅们——的帝王习性,这大大加强了我的信念,即亚历山大不仅是有史以来最才华横溢(且雄心勃勃)的战场统帅,而且与所有的管理才能和理想主义追求全然无涉,那些都是后人,特别是那些单纯觉得这位征服者对于他们的自由主义情感来说有点难以接受的人偷偷赋予他的。我非常肯定,经过修订的第二版不会根本改变这一论断。毕竟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无论我们在细节方面如何计较,关于亚历山大一生的历史事实确实没什么争议。说到底,关键在于我们对它们的阐释。在此基础上,我很高兴看到当前的版本连同它所有的不足,竟能够获得新生。
彼得·格林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199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