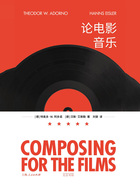
新版导言
只因他是人,
人得有饭吃,
他不会满足于夸夸其谈,
那可给不了他面包和肉。
布莱希特、艾斯勒
如今不言而喻的是,
关于艺术没有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更不用说没有什么是不思自明的。
阿多诺
1934年,好莱坞,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新电影——《救生艇》(Lifeboat),正在二十世纪福克斯的片场拍摄。有一天,电影的作曲者得知,导演决定不在这部片子里使用任何音乐。作曲家感到很困惑。他陷入突然的不安,有些生气,想知道导演为什么会别出心裁。“是这么回事,”有人告诉他说,“希区柯克认为,既然整个剧情都发生在公海上的一艘救生艇里面,那音乐是从哪儿来的呢?”作曲家叹了口气,耸耸肩,听天由命地笑着回答说:“让希区柯克先生解释一下,摄影机是从哪儿来的,我就告诉他,音乐是从哪儿来的。”
音乐,始终是电影媒介中最少被欣赏到、最经常遭到忽视的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也还是最少被论及的方面。当《论电影音乐》在1947年首版的时候,就其对商业电影及电影配乐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本质特性与潜力的理解而言,乃是一份独特而极富挑战的贡献。今天,在汉斯·艾斯勒和特奥多·阿多诺着手其非凡计划的五十年后,作为对电影音乐之社会、政治、美学重要性的学理性分析,这部著作仍然卓尔不凡。你或许不同意其中的部分论点,但你仍然不难感受到它在面对一个很少被严肃看待的领域时,所展现出的罕见的批判性维度。它简练却野心勃勃,大胆而充满启发,是一首丰富而诱人的序曲。两位合作者,艾斯勒与阿多诺,分别代表着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种传统:艾斯勒那种布莱希特式的艺术实践,以及阿多诺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两位作者都无视僵硬的学科界限,因此,阅读《论电影音乐》就意味着投身于美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和哲学性的问题与关切。这样说来,这本书算是出乎意料地清晰易懂的了。
汉斯·艾斯勒(1898-1962),用他一位传记作者的话说,“在一片至今仍被视作逃离政治的庇护所的领域内,为一种社会艺术铺就了道路” 。他生于莱比锡,却在维也纳长大。他的父亲是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母亲是玛丽·艾达·菲舍(Marie Ida Fischer)。他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的兄长和姐姐后来在柏林成为职业革命者。1919年,他开始学习作曲并成为新维也纳音乐学院(New Viennese Conservatory)的卡尔·魏格尔(Karl Weigl)的学生。很快他就厌倦了魏格尔因循守旧、要求不高的那一套教诲,于是,尽管缺乏资助,他还是开始跟随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接受为期四年的私人教学,后者免除了他的学费。他被勋伯格的大师班接纳真可谓欣逢其盛,因为后者此时正处在从无调性向十二音作曲法转折的时期。艾斯勒成为继韦伯恩(Antoh Webern)和伯格(Alban Berg)之后,尝试用新技法作曲的第一人。
。他生于莱比锡,却在维也纳长大。他的父亲是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母亲是玛丽·艾达·菲舍(Marie Ida Fischer)。他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的兄长和姐姐后来在柏林成为职业革命者。1919年,他开始学习作曲并成为新维也纳音乐学院(New Viennese Conservatory)的卡尔·魏格尔(Karl Weigl)的学生。很快他就厌倦了魏格尔因循守旧、要求不高的那一套教诲,于是,尽管缺乏资助,他还是开始跟随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接受为期四年的私人教学,后者免除了他的学费。他被勋伯格的大师班接纳真可谓欣逢其盛,因为后者此时正处在从无调性向十二音作曲法转折的时期。艾斯勒成为继韦伯恩(Antoh Webern)和伯格(Alban Berg)之后,尝试用新技法作曲的第一人。
他在政治上的激进倾向导致他与勋伯格发生冲突,1925年,在历经一个激烈对抗和反叛的时期后,他移居柏林,去追寻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主义音乐。他为共产主义者的合唱团与宣传节目创作过直白而音乐上却相当复杂的歌曲。作为一名投身战斗的作曲家,他后来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写过好几首杰出的歌曲,包括人们非常熟悉的《第三国际歌》(Kominternlied)、《歌唱学习》(Lob des Lernens)以及《统一战线歌》。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关于政治艺术的理念影响,他根据布莱希特的文字编配过大量的剧场作品和清唱歌曲,还为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布莱希特和萧伯纳的戏剧做过配乐。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开始给电影做配乐,与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的文化名流如电影导演沃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 以及斯拉坦·杜多夫(Slatan Dudow)
以及斯拉坦·杜多夫(Slatan Dudow) 等人合作。他与左翼政治的牵连最终导致他永远地离开了德国。
等人合作。他与左翼政治的牵连最终导致他永远地离开了德国。
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主持过一个为期不久的国际音乐办公室,并在维也纳、布拉格、巴黎、伦敦以及哥本哈根等地工作过,直到最终移民美国。战后他遭到驱逐,最初安顿在维也纳,继而,从1950年直至去世,他一直生活在东柏林,在艺术学院主办一个作曲大师班并为大型合唱团创作了一系列歌颂无产阶级国家的歌曲,其中包括前民主德国的国歌《德意志交响曲》(Deutsche Sinfonie)。
特奥多·维森格伦德·阿多诺(1903-1969)曾被称为“德国最杰出的学院教师和西欧先锋派的一位卓越公民” 。他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身为独子,他的父亲奥斯卡·维森格伦德(Oscar Alexander Wiesengrund)是一个富有的归化犹太商人,其妻子玛丽娅·加尔维利——阿多诺(Maria Calvelli-Adorno)是天主教徒,一位生于热那亚的科西嘉歌手(在1938年流亡前夕,依照同事们的建议,儿子决定用母亲娘家的姓取代他的父姓维森格伦德)。
。他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身为独子,他的父亲奥斯卡·维森格伦德(Oscar Alexander Wiesengrund)是一个富有的归化犹太商人,其妻子玛丽娅·加尔维利——阿多诺(Maria Calvelli-Adorno)是天主教徒,一位生于热那亚的科西嘉歌手(在1938年流亡前夕,依照同事们的建议,儿子决定用母亲娘家的姓取代他的父姓维森格伦德)。 由于音乐和智力上的早熟,他于1921年即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
由于音乐和智力上的早熟,他于1921年即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 学习哲学、社会学和音乐,并于192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翌年,他前往维也纳,跟随阿尔班·伯格学习音乐。借助他的天赋和母亲的家族影响,阿多诺很自然地也和勋伯格、韦伯恩、克里内克(Ernst H. Krenek)、斯特约尔曼(Eduard Steuermann)、考里施(Rudolf Kolisch)及其他现代乐派的代表人物建立起私人交情。不过,他最亲近的人还是伯格,对阿多诺而言,这是一位介于勋伯格的现代性和马勒的乡愁之间的作曲家。
学习哲学、社会学和音乐,并于192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翌年,他前往维也纳,跟随阿尔班·伯格学习音乐。借助他的天赋和母亲的家族影响,阿多诺很自然地也和勋伯格、韦伯恩、克里内克(Ernst H. Krenek)、斯特约尔曼(Eduard Steuermann)、考里施(Rudolf Kolisch)及其他现代乐派的代表人物建立起私人交情。不过,他最亲近的人还是伯格,对阿多诺而言,这是一位介于勋伯格的现代性和马勒的乡愁之间的作曲家。 虽然他在1927年返回法兰克福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还是跟维也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在1928年到1932年间主编影响颇大的刊物《安布鲁赫》(Musikblätter des Anbruch)。
虽然他在1927年返回法兰克福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还是跟维也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在1928年到1932年间主编影响颇大的刊物《安布鲁赫》(Musikblätter des Anbruch)。
他从1931年起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掌的教席在1933年纳粹掌权之后日益岌岌可危。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生涯和生命历程,阿多诺与艾斯勒同样也不例外。他极不情愿,却只好离开故国。在余生中,他将对他自己以及流亡者同伴们“被毁掉的生活”展开反思。在短暂栖身牛津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 Oxford)之后,他加入了纽约的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研究所最初在1923年于法兰克福建立,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研究项目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这位阿多诺的老朋友1930年接任所长一职后,其前景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霍克海默与共产党所秉持的历史观、科学主义和政治理论不同,他的研究所提出马克思主义应该忠于马克思最早的批判计划:一种针对当下的理论,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这样一来,研究所重新激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批判理论”,坚决反对一切类型的教条主义,坚定地抵制将一般或特殊这二者中任何一个拜物教化的危险。由此,研究所致力于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规划,意在阐明社会、经济、文化与意识得以复制和变形的一整套机制。
霍克海默与共产党所秉持的历史观、科学主义和政治理论不同,他的研究所提出马克思主义应该忠于马克思最早的批判计划:一种针对当下的理论,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这样一来,研究所重新激活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批判理论”,坚决反对一切类型的教条主义,坚定地抵制将一般或特殊这二者中任何一个拜物教化的危险。由此,研究所致力于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规划,意在阐明社会、经济、文化与意识得以复制和变形的一整套机制。
研究所的理念与阿多诺本人那惊人且非正统的天赋若合符节。无论是在流亡美国期间还是在40年代回归法兰克福(此时他成了新任所长)之后,他的思想都构成了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计划的主导性影响。他坚守“不介入”的理念,不合作,拒绝以实际权宜的名义做出妥协。 他的思想抵制住诱惑,拒绝对任何不成熟的解决方案或是调和给予支持,努力保持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性。他曾经写道:“辩证法以极端的方式前进,以最大程度的同一性驱使思想臻达极点,在那里它们将背离而不是验证自身。”
他的思想抵制住诱惑,拒绝对任何不成熟的解决方案或是调和给予支持,努力保持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性。他曾经写道:“辩证法以极端的方式前进,以最大程度的同一性驱使思想臻达极点,在那里它们将背离而不是验证自身。” 他的风格就是摩擦传统思维的纹路,运用挑衅式的夸张和反讽性的颠倒以使矛盾获得清晰的呈现。“一种思想的价值,”他评论道,“由它与熟悉事物的连续性之间的距离来衡量。”
他的风格就是摩擦传统思维的纹路,运用挑衅式的夸张和反讽性的颠倒以使矛盾获得清晰的呈现。“一种思想的价值,”他评论道,“由它与熟悉事物的连续性之间的距离来衡量。”
“流亡者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写道,“是最敏锐的辩证法家。他们的难民身份是变化的结果,而他们的唯一研究对象就是变化。他们能够从最微小的暗示中推导出最伟大的事件……当他们的敌手获胜时,他们会计算出对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对于矛盾,他们拥有最敏锐的发现目光。” 欧洲移民的数量在1941年达到顶峰。在1933年到1945年期间,基于一项豁免条令,任何在之前两年从事教学工作而且已在美国获得教职保证的移民将不受限额的限制。借此,有613位学院中人移居美国。安置外国流亡学者紧急事务委员会(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为459人找到了职位,其中167人被安置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设立的“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艾斯勒1938年初抵达此处,讲授一些音乐课程。就规模而言,新学院是当时在美移民学者们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不过,当时与移民知识分子有关的重要机构还不止这一处。
欧洲移民的数量在1941年达到顶峰。在1933年到1945年期间,基于一项豁免条令,任何在之前两年从事教学工作而且已在美国获得教职保证的移民将不受限额的限制。借此,有613位学院中人移居美国。安置外国流亡学者紧急事务委员会(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为459人找到了职位,其中167人被安置于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设立的“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艾斯勒1938年初抵达此处,讲授一些音乐课程。就规模而言,新学院是当时在美移民学者们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不过,当时与移民知识分子有关的重要机构还不止这一处。 1934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安排了一个北美总部。研究所的新址位于纽约的晨畔高地公园(Morningside Heights Park),由霍克海默主管,其研究特色突出地表现在阿多诺(他在1938年2月抵达,晚于其他人)、弗朗兹·诺依曼(Franz Neumann)、利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大家的著作当中,继续对政治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根源展开自觉的跨学科理论探究。
1934年,哥伦比亚大学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安排了一个北美总部。研究所的新址位于纽约的晨畔高地公园(Morningside Heights Park),由霍克海默主管,其研究特色突出地表现在阿多诺(他在1938年2月抵达,晚于其他人)、弗朗兹·诺依曼(Franz Neumann)、利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大家的著作当中,继续对政治极权主义的本质及其根源展开自觉的跨学科理论探究。
对于新的环境,阿多诺很不适应,他比其他同事的感受更强烈。“每个移民知识分子,”他后来写道,“都毫不例外地遭到了割裂,如果他想躲在紧闭着的自尊之门背后以免获悉这一残酷真相的话,那他最好是对此也抱有自知之明。” 尽管他也加入了那些申请美国公民权的研究所成员的行列,但对定居美国却并无兴趣。事实上,利奥·洛文塔尔后来回忆说,阿多诺在加入他在美国的批判理论家同僚方面举动迟缓,以至于“我们几乎得动手去拽他”
尽管他也加入了那些申请美国公民权的研究所成员的行列,但对定居美国却并无兴趣。事实上,利奥·洛文塔尔后来回忆说,阿多诺在加入他在美国的批判理论家同僚方面举动迟缓,以至于“我们几乎得动手去拽他” 。他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欧洲人”,认为自己“身居海外的每一天都有此感,而且从未对此加以否认”
。他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欧洲人”,认为自己“身居海外的每一天都有此感,而且从未对此加以否认” 。他的一位新同事注意到:“他看上去就像你能想到的那种心不在焉的德国教授,他的行为举止格格不入,像是那些五月花号上的成员一样。”
。他的一位新同事注意到:“他看上去就像你能想到的那种心不在焉的德国教授,他的行为举止格格不入,像是那些五月花号上的成员一样。” 艾斯勒同样对美国的诸多方面不能适应,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对付长期缺钱这一事实上。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932年在影片《英雄之歌》(Komsomolsk)当中跟艾斯勒合作过,他当时是位于纽约的纪录片制作人协会的主席,艾斯勒希望能获得一些电影配乐的委约。很快,他就建立起了一个由朋友和潜在的赞助者组成的支助网络。
艾斯勒同样对美国的诸多方面不能适应,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对付长期缺钱这一事实上。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932年在影片《英雄之歌》(Komsomolsk)当中跟艾斯勒合作过,他当时是位于纽约的纪录片制作人协会的主席,艾斯勒希望能获得一些电影配乐的委约。很快,他就建立起了一个由朋友和潜在的赞助者组成的支助网络。
尽管大多数欧洲学者都觉得纽约是个适合工作的地方,还是有些移民知识分子或是因为贫困或是出于好奇,选择前往西海岸的加州。1941年,阿多诺搬到了圣莫尼卡,靠近洛杉矶,当时他的同事霍克海默健康状况不稳定,亟须温暖的气候。艾斯勒将于1942年搬去那里,他所牵怀的事项之一就是继续与布莱希特合作。一些意料之外的客人加入了他们。1939年末由几位移民美国的电影制作者在好莱坞创立的欧洲电影基金会,此时开始在片厂为杰出的移民们寻找一些小的工作机会,以便他们能顺利地留在加州。例如,一位上了年纪的历史学家就在一部古装戏中担任“研究人员”,一位音乐学家只能给一名不大出名的电影作曲家担任学徒。有时,这项策略会被加以扩展以便安置新来者。作为迟到的营救措施的一部分,受欧洲电影基金会推动,好莱坞制片厂米高梅和华纳兄弟给紧急营救委员会提供了七十多份“空白”合同,以保证这些优秀的移民获得工作。这差别极大的一群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和艺术家在20世纪40年代初抵达好莱坞,领取象征性的100美元周薪,同时以不同程度的担忧思忖着在电影领域开始新的,或许也是永久的生涯。被选中获取资助的人包括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瓦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阿尔弗雷德·诺依曼(Alfred Neumann)、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路德维希·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和恩斯特·洛塔尔(Ernst Lothar)。这群人中间,只有布莱希特似乎下定决心,同时也是极度悲观地试图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开展工作。
布莱希特把好莱坞描述为“国际麻醉剂交易中心”。 在移民者中间他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当看到他们中很多人要么变得自毁而厌世,要么屈从于物质主义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厌恶。艾斯勒在布莱希特抵达圣莫尼卡之后不久就与之在阿多诺家重逢。在之前的五年里,他们互相之间唯一的接触就是通信。这次重逢给他们很大鼓舞。艾斯勒让布莱希特重新焕发精神。当他再度与艾斯勒恢复工作关系之后,布莱希特在记录中说,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当我在人群中间浑浑噩噩地蹒跚行走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小名”
在移民者中间他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当看到他们中很多人要么变得自毁而厌世,要么屈从于物质主义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厌恶。艾斯勒在布莱希特抵达圣莫尼卡之后不久就与之在阿多诺家重逢。在之前的五年里,他们互相之间唯一的接触就是通信。这次重逢给他们很大鼓舞。艾斯勒让布莱希特重新焕发精神。当他再度与艾斯勒恢复工作关系之后,布莱希特在记录中说,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当我在人群中间浑浑噩噩地蹒跚行走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小名” 。
。
然而,两位艺术家却都无法为他们共同的计划付出太多时间。布莱希特在《好莱坞》这首诗里写到,他每天早上都需要“赶赴市场”, “他们在那里贩售谎言”,以便“赚取我的面包”。他在制片厂找不到适当的合作者;那些自视为共产主义者或是同路人的作者大多痴迷于俄国戏剧,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念。布莱希特和艾斯勒很难维系他们所共有的设想和对于艺术与政治策略的共同感知。特别是艾斯勒,他开始向昔日的老师勋伯格靠拢[艾瑞克·本特利(Eric Bentley) 回忆说当时曾见过这两位待在一起,勋伯格“动作很少,不苟言笑”,艾斯勒做着快速的手势在他周围晃来晃去,开怀大笑并极尽恭维],并且较之以前更多地致力于他的室内乐和管弦乐。为了维持生活,他也一样不得不为制片厂写一些电影音乐。
回忆说当时曾见过这两位待在一起,勋伯格“动作很少,不苟言笑”,艾斯勒做着快速的手势在他周围晃来晃去,开怀大笑并极尽恭维],并且较之以前更多地致力于他的室内乐和管弦乐。为了维持生活,他也一样不得不为制片厂写一些电影音乐。
艾斯勒和布莱希特所交往的群体跟更大的那个避难者社群在两个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主要由艺术家组成,这个群体在政治上通常更加强调左翼与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区分。在这一时期,很多卓有声望的移民常在周日下午汇集于萨尔卡·维埃特尔(Salka Viertel)在圣莫尼卡马波里街165号的家里,举行社交活动。维埃特尔以前是一位演员和作家,自1927年起就移居美国,她是葛丽泰·嘉宝和查理·卓别林的好友,她的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她艺术界和政治界知交好友的一处沙龙。这对一群优秀的艺术家来说是个极为理想的聚会地点:演员彼得·洛尔(Peter Lorre)和路易斯·赖纳(Luise Rainer);指挥家奥托·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作曲家马克斯·施泰纳(Max Steiner)、迪米特里·迪奥姆金(Dimitri Tiomkin)、布朗尼斯劳·凯帕(Bronislaw Kaper)和恩里希·科恩古尔德(Enrich Korngold);导演威廉·迪亚特尔(William Dieterle)、弗里茨·朗(Fritz Lang)、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和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以及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亨利希·曼。在这种松散的场合中,很多出乎意料的友谊建立起来了,很多不可思议的联合也被确定下来。比如,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就是在这里跟布莱希特和艾斯勒交上朋友的,后来就有了他们在首版《伽利略》 中的合作,还有相比起来不那么成功的一次,艾斯勒在一部平庸的影片《凯旋门》(Arch of Triumph, 1948)中被劳顿聘为德语发音指导。也是在这里,阿多诺会时不时地与托马斯·曼讨论后者当时正在撰写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 1947),如曼所说,这部小说事实上“厚着脸皮攫取”了阿多诺关于音乐哲学的论文。
中的合作,还有相比起来不那么成功的一次,艾斯勒在一部平庸的影片《凯旋门》(Arch of Triumph, 1948)中被劳顿聘为德语发音指导。也是在这里,阿多诺会时不时地与托马斯·曼讨论后者当时正在撰写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 1947),如曼所说,这部小说事实上“厚着脸皮攫取”了阿多诺关于音乐哲学的论文。 这里同样也是勋伯格与阿多诺相聚的地方,有时候,它还会引来像克利福德·奥德茨、斯泰拉·阿德勒(Stella Adler)和哈罗德·克鲁尔曼(Harold Clurman),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阿尔蒂 · 肖(Artie Shaw)和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莱昂·孚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和奥逊·威尔斯这样一群戏剧和音乐界的人物。
这里同样也是勋伯格与阿多诺相聚的地方,有时候,它还会引来像克利福德·奥德茨、斯泰拉·阿德勒(Stella Adler)和哈罗德·克鲁尔曼(Harold Clurman),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阿尔蒂 · 肖(Artie Shaw)和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莱昂·孚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和奥逊·威尔斯这样一群戏剧和音乐界的人物。
维埃特尔在她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当中表明,艾斯勒比布莱希特更容易在这些聚会中结交朋友。她说,艾斯勒“已经适应了好莱坞的水土”,他“睿智的头脑和愉悦的心态”使他成为美国文化圈一个广受欢迎的人物。在她的回忆中,那时候布莱希特算是两个人里比较保守的那个,显得冷淡而沉默,因为他“拒绝用一种外语去结结巴巴地自我表达”,这与艾斯勒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浑然不顾语法和他糟糕的口音,哪怕再沉闷的聚会他都能给变得生动起来” 。
。
萨尔卡·维埃特尔还把查理·卓别林介绍给了布莱希特和艾斯勒。在卓别林看来,布莱希特试图为艺术建立起一种系统化的理论,这一倾向常常失之笼统,因而相当可疑,可布莱希特反而对卓别林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热忱而专注的敬仰”。艾斯勒跟卓别林的关系显然更热络一些:艾斯勒向来都把卓别林看成世界上最富才华的电影演员之一,而卓别林后来则在其自传中把艾斯勒描述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1946年,艾斯勒在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Monsieur Verdowx,1947)一片中担任音乐顾问。在写给克利福德·奥德茨的信中,他激动地写下了他在片场的最初体验:
。1946年,艾斯勒在卓别林的《凡尔杜先生》(Monsieur Verdowx,1947)一片中担任音乐顾问。在写给克利福德·奥德茨的信中,他激动地写下了他在片场的最初体验:
查理已经开工了;他做了几个长工作样片之后我就开始看他执导——他的精熟程度真是令人赞叹。他不仅向演员们展示什么是他想要的东西,而且也展示什么是他不想要的东西。他写的剧本非常棒,当然他算不上作家,而且经常有某些弱点和天真的伪哲学观点,无疑是有害的……但这些都是瑕疵,总体上看他正在拍的真是一部杰作。他对音乐有些初步的设想并且自己写了几首唱词和歌曲,不过这些我都不大欣赏。我还不知道会以何种方式跟他合作。但他确实是个绝妙的家伙,晚上跟他待在一块儿总是乐趣无穷。
艾斯勒逐渐开始相信,是他和布莱希特使得卓别林变得激进,而且他相当堂皇地认为,《凡尔杜先生》里那些反讽尖锐的戏剧场面就证明了他们的影响。
然而,一般说来,艾斯勒自己在好莱坞直接的电影制作经验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作为音乐家,他的位置似乎特别不稳定。对于移民者中的作家来说,尽管好莱坞和制片厂体系的很多方面都很难理解,但是他们对畅销小说和商业电影的了解足以让他们领会到市场的期待是什么(即使他们不打算去满足它)。而对于欧洲的音乐家来说,好莱坞的情况跟他们在德国或者奥地利所知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欧洲的电影制作者很少会把整部戏都泡在那种铺天盖地的配乐里面,而这正是美国电影的惯常做法。恩斯特·克里内克(Ernst Krenek)在跟山姆·戈尔德温(Sam Goldwyn)短暂而近乎闹剧的会面之后,返回东岸,到瓦萨学院教书去了。阿诺德·勋伯格在与电影公司打过短期交道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教学工作上。艾斯勒却不太一样,尽管在南加州大学找到了教职,他还是得介入商业电影。
艾斯勒为一些商业电影创作了配乐,包括(与布莱希特合作)弗里茨·朗的《刽子手之死》(Hangmen Also Die, 1943),克利福德·奥德茨的《寂寞芳心》(None But the Lonely Heart, 1944),弗兰克·鲍沙其(Frank Borzage)的《西班牙大陆》(The Spanish Main, 1945),加斯塔夫·马哈蒂(Gustav Machatý)的《嫉妒》(Jealousy, 1945),哈罗德·克勤曼的《夜半血案》(Deadline at Dawn, 1946),道格拉斯·塞克(Douglas Sirk)的《花都绯闻》(A Scandal in Daris,1946),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海滩上的女人》(The Woman on the Beach, 1947),以及爱德华·迪麦特雷克(Edward Dmytryk)的《记忆犹新》(So Well Remember, 1947)。对艾斯勒来说,这些都算不上特别有益或鼓舞人心的经历。甚至他为《刽子手之死》这部有着明确政治倾向并且为他带来一项奥斯卡提名的影片做出的贡献,也由于导演弗里茨·朗跟布莱希特及其合作编剧约翰·维克斯理(John Wexley)之间关于演职人员字幕表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而遭到破坏。如果说布莱希特因为制片厂强加给他的妥协而倍感受挫的话,艾斯勒尽管不像他的朋友那样固执,有时候依然觉得作曲家所处的卑微地位是难以忍受的。
艾斯勒最初是对音乐家和作曲家所面对的严苛工作环境感到震惊。电影制片厂本身设有自己的音乐部门。他们只需要作曲家提供一首旋律最简单的线索,然后他们的编曲者将根据乐手的情况以及整体的“户型”把它扩充成一部配乐。那些为制片厂工作的作曲家,艾斯勒写道,“心里必须具备某种蓝图似的东西,必须在每个特定的场合中对此框架予以填充,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去加以调整,确保填充进去的东西既生动又感人。” 因为已完成的乐谱有可能随即便被导演的剪辑所打乱和扭曲,作曲者不得不养成一种“有规划的即兴”创作的才能,在乐谱的结构中就对这一潜在威胁做好预期准备。
因为已完成的乐谱有可能随即便被导演的剪辑所打乱和扭曲,作曲者不得不养成一种“有规划的即兴”创作的才能,在乐谱的结构中就对这一潜在威胁做好预期准备。 因此,制片厂所青睐的是那些能够根据订单生产音乐的作曲家,其流畅和快速程度在制片厂之外的地方却毫无用武之地。
因此,制片厂所青睐的是那些能够根据订单生产音乐的作曲家,其流畅和快速程度在制片厂之外的地方却毫无用武之地。
正是通过这样的经历,艾斯勒才变成了对电影音乐做出最清晰表达并且充满激情的批评家。在《论电影音乐》中,他批评了音乐部门负责人“往往显得怪诞的艺术上的不合格”,以及作曲家地位的低下。 他反思了作曲家个人在部门当中位置的不稳定。同时,又对懒惰地妥协和充满自豪但却具有毁灭性的反省这两种反应都做出了批驳,他强调指出,这两种态度“都只会表明他的无能”。艾斯勒还批评了电影管弦乐队僵硬的配置(被工会的协议限制在一组有限的弦乐、木管和铜管乐器内),普遍存在的编曲外包现象,还有将指挥的任务交给受欢迎的“名人”或是平庸的乐手这种惯例。他对音乐家本人抱有同情之心,他们被迫忍受“毫无价值且通常不会持久的低劣电影配乐”,忍受一个“毫无意义地拘泥形式和毫不负责地粗制滥造”的、要求颇多的制片厂体制,力不胜任的指挥,还有刚刚连续长时间赶着完成一幕配乐马上接着又是好几个星期的闲置所造成的压力。这样的工作环境,艾斯勒争论道,会鼓励草率和冷漠以及一种“沉默的蔑视”的态度。
他反思了作曲家个人在部门当中位置的不稳定。同时,又对懒惰地妥协和充满自豪但却具有毁灭性的反省这两种反应都做出了批驳,他强调指出,这两种态度“都只会表明他的无能”。艾斯勒还批评了电影管弦乐队僵硬的配置(被工会的协议限制在一组有限的弦乐、木管和铜管乐器内),普遍存在的编曲外包现象,还有将指挥的任务交给受欢迎的“名人”或是平庸的乐手这种惯例。他对音乐家本人抱有同情之心,他们被迫忍受“毫无价值且通常不会持久的低劣电影配乐”,忍受一个“毫无意义地拘泥形式和毫不负责地粗制滥造”的、要求颇多的制片厂体制,力不胜任的指挥,还有刚刚连续长时间赶着完成一幕配乐马上接着又是好几个星期的闲置所造成的压力。这样的工作环境,艾斯勒争论道,会鼓励草率和冷漠以及一种“沉默的蔑视”的态度。
艾斯勒着力最多的,还是他们被迫演奏的音乐所具有的那种程式化的结构:
在好莱坞有一句颇受欢迎的玩笑话:“鸟儿一唱,音乐就响。”音乐必须追随或对视觉事件进行图解,或是直接地模仿它们,或则运用那些与画面的情绪或内容相联系的陈词滥调……山顶的画面必然会引出弦乐颤音以及间或如信号般插入的圆号动机。当有着男子气概的主人公和久经世故的女主人公私奔到农场的时候,伴奏的必然是森林般的低语和笛子吹出的旋律。与一首慢拍华尔兹伴随的是一幕月光下的场景,在那里,一艘船沿着两岸排列着垂柳的河顺流而下……如果场景设在一个荷兰小镇上,其中有运河、磨坊和木鞋,那作曲家就得跑到图书馆去找一首荷兰民歌,以便用它的主题作为工作的基础。
阿诺德·勋伯格已经直接领教过这种羞辱。欧文· G.萨尔伯格(Ivring Grant Thalberg),米高梅公司负责制片的副总裁,曾让勋伯格为赛珍珠的中国传奇《大地》(The Good Earth,1937)改编的电影创作配乐,要求该音乐能够令人联想起他早期的那些“可爱”的作品。勋伯格开出的条件令萨尔伯格感到震惊,他要求对演员们拥有“绝对控制”以确保他们“一音一符”地忠实于他的乐谱,他许诺说,这样才能产生 “类似于《月迷皮埃罗》(Pierrot Lunaire)那样的效果,不过,难度当然会小一些”。事后,等萨尔伯格冷静下来以后,他告诉勋伯格说他已经找到一些中国民歌,音乐部门的负责人已经用它们作为灵感,给影片做出了“可爱”的配乐。 艾斯勒认为,制片厂已经强大到足以忽视道义的姿态。干活的通常都是那些愿意顺应和妥协的作曲家。为电影配乐变得近乎一架标准化的音乐设备所做出的例行挑选,其结果就是要获得戏剧性场景中已经指明的特定视听效果。作曲家变成了从音效库存中挑选适当设备的专家。对受欢迎的古典乐曲的业务知识,由此就构成了典型的好莱坞作曲家的事业基础。例如,对于一部相对低成本的恐怖片比如《木乃伊》(The Mummy,1932)来说,受到像《天鹅湖》这样的音乐的眷顾就算不上新鲜事了。正如马克斯·温克勒尔(Max Winkler)所坦言的那样:“我们糟蹋了莫扎特、格里格、巴赫、威尔第、比才、柴可夫斯基和瓦格纳的音乐——所有不受版权保护因而难免被我们盗窃的作品。”
艾斯勒认为,制片厂已经强大到足以忽视道义的姿态。干活的通常都是那些愿意顺应和妥协的作曲家。为电影配乐变得近乎一架标准化的音乐设备所做出的例行挑选,其结果就是要获得戏剧性场景中已经指明的特定视听效果。作曲家变成了从音效库存中挑选适当设备的专家。对受欢迎的古典乐曲的业务知识,由此就构成了典型的好莱坞作曲家的事业基础。例如,对于一部相对低成本的恐怖片比如《木乃伊》(The Mummy,1932)来说,受到像《天鹅湖》这样的音乐的眷顾就算不上新鲜事了。正如马克斯·温克勒尔(Max Winkler)所坦言的那样:“我们糟蹋了莫扎特、格里格、巴赫、威尔第、比才、柴可夫斯基和瓦格纳的音乐——所有不受版权保护因而难免被我们盗窃的作品。”
音乐向来是阿多诺生活和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电影,至少在他赴美期间,是不大可能被忽视的。40年代早期住在洛杉矶附近时,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机会去见证好莱坞电影那非凡的影响。在为和艾斯勒开始合作而着手准备的时候,他找到了老朋友、同样身为移民的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后者当时正在撰写其有关电影的主要论著)去寻求建议。 他毕竟很清楚,自己对这个主题而言还远算不上是个专家。跟艾斯勒不同,他没在好莱坞片场工作过,他跟电影从业人员的交往,相对来说似乎也不足为训。他更多的经验,是在音乐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方面。事实上,他在美国的早期论著就牵涉到广播音乐的社会学分析。
他毕竟很清楚,自己对这个主题而言还远算不上是个专家。跟艾斯勒不同,他没在好莱坞片场工作过,他跟电影从业人员的交往,相对来说似乎也不足为训。他更多的经验,是在音乐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方面。事实上,他在美国的早期论著就牵涉到广播音乐的社会学分析。
在纽约的时候,阿多诺有一半时间在研究所工作,另一半则是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中从事研究。该项目负责人也是一位移民,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ield)。阿多诺的任务是指导该项目的音乐研究组。研究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张力。拉扎斯菲尔德信奉的是经验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他鼓励阿多诺运用这种方法去验证其关于音乐和大众文化的理论。阿多诺从来不相信这些方法的可靠性,也不认为它们会是理解“我们称之为‘音乐性体验’的晦暗区域”的有益途径: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一台小机器,让听众在音乐演出中摁下一个按钮来表明他的喜恶,这对我们必须探究的问题的复杂性而言是极不恰当的;即便它所提供的数据从表面上来看是客观的。在任何情况下,早在我涉足这个领域去深入考察所谓音乐的“内容分析”之前,我就已下定决心绝不把音乐和程式化的音乐相混淆。我仍然记得当我那位已故的朋友弗朗兹·诺依曼……问我,音乐研究的问卷是否已经发放完毕,而我还是不确定这些问卷是否妥善处理了我认为极其重要的那些问题的时候,自己是多么困惑。
阿多诺坚持认为,文化就意味着“将能够对其进行测量的心智排斥在外”的那种状况。 他找到了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这位志同道合的同行,一位同样也熟悉欧洲传统的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支持他随心所欲的激进和不妥协,并且在他撰写四篇基于该研究的文章时协助过他。阿多诺后来曾对辛普森难以估量的帮助致以敬意:
他找到了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这位志同道合的同行,一位同样也熟悉欧洲传统的美国社会学家。辛普森支持他随心所欲的激进和不妥协,并且在他撰写四篇基于该研究的文章时协助过他。阿多诺后来曾对辛普森难以估量的帮助致以敬意:
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本土美国人比欧洲移民拥有更为开放的头脑,更重要的是,他们更愿意帮助别人。而后者,由于处在偏见和竞争的压力之下,常常表现出比美国人更美国的倾向,而且还易于把每个新来的欧洲同胞都看成是对他们自身“调整”的某种威胁。
尽管阿多诺在辛普森的协助之下已经开始把他鲜明的论点转换成美国社会学的语言,可当194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人不再支持音乐研究组时,他在研究项目中扮演的角色还是被终止了。
事实证明,阿多诺在研究所内部从事的工作本身具有更强的延续性和建设性。在他和霍克海默迁到圣莫尼卡之后,他们开始着手一项关于他们共同立场的重要(但绝非终结性的)陈述:启蒙的辩证法。 他们所关切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因为他们搬到洛杉矶而变得愈显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他们坚持认为,大众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这是一种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的大众文化;远不是它自我呈现的那样,自发地产生于“大众”本身,它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地强加给他们的:“‘人民需要什么’这个修辞性问题之所以显得厚颜无耻,是因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正是那些被蓄意剥夺其个体性的人们。”
他们所关切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因为他们搬到洛杉矶而变得愈显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他们坚持认为,大众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这是一种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的大众文化;远不是它自我呈现的那样,自发地产生于“大众”本身,它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地强加给他们的:“‘人民需要什么’这个修辞性问题之所以显得厚颜无耻,是因为它所指称的对象……正是那些被蓄意剥夺其个体性的人们。” 为了跟传统观念中通俗文化作为一种真正大众的文化的看法拉开距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创造了争辩性的概念“文化工业”。这一表达不能完全从字面上理解:它指的是“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在西方世界,像每个电影观众都很熟悉的那样——也涉及发行技术的合理化,但却并不严格局限于生产过程”
为了跟传统观念中通俗文化作为一种真正大众的文化的看法拉开距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创造了争辩性的概念“文化工业”。这一表达不能完全从字面上理解:它指的是“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在西方世界,像每个电影观众都很熟悉的那样——也涉及发行技术的合理化,但却并不严格局限于生产过程” 。
。
他们指出,文化工业
就其不断承诺的东西而言,永远都是在欺骗其消费者。它为快乐开出的期票借助其情节和布景而被无限拖延;所有的奇观最终所构成的那个承诺是虚幻的:实际上它所确证的唯一事实是,那个真实的点永远也无法抵达,晚餐的满意程度必须以菜单为准。
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体系里面的文化工业,反过来又自上而下地整合着消费者。它的运转是为了确保其自身的再生产,因此它所生产的文化形式就必须与其目标相匹配。文化商品必须立刻就能被辨认而且在充满吸引力的同时必须显得独特而新颖;熟悉的东西必须被当成不熟悉的加以促销,老式的风格被当成常新的:已成定式的标准化由此就被“伪个性化”所遮蔽:
伪个性化比比皆是:从标准化的爵士乐即兴,到一位不同寻常的电影明星将她的发卷垂过眼睛以显示其独特性。个性只不过是普遍性运用其权力给偶然性的细节打上的标签,这样它才能作为个性而被接受。个人所表现出的含蓄抵抗或优雅外表都像耶尔锁一样是被大量生产出来的,其唯一差别仅在毫厘之间而已。自我的独特性是一种由社会所支配的垄断商品;它被错误地再现为自然。它充其量不过是构成刘别谦式笔触(Lubitsch touch)的八字胡、法国口音、一个世故女人低沉的嗓音:就像按在身份证上的指纹,在除此以外的一切场合都是一样的。
我们非常有必要将这一批判放回到它真正的历史语境里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一如既往地寻求一种“针对当下的理论”,一种根据改变了的环境适时调整自身,而不是一劳永逸地进行解释和判断的批判理论。他们处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好莱坞,这是一个被超级制片公司所主宰的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特征由为数不多的、自上而下实施操控的公司所决定:所谓的“五大”电影公司——华纳兄弟、雷电华、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和米高梅——以及规模略小的环球、哥伦比亚和联美。所谓“制片公司体系”的基础,乃是制片公司对于生产、发行和上映的垄断控制。在制片公司体系的巅峰时期,八家主要的公司控制了95%的美国上映影片。由于这些制片公司的电影产量逐年增长,行政管理程序的集中化就在所难免:购买剧本、预定拍摄场地、控制和协调演员的档期、布景和委托配乐,这些都是总揽整个复杂进程的管理人员所应该承担的任务。生产越来越被按照“流水线”的原则组织起来,其特点在于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和权力管控的等级化。编剧有时发现他们受到监控以确保他们一直在写;演员们受到训练、培养,有时候他们的风格会被改变。演员、导演、编剧、音乐家和技术人员都要与制片公司签订合同。每个制片公司都储备着自己的一线演员、类型演员、歌星和喜剧演员队伍。每个公司都会培养一种易于辨识的风格:例如,华纳公司就倾向于在某些特定的类型中有所专长(黑帮片、后台歌舞片以及后来的浪漫冒险电影),这些类型都有一种鲜明的“外表”(低调照明,布景简单)以及显著的平民主义影像,而环球则致力于表现主义风格的恐怖电影,米高梅倾向于大制作古装剧和豪华歌舞片。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观察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置身于理性化商业体系内的、经过计算的多样化表象。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观察到的,正是这样一个置身于理性化商业体系内的、经过计算的多样化表象。
他们觉得,那个时候的好莱坞是文化工业真正的梦工厂。就在这个以前还意味着创新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了模仿。重复已经取代了发展。文化工业的功能就像是一份巨大的没有正确答案的“多项选择问卷”;如今重要的与其说是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人们做出选择这一事实本身。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感到担忧的是,它可能会最终导致社会失去对过去或未来的感知,个人失去记忆或想象;历史将被无尽的当下之流所消解。侵扰着这个世界的幽灵是“失忆之人的幽灵” ,没有能力去回想或梦想到,事物除了其当下所示的面貌还有别的可能。文化工业鼓励遗忘与分心。例如,大多数好莱坞电影气喘吁吁的步伐给观众一方留下的严肃反思余地就微乎其微:“娱乐所允诺的解放就意味着免除思考且拒绝否定。”
,没有能力去回想或梦想到,事物除了其当下所示的面貌还有别的可能。文化工业鼓励遗忘与分心。例如,大多数好莱坞电影气喘吁吁的步伐给观众一方留下的严肃反思余地就微乎其微:“娱乐所允诺的解放就意味着免除思考且拒绝否定。”
阿多诺在他流亡美国之初就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给音乐带来的影响;出于对音乐作品的熟知,他认为,“实际上是它所禀赋的品质的替代品。喜欢它差不多就跟能认出它是一回事” 。标准化过程追求的是标准化的回应。紧随音乐拜物主义而来的是听觉的退化,这种衰退使得听者失去集中于任何事物上的能力而只是关注一首作品最为枝节的碎片。这一过程绝不仅限于对所谓的“流行”音乐的接受。“严肃”音乐的爱好者也倾向于以古典音乐节目所促成的那种三心二意的方式去聆听:“疲惫的商人得以拍打着改编好的古典乐曲的肩膀,去爱抚其缪斯的后裔。”
。标准化过程追求的是标准化的回应。紧随音乐拜物主义而来的是听觉的退化,这种衰退使得听者失去集中于任何事物上的能力而只是关注一首作品最为枝节的碎片。这一过程绝不仅限于对所谓的“流行”音乐的接受。“严肃”音乐的爱好者也倾向于以古典音乐节目所促成的那种三心二意的方式去聆听:“疲惫的商人得以拍打着改编好的古典乐曲的肩膀,去爱抚其缪斯的后裔。” “ 古典”音乐或则分解成不那么珍贵的宝石(“在地铁里志得意满地大声用口哨吹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终曲主题的人大致上已经身陷它的碎片之中”),或则从交换的魔爪之下被解救出来,只是为了它们那古怪的完整表象而将其物化(“如果浪漫化的局部侵蚀了完整的躯体,受到危害的物质就会像通电一样被镀上铜”)。
“ 古典”音乐或则分解成不那么珍贵的宝石(“在地铁里志得意满地大声用口哨吹出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终曲主题的人大致上已经身陷它的碎片之中”),或则从交换的魔爪之下被解救出来,只是为了它们那古怪的完整表象而将其物化(“如果浪漫化的局部侵蚀了完整的躯体,受到危害的物质就会像通电一样被镀上铜”)。 粗俗与魅惑,两个“充满敌意的姐妹,她们并生其中的装置已经统治了音乐领域的大部分地区”
粗俗与魅惑,两个“充满敌意的姐妹,她们并生其中的装置已经统治了音乐领域的大部分地区” 。
。
阿多诺关于电影音乐的专门批评建立在他对文化工业更为宽泛的批判的基础之上。与艾斯勒不同,他并没有为电影作曲的直接经验。他称,好莱坞把音乐简化成了使用该音乐的那部电影的广告。通过给影像提供一种人性的装饰,音乐就掩盖了电影中人性的匮乏这一事实。他把电影开场字幕的配乐比作叫卖者的叫卖声:“大伙这边瞧!你即将看到的东西就跟这个一样大、一样光彩照人和色彩斑斓!知趣点,拍拍巴掌来买吧。”
到20世纪40年代,从很多方面看,阿多诺和艾斯勒都不大像是会在电影音乐的研究中展开合作。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即当1925年阿尔班·伯格促成他们相识的时候就很成问题。阿多诺极其博学、机敏挑剔而咄咄逼人,艾斯勒则积极投身政治,同时又是一位声名卓著的青年音乐家,另外还须说明的是,过度谦虚可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人会被称道的个人品性。他们互相将对方看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尽管看起来,他们还是会承认并尊敬对方的才华。阿多诺为艾斯勒所作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二重奏第七乐章写过一篇非常正面的评论,该乐章曾在同年的威尼斯音乐节上上演。他称艾斯勒为“阿诺德·勋伯格最新一代弟子中代表性的作曲家”,并且赞扬了他富于想象力的天赋,“这一点比起他对旋律的原创性、和声之流畅和对乐器的了解程度,更明显不过地证明了他的个人才华” 。艾斯勒那引发争议的过渡期作品,为人声和钢琴所作的《剪报》第十一乐章,首演于1927年12月的柏林,同样引来了阿多诺善解人意的支持性回应,后者称赞了这些歌曲的活力和独特性。然而,就在艾斯勒反叛勋伯格的同时,这两位也开始分道扬镳。
。艾斯勒那引发争议的过渡期作品,为人声和钢琴所作的《剪报》第十一乐章,首演于1927年12月的柏林,同样引来了阿多诺善解人意的支持性回应,后者称赞了这些歌曲的活力和独特性。然而,就在艾斯勒反叛勋伯格的同时,这两位也开始分道扬镳。
艾斯勒就他所认为的新音乐的精英主义展开了攻击;他相信新音乐对同时代的社会冲突充耳不闻。作为对此精英主义的实际抗议的一部分,艾斯勒开始对音乐文化展开批评,认为它一方面弃绝资产阶级艺术,另一方面却又通过文本内在地运用着资产阶级的方法。艾斯勒宣称,现代作曲家“必须从寄生虫转变为战士”。就在1927年末,当他加入柏林的宣传组织“红色扩音器”(Das Rote Sprachrohr)并成为其作曲家、钢琴家与指挥家的时候,他自己的音乐也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变形。在为这个组织创作的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以一种他觉得劳工阶级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表达自我。这需要一种新的音乐修辞学,一种更基础、更容易上口并且将某些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的“通俗”乐种的元素与现代音乐的资源综合起来的修辞学。艾斯勒为这个组织创作了一批歌曲、应景音乐和歌谣,包括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首,《第三国际歌》。
正是艾斯勒那集合了敏锐的理论意识与迫切的实践活动和坚持不懈的音乐实践冲动,把他跟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大多数作曲家们区别开来。他的计划首先是政治性的:要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视野和劳工阶级的渴望提供具体的音乐表现形式。艾斯勒的战斗歌曲和政治歌谣因其主题与严格的政治内容而有着鲜明的特征,它们的影响力被音乐所加强。这些歌曲是为现代大都市里的工人而作,以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物质利益这一复杂进程为诉求。
这项工作受到了布莱希特这位关键人物的鼓励,他从艾斯勒身上看到一种非常动人而且罕见的、杰出的音乐技巧与迫切的实践诉求的结合。他们持久的合作关系开始于1928年,合作曲目包括说教性的“清唱剧”《措施》(Die Massnahme, 1930)和勋伯格式的组歌《好莱坞挽歌》(Hollywood Elegies, 1942)。为了配合布莱希特的戏剧技巧,艾斯勒发展出一些作曲上的方法,目的在于打破观众对音响的认同与直接关系,以便音乐和歌词能够再度被有意识地加以体验。
阿多诺反对这种说教的艺术形式,他认为这跟保罗·亨德米特(Paul Hindemith)那样的作曲家所作的“社区音乐”一样反动。与布莱希特和艾斯勒有意的“政治”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多诺认为,一种音乐只有在它拒绝安逸的可交流性的时候才可被视作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在阿多诺看来,音乐是创作出音乐的那个文化的索引,因其符码难以解读才更其如是。“艺术作品从不撒谎,”他说,“它们所说的在字面上都是真的,然而,它们的真实性在于,它们是对那些被从外部带到它们面前的问题做出的回答。” 极端的音乐是那些意识到艺术与社会生活已然分裂的音乐,这一分裂不能“在音乐之内得到弥合,而只能在社会层面加以修正”
极端的音乐是那些意识到艺术与社会生活已然分裂的音乐,这一分裂不能“在音乐之内得到弥合,而只能在社会层面加以修正” 。他指出,在现代艺术中,“直接的抗议是反动的”
。他指出,在现代艺术中,“直接的抗议是反动的” 。根据阿多诺的说法,“带着无助的恐惧直视社会”对于音乐来说没有什么建设性可言;音乐承担其社会功能只是在“它通过自身的材料并根据自身的形式法则呈现社会问题——在其最内在的技巧单位之中,音乐将这些问题涵纳于自身”。
。根据阿多诺的说法,“带着无助的恐惧直视社会”对于音乐来说没有什么建设性可言;音乐承担其社会功能只是在“它通过自身的材料并根据自身的形式法则呈现社会问题——在其最内在的技巧单位之中,音乐将这些问题涵纳于自身”。 真正自律的艺术从不安顿,从不停息,绝不允许自身被它自己的规划所吸收:阿多诺观察到“真实对于勋伯格而言就意味着提防所有十二音学派”
真正自律的艺术从不安顿,从不停息,绝不允许自身被它自己的规划所吸收:阿多诺观察到“真实对于勋伯格而言就意味着提防所有十二音学派” 。
。
阿多诺声称,布莱希特公开的政治艺术,最终只会把艺术变得非政治化。尽管阿多诺对布莱希特的意图报以同情(他们二位在个人层面也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对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提出批评。 布莱希特的戏剧技巧远没能使社会现实变得陌生化,倒是使它显得简明易懂——这样一来,当他以如此强制性的方式对其加以呈现的时候,他无非就是投射了另外一重幻影。他那说教式的姿态,在阿多诺看来,“反映出对于那些引发思考和反思的含混性缺乏宽容。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希特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他不惜一切代价想变得有影响力,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会采取管控的措施”。
布莱希特的戏剧技巧远没能使社会现实变得陌生化,倒是使它显得简明易懂——这样一来,当他以如此强制性的方式对其加以呈现的时候,他无非就是投射了另外一重幻影。他那说教式的姿态,在阿多诺看来,“反映出对于那些引发思考和反思的含混性缺乏宽容。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希特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他不惜一切代价想变得有影响力,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会采取管控的措施”。 反过来,布莱希特认为阿多诺和他的研究所同事们在政治上是自足自满的,在他看来,他们消除了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迫切性的面向。尽管他继续与他们交好,他同时也开始把他们及其活动作为素材写进他孕育已久、从未完成的“tui-novel”,一部讽刺那些他从1934年即开始与其共事的知识分子们之丑事的作品。艾斯勒本人曾被阿多诺的批评所刺痛,也鼓励布莱希特建立这样一种批评性的联系。布莱希特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反过来,布莱希特认为阿多诺和他的研究所同事们在政治上是自足自满的,在他看来,他们消除了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迫切性的面向。尽管他继续与他们交好,他同时也开始把他们及其活动作为素材写进他孕育已久、从未完成的“tui-novel”,一部讽刺那些他从1934年即开始与其共事的知识分子们之丑事的作品。艾斯勒本人曾被阿多诺的批评所刺痛,也鼓励布莱希特建立这样一种批评性的联系。布莱希特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跟艾斯勒一起在霍克海默家吃午饭。之后,艾斯勒为“tui-novel”——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故事——提了点建议。一个富有的老头快死了,他为世间的苦难而担忧,就在遗嘱里留下一大笔钱来建一个研究所,以便研究痛苦的根源——显然就是他自己。
(要是注意到,可想而知,他们是在刚刚享受了一顿免费的午餐之后做出上述刻薄批评的话,布莱希特和艾斯勒竟然双双对其中的反讽意味视而不见,这确实是件有趣但无疑又有点让人困惑的事情。)后来,艾斯勒在他民主德国的家里评论说,像阿多诺这样半生不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想比那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更聪明些,却并不想跟他们争论” 。
。
这段公案在两大阵营之间始终是造成紧张的根源。迟至1978年,利奥·洛文塔尔作为那一代批判理论家的最后一位在世者,觉得有必要为研究所提出辩护:“我从未听说悲惨的生活条件和低于标准的营养状况是创造性思想的必要前提。如果马克思和尼采不时地遭受物质匮乏的袭扰而他们的理论创造力得以幸免的话,那么这种痛苦的环境不是原因而是被克服了的障碍。” 他同时也提到,类似这样的批评家有时候在东方“会找到舒适的生活方式”,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很多其他的异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不懂得相时而动之策略的人,“都掉了脑袋”。至于布莱希特攻击阿多诺及其同事没能以一种适当的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洛文塔尔以一种尖刻的讽刺回应道:
他同时也提到,类似这样的批评家有时候在东方“会找到舒适的生活方式”, “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很多其他的异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不懂得相时而动之策略的人,“都掉了脑袋”。至于布莱希特攻击阿多诺及其同事没能以一种适当的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洛文塔尔以一种尖刻的讽刺回应道:
确实,要是阿多诺跟他们的朋友们动手去架设街垒的话,他们一定会在汉斯·艾斯勒的一首革命歌曲里获得不朽。但是想想,要是马克思死在1849年或1871年的街垒当中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了,不会有精妙的精神分析模型,当然也不会有批判理论了。
阿多诺自己也在若干场合中回应过此类批评。“假装积极”,意味着自己为自己的激进姿态额手称庆,以自己额头上的汗来衡量自己的介入程度。他争辩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动的现象。他坚持认为,真正批判性的思想家是那些不畏惧说出真理的人,即使真理是难以接受的;真正坚定的理论家应该是一个“既不在想法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也不允许自己被胁迫而参加行动的人” 。布莱希特将“行动主义”拜物化的对待方式实际上是深刻地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试图借助一项出于意志的行动而超越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结果,而这一分工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图摧毁的。“先锋派精英主义式的隔离,”阿多诺坚持认为,“不应该归咎于艺术而应该归咎于社会。”
。布莱希特将“行动主义”拜物化的对待方式实际上是深刻地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试图借助一项出于意志的行动而超越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结果,而这一分工正是社会主义革命意图摧毁的。“先锋派精英主义式的隔离,”阿多诺坚持认为,“不应该归咎于艺术而应该归咎于社会。” 人们不应该把令人沮丧的现实主义混同于未加证实的悲观主义。
人们不应该把令人沮丧的现实主义混同于未加证实的悲观主义。
不过,在他们共同流亡美国期间,艾斯勒和阿多诺还是足够积极地在1944年协同从事一项关于电影音乐创作与消费的严肃研究。1939年,艾斯勒接到牛津大学委托撰写一本论电影音乐的著作,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那里获得了2万美元的资助以完成一项关于同一主题的研究计划。研究的目标是考察电影和音乐、原声和人工合成声音之间的关系,同时探究新的可能性。理论上的假设是,在电影中激进的新音乐应该比那些如今已成陈词滥调的传统音乐更有建设性,也更容易产生效果。这个假设还需要通过实际的展示来验证,以说明如何将先进的音乐材料引入电影配乐;按计划会有四部实验性的作品,由艾斯勒选取一系列故事片和纪录片片段,对比已有的配乐和他自己提供的替代版本。
这项计划的核心,同时也是后来在这本书里加以系统阐述的那些结论的出发点,是对一部尤里斯·伊文思的早期默片《雨》(Regen,1929)的详尽分析和随后对其进行的配乐工作。伊文思拍出了大量的雨水的视觉效果作为悲伤的象征。艾斯勒所作的音乐形式为五重奏变奏曲,他认为这样能够最好地抓住这些意象所可能蕴含的表现性。完成的作品,《描述雨的十四种方式》(Vierzehn Arten, den Regen zu Beschreiben),被艾斯勒视为他室内乐中最好的作品。
紧随这项计划问世的这本书结合了描述与对策,在阿多诺所批评的标准化的音乐结构和艾斯勒所坚持的、通过暴露它们的机制来克服它们的可能性之间取得了平衡。这本书特定的理论支柱,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开头批评文化工业的部分,清楚地指向阿多诺的影响。书中,两位作者同气相求的时刻,出现在对一般商业电影音乐之缺点进行分析的段落当中。最初两章,特别是“偏见与陋习”和“功能与戏剧性”以及第四章“社会学诸层面”,承载着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观点鲜明的批判那内在的节奏。据称,电影不能被孤立地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去加以理解;“只有把它看作是运用了机械复制技术的当代文化工业之最具特色的媒介,它才是可以理解的”。 这一时期标准化的好莱坞电影以其“直接性的假象”为标志,这一假象遮盖了内在于媒介之中的矛盾(比如媒介的技术性本质与其管理上的偏陋)。电影音乐的功用在于为电影的直接性幻觉和赤裸的生活提供配乐,把“画面带到公众近前,就像画面通过特写把自己带到公众近前那样”;音乐的作用就是“在流转的画面和观众之间插入一层人性的涂料”
这一时期标准化的好莱坞电影以其“直接性的假象”为标志,这一假象遮盖了内在于媒介之中的矛盾(比如媒介的技术性本质与其管理上的偏陋)。电影音乐的功用在于为电影的直接性幻觉和赤裸的生活提供配乐,把“画面带到公众近前,就像画面通过特写把自己带到公众近前那样”;音乐的作用就是“在流转的画面和观众之间插入一层人性的涂料” 。最终,无论是就生产还是消费而言,这些方法和结果都会阻碍电影与其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之间产生真实的接触。
。最终,无论是就生产还是消费而言,这些方法和结果都会阻碍电影与其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之间产生真实的接触。
电影音乐的特征取决于产业的直接需求。音乐没有自主权:就其将自身屈从于一个外在于它自身的文本而言,它正好构成了阿多诺所谓的使音乐产生意义的美学标准的反面。所有的音乐都被打上了实用的标记,以便被“当作外来者加以容忍,有时候会被看作是不可或缺的” (部分因为实际的需求,部分是因为那种拜物教观念认为,所有现存的技术资源都应该被用到极致)。有声片远没有呈现出默片的矛盾,而只是它的延续;音乐仍然居于画面侧旁,表面上出于人为的配乐变成了表面上显得自然的电影画面的存在条件。作者们挑出一些标准化的做法加以批评:主导动机,它的“经典”功能已经“被缩减到了充当音乐性侍从的地步,即便人人都能识别出某个著名段落,它还是会以一种紧要的神情预告主人的出场”
(部分因为实际的需求,部分是因为那种拜物教观念认为,所有现存的技术资源都应该被用到极致)。有声片远没有呈现出默片的矛盾,而只是它的延续;音乐仍然居于画面侧旁,表面上出于人为的配乐变成了表面上显得自然的电影画面的存在条件。作者们挑出一些标准化的做法加以批评:主导动机,它的“经典”功能已经“被缩减到了充当音乐性侍从的地步,即便人人都能识别出某个著名段落,它还是会以一种紧要的神情预告主人的出场” ;旋律与悦耳之音,因为它们“简明的可理解性”而被使用;隐而不显,“假定观众不应该意识到音乐的存在”
;旋律与悦耳之音,因为它们“简明的可理解性”而被使用;隐而不显,“假定观众不应该意识到音乐的存在” ;给视觉做辩护,于此,出于一种在有声时代很常见的对于寂静的恐惧,音乐变成了“一种声响性的舞台道具”
;给视觉做辩护,于此,出于一种在有声时代很常见的对于寂静的恐惧,音乐变成了“一种声响性的舞台道具” ,就像是对于暴风雨的音乐性模仿那样;图解,在这种情况下音乐或是通过低声下气的模仿,或则运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情绪的俗套去模拟视觉事件;地理与历史,在这里音乐就像服装一样,向观众提示故事背景;惯用音乐,它把像《月光奏鸣曲》(Moonlight Sonata)这样的曲子变成一个单纯的招牌,一个声音商标,去给惯用的戏剧性事件伴奏;俗套,这些标准化了的细节有助于“营造典型的环境”;还有标准化演绎,这是伪个性化的一种形式,就像阿多诺在别处写过的那样,“用预先消化来欺骗我们”
,就像是对于暴风雨的音乐性模仿那样;图解,在这种情况下音乐或是通过低声下气的模仿,或则运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情绪的俗套去模拟视觉事件;地理与历史,在这里音乐就像服装一样,向观众提示故事背景;惯用音乐,它把像《月光奏鸣曲》(Moonlight Sonata)这样的曲子变成一个单纯的招牌,一个声音商标,去给惯用的戏剧性事件伴奏;俗套,这些标准化了的细节有助于“营造典型的环境”;还有标准化演绎,这是伪个性化的一种形式,就像阿多诺在别处写过的那样,“用预先消化来欺骗我们” 。
。
书中有一个段落,回荡着阿多诺早些时候论“音乐的物化”和随之而来的“听的退化”的文章的观点。在这个段落里,作者们强调了声学维度的“档案”特征,它能够比视觉维度更有效地保存“前个人主义的集体性特征”,还强调了工业资本主义通过商业化音乐、机械大量复制以及在广告中使用音乐进而贬损聆听之本性的退化过程。音乐接受当中公有的、享乐的和乌托邦性质的因素遭到物化,“被用来服务于商业主义”。音乐,集体性的记忆以及预期,已经变成了“非理性得以理性地展开的媒介” 。商业性的电影配乐鼓励认同:利用音乐语言上的熟悉以及声画同一这样的手段,情感上的亲近得以达成,这同时也就屏除了矛盾而投射出一种完整性的印象,以供观众认同。这就是本书作者尽可能挑衅地提出的问题。不过,问题还是有可能解决的。
。商业性的电影配乐鼓励认同:利用音乐语言上的熟悉以及声画同一这样的手段,情感上的亲近得以达成,这同时也就屏除了矛盾而投射出一种完整性的印象,以供观众认同。这就是本书作者尽可能挑衅地提出的问题。不过,问题还是有可能解决的。
尽管文化工业在施加影响,但电影观众还没有变得完全被动:“抵抗和自发性依然存在” 。当一种批判性的策略被勾画出来的时候,艾斯勒鲜明的看法在此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了。尽管阿多诺认同艾斯勒的信念,也认为批判性的反思和行动依然存在潜力,但他对艾斯勒具体的操作建议却保持怀疑。艾斯勒引用自己为好莱坞电影如《刽子手之死》配乐的切身经验为参照,他坚持认为任务不在于为“普通的音乐配以非凡的乐器”,而是相反,要“为普通的乐器创作出非凡的音乐”。
。当一种批判性的策略被勾画出来的时候,艾斯勒鲜明的看法在此变得更加清晰可辨了。尽管阿多诺认同艾斯勒的信念,也认为批判性的反思和行动依然存在潜力,但他对艾斯勒具体的操作建议却保持怀疑。艾斯勒引用自己为好莱坞电影如《刽子手之死》配乐的切身经验为参照,他坚持认为任务不在于为“普通的音乐配以非凡的乐器”,而是相反,要“为普通的乐器创作出非凡的音乐”。 他说,作曲家需要权利去发挥更大的影响,在电影制作过程中担任顾问和做出贡献,从一开始就介入生产,而不是等到结束,要与编剧和导演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他们工作。电影音乐应该用它自己的声音发言;它既应该配合也应该做出反应。电影中音乐的使用着实应该从“作品内在需求”那里获得灵感。
他说,作曲家需要权利去发挥更大的影响,在电影制作过程中担任顾问和做出贡献,从一开始就介入生产,而不是等到结束,要与编剧和导演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他们工作。电影音乐应该用它自己的声音发言;它既应该配合也应该做出反应。电影中音乐的使用着实应该从“作品内在需求”那里获得灵感。 每部电影必须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关系网。一种“恰当”的戏剧艺术将会在“画面、对白和音乐之间构成鲜明的分野,并且恰恰因此而又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富有意味的联系”。对作曲家来说,适当的目标在于“他创作出来的音乐,即使在一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下被听到,也能在总体上被正确地感知并且充分地实现其功能,而听众不必费尽心机地逐条跟进综合声轨以便领会音乐,这后一种做法恰恰阻碍了其功能的充分实现”。熟悉的东西应该被陌生化,平常的应该被变得殊异,以便促成一种更富挑战性的娱乐类型。好的电影音乐“应当辉光闪耀”,它的作用在于“制造出某种可感知的东西”,尽一切可能使其成效一听即知,而不是“迷失在自身之中”。
每部电影必须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关系网。一种“恰当”的戏剧艺术将会在“画面、对白和音乐之间构成鲜明的分野,并且恰恰因此而又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富有意味的联系”。对作曲家来说,适当的目标在于“他创作出来的音乐,即使在一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下被听到,也能在总体上被正确地感知并且充分地实现其功能,而听众不必费尽心机地逐条跟进综合声轨以便领会音乐,这后一种做法恰恰阻碍了其功能的充分实现”。熟悉的东西应该被陌生化,平常的应该被变得殊异,以便促成一种更富挑战性的娱乐类型。好的电影音乐“应当辉光闪耀”,它的作用在于“制造出某种可感知的东西”,尽一切可能使其成效一听即知,而不是“迷失在自身之中”。
《论电影音乐》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本不那么令人舒服、有时甚至令人沮丧的混杂之书,这反映出(有时同样也试图超越)两位合著者不同的倾向和风格。有些故意的挑衅和巧妙的比喻(比如在评论画面的音乐伴奏时说,音乐“把一记吻转换成一幅杂志封面,把一阵强烈爆发的痛苦变成一出情节剧,把一幕自然的景象化作一幅平版复印画” ),即使搁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本以简练著称的《启蒙的辩证法》里也并无不妥。然而,阿多诺式的并置和夸张更具建设性的地方在于,它为艾斯勒批判性的想象打开了空间,同时又提醒人们注意当前问题的严峻性以及提出对策的迫切性。正如两位作者所说:
),即使搁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本以简练著称的《启蒙的辩证法》里也并无不妥。然而,阿多诺式的并置和夸张更具建设性的地方在于,它为艾斯勒批判性的想象打开了空间,同时又提醒人们注意当前问题的严峻性以及提出对策的迫切性。正如两位作者所说:
为了对能够克服现存僵局的“批判”理念加以强调,我们选择了极端的例证,然而,这些极端的姿态并不预示着它们对于以后现代电影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会变得不再那么有针对性。
然而,这本书在后面部分的讨论尤其缺乏一致性,于此,阿多诺的理论论辩被艾斯勒更加实用主义的方法所掩盖,而且二者显然构成了矛盾。艾斯勒如此明显的自信,部分来自他记忆中自己的好莱坞经验里最美好的时刻,那时他跟一群志趣相投的作家和导演一起工作,比如布莱希特、奥德茨、塞克和雷诺阿。然而,难以知晓的是,如果艾斯勒能够写出一部成功而恰当的配乐的话,情况会是怎样,这样一部配乐必须对它所配的那部电影具有真正的解放性效果,不疏远制作者和消费者这二者中的任意一方,让他们都彻底沉浸在他本人希望予以摧毁的那种认同当中。必须承认,就讨论的结尾来看,阿多诺的批判比艾斯勒的对策更有说服力。
如果说《论电影音乐》有着独特的构想的话,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诞生过程。它最早以英文面世,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47年在纽约出版[丹尼斯·多布森(Dennis Dobson)在1951年出了伦敦版],只有艾斯勒的单独署名。在前言中,艾斯勒声明“这里所呈现的理论与构想均由我(跟阿多诺)在一般美学、社会学以及纯音乐问题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而来”。根据一些材料,阿多诺把他的名字从合著者里面去掉是为了避免被牵扯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对艾斯勒政治交往[汉斯·艾斯勒的哥哥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是一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他本人在1947年就遭到该委员会的质询]的调查中去。 艾斯勒当然被委员会视为一个非常可疑的人物。尽管他和布莱希特一样从来没有真的加入共产党,但他从不试图隐瞒自己的政治信仰。艾斯勒的姐姐鲁斯·菲舍尔(Ruth Fischer)从1941年起就生活在美国,她向联邦调查局告发了艾斯勒和格哈特,还撰写了几篇猛烈批评他们的文章,并登上了美国几家主要报纸的头版。自从菲舍尔在1926年被德国共产党驱逐之后,她就变成了一个过激的人,而新的反共运动则令她如鱼得水。她此时致力于将包括她两个兄弟在内的人驱赶出美国。“你家里发生的事,”查理·卓别林对意志消沉的艾斯勒说,“就跟莎士比亚的戏似的。”
艾斯勒当然被委员会视为一个非常可疑的人物。尽管他和布莱希特一样从来没有真的加入共产党,但他从不试图隐瞒自己的政治信仰。艾斯勒的姐姐鲁斯·菲舍尔(Ruth Fischer)从1941年起就生活在美国,她向联邦调查局告发了艾斯勒和格哈特,还撰写了几篇猛烈批评他们的文章,并登上了美国几家主要报纸的头版。自从菲舍尔在1926年被德国共产党驱逐之后,她就变成了一个过激的人,而新的反共运动则令她如鱼得水。她此时致力于将包括她两个兄弟在内的人驱赶出美国。“你家里发生的事,”查理·卓别林对意志消沉的艾斯勒说,“就跟莎士比亚的戏似的。”
1947年4月,理查德 · 尼克松(Richard Nixon),这位当年度的加州议员,宣布委员会将开始就艾斯勒的活动和关系搜集“事实”。“汉斯·艾斯勒一案,”他以一种不祥的语气说,“恐怕是有史以来委员会受理的最重要的一个案例。” 5月,艾斯勒在好莱坞接受了第一次质询,其后,9月份在华盛顿受到为期三天的质询。主审官罗伯特·斯特里普林(Robert Stripling)告诉委员会主席帕内尔·托马斯(Parnell Thomas)说,他的目的在于“证明艾斯勒先生之于音乐界就如同卡尔·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那样,而且他对此心知肚明”
5月,艾斯勒在好莱坞接受了第一次质询,其后,9月份在华盛顿受到为期三天的质询。主审官罗伯特·斯特里普林(Robert Stripling)告诉委员会主席帕内尔·托马斯(Parnell Thomas)说,他的目的在于“证明艾斯勒先生之于音乐界就如同卡尔·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那样,而且他对此心知肚明” 。艾斯勒回答说,这样一个比较对他“是一种恭维”。他的案子意义重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为他辩护,他还从包括毕加索、卓别林、马蒂斯、考克多、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在内的其他名人那里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公开支持。收效甚微,他明智地决定在1948年初离开这个国家。
。艾斯勒回答说,这样一个比较对他“是一种恭维”。他的案子意义重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为他辩护,他还从包括毕加索、卓别林、马蒂斯、考克多、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在内的其他名人那里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公开支持。收效甚微,他明智地决定在1948年初离开这个国家。
艾斯勒后来没有对他关于电影以及电影中音乐使用状况的基本看法做出根本性的改动;事实上,在他交给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证词当中,他已经公开宣称《论电影音乐》是他的艺术信条。而阿多诺则一方面继续他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另一方面,在60年代他也拓展出一些空间去讨论依然内在于现代艺术的某些层面的批判潜力。
本书略加修订的版本Komposition für den Film,丝毫没有提到阿多诺的名字,在1949年由布鲁诺·亨舍尔和索恩出版社(Bruno Henschel und Sohn)在柏林出版。直到原始版本经阿多诺授权于1969年由罗格纳和伯恩哈德出版社(Rogner & Bernhard)在联邦德国翻译再版,他才最终以作者的身份出现在封面上。 这本书变成了一部奇特的经典:一部记录了关于电影音乐之特性与潜力的开创性研究成果的著作;独一无二地代表着尝试在布莱希特式的实践和批判理论之间寻找共同点的难得的合作;也是一本经常被引用却很少被阅读的书。
这本书变成了一部奇特的经典:一部记录了关于电影音乐之特性与潜力的开创性研究成果的著作;独一无二地代表着尝试在布莱希特式的实践和批判理论之间寻找共同点的难得的合作;也是一本经常被引用却很少被阅读的书。
今天,它应该被重新发现。它令音乐家注意政治,让政治理论家留意音乐;它留下的印记有着鲜明的异端特征。其中的很多讨论仍在博得尊重。好莱坞似乎仍然青睐电影音乐应该简单悦耳并且安分守己之类的看法。比如,商业性的电影原声以唱片的形式面市,这表明文化工业在继续庆祝其整合能力并获益于此。最早那种要求在实践中进行激进变革的需求仍旧没有得到答复。然而,承诺中的音符还在被弹奏,仍然模糊地期望着能被听到。阿多诺曾经把他的理论努力比作“漂于野蛮主义洪流的瓶中信”。
《论电影音乐》就可以被看作这样一封信,仍在漂流,仍在寻找它未知的收信人。